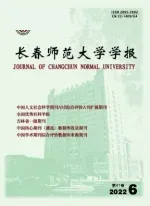論美國后現代派小說中的道德缺席現象
陳彥旭
(東北師范大學外語學院,吉林長春 130024)
美國著名文學批評家琳達·哈茨恩在她2002年出版的著作《后現代主義的政治學》(Politics of Postmodernism)一書中“扣上了后現代主義的棺材蓋,宣稱‘一切都結束了’”[1]。那么,如果后現代主義真的已經終結,繼它之后又出現了什么樣的藝術與文學思潮呢?學術界普遍認為,答案就是出現在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的新現實主義。而新現實主義為何可以取代后現代主義,成為時代的新寵呢?筆者認為,這兩者之間最重要的區別就在于新現實主義小說家與后現代派小說家對“道德”的態度上:前者致力于重建道德意識,并藉此來解決當代人文精神危機;而后者對“道德”抱有一種明顯的漠視甚至否定的情緒。本文就美國后現代派小說中的道德缺失現象進行描敘、探討并歸因。
一、“上帝死了”與“人死了”
眾所周知,西方的基督教思想對人們道德觀念有著深遠的影響,它所宣揚的博愛、寬容、犧牲、公平等思想在神的光環的籠罩下有著不可撼動的震懾力量。“可以說,沒有宗教信仰就沒有道德信仰,沒有宗教,道德就失去了根基”[2]。我國著名宗教學家呂大吉進一步指出,“一方面,宗教將道德抬高為宗教的教義、信條、誡命和律法,把恪守宗教關于道德的誡命作為取得神寵和進入來世天國的標準;另一方面,宗教的教義和信條又被神以道德誡命的形式強加于整個社會體系,被說成是一切人的行為之當與不當、德與不德、善與不善的普遍準則。”[3]據此,西方世界禁不住發出這樣感慨的聲音,“如果沒有宗教信仰,人怎么可能成為真正‘有道德的人’呢?如果不相信上帝是道德的前提,我們怎么可能發展美德,怎么可能有責任感呢?……如果沒有上帝,人類是否全變得貪得無厭而不能善待同伴?如果沒有上帝,我們是否能夠保證人世間的博愛、公正和兄弟情誼?如果沒有上帝,人類是否會放棄道德生活,倒退到茹毛飲血的諸多形態之中?”[4]
然而,哲人尼采在《快樂的智慧》這本書中,借一瘋癲之人所發出的那一聲長長的哀嘆奏響了為上帝而譜寫的挽歌,“上帝死了”這一殘酷的現實標志著以基督教信仰為核心的價值體系分崩離析,其所承載的道德信念也隨之而轟然倒塌。失去信仰的人生命被物化,精神空洞,靈魂無家可歸,流離在這個充滿喧嘩、恐懼、孤單、嘈雜、無意義的世界里,以至于繼尼采之后,思想家福柯再一次語出驚人,宣布“人死了”,實指在后現代人文精神的消亡。
面對著如此的生存窘境,生活在這個時代的美國作家們顯得無所適從。目睹了二戰后血跡斑斑的戰場、國內瘋狂的麥卡錫主義的橫行、熱核戰爭的恐怖及東西方冷戰、不斷挑起矛盾與分裂的越南戰爭、英雄偶像人物如肯尼迪、馬丁·路德·金的暗殺事件、罪惡不公的種族歧視,以及每況愈下的生態環境,他們作為文人所特有的敏感脆弱的心靈不再有勇氣去直面這個混亂無序、不可理喻的世界,而普遍采取了一種隱退消極的態度:他們不再關注外部的世界,而轉為對自我內心世界的審視,認為人的內心深處的直覺與潛意識更為可靠,并開始肆無忌憚地用文字宣泄自己的失望、迷茫、混亂、痛苦等負面情緒。因此,暴力、色情、吸毒、信仰危機、道德淪喪和人性崩潰等主題與情節在后現代派小說中屢見不鮮。
我國學者許汝祉教授曾將美國自由派理論家丹尼爾關于后現代派小說創作主題的論述總結為以下幾點:宣揚暴力與殘忍,作品中充滿著嗜血的細節;宣傳性反常,如對同性戀、異性模仿癖、口交行為與雞奸的描述;宣揚荒謬的虛無主義情緒,情節古怪;宣揚污移,像吸毒、描寫人體排泄細節等。[5]
二、“破碎的鏡”與“昏暗的燈”
后現代派作家的這種極端的寫作傾向顯然是不妥當的,因為他們忽略并否定了文學作品反映現實與道德教化的基本功能。西方文論家艾布拉姆斯曾形象地將這兩種功用比作“鏡與燈”,如果非要把這個比喻生搬硬套地放在后現代派小說頭上,我們看到的至多只能是“破碎的鏡”和“昏暗的燈”。
所謂“破碎的鏡”,是指后現代派小說并不能夠真實地反映現實,多數情況下是對現實丑惡現象的夸大、虛構與極端的描寫。“在小說創作領域,后現代主義作品以‘真實地虛構和冷漠地抒情’為最明顯的特征,明目張膽又故做麻木不仁地向讀者宣告作者是在那里‘胡編亂造。’”[6]著名后現代理論批評家歐文·豪也指出,“后現代作家的創作完全摒棄了英雄與英雄人物的沖突,他只能虛構他所生活的世界上的那些‘極度畸形’和他那‘極度飄忽不定’的經歷之‘病態’”[7]。綜上所述,后現代派小說所描寫的多是夸張的、病態的與畸形的個別人物,這明顯違背了現實主義小說中的“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這一中心創作原則。因此,后現代派小說在很大程度上是反現實主義的,這也說明它與新現實主義之間也必然存在著天生不可調和的矛盾。
而“昏暗的燈”則是說后現代派小說無法照亮人們的心靈,洗滌人們的靈魂,弘揚偉大的精神,從而實現文學作品所肩負的道德承擔。而后現代派小說中對于種種骯臟、丑惡、齷鹺事物的刻意的、赤裸裸的思想以及場景描寫無法帶給讀者任何道德上的愉悅與啟迪。主人公對其自己反道德、反倫理的行為非但絲毫不加掩飾,反而沾沾自喜,引以為榮。
舉例來說,在約翰·霍克斯的著名后現代小說《血橙》中,主人公毫無廉恥地向他人炫耀自己糜爛的性史:“眾神創造男人,就是讓我們去分開女人的雙腿……我曾經跟無數的女人發生過關系,包括我的妻子、我妻子的朋友、我朋友的妻子,還有其他形形色色的女孩和女人,從豆蔻少女到半老徐娘,再從半老徐娘到豆蔻少女。只要時機適當,只要愛神的歌聲響起,我就會毫不猶豫地成就一番風流韻事”[8]。這番無恥的自白實在使得每一個有良知、有道德的人們震驚不已。
再舉一例,美籍俄裔作家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的《洛麗塔》是后現代作品中的經典之作,其主人公亨伯特是個心理與性取向都有些變態的成年男子,對“每一個從身邊經過的快要進入青春期的小姐姑娘欲火中燒”,卻對自己的結發妻子冷諷熱嘲,極盡挖苦丑化之能事:“那個新婚之夜,我享受到了無限的快樂……可是,殘酷的現實很快就暴露了,染過的卷發顯出了黑色的發根;茸毛變成了剃過的下巴上的硬刺;那個靈活濕潤的嘴唇,無論如何使勁地用愛去喂它,仍是不光彩地露出它與那幅寶貝肖像里故去的、癩蛤蟆一般的母親嘴唇有驚人的相似之處……亨伯特手里是一塊骨骼粗大、臉龐浮腫、兩腿短小、乳房碩大、呆頭呆腦的奶油蛋糕。”[9]這本書由于充斥著反倫理的思想與露骨的性愛描寫,觸犯了社會所能忍受的道德底線,早期在尋找出版時屢屢碰壁,在法國遭到短期的封殺,在澳大利亞也被視作禁書。據說有的出版商建議納博科夫將兩個主人公角色換位,即把洛麗塔換成一個年青男子,把亨伯特變為一個土里土氣的農婦,并安排后者去勾引前者,這樣“能給讀者與出版商增加一點道德上的安全感”。
類似的令人尷尬甚至反胃的描寫也出現在巴塞爾姆的《白雪公主》中,在他的筆下,代表著圣潔、純真的白雪公主變成了一個高個子、皮膚黝黑的女人,“身上長著很多美人痣:一顆在乳房上,一顆在肚子上,一顆在膝蓋上,一顆在腳踝上,一顆在臀部上,一顆在脖子后面……”[10],而且她著迷于淫穢詩的寫作,并在浴室中與七個侏儒淫亂,簡直就像一頭不知羞恥、性欲旺盛的母獸。就這樣,扎根在每個讀者童年記憶中的純潔無瑕的、象征著真善美的少女形象被徹底地顛覆與摧毀,兩個截然不同的形象之間的巨大反差也對讀者的道德觀與倫理觀產生了巨大的沖擊。
三、反英雄
后現代派作家們將這種對文學經典作品所進行的扭曲的模仿、嘲笑以及戲謔稱為戲仿,這是他們在寫作中經常使用的手法,表達了他們對傳統歷史價值觀與文學精神的蔑視與否認。這也恰好印證了楊仁敬教授在《美國后現代派短篇小說選》一書的前言中所提及的觀點,“從本書所選的25篇小說來看……它們大多數描寫的都是‘反英雄’”。
那么,何為“反英雄”呢?《郎曼20世紀文學指南》(1981)中提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反英雄’成為金斯萊·艾米斯、約翰·奧斯本、約翰·布雷恩、哈羅德·品特等作家所寫的小說和戲劇中的人物。反英雄否定行為的準則或先前被視為文明社會基礎的社交行為。有些人故意反抗那些行為規范,把現代社會看作是非人的社會;有些人則根本無視那些行為準則”。王嵐教授進一步指出,“他們可能卑微瑣碎,對社會政治和道德往往采取冷漠、憤怒和不在乎的態度,甚至會粗暴殘忍……反英雄走向了英雄的反面,它的出現是對傳統理想中英雄人物的解構,或者說是這些理想概念的破碎和喪失”[11]。
我們知道,“英雄”是正義、理想、道德等一系列美好事物的化身,他們的所做所為也因此往往被當作典范與規矩為人們所效仿。每個時代都有不同的英雄,他們身上所獨有的品質也同時體現了他們所處時代對道德的最高要求與向往。而在主張推翻“中心”、“典范”與“規矩”的后現代,不可能存在一個普遍認可的價值觀,英雄的形象也因此被消解,社會的道德典范難以確立。在一片追逐所謂“道德個人化”和“道德自由化”的嘈雜聲中,英雄人物被趕下圣壇,黯然退場,最終蹤跡難覓,而反傳統英雄品格的“反英雄”則在后現代的文學作品中左右逢源,逐漸站穩了腳跟,像《五號屠場》中的畢利·皮爾格里姆與《第二十二條軍規》中的尤索林都是反英雄的典型人物。
另外,透過以上作品中文字所勾勒出的混亂、荒唐的畫面,我們感受到的是奧地利精神病學家弗洛伊德所提出的“本我”中所包含的、受到壓制而時時刻刻燥動不安的“利比多”。根據弗洛伊德的理論,人格結構共分為三個層次:本我、自我與超我。本我基本上由性本能組成,沒有價值觀念,沒有倫理道德的觀念,按照“快樂原則”活動;而超我“代表社會道德準則,壓抑本能沖動,按‘至善原則’活動”[12];而自我負責協調本我與超我之間激烈的矛盾與沖突,遵循現實原則。
結合上文關于“反英雄”的討論,我們可以看出,由于同樣“代表社會道德規范”的英雄的缺席,直接導致“代表社會道德準則”的“超我”的不在場,從而造成了“本我”的力量無約束而迅速膨脹,這種趨勢發展到頂峰時人便被物化,亦可說獸性壓倒了人性,道德的觀念消失殆盡,人性也變得暗淡無光。
四、結語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美國后現代派的作家在面對現實社會的種種困境時,采取的對策并不是積極地應對,去反映、去揭露現實的種種問題從而指出解決問題的途徑,相反,他們回避現實,轉向自己的內心世界,用凌亂破碎的意象與文字來傾訴自己個人的困惑、壓抑與不滿。這樣的作品完全失去了文學“療傷”的功能,只會強化讀者的迷惑與傷痛心理。而美國大眾在經歷過二戰、越戰、國內麥卡錫主義、經濟蕭條等種種磨難后,期冀看到反映真實問題、解決現實問題的小說。在這樣的情形下,新現實主義小說的興起與后現代主義小說的衰落似乎也成了一種歷史性的必然。
[1]Neil Brooks,Josh Toth,The Mourning After,Attending the Wake of Postmodernism,Amsterdam,New York,2007:15.
[2]魏長領.道德信仰與自我超越[M].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113.
[3]呂大吉.宗教學通論新編[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768.
[4]于文杰.現代化進程中的人文主義[M].重慶:重慶出版社,2006:248.
[5]許汝祉.對美國后現代主義文學的評估[J].外國文學評論,1991(3).
[6]陳剛.后現代的生存[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96.
[7]王潮.后現代主義的突破[M].蘭州:敦煌文藝出版社,1996:146.
[8]約翰·霍克斯.血橙[M].姜薇,孫全志,譯.重慶:重慶出版社,2007:2.
[9]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洛麗塔[M].盧炳瑞,譯.長春:吉林攝影出版社,2001:11.
[10]唐納德·巴塞爾姆.白雪公主后傳[M].虞建華,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5:21.
[11]趙一凡,張中載.西方文論關鍵詞[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6:108.
[12]朱立元.當代西方文藝理論[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