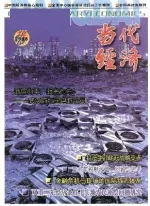論江蘇發(fā)展海洋低碳經(jīng)濟(jì)及產(chǎn)業(yè)選擇
○姚鐵明
(淮海工學(xué)院商學(xué)院 江蘇 連云港 222001)
論江蘇發(fā)展海洋低碳經(jīng)濟(jì)及產(chǎn)業(yè)選擇
○姚鐵明
(淮海工學(xué)院商學(xué)院 江蘇 連云港 222001)
江蘇是人口經(jīng)濟(jì)大省,雖GDP處于全國領(lǐng)先地位,但資源緊缺、能源緊張、高碳排放將是長期制約江蘇發(fā)展的三大因素。江蘇沿海及海域資源、能源、碳匯極為豐富,原生態(tài)環(huán)境良好,大力發(fā)展海洋低碳經(jīng)濟(jì),是破解江蘇發(fā)展難題的必由之路。本文通過分析提出發(fā)展海洋清潔能源產(chǎn)業(yè),是江蘇從長遠(yuǎn)解決能源問題的根本途徑;發(fā)展海洋碳匯科技產(chǎn)業(yè),是江蘇實現(xiàn)全省碳匯平衡可持續(xù)發(fā)展的重大戰(zhàn)略抉擇。
江蘇 海洋經(jīng)濟(jì) 低碳 產(chǎn)業(yè)集群
一、發(fā)展海洋低碳經(jīng)濟(jì)的重要背景
自上世紀(jì)中葉以來,由于全球陸地資源大量消耗帶來的諸多問題,使世界各國對海洋資源的開發(fā)和利用越來越受到關(guān)注。國際社會普遍認(rèn)為,21世紀(jì)應(yīng)該是“海洋世紀(jì)”,因此,海洋經(jīng)濟(jì)發(fā)展也就成為世界性的重要議題。地球上海洋面積占71%,陸地面積占29%,過去由于人類對海洋資源認(rèn)識有限,世界經(jīng)濟(jì)的主體是陸地經(jīng)濟(jì),但隨著人類自身擴(kuò)張和工業(yè)化規(guī)模的擴(kuò)大,現(xiàn)在已面臨陸地資源枯竭、生存環(huán)境惡化的嚴(yán)重威脅。未來人類生存資源的供給正趨向海洋,海洋經(jīng)濟(jì)成為世界經(jīng)濟(jì)主體將是一個必然的選擇。從當(dāng)代科學(xué)發(fā)展的預(yù)測來看,地球上絕大部分資源蘊(yùn)藏在海洋,海洋經(jīng)濟(jì)將是未來最具開發(fā)潛力的經(jīng)濟(jì)領(lǐng)域。
然而,縱觀近半個多世紀(jì)來世界海洋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歷程,海洋資源粗放開發(fā)、肆意揮霍浪費(fèi)現(xiàn)象嚴(yán)重,沿海生態(tài)環(huán)境遭到破壞和污染,海洋經(jīng)濟(jì)發(fā)展基本處于被動狀態(tài)。即使發(fā)達(dá)的西方國家,對海洋資源開發(fā)中的環(huán)境保護(hù)問題做得也仍然不夠。因此,一些科學(xué)家擔(dān)心用過去開發(fā)陸地資源的思維和模式開發(fā)海洋資源,勢必會造成更大的生態(tài)問題。2009年12月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大會,就全球氣候變暖給人類生存、社會發(fā)展帶來的災(zāi)難性后果,再一次敲響警鐘。現(xiàn)在,減少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排放,發(fā)展低碳經(jīng)濟(jì)已成為世界各國的共識。在海洋經(jīng)濟(jì)發(fā)展中倡導(dǎo)低碳經(jīng)濟(jì),是一個引領(lǐng)新時期海洋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新思路。它既是對傳統(tǒng)海洋經(jīng)濟(jì)發(fā)展模式的科學(xué)矯正,又代表著新興海洋產(chǎn)業(yè)低碳化發(fā)展的方向,完全符合世界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潮流。
據(jù)科學(xué)資料顯示,海洋不僅具有解決溫室氣體排放的廣闊空間,而且是未來發(fā)展低碳經(jīng)濟(jì)的資源寶庫。自2005年2月16日《京都議定書》正式生效以來,“碳匯”一詞逐漸進(jìn)入人們的視野。簡單地講,碳匯就是植被、海洋和土壤對溫室氣體二氧化碳的吸收、貯存及大氣的光化學(xué)清除機(jī)制。海洋擁有豐富的藍(lán)色碳匯功能,它吸收貯存二氧化碳的容量驚人。據(jù)聯(lián)合國有關(guān)組織發(fā)布的報告估計,地球上超過一半(55%)的生物碳或綠色碳捕獲是由海洋生物(包括浮游生物、細(xì)菌、海草、鹽沼植物和紅樹林)完成的,而并非是在陸地。海洋中還蘊(yùn)藏著巨大的可再生能源,只要得到充分開發(fā),就可滿足全球的能源需求。海洋能源存在的形式多種多樣,包括海浪、潮汐、洋流、海風(fēng)、海水溫度差和鹽度差等,但到目前為止人類對這些能源的認(rèn)識和利用仍處于起步階段。如果在科學(xué)技術(shù)上對海洋可再生能源全面開發(fā)利用有重大突破,那將大大降低全球化石能源的消耗量,這對于減少碳排放、改善生態(tài)環(huán)境的作用將是無可估量的,甚至可以影響到以石油為核心的世界能源政治的格局變化。
我國既是大陸國家,又是海洋國家,在海洋上有著廣泛的戰(zhàn)略利益。發(fā)展海洋低碳經(jīng)濟(jì)是順應(yīng)新世紀(jì)全球海洋大開發(fā)潮流的客觀需要。我國海洋經(jīng)濟(jì)發(fā)展比較緩慢,與世界發(fā)達(dá)國家相比大約滯后10—15年。2008年2月,我國正式發(fā)布《國家海洋事業(yè)發(fā)展規(guī)劃綱要》,總的指導(dǎo)思想是:海洋事業(yè)要加強(qiáng)對海洋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調(diào)控、指導(dǎo)和服務(wù),提高海洋經(jīng)濟(jì)增長質(zhì)量,壯大海洋經(jīng)濟(jì)規(guī)模,優(yōu)化海洋產(chǎn)業(yè)布局,加快海洋經(jīng)濟(jì)增長方式轉(zhuǎn)變,發(fā)展海洋循環(huán)經(jīng)濟(jì),提高海洋經(jīng)濟(jì)對國民經(jīng)濟(jì)的貢獻(xiàn)率。目前,我國海洋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模式仍然屬于高能耗、高污染和低效益的粗放擴(kuò)張型經(jīng)濟(jì)增長方式,資源浪費(fèi)、環(huán)境污染、掠奪式經(jīng)營等問題依然存在。雖然20年來我國海洋經(jīng)濟(jì)創(chuàng)造了年均增長率超過20%的奇跡,但卻付出了海洋資源破壞、環(huán)境惡化的沉重代價。而海洋經(jīng)濟(jì)是高度依賴海洋資源、環(huán)境的特殊經(jīng)濟(jì)體系,這種特征也就決定了今后海洋經(jīng)濟(jì)可持續(xù)發(fā)展,必須走低碳環(huán)保之路。
二、江蘇發(fā)展海洋低碳經(jīng)濟(jì)是必由之路
2009年江蘇沿海開發(fā)正式上升為國家戰(zhàn)略,2010年國家又將蘇北地區(qū)全部納入長三角發(fā)展規(guī)劃,這是我國改革開放30年后對東部沿海地區(qū)發(fā)展戰(zhàn)略升級的重大舉措。江蘇是人口和經(jīng)濟(jì)大省,盡管目前GDP處于全國領(lǐng)先地位,但資源緊缺、能源緊張、高碳排放將是長期制約江蘇發(fā)展的三大因素。從長遠(yuǎn)看,江蘇要想保持經(jīng)濟(jì)的可持續(xù)及人與環(huán)境的和諧發(fā)展,增強(qiáng)資源自給能力和發(fā)展低碳經(jīng)濟(jì),將是推動江蘇經(jīng)濟(jì)社會平穩(wěn)發(fā)展的“兩大車輪”,缺一不可。現(xiàn)在江蘇的陸域經(jīng)濟(jì)雖然繁榮,以蘇南為典范的一些區(qū)域已率先進(jìn)入小康社會,但毋庸諱言其經(jīng)濟(jì)發(fā)展仍然建立在高能耗、高成本、高排放的基礎(chǔ)之上,資源和能源大部分依賴外援,尤其在碳排放指標(biāo)方面,很難做到碳匯平衡。據(jù)有關(guān)資料顯示,江蘇碳排放總量從1990年到2006年增長了2.37倍,17年間年均增長速度為5.55%,其中蘇南地區(qū)碳排放比重占60%。研究表明,能源消耗是江蘇省碳排放的主體,蘇南、蘇中地區(qū)能源消耗帶來的碳排放,就占碳排放總量的90%。2007年全省溫室氣體排放總量約8.24億噸二氧化碳,人均排放2.95噸碳,幾乎等于國際及全國平均水平的兩倍。因此,用國際低碳經(jīng)濟(jì)、循環(huán)經(jīng)濟(jì)、綠色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理念,來審視以人均GDP為核心指標(biāo)的小康水平,已不足以說明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質(zhì)量和內(nèi)涵,只有使各產(chǎn)業(yè)都基本做到低能耗、低成本、低排放,資源循環(huán)利用,碳匯自主平衡,生態(tài)環(huán)境友好,才能真正實現(xiàn)經(jīng)濟(jì)的可持續(xù)發(fā)展。
江蘇缺少能源和以煤為主的能源結(jié)構(gòu),使得經(jīng)濟(jì)發(fā)展面臨更多來自低碳的壓力。江蘇煤碳占到整個能源消費(fèi)的70%,這必然導(dǎo)致較高的碳排放強(qiáng)度。現(xiàn)在國內(nèi)外低碳經(jīng)濟(jì)背景已對江蘇發(fā)展形成倒逼機(jī)制,節(jié)能、降耗、低碳、環(huán)保發(fā)展勢在必行。因此,江蘇在沿海開發(fā)中,發(fā)展海洋低碳經(jīng)濟(jì)是必由之路。
第一,江蘇海洋經(jīng)濟(jì)崛起后來居上,必須高起點(diǎn)超越已往常規(guī)模式,走新興產(chǎn)業(yè)低碳化發(fā)展之路。在我國東部沿海經(jīng)濟(jì)發(fā)展中,江蘇段沿海確實處于落后狀態(tài),無論港口產(chǎn)業(yè)、沿海城市經(jīng)濟(jì),都與沿海開放的重要地位不相符,更與近鄰山東、浙江沿海的發(fā)展態(tài)勢無法相比。其實這一現(xiàn)象早已影響到了我國沿海整體宏觀戰(zhàn)略和中西部開發(fā)戰(zhàn)略的實施。現(xiàn)在,應(yīng)該把江蘇沿海開發(fā)及時上升為國家戰(zhàn)略層面,這不僅有利于長三角經(jīng)濟(jì)的升級,而且有利于帶動中西部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同時也是對江蘇經(jīng)濟(jì)發(fā)展布局的重大調(diào)整。
江蘇沿海近千公里的海岸線基本保存了良好的原生態(tài)環(huán)境,這在人口密集、各種產(chǎn)業(yè)聚集的長三角地區(qū)顯得尤為珍貴。本區(qū)北起繡針河口、南抵長江口,擁有優(yōu)良的港口、廣袤的灘涂、濕地和海域,其間形成了國際性的自然生態(tài)保護(hù)區(qū),沿海農(nóng)漁資源極為豐富。在新世紀(jì)低碳經(jīng)濟(jì)背景下,江蘇沿海良好的生態(tài)環(huán)境具備了比其他沿海地區(qū)發(fā)展海洋低碳經(jīng)濟(jì)更好的基礎(chǔ)條件。如海洋清潔能源產(chǎn)業(yè)、海洋碳匯科技產(chǎn)業(yè)、低碳港口服務(wù)產(chǎn)業(yè)、沿海生態(tài)休閑產(chǎn)業(yè)、海洋綠色養(yǎng)殖產(chǎn)業(yè)、海洋生物醫(yī)藥產(chǎn)業(yè)、海洋裝備制造產(chǎn)業(yè)等,都是能發(fā)揮本地區(qū)優(yōu)勢而區(qū)別于其他沿海地區(qū)的特色產(chǎn)業(yè)。因此,江蘇海洋經(jīng)濟(jì)必須高起點(diǎn)超越已往常規(guī)模式,走新興產(chǎn)業(yè)低碳化發(fā)展之路。這完全符合江蘇未來經(jīng)濟(jì)創(chuàng)新發(fā)展的戰(zhàn)略。
第二,大力發(fā)展海洋清潔能源產(chǎn)業(yè),永久性提供可再生能源,將是江蘇從長遠(yuǎn)解決能源問題的根本途徑。眾所周知,江蘇是能源消耗大省,又是能源資源小省,是典型的能源輸入型地區(qū)。以江蘇目前的能源供給現(xiàn)狀來支撐江蘇經(jīng)濟(jì)的高速發(fā)展,必然存在高成本、高排放、高污染的現(xiàn)象,經(jīng)濟(jì)發(fā)展風(fēng)險較大。盡管現(xiàn)在千方百計采取節(jié)能減排的措施,但終究是治標(biāo)不治本,可持續(xù)發(fā)展的能源基礎(chǔ)問題并未得到徹底解決。因此,抓住江蘇的創(chuàng)新能源問題,基本就抓住了江蘇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第一命脈,它也是江蘇未來低碳經(jīng)濟(jì)的核心要素。那么,大力發(fā)展海洋清潔能源產(chǎn)業(yè),永久性提供可再生能源,將是江蘇從長遠(yuǎn)解決能源問題的根本途徑。
在江蘇沿海開發(fā)和發(fā)展低碳經(jīng)濟(jì)中,大力發(fā)展海洋清潔能源產(chǎn)業(yè)無疑是第一戰(zhàn)略選擇。它是引領(lǐng)江蘇經(jīng)濟(jì)可持續(xù)發(fā)展的龍頭產(chǎn)業(yè),對調(diào)整江蘇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經(jīng)濟(jì)結(jié)構(gòu)具有方向性的領(lǐng)導(dǎo)作用。一是發(fā)展海洋能源可開辟江蘇解決能源自給的創(chuàng)新之路,以逐漸擺脫長期依賴省外能源輸入的被動局面;二是海洋清潔能源可大大降低碳排放,使江蘇低碳經(jīng)濟(jì)發(fā)展真正建立在低碳能源的可靠基礎(chǔ)上,以減輕未來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節(jié)能、降耗、減排壓力;三是使江蘇的潛在能源資源得到開發(fā),從而開辟更加廣闊的前景;四是從根本上降低企業(yè)生產(chǎn)成本,增強(qiáng)企業(yè)的國際競爭力。
目前,世界上海洋能源利用正處于技術(shù)創(chuàng)新研發(fā)中,波浪能、潮汐能、海流能、溫差能、鹽差能、海洋生物能和海洋地?zé)崮艿壤茫既〉昧诵》秶脑囼瀾?yīng)用成果,而只有海岸(灘)風(fēng)能發(fā)電借助陸域風(fēng)能發(fā)電技術(shù)的成熟轉(zhuǎn)移,得到了長足發(fā)展,形成了規(guī)模化的海上風(fēng)電產(chǎn)業(yè)。如丹麥、瑞典、荷蘭和英國已有成功應(yīng)用的實踐,德國、日本、愛爾蘭、比利時和中國等也都緊隨其后拉開了海上風(fēng)電場建設(shè)的序幕。我國東部沿海的海上風(fēng)能資源豐富,可開發(fā)風(fēng)能資源約達(dá)7.5億千瓦。尤其是江蘇沿海灘涂狹長,輻射沙洲風(fēng)能資源優(yōu)良,是建設(shè)大型海上風(fēng)電場的理想海域。江蘇也是我國較早利用風(fēng)能的地區(qū)之一,2006年江蘇如東15萬千瓦風(fēng)電場首批風(fēng)電機(jī)組正式并網(wǎng)發(fā)電。此后江蘇如東、響水、濱海、射陽等地又陸續(xù)啟動了一批新的風(fēng)電建設(shè)項目,2009年一些國電企業(yè)也積極參與了沿海風(fēng)電資源開發(fā),但現(xiàn)在仍屬于起步階段。由于沿海陸域風(fēng)電場因受風(fēng)力穩(wěn)定性、空間占用、視覺影響等限制,發(fā)展規(guī)模不可能太大,中國工程院專家指出,江蘇風(fēng)能發(fā)電的巨大潛力在海上,海上風(fēng)能是江蘇新能源利用的重要方向,江蘇近海蘊(yùn)藏的可開發(fā)風(fēng)能資源達(dá)到1800萬千瓦,是陸域可開發(fā)風(fēng)能資源的3—5倍。因此,江蘇新能源創(chuàng)新發(fā)展,應(yīng)以海上風(fēng)能發(fā)電場建設(shè)為主導(dǎo),以波浪能、潮汐能、海流能、溫差能、鹽差能、海洋生物能和海洋地?zé)崮艿壤醚邪l(fā)為儲備,并重發(fā)展陸上清潔能源,逐漸形成多元化的清潔能源系統(tǒng)格局,從而替代高碳化石能源,實現(xiàn)能源自給的目標(biāo)。
第三,大力發(fā)展海洋碳匯科技產(chǎn)業(yè),永久性吸收轉(zhuǎn)化陸域過剩碳排放,是江蘇未來真正實現(xiàn)全省碳匯平衡、經(jīng)濟(jì)社會可持續(xù)發(fā)展目標(biāo)的重大戰(zhàn)略抉擇。碳匯就是植被、海洋和土壤對溫室氣體二氧化碳的吸收、貯存及大氣的光化學(xué)清除機(jī)制。海洋碳匯就是海洋吸收二氧化碳的作用機(jī)理。海洋可吸收大氣中40%的二氧化碳,而有機(jī)碳93%產(chǎn)自海洋,海洋是地球氣候的調(diào)節(jié)器。資料顯示,浮游生物、細(xì)菌、海草、鹽沼植物和紅樹林等海洋生物,可以將二氧化碳吸收、存儲并轉(zhuǎn)化為海洋沉積物。盡管它們的數(shù)量只占到陸地生物量的0.05%,但地球上55%的生物碳或綠色碳捕獲都是由它們完成的。據(jù)科研結(jié)果顯示,現(xiàn)在我國臨近的海域每年可從大氣中吸收二氧化碳,渤海為284萬噸,黃海約900萬噸,東海約2500萬噸,南海可達(dá)到2億噸左右。那么,如果我國大力發(fā)展海洋碳匯科技產(chǎn)業(yè),大大增加近海藍(lán)色碳匯,就可永久性吸收轉(zhuǎn)化陸域過剩碳排放,這對沿海區(qū)域發(fā)展低碳經(jīng)濟(jì)意義重大。
江蘇人口多而集中,經(jīng)濟(jì)規(guī)模較大,碳排放總量高,碳匯不足將是一個長期需要破解的難題。在低碳背景下,盡管江蘇陸域經(jīng)濟(jì)發(fā)展采取了一系列高科技節(jié)能、降耗、減排等措施,取得了明顯的效果,但目前要做到陸域經(jīng)濟(jì)碳匯自主平衡,幾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大力發(fā)展海洋碳匯科技產(chǎn)業(yè),永久性吸收轉(zhuǎn)化陸域過剩碳排放,是江蘇未來真正實現(xiàn)全省碳匯平衡、經(jīng)濟(jì)社會可持續(xù)發(fā)展目標(biāo)的重大戰(zhàn)略抉擇。從世界海洋經(jīng)濟(jì)發(fā)展趨勢來看,海洋碳匯科技產(chǎn)業(yè)前景廣闊,它包括海洋可再生能源、海洋碳匯漁業(yè)、海濱濕地整治、海底森林修復(fù)、海水綜合利用等方面,通過生物碳匯擴(kuò)增、吸收轉(zhuǎn)化二氧化碳,不僅技術(shù)可行、成本低,還可產(chǎn)生多種效益。如中國工程院唐啟升院士提出的以海水養(yǎng)殖業(yè)為主體的碳匯漁業(yè),就是非常適合江蘇近海特點(diǎn)的可大規(guī)模發(fā)展的生物碳匯產(chǎn)業(yè)。它是通過漁業(yè)生產(chǎn)活動促進(jìn)水生物吸收水體中的二氧化碳,并通過收獲把這些碳匯移出水體的過程和機(jī)制,也被稱為可移出的碳匯,這樣就提高了水體吸收大氣二氧化碳的能力,起到了循環(huán)降低大氣二氧化碳濃度的效果。海洋碳匯漁業(yè)不僅包括藻類和貝類等養(yǎng)殖生物通過光合作用和大量濾食浮游植物從海水中吸收碳元素的過程和生產(chǎn)活動,還包括以浮游生物和貝類、藻類為食的魚類、頭足類、甲殼類和棘皮動物等,生物資源種類通過食物網(wǎng)機(jī)制和生長活動所使用的碳,其固碳數(shù)量驚人。資料顯示,在1999—2008年間,我國海水貝藻養(yǎng)殖相當(dāng)于從水體中移出二氧化碳4415萬噸,對減少大氣二氧化碳的貢獻(xiàn)相當(dāng)于造林500萬公頃以上,直接節(jié)省造林價值近400億元。研究表明,海洋大型藻類養(yǎng)殖水域面積的凈固碳能力分別是森林和草原的10倍和20倍。因此,發(fā)展碳匯漁業(yè)是一項一舉多贏的事業(yè),它不僅為百姓提供了更多的優(yōu)質(zhì)蛋白,保障食物安全,同時對減排二氧化碳和緩解水域富營養(yǎng)化具有重要貢獻(xiàn)。
第四,江蘇海洋低碳經(jīng)濟(jì)的產(chǎn)業(yè)選擇。在低碳背景下的江蘇沿海開發(fā),發(fā)展海洋低碳經(jīng)濟(jì)無疑占有重要地位。從經(jīng)濟(jì)學(xué)角度分析,發(fā)展海洋低碳經(jīng)濟(jì)的核心問題就是主導(dǎo)產(chǎn)業(yè)選擇。因此,深入研究和科學(xué)構(gòu)建江蘇海洋低碳經(jīng)濟(jì)的主導(dǎo)產(chǎn)業(yè)集群,對正確把握海洋低碳經(jīng)濟(jì)發(fā)展方向、高起點(diǎn)規(guī)劃產(chǎn)業(yè)發(fā)展戰(zhàn)略,實現(xiàn)江蘇海洋經(jīng)濟(jì)崛起后來居上至關(guān)重要。海洋資源優(yōu)勢是確立主導(dǎo)產(chǎn)業(yè)的基礎(chǔ),依托涉海發(fā)展是確立主導(dǎo)產(chǎn)業(yè)的原則,可科學(xué)劃分宏觀產(chǎn)業(yè)功能區(qū)。江蘇海洋低碳經(jīng)濟(jì)主導(dǎo)產(chǎn)業(yè)集群的發(fā)展應(yīng)該要更好、更多地利用海洋資源,產(chǎn)業(yè)要高效、集約、環(huán)保、循環(huán)發(fā)展,要制定高起點(diǎn)、高標(biāo)準(zhǔn)的配套產(chǎn)業(yè)政策。江蘇海洋經(jīng)濟(jì)主導(dǎo)產(chǎn)業(yè)集群的選擇:一是海洋清潔能源產(chǎn)業(yè)集群——永久性提供可再生清潔能源;二是海洋碳匯科技產(chǎn)業(yè)集群——永久性吸收轉(zhuǎn)化二氧化碳;三是低碳港口服務(wù)產(chǎn)業(yè)集群——創(chuàng)建低碳港口、物流、臨港工業(yè)等服務(wù)體系;四是沿海生態(tài)休閑產(chǎn)業(yè)集群——創(chuàng)建長三角最大低碳生態(tài)休閑示范區(qū);五是海洋綠色養(yǎng)殖產(chǎn)業(yè)集群——健康養(yǎng)殖、綠色加工;六是海洋生物醫(yī)藥產(chǎn)業(yè)集群——高科技利用海洋資源,提供健康藥品;七是海洋裝備制造產(chǎn)業(yè)集群——低碳、高技術(shù)增強(qiáng)海洋作業(yè)能力。
(注:本課題是江蘇省海洋經(jīng)濟(jì)研究中心2010第一號重點(diǎn)課題,編號:HK201001。 )
[1]徐從才、石齊、胡榮華:江蘇產(chǎn)業(yè)發(fā)展報告2009[M].北京:中國經(jīng)濟(jì)出版社,2009.
[2]孫加韜:中國海洋低碳經(jīng)濟(jì)發(fā)展模式探討[J].現(xiàn)代經(jīng)濟(jì)探討,2010(4).
[3]我國海洋經(jīng)濟(jì)結(jié)構(gòu)面臨深度調(diào)整[N].中國海洋報,2010-03-09.
[4]廖洋、寇大鵬:搶占低碳經(jīng)濟(jì)先機(jī)發(fā)展海洋碳匯技術(shù)[N].科學(xué)時報,2010-05-27.
(責(zé)任編輯:胡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