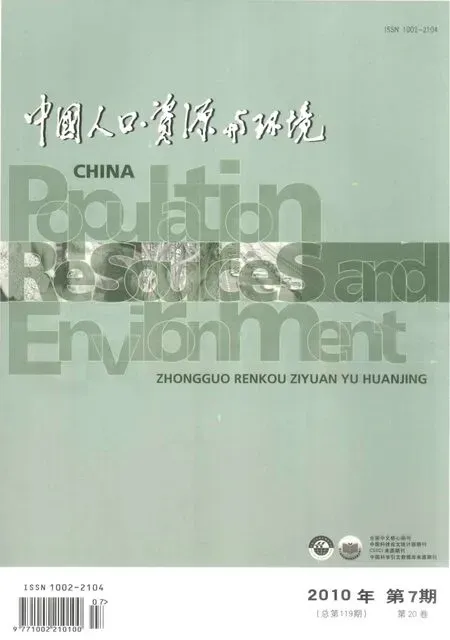流域系統復雜性與適應性管理*
金 帥 盛昭瀚 劉小峰
(南京大學工程管理學院,江蘇南京 210093)
流域系統復雜性與適應性管理*
金 帥 盛昭瀚 劉小峰
(南京大學工程管理學院,江蘇南京 210093)
資源、環境與生態已經成為制約我國長期可持續發展的主要瓶頸。本文在分析我國面臨的流域性水危機主要特征的基礎上,一方面,從復雜系統角度對流域社會-經濟-自然復合系統進行分析,揭示了流域管理面臨的復雜性與不確定性導致其必定是一個長期、復雜、艱巨的系統工程;另一方面,結合我國重點流域治理歷程對現行流域管理模式進行剖析,總結現行管理模式在管理范式與手段、政策與規劃制定、社會參與等方面存在的不足與缺陷,它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流域性問題。進而通過對適應性管理的分析及其與現行管理模式的比較,強調了適應性管理是完善流域綜合管理的有效策略。最終,從管理環境、管理體系、決策機制、管理手段以及科學研究職能等五個方面對我國流域管理轉型提出政策建議。
流域復合系統;適應性管理;復雜性;不確定性
流域是人類生活的主要生境,對人類生存與社會發展起著重要支撐作用。然而,數十年來隨著我國人口的快速增長以及經濟的迅猛發展,流域自然資源遭受嚴重破壞,生態環境持續惡化,多種環境資源危機共存且日益加重,并呈現流域性特征,使流域社會-經濟-生態可持續發展面臨重大挑戰[1-3]。突出表現在:流域性復合型水污染問題在眾多流域日益突出;水資源短缺問題從干旱地區季節性缺水轉變為普遍的季節性缺水與水質型缺水并存的局面;流域內生物多樣性降低、濕地破壞、生物群落退化等生態問題凸顯,并呈現“局部改善、整體退化”的總體格局;在全球氣候變化的影響下,水災害與突發事件的頻率、強度以及風險都在進一步加劇。我國自然生態與環境先天脆弱性及經濟持續高速發展,導致這些本應在不同發展階段出現的流域危機在短期內集中顯現與爆發[4-6],各種問題相互作用、彼此疊加,使流域資源、環境與生態問題越來越復雜化與多樣化,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與突出。而我國要以稀缺的水資源、有限的水環境容量和脆弱的水生態,承載不斷擴張的人口規模和高增長、高強度的社會經濟活動[7],面臨著比世界上任何處于同一發展階段的國家所面臨的都要復雜、嚴峻的流域性問題與前所未有的壓力[3]。
1 流域復合系統及其復雜性分析
流域水問題的系統性、復合性、多樣性、突發性和嚴峻性等特征[1-6]要求基于復雜性科學的視角,站在流域社會-經濟-自然復合系統的層面對其進行分析,以清晰全面認識其成因與復雜性,進而用科學方法進行管理。
1.1 流域復合系統
流域社會-經濟-自然復合系統是人為主體、要素眾多、關系錯綜、目標功能多樣的復雜開放巨系統,具有復雜的時空結構與層次結構,呈現整體性、動態性、非線性、適應性以及多維度等特性[8-10]。水是流域系統的紐帶,具有多重屬性。它既是一種自然資源,又是物質生產資源,同時還是一種生活資源。而人作為系統中最活躍的要素,具有一定的經濟行為和社會特征,通過資源開發與利用等社會經濟行為將資源和環境緊密聯系在一起,人的廣泛參與及其有限理性造就了流域系統的高度復雜性。
構成流域復合系統的三個不同性質的系統——自然子系統、經濟子系統與社會子系統,各自又是復雜自適應系統,有特殊的結構、功能和作用機制,而且他們自身的存在和發展又受其他系統結構、功能的制約。如圖1所示。

圖1 流域社會-經濟-自然復合系統分析框架Fig.1 Framework of social-economic-natural complex watershed system
(1)流域自然系統是一個完整的生態系統,具有自組織、自調節與自生長能力[4],是復合系統形成的基礎。系統內部存在著復雜的非線性反饋機制,并與社會經濟系統存在物質、能量與信息的交換,以生物與環境的協同共生及環境對流域內活動的支持、容納、緩沖及凈化為特征[11]。人類對自然生態系統的影響主要體現在環境污染型與資源破壞型影響,其又通過一系列自然過程、物理過程、化學過程及生物過程等使自身狀態與結構發生變化,進而決定其服務功能。自然生態系統可以通過兩種方式進行調節:外部組織或者自組織[4]。許多傳統的保護工程方式就是外部組織,但是它們結構僵硬且適應變化的潛力較小。
(2)流域經濟系統以資源為中心,經濟活動主要由市場機制與宏觀反饋控制體系進行調節。市場機制是經濟內在本體機制,市場把流域內外各種經濟活動與需求緊密聯系在一起,對資源配置和經濟運行起著重要自調節作用。而反饋控制機制體現在政府通過行政手段與經濟政策對經濟系統進行宏觀調控與干預。流域內經濟結構本身就是市場機制與宏觀控制機制相互作用下形成的。其中,反饋控制機制與資源環境壓力是對經濟系統的約束;而市場機制的作用過程是在前兩者作用下,系統內微觀主體受價格、供求與競爭等影響,不斷調整其經濟行為,逐步自組織、自適應的過程。單純依賴政府直接干預或市場自我調節都是過于簡單的做法,因此,在實踐中兩者之間的力度把握與時機選擇是相當復雜的問題。
(3)流域社會系統以人為中心。流域系統的基本功能是為了滿足人類生活的需求。在市場化逐步健全的今天,人類生活用品絕大部分是從經濟系統中獲取,因而人類生物質與文化需求是推動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人類在改變其生存環境與生活質量的過程中,直接或者間接地對自然系統產生了影響。所以,社會系統在復合系統中起主導作用,其主體的價值取向與行為方式主要受到文化傳統、價值觀等內化因素與法律規范、經濟刺激等外部因素的影響,只有對主體價值取向等有很好的規范才能保證流域經濟、自然的健康發展。
在這三種機制及其相互作用下,流域系統表現出強烈的整體性、動態性、涌現性等特點。如,人類追求經濟發展與社會穩定帶來的資源過度開發與污染排放,使流域生態狀況惡化,并嚴重影響生態系統自調節與自適應能力;而自修復能力降低導致其環境容量同步下降,加速惡化趨勢。同時,經濟發展與人口膨脹致使水資源需求量及水污染排放量同步擴大,而污染引發的水質惡化進一步加劇水資源短缺。流域生態持續退化,不但造成區域生存與發展的自然條件退化;而且大范圍生態失衡,加劇了災害風險和生態危機,使經濟難以持續增長并引發社會不穩定。然而,人類筑堤修壩、圍湖造田、超采地下水等經濟活動或抵御災害行為,一方面卻使生態環境的脆弱性更加顯著,尤其是大量水利工程設施使流域被人為地渠道化、破碎化,污染物凈化能力、水生生物生產能力等不斷下降[3];另一方面人類自身抗災的能力日益下降。進而,在多重因素影響下,流域災害層出不窮和快速增長,并以誘導型自然災害為主[5]。
總之,流域系統中社會、經濟、環境、資源相互聯系、相互制約和相互作用,構成了人與自然相互依存、共生的復合體系,具有強大的交互反饋能力[12]。流域水危機從表面上看是各種水問題相互影響、彼此疊加而愈演愈烈;但從本質上講,人的社會生活與經濟生產等對流域系統產生的干擾已不再是對流域自然過程的簡單干擾,而是社會過程、經濟過程與自然過程交織作用的集中體現[13]。
1.2 復合系統管理中的不確定性
流域復合系統的復雜性與強大的交互反饋能力,造就了在管理實踐中普遍存在的不確定性,而且許多不確定性是難于預測的。不確定性已成為流域管理取得成功的巨大障礙與必須直面的問題[14-21]。
(1)系統認知的不確定性。流域復合系統是開放的復雜巨系統,人們對其認識具有不完全性與漸進性。因而,系統認知不確定性是固有的,不僅表現在系統狀態的部分可觀測性、系統結構與過程以及歷史發展趨勢的不確定性[14],而且產生這些趨勢的系統要素及其交互關系包括非線性、反饋回路、延遲等都具有不確定性[15]。同時,自然過程、社會過程與經濟過程共同存在且作用于流域系統,使得單一學科知識并不能對其進行有效分析與總結。
(2)管理目標的不確定性。目前廣泛研究的流域綜合管理是以實現流域可持續發展為總目標,但由于系統演化及其管理涉及的時間與空間尺度較大、系統漸進認知帶來的認識滯后性等在構造該目標體系上存在很大分歧與抽象色彩,尚不存在一個明確并具有操作性的普遍認同體系[2,21]。在實踐中,人們又對問題的原因、利害關系等識別上存在分歧,不可避免地從不同的視角與利益出發提出管理的目標或需求。同時,流域內社會經濟發展以及全球經濟的影響會給管理帶來更多新的需求與問題。
(3)管理依據的不確定性。流域系統的復雜性使其狀態和干擾因素難以簡單概括為一些易測定的指標;生態修復的長期性也需要長期的可重復試驗和觀測。而且流域系統的時空特征帶來的尺度效應、累積效應、外部因素干擾以及抽樣和測量誤差,使得精確識別與量化系統狀態以及影響源及其效果分析變得異常復雜。此外,特別是由于對系統功能及過程的認識不足,管理方案不得不建立在某種模型假設前提上,而模型參數與結構的不確定性使理論結果與管理輸出之間存在差距。因此,管理的理論與實證依據具有巨大的經濟成本與時間成本效應以及潛在風險,對管理實踐提出了巨大考驗。
(4)管理決策的不確定性。決策制定者、利益相關者與科學研究者之間不協調給管理決策帶來了不確定性[2]。他們對問題的產生原因與合理的解決方案可能有不同的看法,而這些看法會影響他們對系統的認識、具體管理目標、具體管理措施成功的可能性等的判斷[16]。具體表現在研究者主要從專業學術角度對系統或特定問題進行研究;利益相關者傾向于從切身利益出發提出要求;而決策者偏重從社會經濟發展的宏觀視角去解決實際問題。
(5)系統行為的不可預測性。流域系統的自適應性也決定了系統對管理行為的響應具有不確定性。社會、經濟、人口、生態等因素的變化性使得通過觀察難以直觀推斷系統狀態以及影響源,并預測他們對管理行動的反應。個體行為的主觀性使得流域治理的社會經濟政策實施效果無從精確預測,即管理者對系統部分可控制[14]。系統的開放性還決定了系統要受到外界物質、資金與人員等方面的隨機干擾,進一步加大了系統響應的不確定性。此外,還有某些因素的不可預測性內在于系統行為中,如極端氣候條件以及不斷呈現出的新型污染物等。
綜上所述,流域復合系統作為一個復雜開放巨系統,其復雜性主要體現在流域系統及其子系統自身結構、功能與內在規律以及流域內各要素相互作用機制的復雜性,人類并不足以對它具有充分理解并實施控制。而復合系統的復雜性特征使得系統一方面呈現出極大的隨機性、模糊性、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另一方面由于系統內在自適應能力與作用規律則表現出秩序性、確定性、必然性和規律性,使得流域治理必定是一個長期、復雜、艱巨的工程。
2 我國現行流域管理模式分析
回顧我國重點湖泊及流域治理歷程,不難發現,流域治理正在經歷由單一的水利工程或者生態治理工程為主向以流域復合系統社會、經濟、生態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系統工程轉變。
從管理目標與范圍看,流域管理在不斷根據出現的問題進行調整趨于合理,而且在對流域的科學認知方面也在不斷的加深。例如,《太湖水污染防治“十五”規劃》就明確體現了政府在水環境治理方面的四大轉變:從工業點源污染控制為主向工業點源與農業面源污染控制相結合;從城市污染控制為主向城市與農村污染控制相結合;從陸上控制為主向陸上與水上污染控制相結合;從治理污染為主向防治污染與生態環境保護并重轉變,力圖進入污染控制、污染治理和生態修復的綜合治理階段。而且,管理者認識到流域治理是具有長期性、復雜性與艱巨性的系統工程,必須統籌規劃,分步實施;預防為主,防治結合;標本兼治,綜合治理;突出重點,全面推進。
盡管如此,近20年來流域治理中各類“零點行動”、“環保風暴”等執法行動與“綜合規劃”的實際效果卻差強人意,流域性污染尤其是在大型湖泊流域性污染并沒有得到有效控制,眾多湖泊富營養化趨勢仍未扭轉,污染反彈甚至惡化時常發生,大部分流域污染物排放總量不降反升。這無疑也說明了現行管理模式還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流域性問題。因此,有必要對現行管理模式進行剖析。
2.1 管理范式與手段
流域治理普遍采用機械唯物的“預測-控制式”管理范式,認為系統對管理行為的響應可以預測,進而設計最優控制策略[17-18]。尤其是近年來,國內外對小流域及其治理作了大量研究,從短期看確實解決了實踐中存在的難題。但它們大多把流域系統看作一個具有線性、規范性與平衡性等特點[13]的可簡單預測、容易控制的理想系統,針對流域中矛盾的某部分進行研究與治理,把問題當作遵循簡單線性因果關系的確定性問題來對待與處理,以試圖減小問題的復雜性及其維度[19];認為規劃制定者可以分析系統內存在的一系列明確的杠桿效應,并應用它來引導已知的反應[20]。這無疑低估了政策干預所帶來的非線性反饋效應、時滯效應以及人的自主性的重要性。這種簡化方法具有誤導性,它或許能夠在短期內成功應對某些局部問題,而長期看來卻時常具有超過短期利益的負面影響[18]。
基于這種管理范式,流域管理還是以“自上而下、層層分解”的行政命令-控制手段為主,而市場化和社會化管理手段較弱。這種手段雖然簡單易行、針對性強,但是缺乏柔性與持久性,在高不確定性的環境中效果較差。
2.2 政策與規劃制定
流域治理強調自上而下統一規劃,但很容易產生政策時滯效應,包括認識時滯、執行時滯與效力時滯三方面。現在通過成立專門流域管理機構,政府正有效縮小執行時滯,但相關機構的理論水平與預測能力往往存在很長的認識時滯;同時,流域管理中涉及復雜的社會、經濟問題,它們會讓各種政策難以發揮應有效力。例如,2007年無錫供水危機事件爆發后引發學界和政府持續討論,隨后通過國家和地方的逐級反饋與審批,到2009年才有完備的地方性措施出臺。而這些措施從出臺到實施、再到奏效需要更長的時間。
其次,綜合治理雖然以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為目標,但是規劃重在考慮水資源可利用量、水環境容量等生態因素,人文與技術因素在規劃中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與納入[21],難以充分考慮到各種利益相關群體對政策規定的可承受能力,使遵守法規和政策與生存和發展產生矛盾,從而導致現實中利益相關者為了生存而不顧生態極限。而且水環境容量測算本身就存在較大的爭議。
第三,統一規劃雖然采用綜合管理的形式,但并沒有出臺流域性的政策和實現政策間的協調。我國水資源與水環境雙重管理體制決定了流域水資源管理與水環境治理分開進行。總量控制與配額管理是規劃決策制定的依據。水資源可利用量、污染物減排目標和污染治理投資等主要依據行政區劃逐級分解,沒有遵循流域特征和污染變化趨勢以及目標的現實性[3]。
第四,在規劃制定中,低估了問題的復雜性與長期性,目標設定不合理、備選方案不足、風險管理困難等致使無法進行柔性化管理。規劃內容中對生態系統進行人為控制的色彩比較濃重,多偏重且依賴生態治理工程、大型調水工程等水利設施建設以改善流域環境。部分工程重復建設、重復投資、運行效率低下問題嚴重。
此外,有些部門集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于一身,導致權力尋租、部門利益化等問題,協調管理難度加大;監測與評估不能客觀公正,進而管理者也沒有動力與壓力來及時發現政策或工程方案存在的問題并進行調整。
2.3 社會參與
社會參與在目前流域管理中觀念極其淡薄。在管理決策中,由于參與渠道不暢通、制度保障缺乏、信息公開不足等諸多因素,NG O、科研機構以及社會公眾參與力度、范圍及深度都十分有限,即便重要利益相關者的參與力度仍不足。決策更多是一種“自上而下”被動接受的過程,這不但使公眾利益難以得到保障,對公眾及利益相關者支持度與目標可實現性也考慮不足,實施效果難免產生很大偏離[22]。而且流域治理過多地依靠國家投入,缺乏社會資金的有效注入,資金不足成為制約瓶頸。
同時,社會參與不足,不但造成公眾意識不到治理的困難與復雜,使他們傾向于抵觸有損自身利益的政策,而對環境短期內得以改善抱有很大期望;而且,公眾很容易產生路徑依賴,傾向于依賴行政機構解決環境資源問題。
3 適應性管理
不可否認,當前管理模式在流域治理中取得了長足的進步,流域問題得到了一定遏制。但這種以行政控制為主的管理模式,面對新時期日趨嚴峻的流域復合性水危機、流域系統的高度復雜性與不確定性,難以通過傳統的理性主義、還原主義決策模式對未來做出精確預測與評估,治理不到位和部分失效在所難免。近年來中外眾多學者指出,中國面臨的水危機實質上是治水體制變革長期滯后于治水需求變化累積形成的治理危機,解決核心是治水模式轉變[1]。例如,世界銀行和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等發表的中國環境問題戰略研究報告都把解決環境問題的治理結構和體制改革放在優先行動中[23]。因此,有效的管理模式與制度框架才是應對流域可持續發展挑戰的關鍵[7]。
在充分考慮生態系統的不確定性、復雜性、時滯性的基礎上,Holling于1978年提出了適應性管理理念,隨后這一思想得到了深入研究[15,24-25],并應用到生態系統管理眾多領域。適應性管理的前提是人類對任何生態系統主要驅動力及系統行為和響應的認識能力存在固有局限性,因此管理必須具有適應性和通過積累并吸收以往經驗和見解改變管理實踐的能力,通過不斷調整戰略、目標及方案等,以適應快速變化的社會經濟狀況與環境變化維持可持續的社會生態系統,其目的在于維持和增強生態系統恢復力,即關鍵生態系統結構和過程對自然和人類社會干擾的持續性和適應性,而不是對生態系統進行控制[26]。因此,適應性管理是一個通過從已實施策略結果中學習來持續改進管理政策與實踐的系統過程[15],即通過管理學習來學習管理的過程[27]。
適應性管理通過進一步融合協同管理的思想在歐美眾多流域治理中得到了很好的應用與推廣[28],并已有了不少成功案例,如美國密西西比河流域野生物種與魚類保護計劃[29]、密蘇里河流域生態恢復工程[30]、澳大利亞大堡礁水質改善項目[31]等。通過對這些治理經驗的分析,總結到適應性管理的特征及其與傳統管理模式的區別還體現在以下方面:
(1)強調對管理過程的管理。適應性管理是從廣泛的研究與溝通中形成的,它以社會參與且政府、利益相關者等分享管理權利與責任為先決條件的。實現適應性管理還需要體制建設、構建信任與社會資本的發展與完善[28]。而且,為了綜合考慮管理中不同種類的不確定性,適應性管理并不是簡單地表現為“反復試驗”[29],而是認為政策制定到實施的全過程是一個由問題識別、政策形成、政策實施、系統監測以及評價與反饋等一系列行動組成的迭代循環過程[14-19],并提倡對政策進行全生命周期管理。
(2)強調從知識管理到知識創新的轉變。生態系統管理與人類社會經濟管理是一個信息密集型的跨學科、跨領域嘗試。它需要對復合系統復雜性的綜合了解,以在多重尺度上監測系統各方面狀態、制定決策并對系統反饋做出反應[23]。因為這種復雜性,任何組織或機構難以擁有管理所需要的全面知識與信息。適應性管理的明顯特征之一就是將管理者、科學研究者以及利益相關者通過交流、溝通等方式使知識從個體私有向群體共用轉變,實現知識共享與知識創新,并形成良好的互動。
(3)強調群體決策過程。綜合視角下流域管理對象不再局限于自然系統,而是涉及到社會經濟領域。對自然生態系統科學認知的不足,單純的環境管理可以采用控制等硬系統方法;但是,人的主動性與不確定性決定了對復合系統特別是非結構化問題的管理上需要應用軟系統方法。適應性管理把利益相關者引入到決策制定過程中,能夠更有利于資源爭端與環境沖突的解決。在政策形成階段,綜合考慮不同利益相關者的視角、利益與價值觀,在多框架下,通過溝通、協商與談判達到對問題的普遍認識與共同的階段性目標,保證管理決策的公平性與公正性。只有這樣,決策才能得到廣泛的支持。因此,這個過程同樣也是信任構建的過程[28]。正如Pahl-Wost所說:管理不是為了尋求問題最優解決方案,而是持續的學習與溝通過程,其中最優先的是交流、共享觀點和提出適應性群體策略[32-33]。因而,把公眾引入到管理之中,一方面有利于公眾或利益相關者從“被動接受”向“主動商議”轉變,提高政策的公正性與支持度;同時,能夠更好地吸納社會資本,而不是依賴政府投資。
(4)把社會學習作為出發點。社會學習是貫穿其中最核心的特征[24-25,29]。社會學習理論強調社會的主動參與,強調在價值與同一性形成中人與環境的動態交互。在環境資源管理中,基于學習的方法用來處理管理中的不確定性,社會學習不單要注重構建學習型政府,而是在更為廣泛的空間開展學習,包括政府、科研機構、企業與組織以及社會個體層次。基于現行或未來的新技術為依據,通過反復實踐、評價及調整,在實踐中學習尋求適應企業或個人的“最佳管理實踐”,從傳統以保護為特征的專家知識灌輸向基于團體的學習轉變。
結合目前我國流域狀況和管理現狀,我們可以看出,適應性管理具有很大的優越性,見圖2。適應性管理是更合理治理模式的一個嘗試,是流域未來治理的一個方法創新,我們應該積極探討其在我國流域治理中的應用。

圖2 現行管理模型與綜合視角下的適應性管理模式的比較Fig.2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current management regime and adaptive management regime
4 流域適應性管理模式初探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清醒地認識到,處在社會經濟轉型期的中國面臨多方面的挑戰,推行適應性管理并非一蹴而就,還要接受來自法律法規、社會傳統、管理手段等多方面的挑戰,單純依靠以往經驗的延伸并不能順利地實現向新管理模式的轉型。本文主要從管理環境、管理體系、管理手段、決策機制以及科學研究等五個方面作初步探討。
4.1 從單獨立法到綜合立法:管理環境轉變
健全的流域管理法律與法規是實施流域適應性管理的基本環境與根本保障。據我國水法與水污染防治法及其相關法律法規,現行流域管理以流域統一管理為主、以部門管理和行政管理為輔的統一管理模式。然而,在管理實踐中情況卻與理論設計相反,國家管理機構與地方機構條塊分割,以河流流經的各行政管理為主,涉水部門甚至行業管理部門各自為政,形成了區域和行業在水資源及其它資源管理、開發、利用等方面的決策分散化狀況,而流域綜合管理機構權力被瓜分無法履行協調管理職能。究其原因是目前我國尚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流域法,有關流域管理的法律法規通常是部門或行政區立法,一方面,人為割裂了流域內環境資源與社會、經濟的內在聯系;另一方面,各部門與行政區立法重復甚至沖突,相關利益者的權利與義務、職能部門的權力與責任等方面不夠明確,加重了流域管理和協調的難度。而且,現行法律法規大多是實體性立法,缺乏跨部門、跨行政區管理以及利益相關者參與的程序性規定,實體性規定沒有程序性制度相配合將導致實體性規定的目標難以實現。
4.2 從集中管理到多中心治理:管理體系創新
適應性管理體制是以政府為主導、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多主體互動合作的多中心治理格局[34],這種合作治理模式實質上通過建立一種在微觀領域對政府、市場的作用進行補充或替代的制度形態,有利于大量的社會力量參與治理,形成“政府、社會、市場”上下互動的管理過程與公共行動網絡。它要求流域管理中多元利益相關者、社會公眾及科學機構有直接參與決策的權利與義務,如果失去了這一點,流域管理很容易又走入政府專行的集中管理局面。在新的管理體制下,管理能夠更科學公正地進行決策,而且能夠針對管理效果的反饋以及突發性做出及時果斷的反應,避免傳統層級審核與命令方式在時間上的延遲。Ostrom等已經論證了多中心治理在發展中國家的可行性[34]。尤其是當前我國一些湖泊流域非點源污染已經替代點源成為水質問題的主導要素,其分散性、隱蔽性、隨機性、不易監測、難以量化等特征使得政府管制難度越來越大。引入以社區、村鎮為單位的自主治理是十分有必要的。它能夠充分利用成員的合作優勢與監督力量,在微觀層面對環境治理形成共識。
然而,建立這種體制需要從各個層面逐步開展。在國家層面上,完善公眾參與的相關法律制度是基礎,加強對NG O及利益相關者等參與流域管理的權益規定,并出臺公眾參與的具體程序性規定;在流域層面上,轉變傳統管理觀念積極推動機構改革,建立制度化的參與機制,進而組建社會參與的綜合性流域管理機構;在部門與地方層面上,信息披露要及時全面,意見征求要切實落實[35];在社會層面上,宜鼓勵社團組織、公眾社區等民間組織的創建與發育,并通過一定的賦權使他們有效地行動起來,形成環境資源治理的基礎。
4.3 從單一管理到綜合集成管理:決策機制創新
適應性管理雖然強調自組織管理與群體參與,但是最終還是要以科學決策機制為支撐來保障其發揮效用。目前,盡管各類計算機信息系統和水質監測裝置普遍運用,但參與式的群決策機制還處于概念化層面,缺乏系統性和科學性。有關參與式決策機制、群體決策支持平臺研究幾乎是空白,國外也沒有完整、直接現成的成果可供借鑒。錢學森先生提出的綜合集成研討廳體系是在長期實踐背景下融合多學科與多領域的技術與方法而形成的可操作的、行之有效的方法體系和實踐方式。宜以該方法為指導,通過綜合集成定性定量相結合、專家研討、信息處理與數據融合、人工社會與虛擬現實、群體決策及定性推理技術和分布式交互網絡環境等多種技術與方法,從“定性綜合集成”到“定性定量綜合集成”再到“從定性到定量綜合集成”循環往復、逐次逼近,建立創新型的治理決策機制,用結構化的決策序列來逼近流域管理中非結構化問題。
4.4 從剛性管理到柔性管理:管理手段豐富
行政手段面對日益復雜與高度不確定的環境已經顯得力不從心。而當前我國流域管理中依然未培育出良好的市場經濟手段。這使得政府職能主要集中在興建、運營水利工程及污染末端治理。所以,宜充分重視利用經濟手段把環境成本內部化,從經濟上刺激環境資源破壞者行為與價值觀的轉變。具體來講要完善流域資源的有償使用制度,推進水價改革與排污權制度并形成合理的價格機制,促進水權、排污權等各類市場的發育,建立與現有技術相適應的排污標準以及通過特許經營開放傳統政府壟斷的水務市場。除經濟手段與市場建立外,更要充分認識社會化管理手段的重要性。一方面,通過推行社會教育與培育社團組織、公眾社區等非政府組織,提高公眾資源節約與環保意識,引導與規范流域內居民的生活方式與行為;另一方面,鼓勵公眾參與到管理決策制定與持續監督中,并通過決策參與使人們能夠更積極地支持政策實施與改變生活方式。同時,注重行政手段與經濟手段、社會化管理相結合,傳統政策優勢與體制機制創新相結合,提高各類手段的綜合效力。最終在此基礎上,使行政管理機構完成向社會管理與公共服務的職能轉變。
4.5 從經驗治理到科學治理:科學研究職能轉變
盡管政府一直強調強化流域治理科技支撐體系,但重心放在污水處理、生態修復、綜合防治等技術原始創新、集成創新和推廣示范上;而一些交叉學科研究與實際應用脫軌。決策大多在國內外經驗與利益權衡的基礎上制定,而非科學認知。由于流域有自身社會經濟、地理等特性,單純經驗治理難免走許多彎路。因此,針對特定流域,需要采納多維度、多尺度和跨多學科的研究視角,構架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科學與政策、流域社會與環境之間溝通、協作的橋梁。在研究中注重自然、經濟、社會等多要素的集成分析,以揭示系統結構與過程的演變規律與特征;注重自然過程與人文過程的集成研究,強調人類活動影響下流域過程的綜合研究;針對不同尺度社會-生態過程機理開展研究,通過尺度效應分析和尺度轉換展開多尺度研究,以保證研究的整體性。
與此同時,科學研究要完成從管理顧問向決策支持的角色轉變。研究人員要在對流域系統科學認知的基礎上,結合流域的現實狀況,通過系統分析、構建模型及情景模擬等對決策方案進行風險、效果評估及優化設計,進而為決策提供科學依據。
(編輯:劉呈慶)
References)
[1]中國科學院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組.2007中國可持續發展戰略報告——水:治理與創新[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7.[Chin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y Study Group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Chin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y Report 2007:Water:G overnance and Innovation[M].Beijing:Science Press,2007.]
[2]楊榮金,傅伯杰,劉國華,馬克明.生態系統可持續管理的原理和方法[J].生態學雜志,2004,23(3):103-108.[Yang Rongjin,Fu Bojie,LiuGuohua,MaKeming.Principles and Methods of Sustainable Management of Ecosystem[J].Chinese Journal of Ecology,2004,23(3):103-108.]
[3]陳宜瑜,王毅,李利鋒,于秀波,等.中國流域綜合管理戰略研究[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7.[Chen Y iyu,Wang Y i,Li Lifeng,Yu Xiubo,et al.Research on Integrated River Basin Management Strategies in China[M].Beijing:Science Press,2007.]
[4]Mitsch WJ,Jorgensen S E.Ecological Engineering:A Field Whose Time has Come[J].Ecological Engineering,2003,(20):363-377.
[5]黃朝恩.人類活動所激化的自然災害[J].環境教育季刊,2000,(41):49-56.[Huang Chaoen.Natural Disasters that Intensified by Human Activities[J].Environmental Education Quarterly,2000,(41):49-56.]
[6]許振成,王俊能,彭曉春,郭梅.中國環境管理的戰略創新[J].生態環境學報,2009,18(3):1189-1193.[Xu Zhencheng,Wang Junneng,Peng Xiaochun,Guo Mei.Strategic Innovation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in China[J].Ecology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2009,18(3):1189-1193.]
[7]中國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委員會.給中國政府的環境與發展政策建議[M].北京: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2005.[China Council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nEnvironmentand Development.Policy Recommendations to theChineseG overnment onEnvironmentand Development[M].Beijing:China Environmental Science Press,2005.]
[8]馬世俊,王如松.社會-經濟-自然復合生態系統[J].生態學報,1984,4(1):1-10.[Ma Shijun,Wang Rusong.Social-Economic-Natural Complex Ecosystem[J].Acta Ecologica Sinica,1984,4(1):1-10.]
[9]劉永,郭懷成.湖泊-流域生態系統管理研究[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Liu Y ong,Guo Huaicheng.Lake-Watershed Ecosystem Management[M].Beijing:Science Press,2008.]
[10]聶華林,王水蓮.區域系統分析[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Nie Hualin,Wang Shuilian.Region System Analysis[M].Beijing:China Social Science Press,2009.]
[11]劉建康.劉建康.生態學文集[M].北京:化學工業出版社,2007.[LiuJiankang.Collected Works of LiuJiankangon Ecology[M].Beijing:Chemical Industry Press,2007.]
[12]CostanzaR,Low B,OstromE.Institutions,Ecosystemsand Sustainability[M].Boca Raton:Lewis Publishers,2001.
[13]楊桂山,李恒鵬,于秀波.流域綜合管理導論[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4.[Yang Guishan,Li Hengpeng,Yu Xiubo.Introduction of Integrated Watershed Management[M].Beijing:Science Press,2004.]
[14]Owens P.Adaptive Management Frameworks for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at the Landscape Scale:Implications and Applications for Sediment Resources[J].Journal of Soils and Sediments,2009,9(6):578-593.
[15]Pahl-Wostl C,Sendzimir J,Jeffrey P,et al.Managing Change toward Adaptive Water Management through Social Learning[J].Ecology and Society,2007,12(2):30.
[16]Dewulf A,Craps M,Bouwen R,et al.Integrated Management of Natural Resources:Dealing with Ambiguous Issues,Multiple Actors and Diverging Frames[J].Water,Science and Technology,2005,52(6):115-124.
[17]Moberg F,Galaz V.Resilience:G oing from Conventional to Adaptive Freshwater Management for Human and Ecosystem Compatibility[R].Sweden:Stockholm International Water Institute,2005.
[18]Pahl-Wostl C.The Implications of Complexity for Integrated Resources Management[J].Environmental Modeling&Software,2007,22:561-569.
[19]Sterman J.Business Dynamics:System Thinking and Modeling for a Complex World[M].Boston:McGraw-Hill,2000.
[20]孫建.適應性管理[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Sun Jian.Adaptive Management[M].Beijing: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2006.]
[21]Ludwig D,Hilborn R,Walters C.Uncertainty,Resource Exploitation,and Conservation:Lessons from History[J].Science,1993,260(17):17-36.
[22]Smith J.A Critical Appreciation of the“Bottom-up”Approach to Sustainable Water Management:Embracing Complexity rather than Desirability[J].Local Environment,2008,13(4):353-366.
[23]世界銀行.中國:空氣、土地和水——新千年的環境優先領域[M].北京: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2001.[The World Bank.China:Air,Land and Water:EnvironmentalPriorities of a New Millennium[M].Beijing:China Environmental Science Press,2001.][24]Holling C.Adaptive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and Management[M].New Y ork:John Wiley and Sons,1978.
[25]Lee K.Appraising Adaptive Management[J].Conservation Ecology,1999,3(2):3.
[26]Gunderson L,Holling C,Light S.Barriers and Bridges to the Renewal of Ecosystems and Institutions[M].New Y 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5.
[27]BormannB T,Cunningham P G,Brookes M H,et al.Adaptive Ecosystem Management in the Pacific Northwest[R].Portland: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Forest Service,Pacific Northwest Research Station,1994.
[28]Berkes F.Evolution of Co-management:Role of Knowledge Generation,Bridging Organizations and Social Learning[J].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2009,90:1692-1702.
[29]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Adaptive Management for Water Resources Project Planning[M].Washington D C:National Academies Press,2004.
[30]Prato T.Adaptive Management of Large River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Missouri River[J].Journal of the American Water Resources Association,2003,39(4):935-946.
[31]Broderick K.Adaptive Management for Water Quality Improvement in the Great Barrier Reef Catchments:Learning on theEdge[J].Geographical Research,2008,46(3):303-313.
[32]Berkes F,Colding J,Folke F.Navigating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Building Resilience for Complexity and Change[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
[33]Pahl-Wostl C,Hare M.Processes of Social Learning in Integrated Resources Management[J].Journal of Community and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2004,14:193-206
[34]Ostrom E,Schroeder L,WynneS.InstitutionalIncentive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M].Boulder:Westview Press,1993.
[35]王毅,王學軍,于秀波,王亞華.推進流域綜合管理的相關政策建議[J].環境保護,2008,(19):22-24.[Wang Y i,Wang Xuejun,Yu Xiubo,Wang Yahua.Policy Recommendations Related to Promoting Integrated River Basin Management[J].Environmental Protection,2008,(19):22-24.]
AbstractResources,environment,ecology become the main constraints to China’s long-term sustainable development.On the basis of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s of China’s water crisis,Social-economic-natural complex-watershed-system is analyz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plex systems,revealing that the complexity and uncertainty in watershed management make the management a long-term,complex and arduous systematic prosect;on the other hand,the shortages and weaknessesof current management regime are discussed through analyzing the course of water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 management in China,and current regime could not solve watershed problems.Then,the paper proposed that adaptive management is an effective strategy for improving management capacities.At last,policy recommendations on management environment,management structure,decision mechanism,management measure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are made through the comparison between adaptive management and current management regimes.
Key wordscomplex system;adaptive management;complexity;uncertainty
Complexity Analysis on Watershed System and Adaptive Management
JIN Shuai SHENG Zhao-han LIU Xiao-feng
(School of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Jiangsu 210093,China)
TV213
A
1002-2104(2010)07-0060-08
10.3969/j.issn.1002-2104.2010.07.010
2010-03-12
金帥,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為計算實驗與環境經濟政策。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點項目(No.70731002);高校博士學科點專項科研基金(No.2009009111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