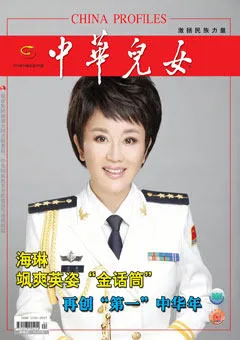馬益民 用藝術對話自然
2010-12-29 00:00:00章英
中華兒女 2010年24期






2010年10月底,第二屆7坊街新疆藝術進京展在北京王府井大街舉辦。帳篷式的展廳里,一個展臺上的幾塊石頭畫讓每個參觀者都眼前一亮,繼而又心中一凜。那畫中,分明是狼,那“畫布”分明是石頭。
這是畫家馬益民的作品——石頭畫,主題都是狼。他愛畫畫,卻不甘于紙面的力道,轉而將筆觸落向石頭,開創了石頭畫。在紋理中落墨,似乎是要把油畫的色彩融進大漠的萬種風情。
獨辟蹊徑畫石頭
馬益民從小在城市長大,家里沒有與藝術有關的人。
或許生命中注定要去發現、贊美家鄉獨特的美,馬益民很小就對繪畫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新疆絢麗的少數民族風情、迷人的自然風光,都讓這個生長在新疆的孩子發自內心地愿意去細細感受、耐心品味。
彼時沒有相機,他就選擇了畫筆。
那個年代,功課從來不是學生頭頂的大山,課余時間背著畫板去寫生采風,成了馬益民童年、少年的記憶中最美好的風景。
而他的美術基本功,也恰是在這個階段打得扎實、牢靠。不過,命運似乎并沒有讓他一路沿著五彩斑斕的藝術之路走下去,中間的動蕩與波折,似乎總是告訴馬益民,藝術并不屬于他。為了能夠畫畫,他去當兵,可是在部隊,似乎也和真正的美術沒有太多關系;復原之后,馬益民又去了單位的工會,可是他的美術夢依舊難以照進現實,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他做的最多的是單位的板報,刷美術字;他一度放下了畫筆,因為看不到方向;他又不忍就這樣向心中的最愛告別,屢屢又重新拾起夢想。
然而揮筆調色之間,總好像缺了一點什么。
直到有一天,馬益民看到了石頭。石頭,是大漠中最常見的東西,它們常年在滾滾黃沙中棲身,被埋沒抑或在大風中裸露出來,沒有人注意它們,它們就默默地證明自己的存在,歷經四季、晝夜、大風陽光,從不示弱。“這是一種精神。”馬益民開始嘗試用柔軟的畫筆與這些堅硬的石頭對話。他不光賦予它們色彩,還賦予它們靈性。
新疆隨處可見的石頭,是在風沙磨礪下變得粗糲卻外形圓潤的石頭。它們很快就會吸收涂上去的油彩,就像它們其實渴望被理解。馬益民被打動了,正如他沉寂多年的畫筆找到了對話的對象。馬益民是學油畫出身的,他把油畫的筆法運用到石頭畫上,細膩的筆觸和柔和的色彩,在暗淡卻沉著的石頭表面上附著,立體而不突兀、柔和卻不失凌厲、準確卻不扎眼。馬益民一發不可收拾。
石頭,成了他的畫布。在這里,馬益民完成了自己與自然之美、藝術之美的對話。
追尋狼圖騰
馬益民是個溫和儒雅的人。
可是看他捧出的石頭畫,主題幾乎只有一個——狼。它們是草原上的狼、荒漠中的狼,雪地里的狼、夜幕下的狼……它們有的三五成群、有的孤身而立、有的帶著幼崽,可是不論怎樣,它們都是一副桀驁的氣勢,擺出凌厲的眼神,似乎注視著幽怨的遠方。
馬益民說,他喜歡狼,崇拜狼。在他看來,狼的獨立、堅韌與靈性,似乎同自己內心深處的追求有所神似,有所共鳴。那是他所走過的艱難的日子。為了追尋心中不可磨滅的美術之夢,他離開了“鐵飯碗”,探索石頭畫的技法。但是這畢竟是一門新興的藝術品種,前無方向,也沒有可供參考借鑒的范例,身邊也沒有同行的相互勉勵、競爭。或許孤獨是人最難以承受的壓力,馬益民那段時間很難。
他一度想要放棄,雖然妻子、孩子的支持,讓他始終懷揣溫暖,但畢竟現實的艱難讓這個當時已經奔向不惑之年的漢子有些猶豫和動搖。
每天,他把自己關在屋子里畫石頭,用筆下的線條和色彩向心中的夢想發問。他也一次又一次琢磨他最愛畫的狼的性情和品格,只有充分地把握它們的性情才會有富有神韻的作品問世。去戶外采風、認真地琢磨他從各種地方看到的狼的眼睛、研究關于狼的資料……馬益民漸漸讀懂了這種被許多民族奉為圖騰的動物。
即便在最喧囂嘈雜、人心浮躁的地方,它們也能一如既往地不疾不徐,保持著自己冷靜的思維、堅決的立場、堅定的目標。它們經常獨行,卻從不畏懼孤獨;它們具有很強的集體精神,敢于奉獻。“就應該把這樣的精神呈現出來。”馬益民首先在心里為自己樹立了一種精神的立柱,再把這些精神落墨于筆端,刻畫在石頭上。
人最需要的是一種精神。馬益民的石頭畫以新穎的形式、獨特的搭配以及畫面中撲面而來的濃烈的氣質,開始吸引越來越多的觀眾。他們從好奇到喜愛,甚至膜拜。2009年,馬益民終于在新疆7坊街創意產業集聚區有了屬于自己的工作室。在不到一年時間里,就有數十件作品被收藏,有些作品還作為政府禮品,被遠方的客人珍存。
馬益民正在走向一條通往心中夢想的成功之路,然而他依舊謙虛。他為自己做的注腳是“看自己愛看的,寫自己愛寫的,畫自己愛畫的”。的確,相對于名利,他更珍惜這些與狼共舞追尋夢想的日子。
責任編輯 李菡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