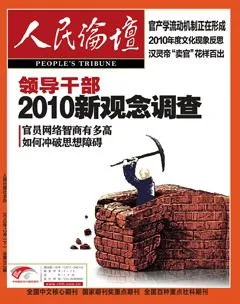如果強拆一如既
強拆所捆綁的很多“規劃” 或 “項目”,其公益性大受質疑,其突破改革倫理底線是遭致強 烈抗爭的根本原因
無恒產則無恒心
中國人素有“安土重遷”的傳統,這一傳統孕育出淳樸的鄉民、重義的道德、團結的社區和超穩定的政治結構。盡管經歷了現代化的沖擊與革命的顛覆,中國人的深層心理結構與倫理內核并未根本斷絕。
在重新重視傳統文化、倡揚和諧的今天,此起彼伏的“拆遷戰爭”卻繼續著一種粗暴的逐利邏輯和殘忍的文化自戕,將廣大的城市平民和農村居民推向漂泊的市場和無盡的抗爭深淵。
無恒產則無恒心,無恒心則或盜或搶或自焚,一切的亂象都可以與近年來最具影響力的那個社會關鍵詞——“拆遷”相關聯。在規模越來越大、抗爭越來越烈的“拆遷”中,仁愛、寬容、誠實甚或保守等社會核心倫理價值,被“利益”撕扯得七零八落。這是理想與實踐的嚴重背離。其中深伏的危機不能不引起人們反思,尤其是那些處于“拆遷”第一線的、或官或商的“精英們”。
地方強拆有理之辯
如此普遍類似、席卷全國的“大拆遷”,其動力何在?地方官員最冠冕堂皇的理由無非兩個:一是央地財政關系里面“事權大、財權小”的結構性矛盾,“強拆有理”;二是各種拆遷與地方發展項目掛鉤,其對地方GDP的貢獻直接成為官員晉升的政績基礎,強拆“更有理”。
關于央地財政矛盾的訴求有一定合理性,從實際情況來看,大部分工業欠發達地區的政府財政對土地收益的依存度很高,而同時中央事權又不斷向地方攤派,這一“擠壓”形成了推動地方政府強拆的經濟動因和心理支持。但是,假如說地方沒錢所以才要搞拆遷,那么地方搞了拆遷有錢了,公共服務的數量和質量是否跟隨強拆而大幅提升呢?
關于拆遷與地方發展、政績考核的關系,則存在可辨別之處。任何改革或發展都存在倫理底線,或曰“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或曰“帕雷托改進”,或曰“增量邏輯”,道理只有一個:不能損人利己,尤其不能損害大多數人的利益。強拆所捆綁的很多“規劃”或“項目”,其公益性大受質疑,其突破改革倫理底線是遭致強烈抗爭的根本原因。政績觀不改變,改革倫理不確定,這樣的改革與發展只能越來越撕裂社會,增加對抗。
不能想拆就拆
即便有了拆遷的動力,為何地方政府總能夠做到想拆就拆呢?不是有《憲法》、《物權法》保護私有財產嗎?不是有各級黨委、人大、政府和法院制約官員的沖動嗎?為何這些都沒能有效阻擋拆遷的車輪?在技術層面上,這是因為調整拆遷法律關系的具體制度嚴重滯后。廣受詬病的《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將拆遷補償關系錯誤地界定為民事法律關系,放棄了政府的保護與補償的責任。
于是在現實中,圍繞土地和財產而展開的博弈,便演化為為有錢有勢的開發商與孤立的被拆遷“散戶”之間的流血沖突,政府還不時對強勢的開發商施以援手。開發商既然已經付出了各種成本并與地方政府達成了分利默契,豈可指望其尚存“仁慈”?向上游制度走,問題出在規劃上。城市(城鄉)規劃中嚴重缺乏信息公開和民主參與,具體的財產權頓成“規劃海洋”中的孤島,被隨便漫溢和侵占。再看補償,舉著“公益”招牌,不談市場規則,利用差價大肆套利,漸具市場意識和權利觀念的民眾怎會服從?這一制度已成改革倫理的“吞噬器”,不改不行。
“強拆”透支政治合法性
大體而言,此種“強拆”模式顯然已經疲軟,因為它突破了改革倫理的底線,因為它遭遇到了最強烈的社會抵抗并最為“奢侈”地透支著現有體制的政治合法性。
具言之,有四方面的理由要求禁止掠奪式“強拆”:第一,“強拆”是政府與民爭利的行為,傷害了亙古以來“官不與民爭利”的政治倫理;第二,民眾日益理性和具有權利意識,地方政府強拆將遭遇更加強烈、更大范圍的抵抗,甚至可能演化為階層與地區對抗,最近仍在繼續的“自焚”悲劇等各種形式的“吶喊”,足可為證;第三,強拆模式不適應產業結構調整與包容性增長的新發展模式的需要,強行堅持只能越來越抹黑地方形象,惡化官民關系,拖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后腿;第四,強拆反映的是掠奪性質的“零和博弈”,與改革倫理里的“增量邏輯”相悖,不及時糾正將無法彌合這一行為對根本政治合法性的傷害。
政府和民眾都應當從共同的行動中進行反思,增進社會公共理性。在社會層面上,改革就是一個不斷提供社會系統“負熵”的過程。強拆的利益化本性已經顯現出其破壞社會系統穩定的后果,不改不行!
不久前,江西宜黃一位地方官員振振有詞:“沒有拆遷就沒有新中國”;應該反問一句: “如果強拆一如既往,中國‘新’在何處?”(作者為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