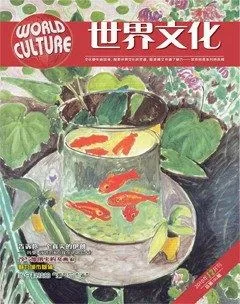追憶謝甫琴柯
最初聽到謝甫琴柯的名字,是上世紀50年代初,從父親自前蘇聯帶回的《謝甫琴柯畫冊》上。那時年紀還小,只記得他是19世紀烏克蘭著名詩人、畫家。待我們捧讀戈寶權譯的《謝甫琴柯詩選》,并漸漸走近他,已是在北大讀書的時候。記得魯迅先生在《摩羅詩力說》一文中,曾滿腔熱誠地推介了拜倫、裴多菲等一批19世紀“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的“摩羅”(即“反抗”)詩人,說他們“無不剛健不撓,抱誠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隨順舊俗”;而“發為雄聲,以起其國人之新生,而大其國于天下”。實際上謝甫琴柯也應屬“摩羅”詩人之列:“別等待/等待自由——徒勞!/自由已睡去,/是沙皇迫使它——昏倒!/如何使沉睡的自由醒來?/我的人民啊/快舉起所有的棍棒/還有那,烏克蘭寶刀!/那時候,自由——才能來到!”讀讀這些驚雷與號角般“叫喊與反抗”的振聾發聵的詩句,能不“心神俱旺”,熱血沸騰嗎?
謝甫琴柯1814年3月9日生于烏克蘭基輔省一個叫麥瓦茨的小村莊,祖輩都是農奴。他只活了47歲,卻當了27年農奴;被充軍流放了10年;剩下的13年過得也如他所說,是“用鏈子拴著的狗”一樣的“自由”生活。那時的烏克蘭不僅受到俄國沙皇的專制統治,還受到列寧說的“最殘暴的亞洲式的農奴制度”的壓迫。在農奴主眼里,他不過是“會說話的牲口”。他自幼聰穎、伶俐,烏克蘭民歌和美麗的原野又滋養與激發了他的藝術天賦,放牧間隙他注意搜集民歌和描摹自然風光。農奴主發現他的藝術才能,把他帶到彼得堡,想把他變成一株搖錢樹。1838年著名畫家勃柳洛夫器重謝甫琴柯的天賦,又同情他悲慘的身世,用賣畫籌得的2500盧布巨資,幫他贖身,并送他進美術學院深造。
有了“自由身”的謝甫琴柯更加發奮地學習繪畫技巧,并開始了詩歌創作,1840年他的處女作《科布查爾》(烏克蘭民間流浪歌手的統稱,多系盲人)為他在烏克蘭和俄國贏得了廣泛聲譽。在莫斯科《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作者奧斯特洛夫斯基紀念館中,陳列著一本謝甫琴柯的《科布查爾》,那是奧斯特洛夫斯基生前最愛讀的書。他在躍馬揮刀戰事倥傯中,也將它帶在身邊,每每思念烏克蘭鄉土,都會吟誦謝甫琴柯的詩和哼著烏克蘭民歌:“滔滔的德聶伯洶涌澎湃/狂風怒吼,落葉紛紛/你看那月亮蒼白暗淡/在烏云后面徜徉不停/就像扁舟飄在海上/隨波起伏時現時隱。”由于經常翻閱,封面和邊角都已磨損,后來纏綿病榻,這本詩也—直放在他的枕邊。
1841年謝甫琴柯創作的《吉卜賽占卜師》在彼得堡畫展中為他贏得第三個獎項的同時,他的以18世紀烏克蘭反對波蘭的農民起義為題材的長詩《蓋達馬克》,也為他帶來更廣泛的聲譽。他的名聲也傳到沙皇耳中。那個年代能被沙皇召見,是難得的寵幸,而謝甫琴柯對此卻不以為然。相傳其余被召見者步入召見大廳,都無一例外地躬身向沙皇致敬,唯獨謝甫琴柯一動不動。沙皇問:“你是什么人?”他不卑不亢地回報了姓名。沙皇說:“我是一國之君,舉國上下誰見到我都要躬身行禮,你為何這般無禮?”他回答說:“是你要見我,不是我要見你。如果我也像其他人那樣垂首躬身,你如何看得清我呢?”這傳說真偽無須細細考證,人民愛戴他、敬仰他,他們都知道他在權貴面前,從來不是“恭順的奴隸”:“有一天,我走在涅瓦河畔/那時正半夜更深/我一邊走,一邊思忖/如果奴隸們不那么恭順/這些被玷辱的高樓/就不會立在涅瓦河濱/人們就會變得親如姐妹、弟兄/可現在,這兒只見無數眼淚和苦痛/既沒有上帝,也沒有神靈/是一群獵狗的看管人在霸道橫行……”沙皇在他的眼里,不過是“一群獵狗的看管人”。
1847年剛剛贖身做了10年“自由人”的謝甫琴柯,又由于在長詩《夢境》中譏諷沙皇暴政和參加秘密政治社團而被捕,并被發配到偏遠的烏拉爾山的奧倫堡服役,沙皇尼古拉一世親批:“嚴加監管,禁止寫作、繪畫。”然而枷鎖與酷刑都無法摧毀他的意志。透過牢獄的小窗,他凝望夜空,在小紙片上寫著對故鄉的懷念:“田野、山峰沉入黑暗/一顆星出現在深邃的遠天/我禁不住悄悄流淚/星兒喲,此刻你是否也出現在烏克蘭……”他把這些紙片藏在靴筒里,后來集印成詩集《在囚室里》,這些詩還有一個別稱——靴筒詩。后來,他又轉赴曼格什拉克半島羈押,直到1857年才恢復自由。
雖說恢復了自由,卻依舊受著監視,流放與苦役又嚴重摧殘了他的健康。晚年他唯一感到寬慰的是有機會同托爾斯泰、車爾尼雪夫斯基、涅克拉索夫、屠格涅夫等同時代俄羅斯最著名的文學家們交往。這些人和謝甫琴柯一起,一直在為他的兄弟和妹妹解脫農奴身份而奔波。1859年,謝甫琴柯拖著病體回家鄉看望妹妹雅琳娜,途中他曾寫過《寫給妹妹》這首詩:“……我一面走,一面思量/仿佛走進夢鄉/我看見一座春光明媚的花園/山丘上有一處小巧的住房/好像少女穿上了嫁妝……/櫻桃樹下坐著我的妹妹/她是個神圣的、受難的女郎/目不轉睛地盯著德聶伯河/把我這不幸的人盼望/她看著我的小舟從浪花里浮起/漂著,漂著,卻沉入無底的汪洋/我聽見她在呼喚:‘你在哪里,哥哥呀!’/我從夢中驚醒/依舊滿懷悲憤/妹妹仍在服著勞役/我呢——還在囚禁……”那時,整個俄羅斯都是“沒有上鎖的牢獄”,即使是“自由人”,不同樣在囚禁嗎?!
1861年3月10日,謝甫琴柯剛剛度過他47歲生日的第二天,便在政治迫害與物質生活窘困中離開了人世。就在他去世不久,農奴制終于被廢除。他未能看見沙俄統治與農奴制度的垮臺,但他堅信這一天終會到來。他在那首著名的《遺囑》中說:“當我死后/請把我葬在烏克蘭遼闊的草原上/讓我能望見廣袤的田野/能望見德聶伯河邊的峭壁/和聽見河水的喧響。”他呼吁:“起來!砸開鐐銬/用殘暴的敵人的血/把我們的意志澆灌!”他預言總有一天“河水把敵人的血/從烏克蘭身上沖洗下來/沖入藍色的大海”。并深情地期望,在那一天到來的時候,烏克蘭人民,“在偉大的自由的新家庭里/請別把我忘記/常用親切溫存的話語/把我追憶。”他死后,友人根據他的遺愿,把他的遺體運回故鄉,安葬在德聶伯河岸邊的卡尼夫的僧侶山——后改稱謝甫琴柯山。
謝甫琴柯是烏克蘭肥沃的黑土地上生長的一株大樹,他深深扎根在人民中間,用他的詩歌傾吐他們的疾苦,反映他們的斗爭,表達他們對自由、對光明和未來幸福生活的向往,與他們肩并肩地同黑暗專制統治奮戰了一生。他繼承和發展了俄羅斯文學的優良傳統,創建了烏克蘭文學語言和獨特的民族風格,是烏克蘭現代文學的奠基人。早在1921年茅盾先生就將謝甫琴柯的《獄中隨想》譯成中文,并將他列入《俄國文學家三十人合傳》,推介給中國讀者。此后,他的作品不斷被譯成中文,深受中國廣大讀者歡迎。戈寶權、夢海、藍曼、高莽、魏荒弩等翻譯家都譯介過他的作品。1961年為紀念他逝世一百周年,又編印出版了他的三卷文集。父親應約在他逝世一百周年紀念會上做報告時,一改通常的“年表加空洞概念”的枯燥模式,而是用“親切溫存的細語”,和聽眾一起“追憶”這位烏克蘭的農奴詩人。報告的結尾更出人意料地用詩來呼應謝甫琴柯的囑托:“……在你離開我們一百年的時候/不僅烏克蘭人/不僅全蘇聯人/都不會把你忘記/都在用你所愿望的/‘親切溫存的細語’/把你追憶∥而且啊,在這兒,在你曾關切過的中國/也在用‘親切溫存的細語’/把你追憶//春風呵,托你帶著這/‘親切溫存的細語’/掠過蒙古沙漠/穿過貝加爾湖/越過烏拉爾山/送到德聶伯河畔/送到塔拉斯耳邊……”有作家曾評論說,這樣的報告就像是感受到從烏克蘭草原上“吹來的一股清新的風”。
如今,又五十年過去,中國人民依舊懷念謝甫琴柯這位偉大的詩人。前不久,翻譯家高莽在烏克蘭駐華使館受烏克蘭總統之托,為表彰謝甫琴柯為烏中兩國文化交流做出巨大貢獻的授勛儀式上的發言中,還提到謝甫琴柯生前對中國太平天國農民起義給予的道義上的關注與支持。謝甫琴柯不僅生活在烏克蘭人民心中,也生活在中國人民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