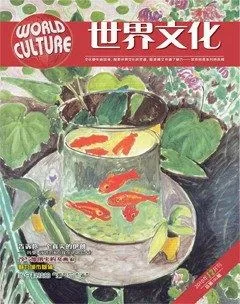當詩歌遇到雕塑
1902年7月為了維持生計,當時一文不名的小詩人里爾克不得不為里夏德·穆特爾編輯出版的德國新藝術專題叢書寫一本評論羅丹作品的小冊子。當然很快證明這件事的意義遠遠超過了它的意圖。因為與羅丹的接觸為詩人徹底打開了詩歌觀察、感受和創作的新視野。因為與靈魂世界的真實相比,作為客觀存在物的雕塑要真實可感得多。它不僅具有形式,而且能夠幫助陷入無形的精神危機的人確認存在,定義真實。而作為賦予手中藝術品以物的存在意義的雕塑家,羅丹在創作過程中也開辟了自己的物的世界,這物的世界填補了精神危機的空白。
此時的里爾克看到的是巴黎的骯臟、貧窮、冷漠、死亡,是令人厭惡的“惡之花”。以巴黎為背景的《布里柯隨筆》開篇便充滿絕望,“人們來到這里,為了生存,而我卻認為,這里正在死去”,面對這樣的丑惡,詩人感到“恐懼”,并對生命的意義產生懷疑,對精神的價值產生了動搖。因為里爾克發現在標榜文明的大都市人類物欲橫流、道德淪喪,這完全不是自己早期詩歌創作的追求,在這樣的現狀面前那些憂郁的心靈的呻吟顯得多么蒼白無力。但這“恐懼”并未使他逃離,在一封致莎樂美的信中他提到波德萊爾的《腐尸》,說此時他真正理解了這首詩,面對這可怖的存在物,不能挑選,也不能拒絕。詩人能做的只能是改變自己,要從虛幻的主觀走向實在的客觀,從內走向外,從靈走向物。
在雕塑家客觀觀察“物”的影響下,里爾克成了一位詩界的“寫生者”,他到巴黎植物園直接冷靜面對審美對象寫出名詩《豹》和《瞪羚》,到盧浮宮希臘廳認真欣賞雕像阿波羅,寫出《早年阿波羅》,依照羅丹花園里的一尊佛像寫出《佛》……里爾克以他一系列的創作實績開創了詩壇獨一無二的“物詩”之風,即以造型藝術為榜樣,僅以感性的具體事物為主題,盡量摒棄主觀感情的詩體。他當時的名言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詩并非如人所想只是感情,感情我們已經有得夠多了;詩是經驗。”寫于1902-1907年的《新詩集》便是“物詩”的最好代表。從內在走向外在,從靈魂走向物,其最終目的仍是尋找與確立人性的真實——觀察物,走進物,尋找的是物中永不改變的本質與奧秘,從而最終找回失落了的人性。
作為“物詩”典范之作的《豹》極好地證明了“出于恐懼造物”的人性本質:
他的視力因柵木晃來晃去
而困乏,別的什么再也看不見。
世界在他似只一千根柵木
一千根柵木后面便沒有世界。
威武步伐之輕柔的移行
在轉著最小的圓圈,
有如一場力之舞圍繞著中心
其間僵立著一個宏偉的意愿。
只是有時眼簾會無聲
掀起——于是一個圖像映進來,
穿過肢體之緊張的寂靜——
到達心中即不復存在。
全詩分為三層。對處于牢籠中的豹的客觀描繪已遠遠超于豹之上。第一層中阻隔豹的視力的“柵木”也是人類割裂自身與世界的界限,人類為自己設置的鐵欄讓豹,也讓人類看不到世界。第二層,對于無止境的“力之舞”(精神)的追求,使豹陷于“最小的圓圈”,只偶爾獲取的客觀圖像經由眼簾“穿過肢體”最終印入“心中即不復存在”。
整體看來,作為在羅丹影響下所得到的“一種嚴格的良好訓練的成果”,《豹》恰恰在一種刻意追求的客觀描寫中,描述了對人性本質的探尋。人陷于人為的(主觀觀察)困境,最終只能通過客觀角度重新認識世界,從而達到了人與物的融合。從觀察出發,經由感受,達到感悟,詩人將自己隱入豹中,高度概括了從追求主觀靈魂再到客觀描摹而獲得生機的過程。
當時的羅丹雖然聲名顯赫,但遭受著很多人的攻擊。因為19世紀以來的歐洲,雕塑的地位要比繪畫遜色得多,學院派的傳統勢力_直在雕塑界占有上風,出身平凡的羅丹晚年仍然是主流藝術的叛逆者。作為一位個性獨特,才華橫溢的藝術家,羅丹從不相信靈感,這讓里爾克開始認真思考自己早期依靠冥想和感受的情緒化創作。因為早在沃爾普斯韋德的畫家那里,里爾克已受到了繪畫的啟發,試著寫了_些客觀化的詩作。詩人在羅丹一絲不茍的艱苦工作中,在雕塑家對作品細節的刻畫中,再次看到了藝術家深入觀察和感知事物的方式。
在羅丹眼里,沉迷于主觀抒情的詩人的作品枯燥無比,因為他的作品是幻想的結果,那不是事物的本質和真實。
“一切通過雕像上的隆起部說出,其他什么也沒有……他對生活別無他求,只想通過一要素表達自己,表達自己的一切……”他沉默了片刻,然后說,然后極其嚴肅地說:“應當工作,只要工作。還要有耐心。”
羅丹讓里爾克明白藝術家必須“工作”,必須探求存在的世界的真實性,而不是流連在個體的內心里去冥想與創造主觀的真實。存在的化身,世界的本質精髓不再是“上帝”,而是“物”。1903年8月15日,里爾克在致莎樂美的信中寫道:
哥特體的物,雖然從時間上離我們近得多,和自然中的物一樣恢宏,一樣偏遠,一樣不可名狀,一樣孤獨而自由,一樣無根無源。這些物以及出于羅丹之手的東西將我們引向最為遙遠的藝術物,引向古希臘之前。羅丹雕刻的毫無顧忌正是以后者的本質為基點的,一種特性,像鉛一般沉重,山一般堅硬。各種親緣相互重合——這誰也不曾感覺過——各種關系彼此銜接,組成一股貫穿各個時代的洪流。可以從人類歷史中預感無窮無盡,代代更替的物的歷史,預感這種較為緩慢,較為平靜,較為深刻,較為緊密,較為堅定不移的發展的結構。
雕塑進入詩歌決不是里爾克的新發明,因為近半個世紀以前,唯美主義的戈蒂耶和巴那斯派就明確提出過將造型藝術特別是雕塑移植到詩歌領域,制造出“硬”的詩歌,以此反對浪漫主義的軟性詩。但是與戈蒂耶不動情感,只與審美的對象保持無利害關系的“雕塑詩”相比,里爾克的“物詩”的雕塑感卻豐富得多,這種冷峻雕塑感下所蘊含的生命力,則得益于羅丹。
里爾克在《羅丹論》中說:“羅丹的雕像不是擺姿勢,而是生命,而且只有生命。”《新詩集續編》中《遠古阿波羅裸軀殘雕》就是一個極富生命力和雕塑感的“物詩”的代表:
我們不認識他那聞所未聞的頭顱,
其中眼珠如蘋果漸趨成熟。但
他的軀干卻輝煌燦爛
有如燈架高懸,他的目光微微內注,
矜持而有光焰。否則胸膛
的曲線不致使你目眩,而腰胯
的輕旋也不會有一絲微笑
漾向那傳宗接代的中央。
否則眼見肩膀脫位而斷
這塊巨石會顯得又丑又短
而且不會像野獸的皮毛那樣閃閃放光;
而且不會從它所有邊緣
像一顆星那樣輝耀:因為沒有一個地方
不在望著你。你必須把你的生活改變。
一尊缺損了的阿波羅像,雖僅剩殘軀,但在詩人眼中,石像斷肢的每個殘端都進出光熱“輝煌燦爛”,雖然他沒有頭顱,但他的目光仿佛“矜持而有光焰”,“因為沒有一個地方不在望著你”。全詩蘊含的熱情迫使我們“必須把你的生活改變”,這首彼特拉克體十四行詩極富雕塑感。原文用德語寫成,經詩人的“刀鑿斧刻”,古典結構的形式微有變化,詩人把許多句子在行末截斷(如石像的斷肢),總計十四行詩中,原文有七行在行末跨行。這種音流的斷裂與圖像及內容相配合,有力地刻畫出一尊古代殘損石像。
從羅丹那里,里爾克不僅真正完成了自己從早期的主觀冥想向客觀刻畫的“物詩”的轉變,而且詩人也從大師手下刀鑿斧刻的作品中獲得了要以文字為材料,構筑富于雕塑感物詩的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