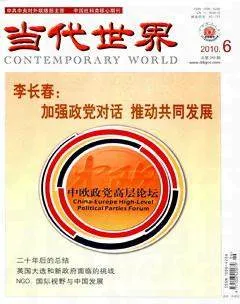奧巴馬政府對小布什“信仰倡議”之繼承與發展
長期以來,美國政府和宗教非政府組織在提供社會服務方面建立了密切而廣泛的合作關系。美國聯邦、州和地方各級政府從提供社會福利的主導角色逐漸淡出,越來越多地依靠社區組織,共同應對艱巨的社會問題。宗教非政府組織正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和速度在國際、國家和地區各層次的事務中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憑借其獨具的信仰凝聚力和機構組織,成為濟貧、反戰、環保等事業的先驅。整合宗教非政府組織這股常駐力量及其優勢,用于更好地服務社會,對政府來講是一舉多得之計。
鼓勵宗教非政府組織參與社會公益項目在美國長期得到兩黨支持。1996年美國國會通過《聯邦福利改革法》中“慈善選擇”條款,規定宗教非政府組織有權申請政府資助的社區項目,并可保留以信仰為標準遴選工作人員的權利這一條款為“信仰倡議”(Faith-based Initiative)的出臺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克林頓執政期間,已安排官員著手創建正式的白宮信仰辦公室。小布什率先將新出臺的“慈善選擇”條款在得克薩斯州實行,繼而把“信仰倡議”作為1999年大選的主要競選政策之一。
小布什“信仰倡議”的出臺
小布什入主白宮后第二周,簽署行政命令成立了白宮信仰與社區倡議辦公室(White House Office of Faith-based and Community Initiative),在司法部、教育部、勞工部、健康與公共服務部和住房與城市發展部設立分中心。此后,他利用各種場合重申這一倡議的重要性,卓有成效地在聯邦、州及地方層面大力推進這一政策。到奧巴馬接任時,有11個聯邦內閣部門(司法部、教育部、勞工部、健康與公共服務部、住房與城市發展部、商務部、退伍軍人事務部、小企業管理局、農業部、國土安全部、美國國際開發署)設有分中心,國家與社區服務局下設聯絡處,36個州建立了聯絡處,包括民主黨擔任州長的19個州,100多名市長也紛紛響應白宮政策,成立了信仰辦公室。
“信仰倡議”成為小布什任期的一大標志。他向國會和公眾賣力推銷這一政策,試圖克服重重立法阻力和司法挑戰,但因觸及民眾普遍關心的政教分離問題,引起巨大的反響與爭議。反對者對倡議的合憲性以及具體項目的合法性、公正性與透明度提出廣泛的質疑,指責白宮利用信仰辦公室作為政治工具,拉攏黑人及西班牙裔選民,收買基督教福音派,爭取共和黨票倉如宗教保守派的支持。這一倡議引發的宗教政治化的潛流與壓力使信仰辦公室一些成員相繼離開。加上國會中的黨派紛爭,民主黨人往往不愿支持一位共和黨總統提出的極富爭議的政策倡議,阻礙了立法進程,給這項倡議的長遠發展帶來很多不確定因素。
奧巴馬上任以來“信仰倡議”的發展
奧巴馬上任后完整地保留了前任創立的信仰辦公室體系,但也不乏創新之舉,除象征性地把“白宮信仰與社區倡議辦公室”更名為“白宮信仰與街區合作辦公室”(White House Office of Faith-Based and Neighborhood Partnerships),還成立了信仰與街區合作咨詢委員會,邀請25位宗教界領袖和世俗精英擔任顧問,負責政策建言。
奧巴馬指出小布什沒有兌現最初的承諾:信仰辦公室未能與基層草根組織建立密切聯系;服務低收入人群的福利項目長年缺乏資金投入;難以判定“信仰倡議”的實際成效;倡議旨在促進所有宗教團體公平參與,卻往往為黨派斗爭提供理由;非猶太一基督教的宗教團體如穆斯林組織和其他少數教派仍然受到諸多限制或歧視,政府很難做到不偏不倚。此外,“信仰倡議”仍然面臨立法瓶頸和司法挑戰。主流觀點堅持認為信仰辦公室掌控著白宮授權的大筆款項,只有少數有政治背景的組織才能從中分一杯羹。
奧巴馬信仰團隊強調信仰辦公室沒有撥款權限,而是致力于為草根組織提供資源和技術支持,劃出四大關注領域:經濟復蘇與扶貧事業;支持婦女兒童;推廣“富有責任感的父親行動”;促進宗教間對話與合作。奧巴馬采取以問題為導向的新思路,通過切實有效的項目改善社區服務大眾,消除輿論對“信仰倡議”的誤解。咨詢委員會的設立也遵循這一原則,25位成員在族裔、宗教信仰以及一系列重要議題的立場觀點都呈現出高度的多元性。奧巴馬巧妙地向公眾表明,無論宗教背景或政治立場,公眾意見都受到信仰辦公室和咨詢委員會的歡迎和重視。咨詢委員會分為六個專題小組,分別負責白宮信仰辦公室改革、經濟復蘇和國內貧困問題、“富有責任感的父親行動”與健康家庭、宗教間對話與合作、環境問題與氣候變化、全球貧困與發展。首屆咨詢委員會已將一年的工作成果——《新時期的伙伴關系:致總統建議報告》于2010年3月10日提交給奧巴馬。
奧巴馬與小布什的“信仰倡議”政策對比
奧巴馬帶著“變革”的口號入主白宮,但從根本戰略目標來看,其政策變革多為戰術或戰略調整以及具體政策的修正,維護美國霸權并主導世界的戰略定位并未改變。
奧巴馬繼承小布什“信仰倡議”政策表現出的務實靈活、多聽少說的態度,與他在國際社會倡導多邊主義、淡化意識形態的實用主義理念一脈相承。國際層面,金融危機、恐怖主義、氣候變化和核擴散等現實,迫使奧巴馬重視多邊主義,加強與國際社會的合作。國內層面,政府需要動員民間的力量和資源攜手解決失業、貧困等艱巨的社會問題。兩屆總統對“信仰倡議”均青睞有加,是因為宗教非政府組織得天獨厚的優勢與社會資源。美國政府鼓勵信仰與社區組織參與公共事業的出發點是解決社會問題的現實需要,賦權給這些組織以更好地服務社會,雙方各取所需,并形成優勢互補,實現社會公益最大化。這使得奧巴馬與小布什的“信仰倡議”政策表現出很大的延續性。
奧巴馬象征性地給白宮信仰辦公室改名,并退居二線,將前臺工作留給信仰辦公室和咨詢委員會,這是區別于小布什本人作為政策制定與倡導者這一模式的重大調整。奧巴馬糾正了小布什政府對基督教保守派的政策傾斜,提倡不同信仰間通融調和,建立共識,加強與不同宗教背景以及世俗組織間的聯系。新成立的咨詢委員會,代表著宗教非政府組織晉升到白宮政策建言者的地位,倡議重心從大刀闊斧的制度改革轉向政策微調與優化。基于咨詢委員會建言報告所形成的官方政策更具有代表性,因而更易為大眾接受。白宮作出廣進民意的姿態,擁護宗教多元化,同時也謹慎地避開政教分離這一敏感的政治漩渦。
奧巴馬“信仰倡議”關注領域之廣,范圍之大,目標之高,是在小布什基礎上的極大延伸和擴展,在經濟低迷的當下,可能出現力不從心的局面。但他極少像小布什一般對“信仰倡議”持續給予熱情關注與高調宣傳,上任后一直忙于應對經濟危機、醫療改革等直接影響民生的問題。
奧巴馬深知宗教的巨大政治能量,在競選期間為贏得宗教選民的支持做了大量工作。他深諳宗教語言,與許多宗教界領袖保持著良好關系,走溫和派路線,博得了宗教界的認同與贊賞。他在宗教問題上的積極表現,不僅獲得中低收入階層中人數眾多的天主教徒的支持,對吸引基督教福音派也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當選后,奧巴馬領導的民主黨政府迫切需要鞏固競選期間爭取到的宗教選民,并在基督教福音派與共和黨的聯盟關系出現松動之際,尋求更廣泛的宗教界支持。因此,奧巴馬繼承小布什的“信仰倡議”,也巧妙地延續了競選期間“擁抱宗教”的路線。奧巴馬設立咨詢委員會,邀請眾多極富影響力的宗教領袖和世俗精英出任顧問,建立密切與高層溝通渠道,能夠有效地鞏固并改善白宮與這些影響非凡的宗教組織和世俗機構的關系。這比小布什明顯倚重于宗教保守派的做法更加含蓄、高明,使“信仰倡議”的政治動機更具有隱蔽性。
奧巴馬上任一年多來,新的“信仰倡議”也暴露出一系列問題:媒體關注度低、國會相關立法遙遙無期、前任的遺留問題大量存在、咨詢委員會工作進展緩慢;一些宗教界領袖,懷疑奧巴馬的“信仰倡議”與小布什期間如出一轍,為白宮向宗教界人士進行政治公關而服務;奧巴馬上任后對“信仰倡議”沒有給予足夠重視,進行的改革往往形式多于實質,枝節性調整多于整體性變化,在關鍵爭議問題上多采取拖延戰術和回避態度;首屆咨詢委員會歷時一年有余得出的建言報告至今尚未獲得白宮正面回應,同時面臨著成員期滿換屆的問題,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咨詢委員會在目前象征意義大于實際作用的本質。
盡管“信仰倡議”發展前景尚不明朗,仍面臨著諸多爭議與挑戰,如包括“慈善選擇”條款在內的一些法律條文臨近到期,將在國會重新討論,立法進程與結果都不是白宮能完全左右的。但相關政策歷年得到兩黨支持的事實說明,“信仰倡議”仍然具有持久而旺盛的生命力,將在不乏爭議的政策改革中繼續蓬勃發展。
(責任編輯:李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