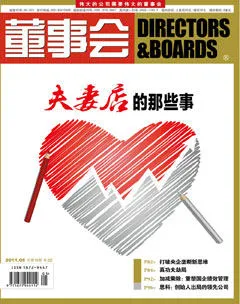根治欺詐為何決心難下
監管機構去做的是自己力所不能及的事情,而原本該負起主要責任的保薦人顯得無足輕重,上市的關鍵變成了保薦人和發審委之間的博弈
深滬股市按規模排名還遠在歐美之后,發行中的各種造假欺詐卻更多,香港也無法與之相提并論。這里面可能有多種原因,最常見的區別在于發行和監管制度上的差異。
保薦人制度已經被廣泛接受,然而,這個制度作為舶來品,如不針對中國情況加以改造,則形同虛設。這個制度建立在個人信用的基礎上,保薦人代表如不盡責,則需承擔無限責任,可能因此失去從業資格,被逐出市場,并承擔相應的刑事和民事責任。而在國內,個人信用體系缺失,行業自我監督和約束機制基本沒Dr21igrrfCOZcva+gzkdAA2BxFe4fe6pr9IsMd9zSOY=有,使得該制度毫無約束力。2010年,某券商保薦的多家公司都出現了嚴重違規,然而,至今未見到該機構和相關項目的保薦人代表受到任何懲罰。
筆者曾經提出,對保薦制度加以修改,將保薦人代表不能盡責的懲罰不僅要落實到個人,而且應追究其所代表的機構責任,對于嚴重違規的個人和機構,吊銷相關業務資格,并按律追討其所造成的損失。在個人信用體系不在位的情況下,變通的做法是將個人和機構綁在一起,增大違法成本,應可提高該制度的有效性。
公司在發行上市時造假,除了投資銀行未盡責之外,企業也難逃其咎。俗話說,一個巴掌拍不響,如果沒有企業的配合,造假是無法完成的。在國內,退市的情況基本是不存在的。2010年在香港市場的洪良公司,經人檢舉揭發,保薦人代表與公司串通,聯合核數的會計師在賬目上造假。證監會和廉政公署都采取了果斷措施,該公司上市募集資金被凍結,保薦人代表、核數師被調查,所有犯錯人員和機構都難逃刑民事懲罰,募集資金被退還給投資者,并要求企業做出更多的賠償。這是一個發生在規范市場的典型案例。正是因為有這樣的嚴肅追究的體系,才使得公司不敢鋌而走險,做出得不償失、徒使事業毀于一旦的行為。
發行制度的另一個屢被詬病之處是監管機構的過度管理。表面看來,批準制比核準制的控制程度更高。每一個上市申請都要經過證監會的上市評審委員會的評審。然而,評審實際只不過是進行形式審查,而根本無法做到對企業經營情況的了解和把關。看似嚴絲合縫的安排,實際上同時弱化了保薦人制度和上市前審查制度。監管機構去做的是自己力所不能及的事情,而原本該負起主要責任的保薦人顯得無足輕重。上市的關鍵變成了保薦人和發審委之間的博弈,只要過了這一關,前面就是一馬平川的“圈錢”大道了。這就難以避免投行的各種公關行為的發生,在審核層面的腐敗更是大家心照不宣的不公開秘密。
公司上市本來是一件非常嚴肅的事情,對企業而言,要用一定的損失換取上市地位。而在缺乏對投資者保護、缺乏監督和約束的中國,情況卻完全不是這樣。上市只是意味著能從投資者那里拿來很多的錢,而無需承擔很多責任。收益與成本相比,成本基本可以忽略不計。而投資者也少有長期持股的打算,大家只是想把股價炒高,短期內退出并快速獲利。這種市場生態,決定了投資者、中介機構和上市公司的行為模式。監管的低效率使得這種不正常已經成為常態。如此看來,A股成為莊家市、政策市、賭場,有什么值得大驚小怪呢?
其實這不過是老生常談了。股市并非新事物,即便在中國,也已經有連續20年以上的歷史了。陽光之下,為什么明擺著的問題就是長期得不到解決?這不是能與不能的問題,而是有沒有決心去面對,否則,即便再說10年也是徒然。企業作為上市的法律主體,如綠大地、雙匯等,必須為自己的錯誤行為負責,但要想根本解決企業欺詐,上述任何環節都不能放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