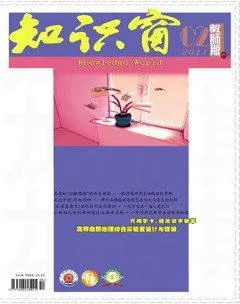詩歌是生活的審美超越
新世紀開始以來的詩歌界一直是比較沉寂的,然而“惡搞梨花體”“裸體詩朗誦”等事件的發生,打破了詩歌界持續已久的沉寂狀態,引發了人們對現代漢詩命運的又一次思考:詩歌的本質到底是什么?現代漢詩應該是什么樣子的?
古人云:“詩言志。”也就是說,詩歌是表達人的內心情感的。盡管胡適、陳獨秀等人倡導“文學革命”時對古典詩歌進行了大力否定,但是他們并沒有完全拋棄那些可以超越時代的具有普遍意義的詩歌觀念。即使在現代詩歌受到人們廣泛質疑的今天,“詩歌是人的內心情感的表達”的看法恐怕還是具有合理性的。然而,詩歌所表達的“內心情感”是從哪兒來的呢?艾青說:“生活是藝術所以生長的最肥沃的土壤,思想與情感必須在它的底層蔓延自己的根須。”只要翻開郭沫若、聞一多、徐志摩、馮至、戴望舒、艾青、穆旦等人的作品,我們就會發現他們的詩歌所表達的情感與現實生活之間的密切聯系。詩歌中蘊涵的內心情感絕不是詩人的任意發揮,而是從現實生活中得來的。盡管人們可能因為生活境遇的不同而對詩歌的本質有不同的理解,但只要是真正的詩人,他就無法拒絕現實生活在詩歌情緒生成中的決定意義。
雖然現實生活是詩歌情緒產生的基礎,但這并不意味著只要生活著就會有新的詩歌情緒發生。詩人不但要生活著,而且要生活得更具廣度、更有深度。詩人的生活范圍不應當只局限在個人的小圈子里,而應該面向廣闊的社會生活,與普通大眾生活在一起,進入到他們的精神世界里去。胡風說:“詩歌是發自作者對于現實人生的感受或追求,只有人生至上主義者才能夠成為藝術至上主義者。但不幸的是,對于許多詩人,這還是一個常常被顛倒了的致命的問題,他們常常忘記了丟掉了人生就等于丟掉了藝術自己。”其實,對于真正的詩人來說,生活與藝術是統一的,詩歌的情緒蘊藏在深厚的生活土壤中。詩人應當經常地詢問自8CpIzjyHdybq0RnJTInIcAYTnq0z8RPexeGjbZ7s8S8=己:“我被生活感動過嗎?”如果生活感動了詩人,這表明詩人是在以一種積極的人生態度生活著,是在真正體驗著普通大眾的人生。只有生活在感動的世界里,詩人所獲得的詩歌情緒才會是真誠的,包含了人類普通的精神追求,而不至于純粹是一種封閉孤獨的自我情緒的宣泄。
在現實生活中產生的情緒和感受,并不能全部進入到詩歌的創作中。因為,文學的創作過程是一種審美選擇的過程,是一種情緒升華的過程,詩歌的創作需要飽滿的情感。讀郭沫若的詩,我們感受到的是詩人渴望民族新生的期盼;讀艾青的詩,我們感受到的是詩人面對民族抗爭的悲壯;讀穆旦的詩,我們感受到的是個體生命在艱難境遇中的痛苦。所以孫犁說:“在創作中,不能吝惜情感。情感付出越多,收回來的就越大。”然而,進入詩歌中的情感必須是以真善美為核心的,詩人要在真善美的表達中“給人以力量,給人以希望,給人以美好的感受”。像郭沫若、艾青、穆旦等現代詩人的詩歌之所以能夠感動讀者,就是因為他們作品中的情緒和感受是經過了詩人的審美超越的。這樣說,并不是意味著個人的生存感受就沒有價值。相反,那些在與普通大眾相互交融的生活中產生的情緒體驗,往往是最接近真善美的,是最具有人文情懷和精神深度的。
詩歌創作中的審美超越,不但是一個情感的把握過程,而且也是一個語言的選擇過程。日常口語可以成為詩歌的語言,但是它必須是經過詩人的審美加工。也就是說,現代漢詩的口語化不僅是詩歌語言的藝術化,而且也是詩人以詩意化的語言表達自己生活情感的審美化。卞之琳的《斷章》雖然只有短短的四句——“你站在橋上看風景,看風景的人在樓上看你。明月裝飾了你的窗子,你裝飾了別人的夢”,但是詩人卻通過日常生活語言和意象的排列與組合,表達了常人司空見慣卻又難以言說的人生體驗和情緒。托爾斯泰說過,一個高明的作家“并不在于知道他用什么語言寫什么,而在于知道不需要用什么語言寫什么”。當我們的詩人也知道這樣做的時候,現代漢詩的口語化也就不會成為一個廣受人們爭議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