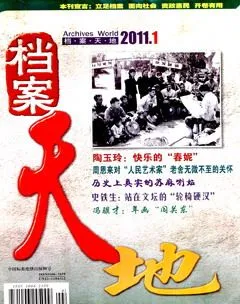年畫“闖關(guān)東”
年畫,的確是個滿身神秘的東西,即便是深入研究,恐怕也鉆研不透。現(xiàn)在,從文化的角度講,老百姓對山東人“闖關(guān)東”那個壯舉的興趣是,他們給關(guān)東帶去了哪些齊魯?shù)奈幕窟@些文化被那塊冰雪大地,吸納融合了嗎?
“闖關(guān)東”是求生渴望所驅(qū)使的民眾遷徙。它帶去的不會是精英文化,而是隨身的鄉(xiāng)土文化。精英文化是自覺的,民間文化溶化在溫暖的生活與情感里,往往是不自覺的。只要生活融合了,文化就會生出根須,往那塊陌生的土地有力地扎下去。那么,怎樣才能找到“闖關(guān)東”所特有的文化蹤跡呢?
如果你在認(rèn)真尋找一種東西,那種東西一定也在找你。關(guān)鍵是它出現(xiàn)時,你是否識出它來。
多年來,在走南闖北的文化搶救中,每到一處,都會擠出時間去看看當(dāng)?shù)氐墓哦袌觥R粋€個時代,像一只只歷史的大鳥。大鳥飛去,那些散落四處美麗的羽毛,常常出現(xiàn)在一些古董店里。一盞銹跡斑斑的油燈,或一枚筆劃模糊的老印章、一張告示揭帖、一件式樣別致的坎肩、一件形制奇特的小器物……往往會喚回一片消失在時光隧道中過往的情景,激活人們對那只飛去的歷史大鳥,無邊的想象。
非常著名的年畫,就是年時應(yīng)景的裝飾,也是消費品。這種東西用后便棄,不會存藏。因而,不管歷史上制作的規(guī)模如何巨大,遺存卻總是寥寥。上個世紀(jì)末,各地古董市場已鮮有古老的年畫及老版出現(xiàn),但進(jìn)入21世紀(jì),大量的老年畫忽然源源不斷,一涌而出。每過眼前,竟發(fā)現(xiàn)大多是山東幾個產(chǎn)地的風(fēng)格。
山東屬于年畫產(chǎn)地最多的省份。大產(chǎn)地有四個:楊家埠、高密、平度和東昌府。如今,這些產(chǎn)地的古版年畫,早已是一畫難求,怎么會一下子冒出這么多呢?尤其是高密的畫,數(shù)量居首,很多畫種畫法從未見過。比如“撲灰”的《對美》,常常在身上或臉上刷一道很厚的明膠,好像涂一層漆,極其光亮,是怕磨損,還是為了更鮮亮?
還有一種木版,印繪的戲出人物,以武戲居多,市場上稱做“刀馬人”,先前也未見過。畫中人物臉胖眼長,身軀肥碩,版線很細(xì),以水紅色手工渲染,背景常刻印一些方點狀的深深淺淺有靈氣的小格作為裝飾——這都是未曾謀面的畫風(fēng)與畫法。如果畫上不是清清楚楚,署著高密某鄉(xiāng)某村,誰敢說是高密人畫的?這些畫怎么都跑到東北三省的民間了?
這使我聯(lián)想到,從19世紀(jì)末到20世紀(jì)初,俄羅斯植物學(xué)家科馬羅夫。他在沈陽和吉林等地就買到過大量年畫,現(xiàn)今,收藏在俄羅斯的國家地理學(xué)會。2004年,我在訪俄期間鉆進(jìn)圣·彼得堡一個窄如巷子的小街深處,尋到這個聞名世界的地理學(xué)會,在學(xué)會的資料室里受到熱情接待,有幸看到那批一百多年前來自中國的民間杰作。我輕輕地一頁一頁掀動著碼在桌上足有一尺多高的古版畫,仔細(xì)辨識這些畫的產(chǎn)地。中國北方各個年畫產(chǎn)地,竟然一處不缺。這表明,東北三省廣大的民間,一直是中國木版年畫巨大的市場。千千萬萬闖關(guān)東的山東人,無疑是創(chuàng)造這個市場的生力軍。
為什么說是“市場”而不說“產(chǎn)地”呢?因為照以往專家們的說法,東北三省本身沒有年畫產(chǎn)地。它只是一片廣闊無邊的消費年畫的世界。連《遼寧省志》都說,他們那里一直到民國年間,也沒有專業(yè)的年畫藝人。故而,從來沒有人去東北研究年畫。連畫都是外來的,還研究什么呢?
然而,在過去,專家們多從民藝學(xué)和美術(shù)學(xué)——很少從文化學(xué)來研究年畫。
直到近些年,東北地區(qū)一些古董市場年畫漸漸走紅,專事年畫收藏的人日見其多,才使現(xiàn)代人想到它背后一個重要而不可忽視的人文背景,那就是天下聞名的壯舉——“闖關(guān)東”。
從清初至民初這二百多年間,兩三千萬山東人,前仆后繼地奔赴到廣袤又肥沃的東北大地謀生。民俗是一種無法丟棄的頑固的文化心理;而且,情感濃重的山東人,一定還把故鄉(xiāng)的習(xí)俗,作為鄉(xiāng)情鄉(xiāng)戀最深切的表達(dá)方式。于是,盛行于齊魯民間的年畫,便被千里迢迢帶到這里,一年一年滲入到本地歲時的生活里。
東北很多地方的地方志,例如,從黑龍江的《蘭西縣志》、《樺南縣志》、《寶清縣志》,到遼寧的《桓仁縣志》、吉林的《白城縣志》、《農(nóng)安縣志》、《榆樹縣志》等等,都有臘月底,張貼年畫和門畫的風(fēng)俗。這些地方都是山東人“闖關(guān)東”的落腳地。
前年,我們在河南滑縣李方屯年畫考察中,曾發(fā)現(xiàn)一幅繪著觀音、關(guān)公和財神比干的《三像》,上邊的文字全是滿文,顯然,這是一幅為關(guān)外滿族特制的年畫。它表明,“闖關(guān)東”的山東人,已經(jīng)把漢民族的文化,深深地融入到那里少數(shù)民族的生活中了。
可是,山東人“闖關(guān)東”是漫長的二百多年呵!東北三省使用的年畫一直都是由關(guān)內(nèi)供應(yīng),或是山東人從老家捎去的嗎?既然東北有那么巨大的年畫需求,山東人會不會把他們的作坊搬過去,甚至在那里也形成一些小產(chǎn)地呢?是否可以這樣推測,因為很多年畫產(chǎn)地的源起,都始自一些心靈手巧的外來藝人,他們慢慢地把刻版印畫等手藝帶過來了。
我把關(guān)于“闖關(guān)東年畫”的想法,告訴給家在吉林的中國民協(xié)副主席曹保明,請他下去先摸摸情況;弄清楚“闖關(guān)東”的年畫到底是一種文化現(xiàn)象,還是東北曾有年畫作坊和產(chǎn)地——只不過現(xiàn)代人對此無知?曹保明是保護(hù)東北民間文化的一員大將。人熟地更熟。田野工作是他的強(qiáng)項。他寫過不少關(guān)于獵手、漁夫、伐木與馴鳥高手的口述史,都是田野記錄的上品。
一天,曹保明忽來電話。他興奮的大喊大叫,把我的手機(jī)變成擴(kuò)音器。他說,他接到我的電話,立即對“闖關(guān)東年畫”做了專項調(diào)查,孰料不多時就有了成果。他們在吉林北部挨近黑龍江的白城的通榆,竟然發(fā)現(xiàn)木版年畫的作坊!這可是民藝學(xué)一個大發(fā)現(xiàn)。它能填補(bǔ)東北三省沒有年畫產(chǎn)地的歷史空白嗎?
白城,地處嫩科爾沁草原。滿人入主中原后,把這片草原劃給曾經(jīng)有助清王朝的蒙古族貴族。后來,蒙古貴族大塊大塊地把草地出賣給來開荒播種的山東人。這里就成了“闖關(guān)東”的熱土。山東人在栽種生活時,無意中栽種了文化。年畫也扎下根來。
曹保明的調(diào)查結(jié)果,印證了現(xiàn)代文人的推斷不謬。通榆年畫作坊的歷史,可以上溯到百年以上。上一代故去的最知名傳人有劉長恩(1931年—1996年)、劉佩行(1953年—2006年),他們?nèi)巧綎|濟(jì)南歷城千佛山人。如今,健在的年畫傳人李向榮,以及剪紙藝人高靜,祖籍也是山東,登州人。他們的手藝是曾祖一輩“闖關(guān)東”時帶到草原上來的。這些都證實了此地的年畫制作,與“闖關(guān)東”這段歷史的直接關(guān)系。
據(jù)初步調(diào)查獲知,李向榮一家所擅長的年畫,全是中原的傳統(tǒng)題材。諸如門神、灶王、神像、戲出故事、歷史人物、神話傳說、娃娃仕女、吉祥圖案等等,一樣也不少。他們自己刻板,自己印畫,連染紙也自己做。他家印制的年畫行銷遠(yuǎn)近很多地方,連周邊的包拉溫都、瞻榆、糜子荒一帶蒙古族村子也掛他家的畫。可惜,由于歷史久遠(yuǎn)和“文革”之難,世代相傳的數(shù)百幅古版,全劈成碎木燒了。沒有版就沒有版畫的生命,從此,也就中止了年畫制作,一些年畫藝人全改行了。如今,傳人李向榮還是技藝在身,工具依存,但空無畫版。去年,通榆木版年畫,曾申報省級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由于歷史資料匱乏,未能被認(rèn)定為“遺產(chǎn)”。
為此,我請曹保明對“闖關(guān)東年畫”做繼續(xù)延伸調(diào)查。一是,擴(kuò)大普查范圍,進(jìn)行地毯式文化搜查,重點是找尋年畫制作的傳人與后代;二是,對白城博物館現(xiàn)藏的為數(shù)不少的民俗年畫進(jìn)行鑒定,找出確定無疑的本地作坊的年畫遺存;三是,從東北各地的古董市場和收藏家手里找尋物質(zhì)性見證。等到材料充分和明確,就會在吉林或黑龍江什么地方,召開“闖關(guān)東年畫”學(xué)術(shù)研討會。至于“闖關(guān)東”年畫的藝術(shù)特色,以及畫中東北地區(qū)的人文內(nèi)容,都需要下一步深入地研究與探討的。“闖關(guān)東”年畫肯定是一個尚未開發(fā)的文化富礦。
盡管這只大鳥已經(jīng)遠(yuǎn)去,消隱在逝去的時光里;我想,現(xiàn)代人一定會綴拾所有遺落的羽毛,在時光隧道中,描繪出它往日雄健的影像。我對這一田野工作充滿熱切的期待。當(dāng)然,對中國文化滿懷熱心的人們,還要背后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