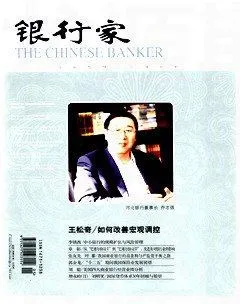從百年前的“超穩定結構”到今天的“中國模式”(中)
2011-01-01 00:00:00高續增
銀行家
2011年5期
“超穩定結構”社會的兩個階段
我發現,在金觀濤先生的這本書里,在他們看來,中國傳統社會從一開始就是那個“超穩定結構”所描述的樣子,直到它在1911年走到了盡頭。
其實不是這樣。我認為,應當把這兩年分為兩個階段,隋唐以前是“不規則的超穩定結構”,原因在于秦漢魏晉時期的社會并不成熟,主要缺陷是政府結構的組織方法不完善。那時的政治人物來源主要靠舉薦,這樣的人事安排很容易受到偶然因素的干擾。因為那個被稱為“舉孝廉”的選材過程,很快就成為了士族大戶往朝廷里面安插親信的手段,那時有“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這樣的說法。往往在社會剛剛穩定下來之時,朝廷很快就會成為利益集團的角力場。其中,最反復出現的是外戚集團,其次是宦官集團,當他們斗得不可開交的時候,就會有地方諸侯出面調停,這就形成了第三股勢力。社會在這主要的三股勢力的殘酷而無原則的競爭中,逐漸失去了控制,這也是隋唐以前中國難有大的封建王朝長期支撐局面的原因。當然,西漢是個例外,它享受了一股“紅利”——對外戰爭的戰果,使北方游牧民族向西方的中亞細亞而不是向南方的中原發展。別的和更多方面的原因此處就不多加分析了。東漢雖然也延續了195年,但除了劉秀在位的30年社會較為穩定外,其他時間社會也都是一片混亂,與割據時代沒有太大的區別。
偉大的隋文帝總結了社會不穩定的原因后,作出了一項制度創新一考試取仕,即用公平的考試從民間搜羅人才,組成精干的政治機構。……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