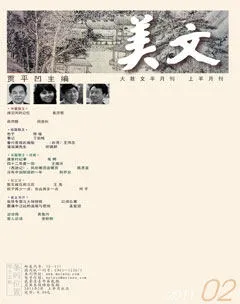“一部書救活一家出版社”
王維玲 1932年生,1950年至1994年供職于中國青年出版社,歷任宣傳科副科長,文學編輯室編輯、主任,中青社編委、副總編輯。1975年至1981年擔任《李自成》第二卷、第三卷責任編輯。1979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1980年任《青年文學》主編。1987年任《中華兒女》主編,同年評為編審;1994年起享受國務院頒發的政府特殊津貼。著有《話說<紅巖>》《歲月傳真》等百萬余字評論文章和紀實文學。
就這樣,在大家幫助下,他也在工人體育場附近搭建了一個防震棚。在露宿街頭防震棚的那些日子里,生活條件簡陋到不能再簡陋了,但姚雪垠先生靜坐一角,堅持工作,專心地審定《李自成》第二卷校樣。他說:“只要大地沒有陷下去,我的工作就不會停止。”這部八十多萬字的校樣,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一字一句看完的。
姚雪垠先生聽了哈哈大笑,對大家說:“你們說得對極了,我是做了一些枉費心血的勞動。”……所以在第二卷付印前,便把這些文字刪去了。但由于第二卷的部頭較大,仍有小的遺漏,用姚雪垠先生的話說:“難免留有蛇足。”后來在第二卷第一版第二次印刷時,姚雪垠先生又通讀檢查一遍,洗刷得比較干凈,算是把這塊心病去掉了。
這份報告是以中青社的名義寫給團“十大”籌備組并中央的請示報告,團“十大”籌備組另擬一函,于18 日一起上報。25 日下午四時半,團“十大”籌備組打來電話,告知中央已批準,于一小時后把批件送到中青社。至此,中國青年出版社在團中央報刊社中率先宣布恢復了出書業務。這就是后來所傳“一部書救活了一家出版社”之說的由來。
費心斟酌的第二卷
《李自成》第二卷出版后,在不長的時間里,就發行了一百八十多萬冊,在國內外產生了很大影響。第二卷十個單元,五十五 章、八十三萬字、分上、中、下三冊。
“商洛壯歌”是第二卷最大的一個單元,有十五章。這個單元跌宕起伏,變化多端,處處有懸念,讓人讀時凝神屏息,緊張萬分!茅盾先生對這個單元給予了極高的評價。他說:“整個單元,大起大落,波瀾壯闊,有波譎云詭之妙;而節奏變化,時而金戈鐵馬,雷震霆擊,時而風管鹍弦,光風霽月;緊張殺伐之際,又常插入抒情短曲,雖著墨甚少而搖曳多姿。開頭兩章徐徐展開……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最后兩章……開拓以下單元,行文如曼歌緩舞余韻繞梁,耐人尋味。”
“紫禁城內外”是第二卷中冊最有特色的一個大單元,有六章,是《李自成》出版后,各界讀者公認寫宮廷生活和朝廷內外錯綜復雜的深刻矛盾和激烈斗爭,最出彩、最有看點的一個單元,也是一個很難寫好的單元,寫好這個單元要下大工夫、下苦工夫的。首先是宮廷生活,這里邊包括皇帝生活、皇后生活、皇妃生活、宮女生活,太監生活等等。還有朝廷生活,包括皇帝和眾大臣的生活,朝廷上下大臣之間的生活。不僅如此,還有皇城內環境的格局,大小宮殿的位置,皇宮內臣和當朝大臣各自不同的行進路線以及皇宮內的禮儀、服飾、擺設、習俗、典章、制度,吃的、喝的、用的各種器皿的式樣和使用方法,都要寫得真實準確,詳細生動。所以姚老在寫作中為了一件服飾的描繪,一個物件的稱呼,一句話語的使用,常常要花上超出寫作幾倍的時間去查證,確認無誤后才能動筆。從人物到環境,“紫禁城內外”為我們提供了一幅長長的精致的宮廷畫卷。
由于參加《李自成》第二卷稿的編輯工作,我與姚雪垠先生接觸的機會就多了起來,這里邊有我對姚雪垠先生的求教,有他對我的指點,也有不同看法的交流,甚至爭論。這一切使我與姚雪垠先生的關系更親近,更融洽,更密切了。
最近我發現一本三十多年前的筆記,其中記錄了第二卷發稿前后我與姚雪垠先生的一些交談,雖然記的很簡單,但仍可看出姚雪垠先生寫第二卷時的一些思路。
《李自成》第二卷第一章寫李自成被圍困在商洛山中,劉體純來老營向李自成稟報軍情,李自成問他:“鄭崇儉、丁啟睿懷的什么鬼胎?”劉體純分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回答。我覺得行文過長,也有些呆板,便向姚雪垠先生提出,可否換一種寫法?姚雪垠先生說:“前面已逐次將戰爭形勢寫出,這里是想通過劉體純的話,總寫一段,表明義軍對官軍的企圖了若指掌,不改了。”
第十七章寫李侔向宋獻策談起李信如何看重紅娘子,并把他花了一百五十兩銀子買的一把上好的古劍贈給紅娘子時,宋獻策說:“令兄如此看重,必定是色藝雙絕,名不虛傳。”我提出,這里用“色藝”二字是否可再斟酌一下?姚雪垠先生說:“這段話帶有歷史特色,直到民國初年,士大夫評論女藝人、旦角,仍從‘色藝’二字著眼。這里反映了宋獻策的思想感情,刪去不妥。”但姚雪垠先生斟酌后,在李侔回宋獻策的話時仍加了幾句話:“紅娘子雖然長得不丑,但對她不能將‘色藝’二字并提”, 紅娘子“武藝出眾”“義俠肝膽”“原是清白良家女子,持身甚嚴,并非出身樂籍”。姚雪垠先生借李侔之口,不僅回駁了“色藝”二字,而且把紅娘子的為人、品格也作了勾畫。
第十八章宋獻策在禹王臺和李信相聚,二人圍繞推背圖、京城形勢展開議論,姚雪垠先生很欣賞這段描寫,問我讀后的感覺如何。我說:李信寫得較深,宋獻策寫得較活。姚雪垠先生很有興致地圍繞李信這個人物的性格以及李信與宋獻策的思想差異和我進行了交談。姚雪垠先生說:“天啟末年,不僅地主階級的讀書人,包括一般市民都明白依附閹黨為可恥,所以這里寫李信不同情父親倡立生祠諂媚魏忠賢,這是給李信一個思想起點。倘若李信沒有這個起點,則李信就沒有以后的發展,作為閹黨之子,他也就不可能在故鄉獲得一定聲望。這章的后邊就著力寫李信的思想感情及其矛盾。宋獻策與李信不同,宋獻策談陰陽五行,是他的職業和性格特點,也是歷史特色,李信有樸素的唯物主義思想,不信這一套。后面幾章還有進一步的發揮和批判。”
第二十七章李自成冒險前來與張獻忠會面,張獻忠的軍師徐以顯以“成大功者的六字箴言”——“心狠、手辣、臉厚”動員張獻忠在李自成尚沒有成氣候時,把他干掉。張獻忠雖然沒有聽從軍師的話殺掉李自成,但他對徐以顯說的“六字箴言”卻是很欣賞的。我問姚雪垠先生對張獻忠的性格是怎么把握的,姚雪垠先生說:“在小說中,我也寫了張獻忠的長處,但對他的惡劣表現決不諱言,常有誅心之筆,作為批判。”
第三十一章寫崇禎皇帝看到國家事一日壞似一日,看不見一點轉機,心中嘆息不止,這時他想到督師楊嗣昌和正在秘密與滿洲議和的兵部尚書陳新甲,感慨地說:“難得有這兩個對內對外的得力大臣……”我提出了可否把“對外對內”四個字刪去。姚雪垠先生說:“這里的‘內’和‘外’都是指本朝而言,與今天說的‘內’和‘外’的含義不同,這里是寫崇禎的思想和處境,點出他‘內交外困’,不要刪去。這里是出于藝術上考慮,與茅公(即茅盾)從政治上提出的,不是一個范疇的問題。”
第三十二章寫明軍由優勢轉化為劣勢,崇禎內心常常冒出一種“亡國”之念。按一般理解,“亡國”是指國家滅亡,而李自成和明朝的戰爭,并非外來侵略者的民族戰爭。我提出用“亡朝”或“敗亡”似更確切些。姚雪垠先生說:“你理解錯了,古人思想中的‘亡國’就是‘亡朝’。‘民族’‘國家’的觀念是近代產物,這里是寫崇禎的心中想法,不改為好。”
第三十五章寫李自成大部隊進入河南時,李自成率領親兵親將五十人先行,來到荊紫關時他到一個小飯鋪休息。就在這時陜西三邊總督鄭崇儉的標營騎兵追來了。李自成把開飯鋪的男人叫來,賞他一把散碎銀子,叫他趕快逃走,免得被官兵抓到殺良冒功。那男人不知他就是李闖王,見他如此仗義,趴在地上就給闖王磕頭。我告訴姚雪垠先生征求意見時,有人建議不要磕頭。姚雪垠先生說:“古代磕頭類似近代鞠躬,非常普遍,不同于正式跪拜。那飯鋪的男人雖不知他面前的大漢是闖王,但從大漢的神情和他帶有隨身親兵親將,也會判斷出這大漢是義軍首領,不行磕頭禮是不合理的。為了保持歷史習俗,不能過分遷就部分讀者。”
第三十七章,在《李自成》第二卷將要進行第二次印刷時,姚雪垠先生把新寫的有關宋獻策獻讖記的一段文字送給我,讓我把原來那段文字抽去。現在我把兩段文字都抄錄如下。
原來的文字(中冊,第929 頁):
對于宋獻策所獻的讖記,李自成在當時也喜出望外。他是那種慣于動腦筋思考和喜歡讀書的人,曾在戎馬之間陸陸續續閱讀過一些史鑒之類的書。雖然他也知道許多朝代鬧騰著獻讖記,頌符命,獻祥瑞,多是假的,但是他斷定宋獻策決不會假造讖記獻他。他不是超人的英雄,而是封建社會的、落后的小農經濟條件下產生的農民英雄,是在歷史給他的局限性之內領導了一次轟轟烈烈的農民革命戰爭。李自成的思想上雖然沒有擺脫對天命觀的迷信,但是他的杰出之處是他在考慮問題時和在實踐上更看重人事,入河南后積極地推行他所制定的有利于革命戰爭的軍事路線和政治路線。宋獻策所獻的讖記,不管他的實質和來源多么荒唐,在當時歷史條件下卻對李自成及其連遭挫折、重新號召起來的大軍起了巨大的鼓舞作用,能夠幫助擴大他的威望,增加廣大百姓對他的向心力,也成了他同崇禎皇帝斗爭的一種精神武器。僅僅再過兩個月,即破洛陽之后,他就將自己的稱號定為“奉天倡義文武大元帥”。僅僅再過一年,崇禎害怕他真有“天命”,密諭新接任陜西、三邊總督汪喬年指示米脂知縣邊大受掘毀他的祖墳,要破壞所謂“王氣”。僅僅再過兩年,他建立新順朝,后改大順,取“順天應人”之意。
新寫的文字:
經過了十二年的武裝斗爭,千辛萬苦,艱險備嘗,尤其是在近兩三年連遭重大挫折之后,如今初來河南,開始走上順利道路,長久以來夢想中的宏圖大略看來并非空想,正在此時,宋獻策來到軍中,獻上“十八子主神器”的讖記,對李自成和全軍上下都起了十分巨大的振奮、鼓舞作用。闖王暗想:過去只有人說我李自成日后能得天下,不意果然是上膺之命,見于圖讖!劉宗敏等眾將領想道:只要闖王上膺天命,縱然肝腦涂地也是值得的。同時從上到下,都想著今后應如何齊心戮力,整飭軍旅,除暴救民,佐闖王早定天下。高夫人知道了宋獻策獻的讖記,同左右的女兵們激動得滾出熱淚,立刻在院中擺上香案,焚香拜天。明朝人由于朝廷提倡,最為崇奉關羽,稱為關帝。高夫人拜過天以后,又對著關帝牌位,燃燭焚香,虔誠禮拜,默求神佑,使闖王早建大業。老營將士自動地敲鑼打鼓,燃放鞭炮,高呼萬歲!
宋獻策來到闖王老營獻讖記的消息很快地傳知了各處將士,到處一片歡騰,鳴放鞭炮,呼喊萬歲。這一振奮人心的新聞也在民間迅速流傳。雖然那些據守山寨的土豪鄉紳們不肯相信,有些人半信半疑,但是廣大饑民,特別是年輕人,都相信這讖記句句皆真,認為“李繼朱”是天命注定。從此,來投義軍的百姓更加踴躍,成群結隊,川流不息。
把這兩段文字一比較,不難看出,前一稿對李自成自身的天命觀,有更多的解釋,而在后一稿則不僅對李自成,而且對他的左右親信和整個義軍都寫得更直率了,這就更接近姚雪垠的實際想法。我深感到,在寫李自成天命觀這一點上,姚雪垠先生自始至終保持堅定而清醒的看法。他始終保持這樣的原則:李自成的天命觀是歷史事實,他絕不在《李自成》中故意宣揚李自成的迷信思想,但卻不能回避這個歷史事實,更不能把李自成寫成是一個超越歷史局限的人,他是三百年前的歷史產生的農民英雄,不是二十世紀的無產階級英雄。可能就是出于這樣考慮,在第二次印刷時,他把那些為李自成辯解的違心文字通通刪去,重寫了這一段更符合當時歷史和李自成實際的文字。
第四十八章:寫福王府……白晝宣淫。我覺得不寫也可以,寫,意思不大。姚雪垠先生不同意,他說:“朱由松在南方登基后,不管清兵正在南下,還大選宮女,白晝宣淫。一日看戲,忽然將他看中的女戲子叫進宮中行淫。此處描寫所揭露的內容,并不過分。”
第四十九章寫高夫人向紅娘子提婚,說闖王和軍師的意思是李公子,問她意下如何。紅娘子深深低下頭,喃喃說:“我既無父母,又無兄長,闖王和夫人就如同我的親生父母。兒女的終身大事,只能聽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何必問我。”征求意見時,有的讀者建議把“兒女的終身大事,只能聽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刪去。姚雪垠先生當時表示同意,回來后又覺不妥,對我說:“清樣上紅娘子答話很有歷史特色,這段文字婉轉曲折地表達了她同意這門婚事,前后照應,比較完整,還是保持原來的樣子好。古人對話中的習慣用語,古人應有的感情、風范,只要不犯低級趣味的錯誤,就不應避諱。更何況是古人的語言,不是作者口中的話,也不是作者要宣傳的思想,大多數讀者會明白這個道理的。”
這章還寫到牛金星、宋獻策、李巖要李自成重視近代西洋使用的火器。宋獻策講了一大段火炮的進化和制造,我覺得這段文字敘述過長,讀起來覺得沉悶,建議壓刪改寫。但姚雪垠先生很欣賞這段文字,專門給我捎來一個條子,上面寫道:“我考慮再三,認為宋獻策談兵器進化、鼓吹火炮一段文字,以不壓不刪為好。牛、宋、李三人幾乎同時進入闖王軍中,出身和性格都不同。在這個單元里集中寫‘軍國大計’的討論和決策。他們三人所學,各有專長,各有表現。宋獻策熟于軍事,在此單元之中應有所表現。不然,他在小說中就會給人以突出印象:李自成僅僅是因為他獻讖記才封他為軍師。有了論火器這段文字,使讀者明白他在軍事上確有些獨到見解,闖王絕非輕率地給他軍師地位。在明朝末年,兵器、歷法、天文學等領域,都受了西洋的影響很大,展開新舊思想沖突,宋獻策鼓吹西洋火器,代表一種先進思想。”
第五十章袁宗弟說服李自成啟用郝搖旗時,講了這么一段話:“特別是當一個人倒霉的時候,更要多想想人家的長處,世上人,喜歡錦上添花的多,喜歡站在高枝兒上說風涼話的多,喜歡隨風轉舵的多,甚至還有一種人,看見別人跌倒,趁機踏上一腳,或者落井下石,墻倒眾人推。” 我覺得這些話和郝搖旗扣得不緊,同時也不是性格化語言,有借題發揮之嫌。姚雪垠先生不同意我的看法,他說:“這段話,是古代常見的世俗狀態,韓愈給柳宗元作的碑文中也寫過。一部大部頭的長篇小說,要努力在塑造典型上,安排主題思想上,處理重大歷史問題上,持嚴肅態度。但在古人的對話上,也要保持應有的個性特色,否則對話會變得蒼白無生氣。這段話你所以產生這樣看法,說明我寫得還不夠,否則是不會產生這樣印象的!”果然姚雪垠先生又把這段文字強化調整了一下:“李哥,我們看一個人,不能光看人家有多少短處,犯過多大過錯,還要看看人家有些什么長處,立過什么功勞。世上有些人喜歡錦上添花或站在高枝上說風涼話,很難在別人犯了錯誤時多想想人家的長處。還有一等人,巴不得別人栽跟頭。別人出一點事,他們便來個墻倒眾人推,落井下石,方稱心愿,把如何共建大業的道理全不想了。闖王,李哥,你難道沒有吃過這種苦么?”這么一改,袁宗弟的性格和形象出來了,同時他的話也深深地打動了李自成。
在編輯《李自成》第二卷稿和以后的第三卷稿以及圍繞四、五兩卷中的一些情節和人物的設計和創作中,姚雪垠先生還和我談了不少,只是我沒有全都記錄下來,現在想來,實在惋惜不已。
凌晨三時就伏案寫作
姚雪垠先生在北京,生活是很有規律的,每天吃過晚飯后,看一個小時電視,和兒孫們說會兒話,就上床看書,大約九時左右就睡覺了。姚雪垠先生說:為了寫作,我不得不犧牲晚上看戲、看電影、看電視劇的享受。但我有失也有得,“一日之計在于晨”,凌晨是我的精神最旺盛的時候,也是我的創作精力最活躍的時候。所以,幾十年來,姚雪垠先生總是凌晨三時左右起床,起床后,先用冷水擦洗身子,然后揩凈寫字臺,泡上一杯龍井茶,便坐下來開始寫作。待到天色將明時,便下樓慢跑,在他六十六歲的時候,還能環繞工人體育場的馬路跑上一圈。1975 年姚雪垠先生到京后,曾寫一首七律,題為《到京》前四句是:
快車高臥入京華,筆硯安排即是家。
舞劍仍來殘月外,揮戈慣趁夕陽斜。
第三句是說他仍是絕早起床寫作,第四句是說已到老年,仍在揮戈奮戰。
姚雪垠先生從1975 年12 月來到北京后,工作效率大大提高,1976 年3月13 日他向武漢市委宣傳部報告二卷稿的進程時是這樣寫的:
從去年十二月中旬到今年一月下旬,我將改過的稿子分批交給編輯部同志推敲、提意見。從今年二月上旬起,開始第二步修改工作,即編輯同志們分批提意見,我分批再作修改,然后發排。這一工作如今仍在進行。由于作者和編輯的要求和目的的相同,所以合作得比較愉快。這一卷大概八十多萬字,將分三冊出書。原來出版社希望爭取在“五一”出書,后來放棄了。我平日文思本來比較遲鈍,修改工作進度很慢,加之第二卷比第一卷不僅部頭大得多,在內容上也豐富得多,故事情節和穿插結構上復雜得多,在一個地方改動幾筆,往往影響在另外一個或幾個地方都得作相應的改動,所以進度就更慢、更費心思。等第二卷完全付排之后,方能開始對第一卷進行修改。
1976 年夏季河北唐山市大地震波及北京時,人們是在酣睡之中驚醒的,而姚雪垠先生是在伏案寫作中清醒地感到地震的來臨。開始時,他聽到很大的聲音從馬路上滾滾而來,他正要離開寫字臺到陽臺上觀看,大樓突然搖動,腳下顛簸,無法站穩。事后,姚雪垠先生深有感觸地說:若不是凌晨起床工作,那地震開始時的地聲,就不會聽得那么清楚,地震突然到來那嚴重晃動的恐怖的氣氛,也就沒有那么具體的感受了。我社干部和家屬立即從宿舍大樓搬出,在工人體育場的前面搭起帳篷,老老小小住了進去。考慮到姚雪垠先生年齡較大,又有繁重的寫作任務,我們勸他暫時離京返回武漢,先避一避,待震情平穩之后再回來。姚雪垠先生堅決不同意,他說:唐山遭到那么大的地震,幾天之內,工人下井出煤,鐵路修復通車,報紙復刊。天津市在地震的嚴重威脅下,電廠繼續發電,鋼廠繼續出鋼,工人、干部堅守崗位,戰士們冒著生命危險搶救親人……這些事跡太讓我感動了,我要以他們為榜樣,堅守崗位和出版社的同志一起防震抗震。就這樣,在大家幫助下,他也在工人體育場附近搭建了一個防震棚。在露宿街頭防震棚的那些日子里,生活條件簡陋到不能再簡陋了,但姚雪垠先生靜坐一角,堅持工作,專心地審定《李自成》第二卷校樣。他說:“只要大地沒有陷下去,我的工作就不會停止。”這部八十多萬字的校樣,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一字一句看完的。姚雪垠先生在抗震中的表現,給中青社的職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李自成》第二卷的清樣出來之后,于1976 年10 月10 日分別寄送給共青團“十大”籌備組和湖北省委、武漢市委。在報告里我們是這樣寫的:“姚雪垠同志于去年十二月上旬來京,至今年一月,對全稿通改了一遍;從二月到五月經編輯部審讀后,作者又對全稿作了第二遍修改;從六月到八月上旬,作者又在校樣上進行了第三次修改。經過八個月的修改,作品的思想和藝術都有了一定的提高,雖然作品中有些地方還可以改得更好一些,但有些也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提高的。作者在給毛主席的信中也談到‘由于《李自成》部頭龐大,書中出場的人物眾多,頭緒穿插復雜,反映歷史問題和生活問題較廣,五卷出齊后必須再將全書統改一遍方算完成’。我們覺得這樣好,一、二卷出版后,便能很快聽到廣大讀者和各方面人士的反映和意見,不僅有利于一、二卷的修改,也有利于三、四、五卷的寫作,因此,我們準備在今年內出版《李自成》第二卷,接著再版第一卷(作者已經修訂完畢,即將排出清樣),并繼續為作者提供方便條件,早日寫完三、四、五卷,實現毛主席‘將全書寫完’的殷切希望。”
共青團“十大”籌備組成員、分工主管中青社工作的胡德華同志很快告訴我們,籌備組同意出版社的意見,可安排二卷出版和一卷再版工作。
在“四人幫”未被粉碎之前,為避免在一些字句上被“四人幫”一伙曲解,胡找借口,隨心所欲歪曲寫作意圖,不明不白地遭封殺、挨棍子,姚雪垠先生在個別段落中加了一些作者的表白和議論。當第二卷清樣出來后,我陪姚雪垠先生到讀者中征求意見,這時“四人幫”剛剛被打倒不久,讀者們笑著對姚雪垠先生說:“您以作者身份的那些議論是害怕‘四人幫’打棍子啊,現在就不必要了。”姚雪垠先生聽了哈哈大笑,對大家說:“你們說得對極了,我是做了一些枉費心血的勞動。”好在姚雪垠先生增加這些議論時,是經過反復斟酌才下筆的,大都盡可能不破壞細節的藝術完整性,更不以議論代替描寫,所以在第二卷付印前,便把這些文字刪去了。但由于第二卷的部頭較大,仍有小的遺漏,用姚雪垠先生的話說:“難免留有蛇足。”后來在第二卷第一版第二次印刷時,姚雪垠先生又通讀檢查一遍,洗刷得比較干凈,算是把這塊心病去掉了。《李自成》第二卷于1976 年12 月正式出版。
回想自1963 年進入《李自成》第二卷寫作中艱苦的付出和遭遇到的種種坎坷和磨難以及受到的各種打壓、歧視和刁難……姚雪垠先生感慨之極。又想到自己終于渡過苦難,戰勝厄運,現在第二卷終于出版問世了,想想這十來年的不尋常的經歷,姚雪垠先生心懷激蕩不已。同時他也更加堅定了自己的創作風格和創作道路,想到此,他心有所感,提筆寫了一首題為《〈李自成〉第二卷問世》七律抒懷:
默默送汝初問世,任從讀者自平章。
無言桃李成蹊徑,叱咤風云豈霸王。
工細何曾流纖弱,雄奇未必屬粗狂。
十年寂寞篷窗女,羞學江家時樣妝。
“一部書救活一家出版社”
的由來
我們是在1975 年11 月5 日的下午,從王冶秋在國家文物局的講話中知道毛澤東對姚雪垠先生和《李自成》的批示精神的。“文革”中被康生一伙誣為“修到家的團中央”和它所屬的報、刊、出版社均已停止了出版業務,現在就是想出版《李自成》,中央不批準中青社恢復出書業務,也是白搭。當時我們幾個人覺得應該抓住這個契機,爭取恢復中青社的出書業務。與此同時,我們也聽到人民文學出版社已向文化部出版局提出出版《李自成》的要求,得到批準,并準備去武漢找姚雪垠先生洽談。在當時那種狀況下,如果姚雪垠先生同意交給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中青社是一點辦法也沒有的!想到此,我們更感到形勢緊迫、嚴峻。胡德華、闕道隆、江曉天和我研究后,決定讓江曉天去武漢,一是將毛主席的批示精神告訴姚雪垠先生;二是中青社立即進入爭取恢復出書業務和出版《李自成》的行動;三是勸姚雪垠先生暫不要考慮給別的出版社出版《李自成》。
為爭取時間,江曉天乘飛機前往,7 日買到機票,8 日一早便登機飛往武漢。就因此,江曉天趕在韋君宜的前面見到姚雪垠,掌握了主動權。姚雪垠先生是個很講信義的人,對江曉天的真摯態度和迅速行動很感動,他明確表態中青社如能恢復出書業務一定交中青社出版。江曉天盡心盡力地完成了此行的艱巨任務。
11 月11 日,江曉天從武漢乘火車抵京時,我到車站接他,之后與胡德華、闕道隆一起到團中央向團“十大”籌備組副組長王道義匯報,王道義要我們迅速寫個報告,由他們上報中央。次日上午我們研究報告內容,下午我與江回到宿舍,在江家擬寫報告初稿,之后送給胡、闕閱改,當晚送交王道義。14 日下午團“十大”籌備組又把我們叫到團中央,聽取王道義和幾位籌備組成員的意見,當晚回來連夜修改定稿,于第二天一早送給王道義。這份報告是以中青社的名義寫給團“十大”籌備組并中央的請示報告,團“十大”籌備組另擬一函,于18 日一起上報。25 日下午四時半,團“十大”籌備組打來電話,告知中央已批準,于一小時后把批件送到中青社。至此,中國青年出版社在團中央報刊社中率先宣布恢復了出書業務。這就是后來所傳“一部書救活了一家出版社”之說的由來。
第二天一早江曉天先給姚雪垠先生發電報(當時姚家還沒有電話),告知中央已批準我社復業出書。同時打電話給武漢市委宣傳部文藝處長丁力,請他把這個消息報告省、市委和省、市文聯。
28 日江曉天終于和姚雪垠先生通上了長途電話,姚雪垠先生高興地告訴江,月底先將二卷修改稿寄來三十萬字。也正是這一天,文化部出版局正式通知我社:《李自成》仍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別的出版社不能出版。29 日,我們將這個通知向湖北省和武漢市作了通報。
湖北省市委、省市文聯和有關領導同志鼎力相助,都支持姚雪垠先生來京定稿。很快,姚雪垠就正式接到省、市委批準他來京的通知。姚雪垠先生以無比愉快的心情給我們寫來了一封信:
道隆、維玲同志:
我打算在本月20日動身,上車前將有電奉閱。今后我們將為著共同的文藝事業并肩戰斗,一起為黨和人民做出微薄成績。十幾年來,我得到你們的幫助很大,非一般泛泛的業務關系。正因為這里有關的省市領導深知我同你們有非泛泛的關系,所以這次《李自成》的出版問題在此間得到重要的精神支持。曉天同志雖然離開中青,但是我們的融洽合作會在毛主席指示后的巨大的鼓舞和鞭策下繼續前進,合作得更有活力,也更為密切無間。我的工作今后完成如何,你們的具體幫助十分重要。到京以后,大體要保持我在武漢的多年習慣,即埋頭工作,耐得寂寞,勤學苦練。“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后我習慣于埋頭工作,朋友們和領導有時來看我,我極少回看,日久大家都能諒解。像寫《李自成》這樣的大部頭長篇,確實需要窮年累月,無論寒暑,進行讀書、研究、構思和執筆寫作。到北京后,只能繼續保持這種多年行之有效的工作習慣,方能期望更快更好地完成計劃,報答毛主席的關懷和讀者的殷望。
當然,北京文藝和學術界的老朋友多,非武漢可比,完全不來往也不可能。但是我將力求將不十分必要的來往限制在最小限度。每日凌晨和上午,我照例除非有緊急他事都專心寫作。午覺睡片刻后,一般是讀書,抄筆記,做點雜事。有人想來看我,知道我的習慣,也多在下午。到京后,將仍這樣安排時間。
第二卷校改稿,數日內再寄上一批。
姚雪垠
1975年12月8日
當時江曉天雖已調到《中國文學》雜志社,但為把《李自成》這部書稿編好,出版社正式出函,請他參加第二卷的編輯工作,一直到第二卷定稿。這個情況姚雪垠先生在寫這封信時是不清楚的。
幾天后,姚雪垠先生又來信,打算在京長住,不僅要把二卷改定,還要將一卷修訂再版,還想寫完第三卷,時間大約需要三年,要出版社安排住房時,把這些情況考慮進去。我社研究后,決定在宿舍大樓內騰出一套兩室一廳的房子,專供姚雪垠先生寫作居住。
1975 年12 月12 日姚雪垠到京,江曉天和我到車站迎接,把姚雪垠先生迎進了我社宿舍——工體北路幸福一村一樓333 號。
此后,姚雪垠先生在京無論是外出開會訪友,還是到北京圖書館查閱有關圖書資料,或是到琉璃廠中國書店選購古舊圖書,到榮寶齋購置筆墨宣紙以及外出參加一些必要的社會活動,均由我社派車接送。寫作中添置的中文打字機、錄音機以及文具稿紙,包括家用炊具以及節假日副食品供應,均由我社提供。在他的夫人王梅彩到京后的生活、工作安排和幫助姚雪垠先生解決助手等事宜上,中青社有關部門、有關同志本著貫徹毛主席“讓他把書寫完”的指示精神,力所能及地、最大限度地為姚雪垠先生提供了方便條件。二十多年來,姚雪垠先生一家與中青社一直處的和諧融洽,感情誠篤,他常對人說:“中青社是我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