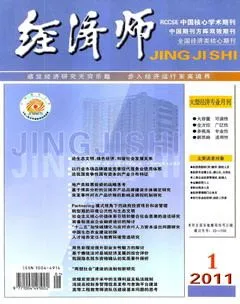馬克思與馬爾庫塞的技術批判風格比較
摘 要:技術本屬中性,可為什么其運用卻往往伴隨著技術陷阱?馬克思與馬爾庫塞都從技術異化入手進行解構,不過前者總是遵循實踐論感性到理性的路徑,善于從異化表象去發掘背后深層的政治經濟學意義,后者基本拋棄社會矛盾分析法,只從人性、意識形態層面進行解讀,二者的技術批判路徑大相徑庭,一個寫實,一個略顯浪漫,其留給后人的遺產自然不盡相同。
關鍵詞:馬克思 馬爾庫塞 技術批判
中圖分類號:F20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1)01-046-02
技術是人類智慧結晶,與人、自然和社會的互動構成歷史進步的動力之一。但在資本主義社會,技術運用卻時常產生與人類預期截然相反的結果,似乎技術進步就是一個美麗的陷阱,學界稱為“技術悖論”。對于這個命題,生活在資本主義技術上升期的馬克思給予較早關注,他說:“在我們這個時代,每種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們看到,機器具有減少人類勞動和使勞動更為有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卻引起了饑餓和過度的疲勞。……技術的勝利似乎是以道德的敗壞為代價換來的……”馬克思正是通過考察技術異化,從而開創了技術批判先河。馬爾庫塞生活在資本主義技術相對成熟期,其時,技術已侵入并控制社會各領域,作為法蘭克福學派激進哲人,他敏感地意識到技術社會的極權性和奴役性,在《單向度的人》導言中他開宗明義:“生產裝備趨向于變成極權性……面對這個社會的極權主義特征,技術‘中立性’的傳統概念不再能夠得以維持”,馬爾庫塞也由此構建其技術批判思想。縱覽二者的技術哲學,共同點是他們均從技術異化視角來解構技術的“二律背反”現象,但他們的技術批判路徑卻大相徑庭,前者側重于現實革命主義批判,并試圖揭示資本主義技術進步與背后一系列社會方式的互動,后者卻整體落入舊的現實主義批判窠臼且略顯浪漫,至于人類怎樣走出技術悖論怪圈他們留給后人的啟迪自然不盡相同。
一、馬克思與馬爾庫塞的技術批判路徑與風格比較
馬克思的技術批判總是從唯物史觀出發,按照歷史與現實的邏輯統一,并遵循實踐論“感性到理性”路徑,由表及里,由現象到本質,目的是從技術異化表象去發掘背后深層的政治經濟學意義,因而是一種現實革命主義的批判風格。
馬克思先是從歷史維度考察了技術與勞動的異化。“在工場手工業中,工人是活機構的肌體,在工廠中,死機構獨立于工人而存在,工人被當做活的附屬物并入死機構。”馬克思對資本主義技術史考察發現,技術并沒有減輕勞動強度,相反卻加劇了對工人的肉體和精神的摧殘,“機器勞動極度的損害了神經系統,同時它又壓抑肌肉的多方面運動,侵吞身體和精神上的一切自由活動。”即是說,人類本應是機器的主人,但機器工業社會中,機器與人——工具性與自主性卻變換了自己的位置,機器成為工人異己的、敵對的和統治的權力,工人變成機器的一個器官,就像卓別林在《摩登時代》淋漓盡致的演繹一樣,工廠變成傅立葉所稱的“溫和的監獄”。
馬克思進一步地從現實維度考察了技術與勞動產品的異化。因為機器使用在創造出更多產品的同時也縮短了工人必要勞動時間,引起勞動力貶值,“工人生產的財富越多,他的產品的力量和數量越大,他就越貧窮。工人創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變成廉價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貶值成正比。”在《手稿》Ⅰ中,馬克思認為人是類存在物,產品經過勞動成為人的類生活的對象化,可為什么工人同自己的勞動產品的關系就像同一個異己物的關系呢?是什么因素使然?神?自然界?顯然不是,馬克思通過技術與資本主義最普遍因素——勞動與產品的異化表象入手,按照歷史與現實的邏輯統一進行剝繭抽絲,發現技術異化表象的背后有更深層的根源,它屬于另一個存在物,即工人通過異化勞動生產出來的資本家連同異化勞動的必然結果——私有財產。從異化勞動到私有財產,馬克思認為國民經濟學的一切范疇,商業、競爭、資本、貨幣,不過是異化勞動的特定的、展開了的表現而已。
人類發明機器的目的在于減輕肌肉力強度,將勞動對象變成自己類生活的對象化,但機器的資本主義運用卻使勞動具有強制性和奴役性;同樣,技術本可以增加生產者的財富,但其資本主義運用卻使生產者變成需要救濟的貧民。馬克思以技術異化為批判武器,突破了技術的工具屬性,而是從技術的制度屬性尋找深層根源,認為這是技術被置身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中并執行資本邏輯的結果,他一針見血地指出:“產生勞動的中心機器不僅是自動機,而且是專制君主”,當技術為資本家控制,化身為人格化資本時,成為資本家駕馭勞動的權力和追逐利潤最大化的工具,才使技術背上“悖論”之說,其目的是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階級矛盾進行解構,所以馬克思指出:只要肉體的強制或其他強制一停止,人們就會像逃避鼠疫那樣逃避勞動。
馬爾庫塞技術批判是從技術與人性的異化入手的,他看到技術進步為人類創造了巨大福祉,同時卻催生了大量的虛假需求,諸如“休息、娛樂、按廣告宣傳來處世和消費、愛或恨別人之所愛和所恨”、“小轎車、高清晰度的傳真裝置、錯層式家庭住宅以及廚房設備成了人們生活的靈魂。”他認為,這些虛假需求壓制了人性自由發展,在技術盛世里,如果工人同他的老板享受同樣的電視節目,打字員同她的雇主的女兒打扮得一樣漂亮……,那么,先前那種自由、平等名義下的否定與抗議將不復存在,人也就變成單向度的人。可悲的是人們放棄了人性自由發展卻又自感幸福,馬爾庫塞認為這種看似舒舒服服、平平穩穩的生活,實質上是充斥著虛假的不自由的生活,生活在技術盛世里的工人是受抬舉的奴隸,他由此斷定:“發達工業社會的顯著特征是它有效地窒息那些要求自由的需要”。
之后,馬爾庫塞進一步推演出技術與政治社會的異化——技術社會的極權性。在他看來,技術社會是一個沒有反對派的社會,從政治領域看,“經典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把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轉變設想為一種政治革命:無產階級摧毀資本主義的政治設施,但保留它的技術設施并使它從屬與社會主義。”然而,技術進步卻成功地消滅了危害其繼續存在的政治派別,因為人們都在分享制度好處。除此以外,在意識形態領域,技術的合理性及統治邏輯同樣造成思想、藝術的異化,資產階級成功地控制著話語權,對語言實行全面管理,把多向度的語言縮略并清洗為帶有技術烙印的單向度語言,“正是這些術語命令、組織、引導人們去做、去買、去接受”使得否定性思維變成被擊敗的抗議邏輯。文化與審美也有被技術征服的趨勢,他指出:今天,高層文化與現實的“間距”已被克服,文化中心變成商業中心,早期資本主義文學中那些反叛角色已被征服……,且不再想象另一種生活方式。總之,由否定性思維到肯定性思維,這是技術社會的基本特征。
通讀《單向度的人》發現,馬爾庫塞的技術批判透析著濃濃的人文關懷情愫,從中我們解讀出他對資本主義的技術控制導致人性多維性淪喪有所控訴,這是其技術哲學的閃光點,也是他“人文理性”主張下的名至實歸。然而,這種拋棄上層建筑決定于經濟基礎這個社會矛盾基本分析法,注定了他的技術批判無法觸及技術悖論背后屬于經濟基礎層面的深度因子而整體落入了舊的批判現實主義俗套,僅僅是一個表象走向另一個表象,因而其解構略顯蒼白甚至于浪漫。另外,他基于技術進步對勞動強度的消減、藍領工人白領化以及非生產性工人增加甚至作出“無產階級融合論”這樣離經叛道的判斷,作為西馬學者,是對馬克思的一種徹頭徹尾的悖逆,也是他對千年偉人馬克思無法望其項背的原因之一。
二、為人類走出技術悖論二者寄予不同的期望
技術提升了勞動內涵,而勞動創造了人類福利,盡管技術異化展示了其反人類的一面,但馬克思并不贊同將技術悖論歸因于技術本身,更是堅決反對廢除現代技術,這與技術悲觀主義者給技術戴上“原罪”截然不同,他說:“一個毫無疑問的事實是:機器本身對于把工人從生活資料中‘游離’出來是沒有責任的。”馬克思通過考察技術史發現,工業社會之前,人與技術是和諧的,為什么之后卻時常出現工人毀壞機器現象,工人怠工一浪接過一浪,關鍵在于機器的人格化與資本化,這點馬克思做了精辟總結:“可以寫出整整一部歷史,說明1830年以來的許多發明,都只是作為資本對付工人的暴動的武器而出現的。”由此,馬克思從革命現實主義出發,將技術批判轉化為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批判,從而把矛頭直接指向資本主義私有制和剝削制度,即只有通過社會主義革命把技術從資本主義制度控制下解放出來,人類才能走出技術悖論怪圈,后工業化時期,“……工人要學會把機器和機器的資本主義運用區別開來,從而學會把自己的攻擊從物質生產資料本身轉向物質生產資料的社會使用形式。”
基于技術異化的結果——單向度的人與單向度的社會,馬爾庫塞為人類走出技術悖論設計了烏托邦式路徑。首先是寄希望于人性的否定性回歸,他高舉人文關懷旗幟大聲疾呼:“決定人類自由程度的決定性因素不是可供個人選擇的范圍,而是個人能夠選擇什么和實際選擇什么。”套用我國思想家老子的話就是要“反其性而復其初”,即回復人性的全面自由,反對技術對人性的壓抑與擠出。然后是意識形態革命,他反對充滿技術和商品韻味的文化藝術方式,因為它們令人們失去理性而麻木不仁,不再想象“另一種生活方式”。至于誰堪當此任?他根據技術進步導致新的社會分層,認為“人民,這個先前社會的變革酵素,已經‘上升’為團結酵素。”因為被技術奴性化,他不把人類克服技術悖論寄希望于他們,轉而去尋求新的力量——亞階層,即那些生活在社會底層的流浪漢、局外人和失業者,認為“當他們為爭取公民權聚集起來走向街頭時……可能標志著一個時期終結的開端。”在《單向度的人》結尾處他意味深長地引用了瓦爾特·本杰明的話說:只是因為有了那些不抱希望的人,希望才賜予了我們。
三、二者技術批判思想不同的當代啟迪
技術本屬中性,但其運用卻是一把雙刃劍,正如克隆技術有助于解釋生命現象,同時也產生人倫爭議一樣,所以居里說:科學并無罪,有罪的是不好地利用科學的人。如何避免技術陷阱?馬克思與馬爾庫塞技術哲學給人類留下不同的遺產,值得人類甄別對待。
一是因勢利導還是因噎廢食?不容否認,當今社會仍存在著階級差別與分工差異,徹底擺脫技術陷阱的時候恐為時尚早,只有人類達成馬克思語境中的“自由聯合體”時,那時勞動成為第一需要,技術才完全變成人類本身的和諧因素,達成真正的“技術文明”。馬克思技術觀主張人類應打破技術宿命論,技術無所謂原罪,相反,正如馬克思主張“利用資本本身來消滅資本”一樣,走出技術悖論人類應加強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觀念,學會用發展來解決發展中的問題。馬爾庫塞只看到技術被資本主義成功控制而產生消極現象就將技術悖論歸咎于技術本身,這種對技術采取否定性、激進式的批判容易導致人類對技術的因噎廢食,即技術悲觀主義甚至是反科學技術。
二是如何厘清技術的服務邊界?隨著“技術帝國”與“技術經濟”崛起,馬克思語境中的技術人格化與資本化得到強化,技術越來越脫離活勞動而成為價值的獨立源泉,它們利用技術資本的統治力量在全球化中攫取壟斷利潤,后發國家有被技術邊緣化趨(下轉第51頁)(上接第47頁)勢。技術本然應是普世的,技術無國界,不該只為少數人服務,馬克思說:“資本迫使科學為自己服務,從而不斷地迫使反叛的工人就范。”這句話的后現代取向就是說:只有打破技術服務邊界的藩籬,摧毀技術資本的全球體系,把技術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控制下解放出來,技術才能顯示其普世價值。可惜,馬爾庫塞放棄了技術的制度屬性及階級屬性分析,相對馬克思寫實的批判風格,顯然,他無法給人類走出技術陷阱提供更好藥方,他寄予期望的所謂亞階層,注定也只是他的一廂情愿。
三是如何打破“技術政治”而還原“綠色政治”?《單向度的人》導言指出:“我們社會的突出之處是……利用技術而不是恐怖去壓服那些離心的社會力量。”在馬爾庫塞看來,技術已然拋棄“中立概念”而充滿著政治含義,資本主義統治形式越來越變成了“技術的、生產的、甚至是福利的”,這讓他痛心疾首,他基于人文理性呼吁人的否定性回歸,倡導人們敢于對“技術政治”說不,有其積極的現實意義。馬克思把技術與社會生產方式聯系起來考察,認為技術是社會發展的產物,是否異化取決于技術的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是否協調,是否有科學的技術倫理保障技術與人、社會的良性互動,實際上已給后人打破“技術統治”找到了一座思想橋梁,即打破技術統治藩籬,還原于綠色政治。當今可持續發展、生態主義、綠色GDP等思潮都從他那里汲取了營養,為人類構建工業文明時代科學的技術倫理,克服技術悖論遺留下一筆珍貴遺產。
參考文獻: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