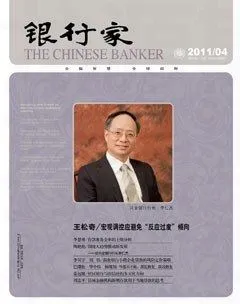貨幣信貸調控中的國內銀行業
2011-01-01 00:00:00安徽銀監局課題組
銀行家
2011年4期
面對國際國內復雜多變的經濟金融形勢,2011年央行貨幣政策重新回歸穩健軌道。在貨幣政策宏觀調控方面,央行創造性地提出了社會融資總量調控目標,并加大了貸款規模控制力度,多次調整準備金率和利率,實行差別準備金制度,由此對正在改革發展中的銀行業經營管理將產生深遠影響。本文試圖對此進行簡要分析,并提出下一步銀行業經營管理應對之策。
宏觀調控產生的積極影響
進一步豐富了貨幣政策調控的工具和手段。與“貨幣信貸”相比,“社會融資總量”更好地代表了社會總需求,與物價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更為穩定,央行可以根據“社會融資總量”的變化來調整“貨幣信貸目標”,這也是今年央行首次沒有明確信貸調控目標的重要動因之一。當債券融資、股權融資規模較大的時候,央行就會適當壓低信貸規模;當債券融資和股權融資規模較小的時候,就適當提高信貸規模,傳統的貨幣信貸目標制就演變為“彈性貨幣信貸目標制”。
合理分散信用風險。一是有助于優化我國社會融資結構,拓展金融市場的深度和廣度。通過社會融資規模的調控,發展了包括政府債券市場、金融機構同業拆借市場、商業票據市場、銀行承兌匯票市場、股票市場、基金市場、保險市場、融資租賃市場、外匯市場、黃金市場等許多不同的市場在內的龐大體系,適當調整社會融資總量過度倚重銀行的格局,有利于分散信用風險。二是有利于調整經濟結構。……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