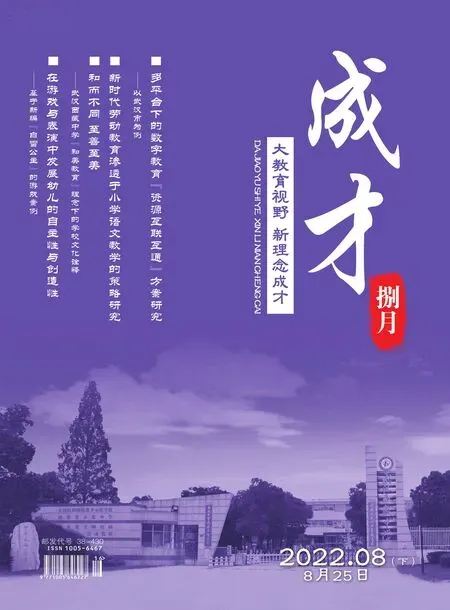微課在高中數學課堂教學中的應用研究
■ 哈爾濱師范大學教師教育學院 呂 靜
一、微課的特點
(一)時間短
微課的“微”字顧名思義就是微小簡短,意味著微課的時長比較短,一般在5-8分鐘,因為學生集中注意力的時間是有限的,微課正是基于這一特點,將時長控制在一定范圍內,符合學生的學習規律。
(二)教學目標明確
微課是圍繞著某個知識點進行完整而簡短的一種教學形式,只圍繞著一個知識點進行展開,因此微課的教學目標明確,在教學設計上也較為精煉。
(三)學習方式靈活
微課的學習方式讓我們不僅局限于課堂當中,在課前和課后也可以學習,課前可以對新課知識進行預習,課后可以進行鞏固復習和查缺補漏,這種靈活的學習方式備受師生的喜愛。
二、高中數學課堂教學的現狀
在傳統的高中數學課堂中,主要依賴教師的講授向學生傳遞信息,以此促進學生對知識的理解,啟發學生的思維。但是講授法的弊端是比較枯燥乏味,難以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在課堂教學的過程中,學生對于部分知識難理解,比如在學習立體幾何時,難以建立模型,長此以往會對這部分內容的學習產生抗拒心理,降低學生學習數學的信心,缺乏學習數學知識的主動性,這就不利于教學效率的提高。
在課堂教學過程中,時間往往比較緊張,教師面臨著較大的升學壓力,更容易把時間用在做題講題中,難以發展學生的探究能力和自主學習能力,在課堂教學過程中會把更多的時間用來講解概念、定理、公式等基礎知識,因此學生會學習動力不足。
在課堂教學中,學習知識只有在學校進行,學生學習效率高的時間就是課堂的45分鐘,這樣傳統的教學方式限制了學生的時間和空間,然而微課的教學方式彌補了這一缺點,它并不受時間和空間的約束,學生可以在家中通過微課進行預習,有利于新課內容的學習。
三、微課在高中數學課堂教學中的應用優勢
(一)豐富課堂,激發興趣
對于傳統的課堂教學來說,教師只能靠語言和一些簡單的教具進行教學,課堂難免枯燥乏味,而且有些教學內容還比較難理解,語言和教具可能難以滿足學生,微課的教學方式可以對此加以補充,輔助教師進行教學,抽象枯燥的知識變得通俗易懂,有利于加強學生的學習興趣。
(二)加強互動,調節氛圍
教師在課堂教學的過程中利用微課,通過視頻動畫等方式提高教學效率,師生之間增強互動,可以增強師生之間的情感。在這個過程中,有別于以往的教師講,學生聽,學生可以感受到課堂教學的趣味性。心理學家認為寬松的課堂教學環境利于學生的學習,借助微課來調節教學節奏,創造輕松愉快的課堂氛圍讓學生們感覺放松,學生的學習效率也會提高,因此微課在營造學習氛圍和構建快樂高效的課堂上的確有優勢。
(三)提高能力,增強信心
數學學科不同于語文英語等其他學科,它更需要學生具備空間想象能力,比如在學習立體幾何時。研究表明,女性在空間想象能力方面要弱于男性,因此教師在課堂教學中應注意到學生學習的困難之處。而對于這種情況,教師可以利用微課,將平面的圖形立體地展現給學生,讓學生直觀明了地理解此類題目,防止學生對立體幾何的學習產生抵觸情緒,提高學生的學習能力,增強學生對學習數學的信心。
(四)提高效率,鞏固所學
作為教學的輔助手段,微課可以對學生起到很好的課后復習鞏固作用。在學生的學習過程中,遺忘是很正常的,有時學到后面,又模糊了前面所學的知識,這時,微課對學生能起到很好的鞏固作用。有些學生在課上沒掌握牢的知識,可以在課下再次回顧。比如在學習某一類型題的時候,學生在課上弄不透,總是不能解出完整的答案,但課堂時間有限,教師的精力也有限,因此,如果針對這一類型題做出相應的微課,學生利用課后時間多次觀看,的確是一種高效率的方式,信息技術的迅速發展,為學生的學習創造了很多便利的條件。
四、微課在高中數學課堂教學中的應用策略
(一)微課預習,培養習慣
預習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學生的預習方式單一,部分學生的預習效果也不理想。如果教師利用微課進行課前預習,這樣的形式可以吸引學生興趣,預習的效果也會變得事半功倍。
例如在學習空間中直線與直線的關系時,可以在微課中引用生活中異面的例子,先直觀的給學生展示出來,再解釋異面的定義,教給學生異面直線的畫法,使學生對異面直線有一定的理解。通過鞏固練習檢驗學生的掌握情況,讓學生試著在幾何體中找到給定直線的異面,并且嘗試用多種方法畫出兩條異面直線。這樣簡單易懂的預習方式學生更容易接受,同時也能提高教師在課堂教學中的效率,提前讓學生預習可以使學生對新知識有所理解,即便是空間想象能力較弱的學生,也能根據動態圖直觀地理解什么是異面直線。學生平時課業壓力大,看教材和資料需要很久時間,可能還抓不到重點,微課不僅簡短明晰還可以反復觀看,的確很受學生歡迎。
(二)微課導入,增趣激疑
眾所周知,導入是課堂教學中較為重要的環節,一個有效的導入往往能讓學生激發興趣,引起思考。在高中數學的學習中,有些只是比較抽象,難以理解,只聽老師的口頭描述還難以理解,因此微課的輔助作用便顯得尤其明顯,圖文聲并茂的視頻更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例如在學習圓錐曲線的光學性質及應用時,用微課的形式引用西西里島的故事,西西里島上的犯人們被關押在巖洞中,他們在夜里小聲地討論如何越獄,但是計劃卻敗露,犯人們互相懷疑卻也找不到告密者。原來這個巖洞是橢圓形的結構,即便犯人們小聲議論也能通過反射傳到看守人那里,由刁尼秀斯設計的巖洞被人們稱為“刁尼秀斯”之耳。圖文聲并茂的小故事不僅集中了學生的注意力,也激發了學生學習的好奇心,與其他方式的引入環節相比確實更加有優勢。
(三)微課教學,突破難點
微課的優勢在于短小精悍,由于高中的數學知識比較繁雜,有些知識對于學生來說難以理解,在學習的過程中存在一定的難度,因此,便于學生更好的掌握重點,突破難點,運用微課有針對性的展示給學生,可以有效地提高學生學習效率。
在高中的數學學習中,學生經常會遇到一些難點,但由于課堂時間有限,學生層次不同,很難做到每個同學都理解。如果教師將一些重難點的知識做成微課分享給學生,上課時學生沒理解的知識,可以在課后學習,還有不理解的可以請教老師,這樣不僅教學效率高,也緩解了羞于問問題和學困生的情況。
(四)微課復習,鞏固所學
高中數學的概念和公式特別多,如果不能及時復習鞏固,很容易混淆,如今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給學生的學習帶來了很大的便利,讓學生們更好地進行課后復習,幫助學生梳理知識的脈絡。
在學完數列這部分內容后,教師可以借助思維導圖整合這部分內容,通過微課的形式播放出來,例如我們在學習數列時根據規律分為一般數列,等差數列和等比數列,而在各個數列下又有各自的通項公式、定義、性質等知識點,學生們在學習后很容易混淆,通過思維導圖將各部分內容整合,有利于學生發散思維,系統地掌握所學。
(五)微課拓展,豐富知識
心理學家羅杰斯指出:教師應以形成良好的課堂心理氣氛為己任,使學生更加充分地、熱情地參與整個教學過程。因此在教學過程中,不僅要讓學生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讓學生感受知識發生發展的過程。死記硬背的數學概念效果并不好,教師可以嘗試對抽象的數學概念進行補充,將數學概念延伸到學生的日常生活中,將復雜抽象的概念生活化,通過微課的拓展,對所學知識理解的更加全面。
五、微課在高中數學教學中的注意事項
(一)提高制作能力
在互聯網時代,教師們要做到與時俱進,樹立終身學習理念。如今受疫情影響,學校上課都改成網課的形式,這就要求老師們熟練辦公軟件。教師應不斷學習,提升制作微課水平。在新技術層出不窮的今天,不進步就意味著要被時代拋棄。
(二)樹立正確觀念
利用微課教學可以提高學生的積極性和主動性,但是目前有些教師對于微課的應用方法有些不合理,一節課大部分時間都讓學生自己看,代替自己講課,這種單純“放電影”式的教學是不可取的。微課只是作為教學的輔助,如果本末倒置,就與微課創立的理念相違背了。
(三)控制微課時間
根據學生的認知特點和學習規律,我們知道學生的注意力是有限的,微課作為短小精悍的碎片化教學方式,時長應控制在10分鐘之內。微課的時長過長,學生可能會產生抵觸情緒,學習效果大打折扣,因此微課的時間要控制好。
六、結語
微課是時代發展的產物,是對目前課堂教學的一種有效補充,但并不能完全代替課堂教學,它只是一種輔助形式。隨著微課的不斷優化和發展,使用微課輔助數學課堂的教學,有利于提高教學的效率,補充了課堂教學的不足,豐富學生的體驗,利于激發學生學習數學的興趣。微課也為社會提供了優質的在線學習條件,實現“泛在學習”,同時,很多優質教師的課我們也有機會聽到,這的確能在一定程度促進教育公平,我相信未來微課平臺會發展得越來越完善,為我國的教育事業貢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