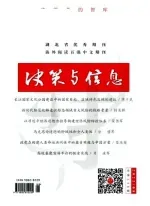如何向世界傳達真實的中國
文/[美]羅伯特·勞倫斯·庫恩
美國和中國之間良好的雙邊關系對21世紀的和平與繁榮極其重要。如果不建立戰略伙伴關系,我們的處境可能會比戰略對手關系更糟糕——而這正是各方都應該重視中國領導人的內在態度和主要關切的原因。
如何向世界傳達真實的中國
文/[美]羅伯特·勞倫斯·庫恩
貿易糾紛、貨幣匯率、人權、財政儲備、自然資源競爭、外交對抗、軍事緊張局勢、甚至企業收購接管等的報道充斥美國媒體,有一部分人對“共產中國”這類駭人聽聞、聽起來像冷戰時期諷刺作品的長篇累牘信以為真。
我認為,美國和中國之間良好的雙邊關系對21世紀的和平與繁榮極其重要。如果不建立戰略伙伴關系,我們的處境可能會比戰略對手關系更糟糕——而這正是各方都應該重視中國領導人的內在態度和主要關切的原因。
自從2005年我所撰寫的傳記《他改變了中國:江澤民傳》——第一本記錄在世的中國領導人生平的書在中國大陸出版以來,我經常被問道:作為一個受過專門教育的科學家和專業投資銀行家,為什么要寫這么一本書?同樣,當我屢屢在美國和國際媒體發表關于胡錦濤主席的理念和政策的采訪和文章,而我的觀點又經常和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們迥然不同時,也會被問及:作為腦科學博士和并購專家,我為何要花時間和精力來解讀一個中國領導人的政治遠見?
兩者的答案是相同的,我之所以撰寫前國家主席江澤民的傳記,之所以解讀胡錦濤主席的政策,是因為我覺得這對于外國讀者了解真實的中國必不可少。
中國領導人的思維
用來減少誤解、減少曲解的一個有效的方法,就是讓外國人理解中國領導人的思維。我試圖讓中國領導人更加透明,想法和態度更易理解,以幫助外國讀者了解中國領導人面臨的挑戰和作出的決定。事實上,在中國,胡錦濤主席被認為是智慧、謙遜、高尚、正直的人,并始終致力于維持穩定,推進改革和建設中國。
我曾有幸訪問中國22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的35個城市,訪問很多當地領導(包括黨、政、商、學術界)以及普通民眾(農民、學生、軍人、工人、外來民工、下崗職工、退休人員、記者和警察等)。在這些旅行中,城市之間往往相隔五六個小時車程,這給我提供了豐富的資源,得以親身體驗當地正在發生著什么,人民、領導和普通民眾在說些什么。我了解了不同的省市面臨的不同問題,以及處理這些問題的不同方法。真實的中國,比許多外國人籠統簡單的看法要復雜得多。
我在行程中發現了共鳴也發現了雜音,兩者組成了一個真實的中國。我目睹中國為對付嚴重的系統性問題所作的多方面努力——經濟差距的擴大、失業、外來民工、腐敗、犯罪、脆弱的金融系統、能源制約、不可持續發展、環境污染、思想信念動搖、道德和家庭觀念的改變等等。有些問題產生于經濟急速增長,有些問題產生于向市場經濟的快速過渡,還有的是出于深化經濟、社會和政治改革的需要。
2006年,我見到了當時的浙江省委書記習近平,盡管我們到訪突然,他還是優雅豁達地向我們提出了如何向世界傳播中國的建議。習近平表示,外國人總是試圖用一句話來描述中國的特點,或用一種方法來壓縮概括中國,而實際的中國要復雜的多。他用盲人摸象來形象地比喻這個問題:“一個盲人摸到了大象的腿,便說大象像一個柱子;另一個盲人摸到大象的背,便說大象像一堵墻,沒人能說出大象的真實面貌,是因為他們沒人摸到了大象的全部,也就沒能獲得大象的全貌。”他還解釋說,這個比喻非常適合中國——一個沿海和內陸經濟差距巨大、擁有56個民族的國家。“中國是個多樣性的國家,那些只呆在東部的人就如同只觸摸到大象鼻子的盲人,而只呆在西部的人又如同只摸到大象背部的盲人。”習近平建議我既要橫向地研究中國不同地區的情況,又要縱向地研究中國的發展歷史。在當時我并不能理解,但在我的新書中,這兩種方式都有了表述:既采用了橫向方法(橫跨各個行業和地域),又嵌入了垂直方法,以洞察中國領導人的想法。
我的兩個目標是,追溯有關中國“創傷”和“變革”的不朽故事,并了解中國幾代領導人決策背后蘊含的動機和機制。對于給予我信任的受訪者,我感到很榮幸,他們中有些人對這些問題從未公開發表過看法,即使對中國媒體也沒有。
我曾公開重復過政治局委員、中宣部部長劉云山的話,他曾告訴過我:“純粹的事實講述著中國的故事。誠信和務實可以把真實的中國講得最好。美化是無益的,真實生活的描述和例證才算數。傳達受訪者真實的語言,挖掘其生活經歷,揭示其內心想法。這樣,才能捕捉到真實的中國。”
“要了解我們為振興中華所作的奉獻,必須了解中國人民為其輝煌的古代文明而擁有的自豪。”中國國家副主席習近平說道:“這是歷史的動力,今天激勵著人民建設國家。中國人民為世界文明作出了巨大貢獻,并享有過長期的繁榮。”他說道:“而后我們的民族遭受了百年軟弱、壓迫和屈辱。因此我們有巨大的自發動力來建設國家。我們的信念和決心植根于我們的歷史和民族自豪感。”
習近平曾反復強調,中國不應為目前取得的成就而沾沾自喜。他說:“相對于我們的漫長歷史,我們的發展速度并不那么驚人,我們花了幾千年才到達今天的水平。我們需要相對地看待自己。”他強調:“但不管怎樣,中國的發展,至少部分地是由民族自豪感和愛國情緒所驅動。”
2006年,在思考中國領導人的責任感時,當時的浙江省委書記習近平說,盡管經過了近30年的改革開放,“公平地說我們是取得了還算不錯的成績”,但是“我們應該對取得的成就做謹慎的評價”。習近平告訴我,中國領導人不會滿足于現狀:“我們決不能高估成就,或沉迷于成就”,他呼吁中國要向下一個更高的目標進發,要認識到“我們現在所處位置和我們必需到達位置之間的差距”,他形容這是一個“持續、不懈的進程”。
政治局委員、中組部部長李源潮強調,正是中國的民族精神,激發人們不斷向前看,爭取更大的進步。“雖然中國人不像西方人那么富有,而且在諸如科技、社會制度和環境保護等很多方面落后于西方國家。”李源潮說道:“我相信中國人民整體來說對國家的發展抱有積極的態度,對未來充滿信心。”
如何真實地傳達中國
2009年,政治局委員、中宣部部長劉云山表示,當前“中國的一項緊迫的戰略任務是使中國的交流溝通能力和中國的國際地位相符。在當今時代,誰獲得了一流的溝通技能和強大的交際能力,誰的文化和價值觀就能被更廣泛地傳播開來,誰就能更有效地影響世界”。
中國領導人認識到了中國形象在經濟政治意義上的緊迫性,他們認為西方,特別是西方媒體過度簡化甚至蓄意歪曲事實。劉部長表示將會增強中國媒體的國內外影響力。
中央電視臺臺長焦利表示,和西方媒體相比,中國媒體相對薄弱,大大低于中國在經濟和國際事務中相對強勁的地位。焦利就任中央電視臺臺長后不久,為中央電視臺設立了宏偉目標,不僅要繼續廣泛開展在國內的發展,包括改版央視新聞節目,還要創新發展形式,成為一個國際媒體公司。“中國必須在全球思想市場上充滿信心地競爭。”焦利這樣說道。
許多中國領導人曾要我坦率地告訴他們,為什么中國的形象在許多美國人眼里不是那么好。我列出一系列理由,這些理由強化了美國視中國為競爭者和可能的對手的擔心。我一開始就說,盡管大家都承認國家以自己最高利益為行為準則,但許多美國人認為中國為自己利益,不惜損害別人。
具體描述如下:中國是一個經濟掠食者,靠使用廉價勞動力和剝削勞工來壓低價格、搶奪美國人的工作,靠人為貶低貨幣價值來消滅競爭;中國支持能源富有的流氓政權,損害國際安全(因為中國想獲取其資源,并向其出售武器來削弱美國);中國是一個專制的社會,司法制度嚴厲,沒有新聞自由;中國社會呆板機械,像機器人一樣的政府官員只會鸚鵡學舌,他們只關心增強國力,卻不幫助人民;還有,中國有擴張野心,想把勢力擴張到國界以外。
中國的官員們傾向于用國情差異來回應彼此理解的隔閡。政府為改變外國人看法的那些想法有時候未免天真(比如說,希望通過在美國發行一款商業雜志來改善中國形象的提議,在我看來,難免適得其反)。

繁華的上海陸家嘴,代表了中國沿海現代化的一面,實際上,庫恩認為,真實的中國要復雜得多。
然而有些時候,批評會激發自我反省。有些領導人承認“有些問題是我們的錯,我們中國人需要學會如何和國外交流,介紹我們真實情況”。
有些領導人也指出中國官員不善于運用幽默,用自謙的玩笑或是輕松的手法處理嚴肅的問題,對很多人來說并不是那么自然。
國新辦主任王晨建議采取以下實際措施:盡早發布權威信息,否則謠言機器就會開始旋轉(如危險性產品);加強和國外主流媒體的交流,邀請更多的管理人員、編輯、記者和主持人來中國;增強中國自身媒體的能力;擴大與其他國家的跨文化活動;對于人權、民主或宗教事務的負面報道,中國應積極進行正面報道,如頒布新的人權法案。
中國的國際形象在2008年得到檢驗。4月份,當中國期盼著奧運會的到來時,奧運會火炬的傳遞在幾個國家遭到抗議甚至攻擊而中斷,起因是西方認為中國對西藏抗議進行了鎮壓,而中國政府說這只是西方媒體的偏見報道和錯誤煽動。
中央文獻研究室主任冷溶,同時也是我的一位老友,在西方國家的抗議活動發生后不久告訴我:“這是一場核心利益的斗爭。”他說道:“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中國的崛起,打亂了世界力量的平衡,是一種文明的沖突。”但他緊接著又說:“然而這種沖突也不是非有不可。”
冷溶說,對火炬傳遞的抗議“并沒有嚇著我們。我們肯定會翻過這一頁,它不會影響我們和其他國家的交往”。然而,他又補充道,反對者提醒了“我們需要改進對外宣傳”——“達賴喇嘛最大的優勢在于能講一口流利的英語……同時,達賴了解西方文化和價值觀,因此容易溝通,而這正是中國的弱點。”
新聞出版總署署長柳斌杰表示,中國已從這些事件中吸取了教訓。在拉薩騷亂后他表示:“禁止外國記者盡早進入西藏是錯誤的,這在全世界引起了誤解。盡管我們盡力澄清事實說明真相。”他補充道:“因為他們不了解到底西藏發生了什么,謠言自然到處播散。”
當時柳斌杰正隨同一位中國高層領導人在國外考察。“當我們把國外同仁的報道與我們知道的情況作了比較后”,他回憶說:“才發現他們歪曲了真實情況,他們對真相一無所知。我們才認識到進一步深化對外開放的迫切需要,這是個深刻的教訓。”
不久之后,當汶川地震發生后,中國政府采取了相反的做法,對外國記者開放該地區。中宣部部長劉云山指出,在特定時期,我們讓外國媒體撤離震區,他強調,這是出于對堰塞湖可能決堤的擔心,或者埋在瓦礫下的腐爛尸體可能造成流行病的擔憂。“對于那些有危險的地方,我們不僅疏散記者,也疏散當地人。對此我們沒有掩蓋真相,我們對每個人的安全負責。”
采取更為開放的做法后,柳斌杰說道,“國際報道地震的信息是準確的。為什么國外媒體在地震方面信任中國,而在西藏騷亂問題上則不這樣?”“透明度!如果我們公開化,在事情一發生就讓外國記者進入西藏,并報道騷亂的第一手材料,我想他們中的大多數都能明辨是非。我相信,信任來自于透明度。”
中國有誠意將這些理念投入實踐的一個標志是,在奧運會之后,中國政府宣布官方認可的外國記者可以在國內其他地區旅行,而不再像2007年以前一樣,需要提前申請。劉云山部長說道:“我們希望更多的記者來到中國,而不是更少。”
對于火炬傳遞事件回應最妙的也許是中國國家副主席習近平了,當時習近平正在訪問卡塔爾,聽到消息他告訴一幫隨行香港記者:“我們不能過于擔心人們是否喜歡在北京舉辦奧運會這件事,世界是個熱鬧的大舞臺,臺上什么人都有。鳥籠子大了,什么鳥都有。如果我們驅逐最能叫喚的鳥兒,那么籠子將不再是個熱鬧的地方……”
這種對有爭議的事輕松自信的回應,反映出新一代中國領導人的理念,這對于未來來說,未嘗不是個好兆頭。

作者名片:羅伯特·勞倫斯·庫恩,傳媒和娛樂公司國際管理集團(IMG)的高級合伙人,美國庫恩基金會董事長,克萊蒙大學研究生院理事,美國科學促進會科學自由和責任分會會員,北京前沿科學研究所副理事長。自1989年起,庫恩就在重組、并購、經濟政策、產業政策、科技、媒體、文化、中美關系、外交事務和國際傳播等方面向中國政府提供咨詢。他致力于向世界講述真實的中國,尤其關注中國的改革開放。他是第一位對胡錦濤總書記“科學發展觀”進行專題講演的外國人,他認為“科學發展觀”是解決復雜多樣的經濟、環境、杜會和政治問題的綜合解決方案。
(本文摘自庫恩在“21世紀論壇”2010會議上的演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