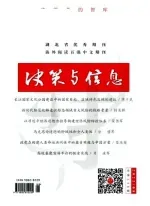新五年看中國方位:科學發展強國富民
文/丁偉 劉曉鵬 張音
新五年看中國方位:科學發展強國富民
文/丁偉 劉曉鵬 張音

過去的五年,極不平凡。經過五年努力奮斗,我國社會生產力快速發展,綜合國力大幅提升,人民生活明顯改善,國際地位和影響力顯著提高,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以及生態文明建設和黨的建設取得重大進展。
從今年開始,我們已進入“十二五”時期。“十二五”時期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是深化改革開放、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攻堅時期。
五年一個刻度,中國躍上新的臺階;五年一個單元,中國站在新的起點。此時此刻,國內外眾多探詢的目光再次聚焦北京。新五年,中國的面貌會有哪些改變?人民的生活會有怎樣的變化?為完成這些改變、達成這些變化,中國又將作出什么部署和調整?
“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取得重大進展,城鄉居民收入普遍較快增加,社會建設明顯加強,改革開放不斷深化”——十七屆五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為新五年的中國勾勒出一幅科學發展、國強民富的路線圖。
一個主題:科學發展
“一個巨變、四個不變”,是判斷中國走向的邏輯起點,也是制定“十二五”規劃的時代背景。
2010年10月23日,在韓國慶州舉行的二十國集團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改革達成協議,超過6%的投票權將從歐洲發達國家轉向新興經濟體及發展中國家,金磚四國晉升十個股東行列,中國的份額升至第三位。國際輿論評價說,這是一次歷史性大改革,股權結構的變化預示著國際經濟秩序的調整。
新中國成立60多年,大致以5年為一個刻度,中國不斷躍上新臺階。特別是改革開放30多年,國家面貌天翻地覆。
過去的“十一五”,同樣是一個濃墨重彩的“歷史單元”。
縱向看,這是中國發展史上極不平凡的五年。抗擊頻仍的重大自然災害,經濟保持平穩較快發展。2006年~2009年,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11.4%,比“十五”時期年均增速快1.6個百分點。2010年前三個季度,中國經濟又實現了10.6%的增長。
橫向看,這是國際地位和影響力顯著提高的五年。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嚴重沖擊,在世界率先實現回升向好,經濟總量繼超過德國之后,2010年超過日本。中國“體量”舉足輕重,中國“動向”舉世矚目。
這個時候,關于中國的未來走向,國內外有各種各樣的議論和估量。有人說,作為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已經不是發展中國家。有人問,國際形勢復雜多變,21世紀頭20年戰略機遇期的判斷是否還成立?
中國的方位到底在哪里?這是一個重大的認識問題,也是一個重大的戰略問題。
“繼續抓住和用好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促進經濟長期平穩較快發展”——《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作出堅定的回答。
這份堅定,源自對天下大勢的清醒判斷。經過幾十年飛速發展,中國發生了巨大變化,但基本國情沒有變,社會主要矛盾沒有變,發展中國家的屬性沒有變。同時,國內外環境總體上有利于發展,中國仍處于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的態勢沒有變。這“一個巨變、四個不變”,是判斷中國走向的邏輯起點,也是制定“十二五”規劃的時代背景。
“一個巨變”告訴我們,經過改革開放的探索和實踐,中國找到了實現現代化的正確道路,今后還要沿著這條道路堅定地走下去。
“四個不變”催促我們,作為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發展中大國,發展是解決所有問題的“總開關”,必須抓住難得的歷史機遇奮發有為。
對一個國家的發展和振興來說,機遇并不常有,機遇來之不易,機遇稍縱即逝。21世紀的頭一個10年,我們抓住了重要戰略機遇期,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舉世公認的巨大成就。21世紀第二個10年是前10年戰略機遇期的直接延續。第二個10年,中國將建成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國際地位也將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這雙重歷史使命,注定中國要發展,中國要大發展。
發展是硬道理,“硬發展”沒道理。這些年來,一輪輪經濟的過熱與過冷,一次次自然的施威與重創,考驗著中國的綜合國力和中華民族的承受能力,也促使我們重新思考質與量、快與好、物與人、人與自然的關系,不斷調整前進的航向。
人們不會忘記,2003年在抗擊非典疫情等一系列事件之后,中國上下對于發展問題的思考。就在那一年,科學發展觀的提出,讓人們對發展這個時代課題有了全新的認識。
2003年10月,十六屆三中全會第一次在黨的正式文件中完整地提出了科學發展觀,要求“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此后的幾年,科學發展觀的認識不斷深化,內涵不斷豐富。
2005年,“十一五”規劃明確提出,要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2007年,科學發展觀作為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堅持和貫徹的重大戰略思想寫入黨章。此后,按照十七大的戰略部署,從2008年9月到2010年2月底,全黨開展了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科學發展的理念日漸深入人心。
“在當代中國,堅持發展是硬道理的本質要求,就是堅持科學發展”——“十二五”規劃建議明確把科學發展作為主題,第一次在五年規劃中明確提出來,標志著對中國發展規律的認識進一步升華。
從“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取得重大進展”、“城鄉居民收入普遍較快增加”到“抵御風險能力顯著提高”,從“把擴大消費需求作為擴大內需的戰略重點”、“合理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到“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規劃對“十二五”的目標設計、戰略部署,貫穿著科學發展理念。
一個主線:轉變方式
繼30多年前的歷史性轉折后,再一次作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大抉擇,由此開啟由大國通向強國的大門。
在當代中國,5年這個時間刻度似乎具有特別的意義。人們習慣用5年來丈量既往,用5年來謀劃未來。于是,5年便成為一個相對獨立的“歷史單元”,成為衡量共和國發展與進步的標尺。
1956年,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毛澤東曾急切地說:“現在我們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壺茶碗,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面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
54年后,“十一五”結束時,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一汽車生產和消費大國,大飛機的研制取得重大進展,翱翔藍天為時不遠。工業和信息化部的統計顯示,全世界大概500種工業產品中,220多種產品產量的“世界第一”屬于中國。
放在以往,這樣的消息肯定會讓人熱血沸騰,而經歷了一個快速發展的階段后,當不全面、不協調、不可持續等問題日益凸現出來,中國人開始用科學發展的眼光冷靜、審慎地看待這些“世界第一”。
同樣耐人尋味的是,當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的消息傳出,與國際輿論鋪天蓋地的熱議相反,中國的反映相當低調。在例行的記者會上,外交部發言人表示,中國的經濟總量看上去較大,但仍是發展中國家,中國的外交政策不會因為GDP的增長改變。
這不是故作低調,而是實話實說。清華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教授劉江永分析,在日本的GDP構成中,個人消費占近六成,而中國的經濟增長主要靠投資和進出口拉動。日本近六成出口為高附加值產品,而中國出口產品相當部分是加工貿易,“設計和利潤留在歐美日,意義有限的GDP和能耗留在中國”。
高速奔跑了30多年后,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舉足輕重的經濟大國,國家現代化“賽程過半”。同時,資源環境約束強化,投資消費嚴重失衡,收入分配差距較大,自主創新能力不強……長期以來行之有效的發展方式面臨挑戰。國際金融危機沖擊下,發展方式的弊端更是暴露無遺,而發達國家意圖在“后危機時代”搶占發展制高點的戰略布局,向中國發出了一個強烈的信號:不加快轉變發展方式,就不能從大國變為強國,也就很難走完現代化的“后半程”。
近年來,從“十一五”規劃提出“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到十七大提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再到2009年底經濟工作會議作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已刻不容緩”的重要判斷,黨中央不斷發出“加快轉變”的號令。
“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十二五”規劃建議又作出了新論斷,提出了新要求。
擴大內需提升到戰略位置;逐步完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培育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第一次在五年規劃中用一個專門章節部署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提出推動文化產業成為國民經濟支柱性產業……細讀規劃建議,會發現“轉變”的主線“貫穿經濟社會發展全過程和各領域”。
轉變發展方式是一場深刻變革,關系現代化建設全局,涉及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建設的方方面面。對此,規劃建議作出了全面部署:堅持把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作為主攻方向,堅持把科技進步和創新作為重要支撐,堅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為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堅持把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作為重要著力點,堅持把改革開放作為強大動力。這“五個堅持”,是一個由導向機制、協調機制、實現機制、操作機制和動力機制所構成的系統工程,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指明了方向和路徑。

30多年前,中國選擇了改革開放,由此演繹出一段世界發展史上罕見的時代傳奇。今天,面對現代化之路上的又一個十字路口,中國堅定地選擇轉變發展方式,站在新的臺階上開啟了由大國通向強國的大門。英國《每日電訊報》評價說,這一轉變有可能繼中國30多年前推行改革開放政策之后,再一次讓中國的發展釋放出更大的活力,影響將遠遠超過5年的范圍。
一個重點:改善民生
順應人民新期待,努力實現居民收入增長與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強國”與“富民”同步部署、同步推進。
再大的數字除以十三億,也會變成一個很小的數目;再小的問題乘以十三億,也會變成很大的難題。簡單的數學計算,對擁有十三億人口的中國國情作出了透徹的解答。
一組數據擺在面前:2010年第二季度,中國的GDP總量達到1.33萬億美元,當季超過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人均GDP不到4000美元,尚不及日本的1/10;人均收入約3600美元,排在世界100位之后。世界各國現代化的歷史證明,當人均GDP達到3000美元門檻后,既是一個黃金發展期,也是一個矛盾凸顯期。一方面,國家財富和國民財富已經積累到一定程度,必然帶來物質和精神的更高需求,經濟發展空間尚大。另一方面,如果不及時調整經濟結構和收入分配制度,就有可能陷入增長乏力、矛盾激化的“中等收入陷阱”,甚至影響社會穩定,阻滯現代化進程。
一個事實無法回避:經過多年發展,中國的綜合國力空前躍升,城鄉居民收入大幅提高,人民生活顯著改善。與此同時,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社會建設相對滯后,社會問題明顯增多,“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
正視問題方能找到應對之策。近年來,民生問題被擺在前所未有的高度,社會建設步伐加快,民生改善收效明顯。“十一五”期間,農業稅徹底取消,幾千年來農民交納“皇糧國稅”成為歷史;真正免費的義務教育全面實行;全國23%的縣啟動新型農村養老保險試點……一項項惠民政策的出臺,一個個民生工程的實施,以及汶川、玉樹等一次次天塌地陷中的不拋棄、不放棄,讓“科學發展”、“以人為本”、“生命至上”等等帶著溫度的詞匯,烙刻在每一個中國人的心中。
順應人民過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十二五”規劃建議強調更加注重以人為本,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這兩個“更加注重”,與更加注重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更加注重統籌兼顧一起,闡釋了科學發展的基本原則,表明社會事業和問題民生將被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要通過發展經濟,把“蛋糕”做大,也要通過收入分配制度的調整把“蛋糕”切好。規劃建議提出合理調整收入分配關系,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低收入者收入明顯增加,中等收入群體持續擴大,貧困人口顯著減少”。
一個國家財富分配的方式,不僅關系經濟發展,而且關系社會公平正義。收入分配制度的調整,將是一個復雜的利益博弈和社會變革的過程,既要量力而行,也要以更大的決心和勇氣盡力而為。規劃建議強調全面推進各領域改革,“增強公共政策制定透明度和公眾參與度”,讓人民創造的財富更好地為人民造福,讓人民賦予的權力更多地為人民謀利。
“這是一個民生色彩最濃重的五年規劃”,“‘十二五’時期,中國將走向‘民富時代’”……五中全會后,“轉變方式”、“關注民生”、“從‘國富’到‘民富’”等詞語頻頻出現在眾多外國媒體上,成為觀察中國走向的關鍵詞。
實際上,“國強”與“民富”本來就是一體兩面、不可分割的。細讀規劃建議,人們發現,科學發展的理念浸潤其中,對“國強”與“民富”的追求交融在一起。擴大內需戰略中,突出了“建立擴大消費需求的長效機制”,一方面是出于經濟發展的需要,一方面又是為了擴大就業、增加收入;加快新農村建設中,重點在工業化、城鎮化深入發展中同步推進農業現代化,同時拓寬農民增收渠道,改善農村公共服務;促進區域協調發展中,提出實施區域發展總體戰略和主體功能區戰略,同時又要把符合落戶條件的農業轉移人口逐步轉為城鎮居民,在制度上保障農民工權益……透過規劃建議的字里行間,我們看到了“物”,更看到了“人”,看到了物與人的有機統一、“國強”與“民富”的內在一致。
因此,“十二五”規劃將是一個“強國”的規劃,也是一個“富民”的規劃,“強國”與“富民”同步部署、同步推進。
說到底,中國共產黨自成立的那一天起,就將國強民富的使命擔在肩上,把國家富強、人民富裕作為矢志不渝的奮斗目標。正是由于政黨信念與國家發展、人民命運高度統一,億萬中華兒女始終跟定共產黨,與祖國風雨同舟、休戚與共。也正因為如此,國強民富始終是當代中國的時代強音,并將穿越中國現代化的歷史進程。當下,一段新的征程正拉開帷幕。
2011年,“十二五”開局之年,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辛亥革命100周年。這三個時間節點疊加在一起,分明讓人感到天地轉、時光迫、只爭朝夕。
“十二五”是關鍵時期,也是攻堅時期。五年以后,再度回眸,綜合國力必將躍上一個更大臺階,人民生活水平必將得到明顯改善,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必將打下具有決定意義的基礎……
一個決策:結構調整
結構調整是一個充滿挑戰的艱難命題,不免要帶來短期增長的“陣痛”;結構調整又是一個刻不容緩的戰略抉擇,它關系到中國經濟社會長遠發展的基石。
回首過往,結構調整的成績單令人欣喜。
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經濟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不僅經濟總量迅速擴大,經濟結構也不斷優化。尤其是“十一五”期間,盡管國際金融危機沖擊和罕見重大自然災害輪番襲來,“保增長”壓力前所未有,神州大地奮力調結構的步伐卻一刻也沒有停歇。
數字清晰反映出“十一五”經濟結構之變:2007年,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第一次超過投資,成為拉動國民經濟“三駕馬車”之首;2009年,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由“十五”末的50.7%上升到52.5%。三次產業結構更加合理,當年中國第三產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由“十五”末的40.3%上升為43.4%。西部大開發、東北振興、中部崛起等宏大戰略向縱深推進,西部地區經濟增速連續3年高于東部,區域經濟發展格局均衡性進一步提高。
瞻望未來,結構調整之路依然道遠任重。
多年的高速發展,我們也付出了很大代價,經濟運行中的結構性矛盾長期累積,發展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問題日漸顯現。中國經濟增長主要依賴投資、外需拉動,內需不足,消費不旺,經濟增長的動力結構不合理,從而影響了經濟的穩定性。從產業結構看,農業基礎薄弱、工業大而不強、服務業發展滯后,也制約了經濟整體素質的提高。
一個焦點:引擎內需
未來5年,應當尋求投資與消費的結合點,以投資帶消費,以消費促投資,把擴大投資和增就業、惠民生有機交融,創造更多最終需求,以期達到事半功倍之效
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既緣于世界經濟大變革的不可逆潮流,更緣于中國經濟發展現階段的內在要求。
本輪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后,世界經濟呈現了一些新趨勢,對中國出口導向型產業的發展帶來壓力和挑戰,但同時也成為中國發力加快結構調整的重要契機。外需易受許多不可預料和突發因素的影響,通過挖掘內需的巨大潛力,破解制約擴內需的體制機制障礙,形成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經濟增長新格局,未來的經濟發展就能更加主動,更加穩定。
擴大內需,重點在于消費需求。建立擴大消費需求的長效機制,需實施更積極的就業政策,增加就業創業機會,為居民開辟更多收入之“源”;需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合理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城鄉中低居民收入,讓百姓消費更有底氣;需擴大社會保障制度覆蓋面,逐步完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改善消費預期。此外,還應加強市場流通體系建設,優化消費環境,促進消費結構升級。
從國際經驗來看,人均GDP達到3000美元后,居民消費將進入加速升級的黃金階段。目前,中國人均GDP已超過3500美元,消費潛能處于快速釋放期。近年來,住房、汽車、數碼產品、旅游休閑、文化娛樂等不斷引發新的消費風潮。盡管以消費為主導的格局尚未形成,但伴隨國民經濟增長和居民消費水平穩步提高,以及社保體制的不斷完善,國內需求尤其是消費需求拉動經濟增長的力量將越來越強。
進入“十二五”,需要大量投資建設的基礎設施和基礎產業將趨于完備,因此,盡管投資的絕對數量不會降低,但投資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會相對下降。“十二五”時期的投資將更多地體現在結構優化上。這既包括投資的產業結構調整,為解決農業基礎薄弱、工業大而不強、服務業發展相對滯后,需加大對“三農”、自主創新和先進制造業、服務業的投資;也包括投資的地區結構調整,對中西部和東北地區等注入的投資量相對較多,以改變地區之間經濟發展不平衡的格局。
在內需構成中,投資與消費并非簡單的此消彼長關系。投資需求與消費需求密切相關,二者完全可以良性循環。因此,未來5年,應當尋求投資與消費的結合點,以投資帶消費,以消費促投資,把擴大投資和增就業、惠民生有機交融,創造更多最終需求,以期達到事半功倍之效。
一個目標:撐起產業
一個國家的現代產業體系,最能體現核心競爭力,是撐起整個經濟肌體的“筋骨”。
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道路,適應國際需求結構調整和國內消費升級新變局,順應技術進步新趨勢,發揮我國產業在全球經濟中的比較優勢,發展結構均衡、組織合理、布局優化、技術先進、清潔安全、附加值高、吸納就業能力強的現代產業體系——“十二五”規劃建議勾勒出未來中國經濟的一條發展路徑。
當前,全球消費市場正在向節能、環保、低碳和智能化等方向發展,新技術、新創意刺激著新的消費熱點不斷涌現。主動應變,才能贏得廣闊市場空間。
補足產業結構中的“短板”,是提高中國經濟競爭力的關鍵。目前,在長長的國際分工鏈條中,中國仍處于收益較低的加工裝配中心的位次,技術裝備和重要零部件的生產能力還比較弱,大量關鍵技術依賴外部支持。大力發展這些“短板”行業和產品,當是產業結構升級的重頭戲。
戰略性新興產業在發展初期,離不開外部條件的有力支撐。制定新興產業發展規劃,完善對其有利的稅收政策,加大政府采購對新興產業自主創新的支持力度,加強金融機構對新興產業的傾斜……多管齊下,將弱嫩的“幼苗”盡快培育成國民經濟的支柱。
服務業的跨越式發展,也是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戰略重點。“十二五”期間,第三產業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將顯著增強。生活質量高了,對三產的發展會產生更多需求,其中,提高生產效率的生產性服務業和滿足人們精神消費的文化創意產業將獲得快速騰躍。發展水平較高的大城市和東部地區,完全有條件形成以服務經濟為主體的產業結構,其他地區的服務業發展也有很大余地。
專家指出,在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進程中,應更加注重發揮市場的基礎性作用,引導企業主動調結構、促升級,讓競爭壓力成為助推產業升級的持續動力,引導社會資本流向有發展前景的高技術產業。政府的職責,則是通過深化改革,進一步完善市場經濟體制,使市場的調節功能充分發揮作用,并彌補市場機制的不足。
“十二五”規劃建議提出,要“堅持把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主攻方向”,“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取得重大進展”,這一定位和航標,給新起點上的中國經濟華麗轉身賦予了深遠內涵,也吹響了“十二五”結構調整攻堅戰的嘹亮號角。
一個個光輝燦爛的前景在向我們招手。一道道考題,等著我們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