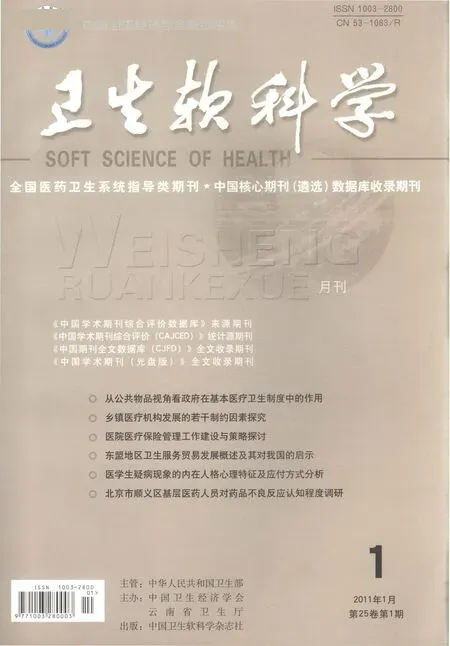大學生負性生活事件與心理安全感的關系研究
黃 妍 ,汪海彬
(1.安徽師范大學心理學系,安徽 蕪湖 241000;2.上海師范大學教育學院,上海 200234)
1 問題提出
安全感指的是“一種從恐懼和焦慮中脫離出來的信心、安全和自由的感覺,特別是滿足一個人現在(和將來)各種需要的感覺”,并且在馬斯洛提出的心理健康標準中,第一條就是個體要“有充分的安全感”[1]。也有人認為心理安全感是對可能出現的對身體或心理的危險或風險的預感,以及個體在應對處置時的有力、無力感,主要表現為確定感和可控制感,并在此基礎上編制了心理安全感量表(SQ)[2]。
自 30 年代 H.Selye提出應激的概念以來,生活事件作為一種心理社會應激源對身心健康的影響引起了廣泛的關注[3]。而這種心理社會應激源勢必會對“滿足一個人現在(和將來)各種需要的感覺”產生影響,勢必會影響個體的應對處置時的有力無力感。盡管心理安全感在心理健康教育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縱觀國內以往關于心理安全感的影響因素研究,更多只在人口學變量上徘徊,并未對安全感和生活事件的關系進行探討,本文旨在了解大學生的心理安全感和生活事件之間的關系,為維護大學生的心理健康作參考。
2 研究方法
2.1 被試
本研究的被試來自大學一年級至四年級學生,發放問卷400份,剔除無效問卷后,得到有效問卷354份。其中男生106人,女生248人;城鎮156人,農村198人。
2.2 研究工具
2.2.1 安全感量表(SQ)
由叢中、安莉娟2004年編制的安全感量表[4]。該量表共有16個題目,采用5級評分,從人際安全感和確定控制感兩個維度來考察安全感,人際安全感主要反映個體對于人際交往過程中的安全體驗。確定控制感,主要反映個體對于生活的預測和確定感、控制感。
2.2.2 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ASLEC)
本研究選用劉賢臣等(1987)編制的青少年自評生活事件量表,共26個項目,由26項可能給青少年帶來心理反應的負性生活事件構成,適用于青少年尤其是中學生和大學生生活事件發生頻度和應激強度的評定。對每個事件的回答方式應先確定該事件在限定時間內是否發生,如果發生過則根據事件發生時的心理感受分5級評定,即無影響(1)、輕度影響(2)、中度影響(3)、重度影響(4)或極重影響(5)。該量表分為人際關系、學習壓力、受懲罰、喪失、健康適應和其他共六個因子[5]。
2.3 數據分析
數據采用SPSS15.0統計軟件包進行相關回歸分析。
3 結果與分析
3.1 大學生生活事件與心理安全感的相關回歸分析
使用 pearson相關,對大學生活事件和心理安全感進行多種維度的相關分析,并用雙側檢驗進行顯著性檢驗。結果顯示生活事件總應激量與心理安全感總分有顯著相關(P<0.01)。人際關系、受懲罰和健康適應與心理安全感之間均存在顯著負相關(P<0.01或P<0.05),學習壓力和喪失因子與人際安全感存在顯著負相關(P<0.01或P<0.05),但與確定控制感相關不顯著;其他因素與確定控制感之間存在比較顯著的負相關(P<0.01或P<0.05),但與人際安全感相關不顯著。心理安全感總分與生活事件各因子之間也存在顯著的相關(P<0.01或P<0.05)。這一結果顯示生活事件對大學生心理安全感有重要影響,這種影響主要來自人際關系、受懲罰和健康適應等因素,見表1。

表1 大學生心理安全感與生活事件的相關矩陣(r)
3.2 大學生生生活事件對心理安全感及各因子的回歸分析
3.2.1 大學生生活事件對人際安全感的回歸分析
利用逐步回歸的分析方法,以生活事件各因子作為自變量,心理安全感中人際安全感因子作為因變量進行逐步回歸分析。進入回歸方程的有受懲罰、健康適應和其他因素,結果顯示,受懲罰、健康適應和其他因素能夠預測人際安全感。而其他因子沒有進入回歸方程,說明其對人際安全感沒有預測作用。模型對安全感的解釋率為10.1%(R2=0.101),具備一定的預測作用,見表2。
3.2.2 大學生生活事件對確定控制感的回歸分析

表2 大學生生活事件對人際安全感的回歸分析
利用逐步回歸的分析方法,以生活事件各因子作為自變量,心理安全感中確定控制感因子作為因變量進行多元回歸分析。進入回歸方程僅有人際關系(Bata=-1.716,P=0.001),結果顯示模型對確定控制感的解釋率比較低,僅為3.1%(R2=0.031)。
3.2.3 大學生生活事件對心理安全感總分的回歸分析
利用逐步回歸的分析方法,以以生活事件各因子作為自變量,安全感總分作為因變量進行逐步回歸分析。進入回歸方程的僅有總應激量(Bata=-0.233,P<0.001),結果顯示負性生活事件總應激量對心理安全感得分的預測作用顯著,但從對因變量的貢獻程度上來看,模型對心理安全感總分的解釋率比較低,僅為 5.4%(R2=0.054)。
4 討論
4.1 大學生生活事件與心理安全感的關系分析
關于生活事件與心理安全感之間的關系,以往的研究并未涉及,因此不具有可比性。從生活事件的各因子與心理安全感各維度的關系分析來看,由于只考察了負性生活事件與大學生心理安全感的關系,各因子與心理安全感各維度之間均呈負相關,并且生活事件總應激量及各因子除其他因素外,均與人際安全感存在顯著的負相關;生活事件總應激量及各因子除人際關系和喪失因子外,均與確定控制感存在顯著的負相關;生活事件總應激量及各因子均與安全感總分存在顯著的負相關。其中與心理安全感關系最密切的因素是健康適應因子,可見在大學生活里,由于大學生長期遠離家庭而不能團聚,面對生活中的各種壓力都需要大學生獨自面對和承擔,而不像以前可以由父母幫忙或代為解決,這造成了大學生產生不確定感、缺乏控制感,從而導致心理安全感的降低;另一個與大學生心理安全感有密切聯系的生活事件因素是受懲罰因子,而生活事件量表中的這種受懲罰的因素主要來源于家庭壓力。這也折射出家庭教養對大學生心理安全感的重要影響,正如A I-Rihani,Su liman對12歲~15歲兒童進行了家庭教養與安全感的相關研究,經多元回歸分析,家庭教養方式對安全感的解釋達49%[6]。人們都希望自己被認同、被接納、被肯定,而經常受懲罰、遭到拒絕、否定的學生,對自我的認識會變得非常消極,在應對生活中的刺激時也會表現出較高的不確定感,這樣還會使他們以否定、拒絕的態度去對待他人,當然也無法獲得較高的人際安全感,這也就必然會導致大學生心理安全感的降低;此外人際關系這一因素也表現出與大學生心理安全感顯著的相關。大學生的生活重心已經轉向學校和社會群體,同伴關系在人際關系中顯得尤為重要。因此能否得到同齡人的認同與接納,能否與同伴保持良好的關系也是大學生心理安全感的重要來源,并且心理安全感其中一個維度即為人際安全感。
4.2 大學生生活事件對心理安全感的回歸分析
在生活事件對心理安全感及各維度的逐步回歸分析顯示,受懲罰、健康適應和其他因素對人際安全感的預測作用顯著,人際關系對確定控制感的預測作用顯著,而生活事件總應激量對心理安全感總分的預測作用也顯著,只是各自的對因變量的貢獻率都不是很高,分別為10.1%、3.1% 和5.4%。較低貢獻率說明了兩者之間有交叉但仍有著較多的空白,可能是因為心理安全感自身的屬性所決定的,因為目前國內并未專門對心理安全感的屬性作過研究,是否心理安全感既有特質屬性又有狀態屬性,人格特質使人們的心理安全感具有某種傾向性,而心理安全感會隨事件而有所波動,當前的生活事件只是影響當前的心理安全感水平,這有待進一步的研究。同時本研究選取的生活事件全部是負性的,這也可能是生活事件貢獻率不高的原因。
5 結論
本研究相關分析的結果表明,生活事件總應激量與心理安全感總分之間存在顯著的負相關,心理安全感總分與生活事件及各因子之間也存在顯著的負相關;多元回歸分析的結果表明,生活事件對心理安全感的回歸能夠解釋5.4%因變量的變異。
[1]Maslow AH.The dynamics of psychological security-insecurity[J].Character and Personality,1992,10:331.
[2]叢 中.安全感量表的初步編制及信度、效度檢驗[J].中國心理衛生雜志,2004,18(2):97-99.
[3]Seley,H.The stress concept.In L.L.Kutash, L.B.Schlesinger& Assoclastes,Handbook on stress and anxiety[J].San Francisco,Jossey-Bass,1980:135.
[4]中國行為醫學科學編輯委員會.行為醫學量表手冊[M].北京:中華醫學電子音像出社,2005:199-200.
[5]汪向東,王希林,馬 弘.心理衛生評定量表手冊 (增訂版)[M].北京:中國心理衛生雜志社,1999.
[6]AI-Rihani,Suliman.The effect of the family socialization pattern on children's feelings of security[J].1985,12(11):1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