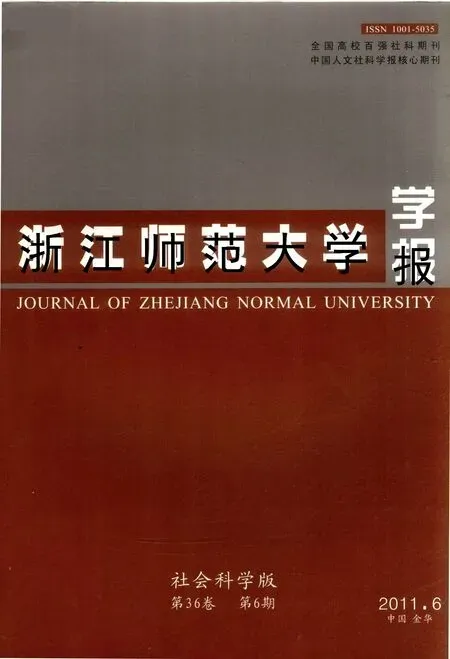《玉海》征引《史記正義》佚文考索
——宋人著作征引《史記正義》佚文考索之一
袁傳璋
(安徽師范大學 文學院,安徽 蕪湖 241000)
一、前 言
趙宋王朝以前學術價值最高的《史記》古注共有三家,即南朝劉宋裴骃的《史記集解》、李唐王朝司馬貞的《史記索隱》與張守節(jié)的《史記正義》,經宋人刊刻而流傳至今。裴骃以東晉徐廣校本為本,“采經傳百家并先儒之說”,又“時見微意”(《史記集解序》),為《史記》一百三十篇作注,仿魏何晏《論語集解》、晉杜預《春秋經傳集解》注例,隨文施注,取合本子注形式,合《史記》本文與裴氏注義為一體,為《史記集解》八十卷。前此,《史記》或有本無注,或有注無本;自裴骃書出,《史記》方有注本行世。裴氏本亦為后世所有注本所從出。宋太宗淳化五年(994)殿刻三史,《史記》即取《史記集解》八十卷為底本而析為一百三十卷。裴骃對《史記》的廣泛流行居功至偉。唐玄宗時成書的司馬貞《史記索隱》與張守節(jié)《史記正義》,均依傍裴骃《集解史記》,仿唐初陸德明《經典釋文》標字列句為注之例,各為三十卷,原不與《史記》本文相附而單本別行。
司馬貞“探求異聞,采摭典故……釋文演注,又重為述贊”(《史記索隱序》),于《史》義探尋頗多發(fā)明。其健于辯駁的文風又與宋人喜尚譏評的學風契合,故以“小司馬史記”名義與“小顏氏漢書”并稱而備受推崇。宋時不僅有多種單刻本《史記索隱》行世,而且南宋將《索隱》附刻于《集解》而成《史記集解索隱》者亦有數(shù)本,故《索隱》舊貌至今猶存。張守節(jié)涉學《史記》三十余年,“六籍九流地里蒼雅銳心觀采,評《史》《漢》詮眾訓釋而作《正義》”,索理允愜,引致旁通(《史記正義序》)。張氏自我期許甚高,然在宋代遠不及《索隱》之被推崇。筆者臆度宋時《正義》似無單刻本,仍以寫本形態(tài)在讀書界流通。司馬貞為弘文館學士,張守節(jié)為東宮諸王侍讀,生當同時略有后先,二人為《史記》作注的底本同為裴骃《集解》,征引資料文獻同出館閣秘書,雖各自為書,但為同一事典所作注文往往相同或相近。宋人合刻《史記》三家注時,以先刻行世的《史記集解索隱》為本注,而以《正義》為增注附刻,凡《正義》注義與《索隱》相同或相近者大都削而不錄。自《史記集解索隱正義合刻本》風行于世,單本《史記正義》遂漸次湮沒以至在中土失傳,明人已無緣復睹《正義》全貌。清代學者如四庫館臣錢大昕、錢泰吉、張文虎等,注意到《史記正義》遺佚嚴重的狀態(tài),并做過程度不同的探究,但總體成績并不理想。
《史記正義》大量遺佚亦引起了東瀛學者的關注。瀧川資言博士從1912年起,費二十余年之功,從日本公、私所藏多種《史記》古板本、古活字本《史記》鈔錄本(京都建仁寺兩足院藏幻云手澤《幻云史記鈔》)欄外標注發(fā)現(xiàn)一千余條《正義》佚文,手輯《史記正義佚存》二卷,將其散入《史記會注考證》相應《史》文之下。1935年《史記會注考證》十冊出齊,瀧川自謂“略復張氏之舊”,讀《史》者亦盛贊其便。但瀧川輯得的《正義》佚文均未注明出處,故遭到了以程金造先生為代表的大陸學人的質疑,認為十之八九出自日人偽托,以致半個多世紀以來,在司馬遷與《史記》研究中,對瀧川輯得的一千余條《正義》佚文依然不敢問津。繼瀧川氏之后,水澤利忠教授為補其闕,廣校日本現(xiàn)存各種《史記》板本、抄本的標注,包括瀧川氏未見之黃善夫《史記》三家注合刻本的校記,于1957-1970年間陸續(xù)刊行《史記會注考證校補》全九冊,為瀧川資言所輯《正義》佚文千百數(shù)十條(實為1418條)以及水澤本人新獲“資言所未見佚文凡二百數(shù)十條”(實為227條)“一一明所據(jù)”。此后,小澤賢二先生又繼水澤之業(yè),涉十余年之功,致力于《史記正義佚存》源流的探索,查明其藍本乃京都東福寺舊藏“栴室本”(心華和尚善本)版面框郭內外所標記的古注,而其古注則源于元亡明興之際由日本五山臨濟僧從中國攜歸東瀛的單本《史記正義三十卷》。小澤的成績?yōu)椤妒酚浾x佚存訂補》,收入水澤利忠所編《史記正義之研究》(日本東京汲古書院1994年刊)。
筆者曾于公元2000年在《臺大歷史學報》二十五期發(fā)表《程金造之“〈史記正義佚存〉偽托說”平議》報告四萬余言,指出:程金造先生認為瀧川資言輯得的“這千三百條[《正義》]佚存,只有十分之一二是可靠的,絕大部分是讀者的雜抄和注解”。本此先入之見,從改制文本開始,作為立論的前提,便有意將讀者引入岐途。他精心搜集的證例和所作的按斷,貌似“考證翔實”,然經仔細辨析,無不以真為偽。程氏本末皆失,他所獨創(chuàng)的“《史記正義佚存》偽托說”,自應推翻,以免貽誤后學。而瀧川資言輯得的佚存《正義》,則使失傳已久的部分《正義》重見天日。瀧川資言不愧為守節(jié)功臣。
不過瀧川資言諸人對《史記正義》的輯佚,僅限日本現(xiàn)存之《史記》古板本、古活字本《史記》鈔錄本之欄外標注,卻未涉及《史記》三家注本以外的宋人著作。
筆者在做《史記》版本源流、敘事起迄與主題遷變研究的過程中,曾對《史記》三家注本以外《史記正義》的留存情況做過一番調查,發(fā)現(xiàn)呂祖謙《大事記解題》、王應麟《玉海》、《通鑒地理通釋》、《詩地理考》、胡三省《資治通鑒音注》中,都大量征引了單本《史記正義》,其中相當數(shù)量為《史記》三注合刻本所未載而成《正義》佚文。筆者當時作了詳細的札記。值得關注的是,呂祖謙、王應麟與胡三省三人的學術素養(yǎng)有先后師承關系。
王應麟,字伯厚,浙東鄞(寧波)人。祖籍開封祥符縣,西漢初置為浚儀縣,故王氏著書署名皆為“浚儀王應麟伯厚甫”。生于宋寧宗嘉定十六年(1223),卒于元成宗元貞元年(1295),享年73歲。十九歲進士及第,三十一歲試博學宏詞科中選。自十九歲入仕,至五十三歲辭歸鄉(xiāng)里,三十多年間除少數(shù)幾年在地方任職外,王應麟絕大部分時間均在朝廷中樞,歷任秘書郎、著作郎、直學士院、秘書監(jiān)兼權中書舍人,官至禮部尚書兼給事中。王氏除天才絕識、好學精進有大過人者外,又得盡讀館閣秘府所藏天下未見之書,故成有宋一代通儒,一生著書三十余種,凡六百九十余卷。《玉海》二百卷,系為博學宏詞科應用而編的大型類書,專精力積三十余年而后成,為應麟最重要的著作。是書分門析類,特為詳密,上自天文律歷,下至禮樂器用,凡分二十一門、二百四十余類;其摭集文獻,則自六經諸史、百家子集、注疏傳記、藝文譜牒、宋室記注,靡有孑遺,纂次詳備,謹而有序。書成之時,即有“天下奇書”之目。《四庫全書總目》稱“其貫穿奧博,唐宋諸大類書未有能過之者”。
《玉海》在王應麟歿后四十余年,即元順宗至元三年(1337)由浙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也乞里不花報經朝廷批準后,命慶元路(今浙江寧波市)儒學以王應麟家藏手稿鳩工鐫刻,至元六年(1340)畢工,稱“元至元慶元路儒學刊本”。十一年后,因儒學刊本訛誤甚多,慶元路總管阿殷圖埜堂乃命王應麟之孫王厚孫重加校讎,得缺漏訛舛六萬字,于至正十二年(1352)補刊,重印問世,稱“至正慶元路阿殷圖埜堂刊本”。此本其實是至元刊本的補刊本,也是《玉海》刊定本。有學者稱至正本為重刊本,不確。可惜此本中國本土早已失傳。康熙二十六年(1687)江蘇學政李振裕欲就明南監(jiān)刊本《玉海》修補,已無善本可資參校。乾隆年間編《四庫全書》錄入的《玉海》底本是“兩江總督采進本”,其非元至正刊本可知。
《玉海》分類敘事,凡涉三代以下、漢武天漢以前的事典,常引館閣所藏的《史記集解》、《史記索隱》、《史記正義》作注。《玉海》征引《史記索隱》凡74條,4條不見于今本《史記》三注本,可見作為王氏征引底本的是《索隱》單行本而非合刻本。所引《史記正義》亦然,因系館閣秘書,其可信度極高。
筆者檢閱、考索《玉海》征引《史記正義》所用的底本,原來是安徽師范大學中國詩學研究中心資料室庋藏的明初南監(jiān)刊行明清遞修本,以臺灣商務印書館1977年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所錄《玉海》為參校本,而與北京中華書局點校三家注合刊本《史記》1982年第2版對照。《玉海》征引《史記正義》有如下的體例:
1.子目敘事若出自《史記》,下引張守節(jié)注,有時僅標“《正義》”,或“《正義》曰”;
2.子目引《史記》文后所標“注”字,必指裴骃《史記集解》;
3.子目敘事若出自《漢書》,下引張守節(jié)注,必標“《史記正義》”,不作簡稱;
4.子目引《漢書》文后所標“注”字,必指顏師古《漢書注》;
5.張守節(jié)注前若無紀事之文,必標“《史記正義》”提明,以與《玉海》引《五經》唐疏所稱之“《正義》”判別;
6.《玉海》征引《史記正義》諸條,有的是從單本《史記正義》全文過錄,有的則視情“刪其游辭,取其要實”而有所裁節(jié);所引《史記索隱》亦同樣處理。
檢視《玉海》全書,共征引《史記正義》105條。以之與中華書局點校三家注合刊本《史記》(1982年第2版)比照,發(fā)現(xiàn)中華本遺佚《正義》計67條。《玉海》征引《正義》及《史記》三家注合刊本遺佚《正義》情況如下:天文門7條,佚1條;律歷門3條,佚1條;地理門25條,佚16條;圣文門3條,佚2條;藝文門13條,佚11條;器用門2條,佚1條;郊祀門21條,佚13條;學校門1條,佚1條;官制門3條,佚3條;兵制門4條,佚2條;宮室門24條,佚15條。
2010年春,筆者在安徽師范大學圖書館特藏部見讀《合璧本玉海》全八冊,由日本京都中文出版社出版,臺北大化書局1977年印行。該書將天埌間僅存的由日本京都建仁寺兩足院寶藏的元至正十二年補刊《玉海》影印面世。筆者將此書與安徽師范大學中國詩學研究中心所藏明初南監(jiān)刊行明清遞修本對勘,發(fā)現(xiàn)至元四年前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胡助《玉海序》雖為“萬歷癸未年補”刻、至元六年婺郡文學中山李桓《玉海序》及至正十一年慶元路總管阿殷圖埜堂序,雖為康熙二十六年補刻,但版式、字體卻與《合璧本玉海》影印元至正十二年補刊《玉海》相同,顯然是據(jù)元刊本葉面摹刻而成。據(jù)明人黃佐撰《南雍記》卷十八《經籍考下篇·梓刻本末》:“本監(jiān)所藏諸梓,多自舊國子學而來也,明矣。自后,四方多以書板送入,洪武、永樂時,兩經欽依修補。”又據(jù)清乾隆三年知江南江寧府事張華年為修復《玉海》所撰《序》言稱“《玉海》一書……書成于宋,鏤版于元。其在江南者,版藏上元學中”,可知所謂“明初南監(jiān)《玉海》刊本”,其實是就慶元路移送金陵國子學的《玉海》版片修補缺損后的刷印本,明洪武初南監(jiān)并未整體刊刻《玉海》。這部書版歲月漫漶,朽蝕嚴重,迭經明正德、嘉靖、萬歷、崇禎、清康熙、乾隆修補,元至正刊板已所剩無幾;但這個本子與元至正本最為接近,文本訛誤遠較《四庫全書》錄入的《玉海》為少。
筆者對《玉海》征引《史記正義》的考索、研究,最終是以日本京都建仁寺兩足院所藏元至元六年初刻、元至正十二年補刊《玉海》影印本(以下簡稱“元刊《玉海》”,標出卷數(shù)與葉碼)為底本,附以《合璧本玉海》(以下簡稱“合璧本”)的冊數(shù)、頁碼,以便查考;以明初南監(jiān)補刊明清遞修本《玉海》(以下簡稱“明刻《玉海》”,標出卷數(shù)與葉碼)及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以下簡稱“《四庫全書》”,標出冊數(shù)、頁碼)抄錄的《玉海》為參校本,共同與中華書局點校三家注合刊本《史記》(1982年第2版)對照。筆者的考索以“傳璋按”標識。
二、《玉海》征引《史記正義》佚文考索
1.《玉海》卷三《天文·天文書下》
《史記正義》: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千四百六十一分里之三百四十八,凡周天一百七萬一千里。(元刊《玉海》,卷三,第三十七葉;合璧本,第一冊,第93頁;明刻《玉海》,卷三,第三十七葉;《四庫全書》,第943冊,第102頁)
傳璋按:此則《正義》當在《史記·五帝本紀》之《堯本紀》“歲三百六十六日,以閏月正四時”句下。《史記集解索隱正義合刊本》此下因有《索隱》長注(見中華書局點校本《史記》,第一冊,第19-20頁),宋人合刻時,棄《正義》不用。《玉海》錄此《正義》當有節(jié)略,節(jié)略者或為在“一度”二字前有“凡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十四字。
2.《玉海》卷十一《天文·律歷·漏刻·堯刻漏》
《選》陸佐公曰:“衛(wèi)宏載傳呼之節(jié),較而不詳;霍融敘分至之差,詳而不密。”《注》:“《漢舊儀》曰:‘夜漏起,宮中宮城門傳,五伯官直符行,衛(wèi)士周廬擊木柝,讙呼備火。’”
《史記正義》按:馬融以昏明為限,鄭元以日出入為限,故有五刻之差。(元刊《玉海》,卷十一,第七葉;合璧本,第一冊,第240頁;明刻《玉海》,卷十一,第七葉;《四庫全書》,第943冊,第271頁)
傳璋按:《選》指梁蕭統(tǒng)編《昭明文選》,《注》指唐李善《文選注》。陸佐公(名倕)文見《文選》卷五十六《新漏刻銘》。由王應麟所引《漢舊儀》“讙呼備火”句,可知此則《史記正義》當原系于《史記·五帝本紀·堯本紀》“日永星火以正中夏”句下。《史記》三注合刻本有裴骃《集解》:“孔安國曰:‘永,長也,謂夏至之日。火,蒼龍之中星,舉中則七星見可知也,以正中夏之[氣]節(jié)。’馬融、王肅謂日長晝漏六十刻,鄭玄曰五十五刻。”又《堯本紀》“日短,星昴,以正中冬”句下有《集解》:“馬融、王肅謂日短晝漏四十刻。鄭玄曰四十五刻,失之。”(見中華本《史記》第一冊,第18-19頁)而無《正義》。張守節(jié)這條佚文“引致旁通”,指出馬融、王肅與鄭玄所說不同的原由,并對《集解》指摘鄭玄“失之”予以駁正,有補正之功。又《文淵閣四庫全書》引陸佐公文“霍融敘分至之差”,“至”字訛作“正”。
3.《玉海》卷十四《地理·漢司空輿地圖》
《史記正義》:天地有覆載之德,天為蓋,地為輿,故云輿地圖。(元刊《玉海》,卷十四,第十五葉;合璧本,第一冊,第300頁;明刻《玉海》,卷十四,第十五葉;《四庫全書》,第943冊,第339頁)
傳璋按:此則《正義》佚文當原系于《史記·三王世家》“御史奏輿地圖”句下。三注合刻本《史記》此句有《索隱》:“謂地為‘輿’者,天地有覆載之德,故謂天為‘蓋’,謂地為‘輿’,故地圖稱‘輿地圖’。疑自古有此名,非始漢也。”宋人將《史記正義》附刻于《史記集解索隱》二注本時,因此則《正義》與《索隱》大同,為避重復而割棄不用,幸《玉海》征引而得留存。
4.《玉海》卷十五《地理·晉太康地志》
《前漢》:《梁王傳》、《地理志》師古《注》、《史記正義》引《晉太康地志》。(元刊《玉海》,卷十五,第二十葉;合璧本,第一冊,第322頁;明刻《玉海》,卷十五,第二十葉;《四庫全書》,第943冊,第365頁)
傳璋按:《漢書·文三王傳》之《梁孝王武傳》“廣睢陽城七十里”句下顏《注》:“師古曰:更廣大之也。《晉太康地志》云:‘城方十三里,梁孝王筑之。鼓倡節(jié)杵而后下和之者,稱《睢陽曲》。今踵以為故,今之樂家《睢陽曲》是其遺音。’”(浙江古籍出版社,百衲本《二十五史》,第一冊,第446頁上欄)而王應麟稱《史記正義》在《梁王傳》亦引《晉太康地志》,則應在《史記·梁孝王世家》與《漢書·梁孝王傳》對應的史文下。今檢《史記》三注合刊本《梁孝王世家》,“廣睢陽城七十里”句下有《索隱》:“蘇林云:‘廣其徑也。’《晉太康地志》云:‘城方十三里,梁孝王筑之。鼓倡節(jié)杵而后下和之者,稱《睢陽曲》。今踵以為故,所以樂家有《睢陽曲》,蓋采其遺音也。’”(見中華本《史記》,第六冊,第2084頁)合刻本此句下無《正義》。而王應麟征引文本《史記正義》有引《晉太康地志》文如《漢書》顏《注》所引者,《玉海》出其事而省其文。宋人以《史記正義》附刻于《史記集解索隱》時,因張守節(jié)所引《晉太康地志》與司馬貞《索隱》所引全同,故未將此則《正義》附刻。幸《玉海》書其事,故得增補《史記正義》一則佚文:
《史記·梁孝王世家》“廣睢陽城七十里。”《史記正義》:《晉太康地志》云:“城方十三里,梁孝王筑之。鼓倡節(jié)杵而后下和之者,稱《睢陽曲》。今踵以為故,今之樂家《睢陽曲》是其遺音。”
5.《玉海》卷二十《地理·山川·禹九山》
《史記》:道九山:汧及岐、至于荊山。
《正義》:九州之山,謂汧、壺口、砥柱、太行、西傾、熊耳、嶓冢、內方、汶。(元刊《玉海》,卷二十,第九葉;合璧本,第一冊,第427頁;明刻《玉海》,卷二十,第九葉;《四庫全書》,第943冊,第488頁)
傳璋按:此則《正義》當為《史記·夏本紀》“道九山:汧及岐至于荊山”的注文。檢中華點校本《史記》,此句下有《索隱》長注(中華本《史記》,第一冊,第67頁)。此則《正義》因與《索隱》前段文字重復,故三家注合刻者將其刪削而未附刻。
6.《玉海》卷二十《地理·山川·禹龍門山》
《史記正義》:龍門山,在絳州龍門縣。《括地志》云:“龍門,在同州韓城縣北五十里。”其山更黃河,夏禹所鑿者也。龍門山,在夏陽縣。(元刊《玉海》,卷二十,第十一葉;合璧本,第一冊,第428頁;明刻《玉海》,卷二十,第十一葉;《四庫全書》,第943冊,第489頁)
傳璋按:此則《正義》當原系于《夏本紀》“道河積石至于龍門”句下。檢中華本《史記》,此處三家無注。此句前“黑水西河惟雍州,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中華本《史記》,第一冊,第65頁),于“龍門”有《集解》:“孔安國曰:龍門山在河東之西界。”有《索隱》:“龍門山在左馮翊夏陽縣西北。”也有《正義》長注,但除“龍門山在同州韓城縣北五十里”文字與佚文相同外,無一重合。佚文針對《集解》引孔安國謂龍門山“在河東”、《索隱》謂在河西的不同說法,《正義》根據(jù)龍門山的山形走勢,兼取二說,而以“其山更黃河”加以調停,更切龍門實際。
7.《玉海》卷二十《地理·山川·周岐山》
《史記正義》:《括地志》云:“岐山,岐州岐山縣東北十里。徐廣云:其南有周原。”(元刊《玉海》,卷二十,第十四至十五葉;合璧本,第一冊,第429-430頁;明刻《玉海》,卷二十,第十四至十五葉;《四庫全書》,第943冊,第491頁)
傳璋按:此則《正義》當系于《周本紀》古公“踰梁山止于岐下”句下。今檢中華點校本《史記》,此句有《集解》:“徐廣曰:‘山在扶風美陽西北,其南有周原。’骃案:皇甫謐云:‘邑于周地,故始改國曰周。’”(中華本《史記》,第一冊,第114頁)而無《正義》。當系宋人將《史記正義》附刻于《史記集解索隱》二注本時,因已有《集解》注,故割棄此則《正義》不用。又案:三注合刻本《夏本紀》“治梁及岐”、“荊岐已旅”、“導汧及岐”三句下,均有與《正義》“岐山在岐州岐山縣東北十里”相同的注文。這是張守節(jié)《史記正義》在不同篇卷中為便于閱讀而設置的重注例。
8.《玉海》卷二十《地理·山川·漢河源》
《張騫傳》:“漢使使窮河源,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昆侖。贊曰:《禹本紀》言‘河出昆侖。昆侖高二千五百里余,日月相避隱為光明’。自騫使大夏之后,窮河源,惡睹所謂昆侖者乎?”《注》:“鄧展曰:《尚書》‘導河積石’,河原出于積石,在金城河關,不言出昆侖也。”
《史記正義》:《括地志》:“河州有小積石山,即《禹貢》‘浮于積石至龍門’者。”然黃河源從西南下,出大昆侖東北隅,東北流經于闐,入鹽澤,即東南潛行入吐谷渾界大積石山,又東北流至小積石山,河始闓。《圖》云:“黃河出昆侖東北角剛山東,自北行千里,折西行于浦山,南流千里至文山,東流千里至秦澤,西流千里至潘澤陵門,東北流千里至華山之陰,東南流千里至下津。”然河水九曲,其長九千里,入渤海。《爾雅》云:“河出昆侖虛,其色黃。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元刊《玉海》,卷二十,第十九至二十葉;合璧本,第一冊,第432頁;明刻《玉海》,卷二十,第十九至二十葉;《四庫全書》,第943冊,第494頁)
傳璋按:此則《正義》當原系于《史記》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傳》太史公曰“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后也,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昆侖者乎”句下。此句下《史記集解索隱合刻本》原有《索隱》長注(見中華本《史記》,第一冊,第3179-3180頁),已略敘黃河源與昆侖山事梗概,故宋人將《史記正義》附刻時舍去此則《正義》。然張守節(jié)此注將黃河源流“委曲申明”,學術價值甚高,宋人未予合刻,殊為可惜,幸《玉海》征引得以復見于世。又按:《史記·夏本紀》“道九川……至于南海”句下《正義》有自“然黃河源”至“至小積石山”凡47字(見中華本《史記》,第一冊,第71頁)。
9.《玉海》卷二十一《地理·河渠·禹九河》
《史記正義》:徒駭在滄州景城,馬頰、覆釜在德州安德,胡蘇、鬲津在滄州胡蘇,簡在貝州歷亭縣界。(元刊《玉海》,卷二十一,第三葉;合璧本,第一冊,第448頁;明刻《玉海》,卷二十一,第三葉;《四庫全書》,第943冊,第513頁)
傳璋按:此則《正義》當原系于《史記·夏本紀》“濟河維沇州九河既道”句下。《史記》三注合刻本此句有《集解》釋“九河”:“馬融曰:九河名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絜、句盤、鬲津。”(中華本《史記》,第一冊,第55頁)而無《正義》。此則《正義》為《集解》補注九河唐代所在州縣。
10.《玉海》卷二十一《地理·河渠·鴻溝》
《史記·高紀》:四年,項羽與漢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溝而西為漢、東為楚。
《正義》:應劭云:“在滎陽東南二十里。”文穎曰:“于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wèi),與濟、汝、淮、泗會于楚,即今官渡水也。”張華云:“大梁城在浚儀縣,此縣西北渠水東經此城南,又北屈分為二渠,其一渠東南流,始皇鑿引河水以灌大梁,謂之鴻溝,楚、漢會此處也;一渠東經陽武縣南,為官渡水。”今鴻溝口在河口西百里。鴻溝歷大梁城東南,入淮、泗,俱入淮,會于楚地。(元刊《玉海》,卷二十一,第三十葉;合璧本,第一冊,第461頁;明刻《玉海》,卷二十一,第三十葉;《四庫全書》,第943冊,第529-530頁)
傳璋按:此則《正義》當原系于《史記·高祖本紀》“項羽恐,乃與漢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溝而西者為漢,鴻溝而東者為楚”長句下。《史記》三注合刻本此句下有《索隱》而無《正義》。《索隱》曰:“應劭云:‘在滎陽東南三十里,蓋引河東南入淮泗也。’張華云:‘一渠東南流,經浚儀,是始皇所鑿,引河灌大梁,謂之鴻溝。一渠東經陽武南,為官渡水。’《北征記》云中牟臺下臨汴水,是為官渡水也。”(見中華本《史記》,第二冊,第378頁)與本則《正義》所征引應劭、張華說文字略同,故三注合刻時舍卻《正義》所釋。但兩相比較,《正義》所引文穎說鴻溝流向及作用,為《索隱》注所缺,且《正義》所引張華說文字亦較《索隱》為全,正符張守節(jié)《史記正義序》所云“六籍九流,地里蒼雅,銳心觀採……郡國城邑,委曲申明”的注釋宗旨。又按:宋人呂祖謙撰《大事記解題》卷八,第四十二頁敘“西楚與漢約中分天下以鴻溝為界”事,所引《史記正義》,與《玉海》所引正同,唯略去“今鴻溝口”以下10字。
11.《玉海》卷二十三《地理·陂塘堰湖》禹五湖《史記》太史公曰:上姑蘇,望五湖。
《正義》:“五湖者,連太湖,在蘇州西四十里。”又曰:“游、莫、貢、、胥為五湖,并太湖東岸五灣。”(元刊《玉海》,卷二十三,第一葉;合璧本,第一冊,第495頁;明刻《玉海》,卷二十三,第一葉;《四庫全書》,第943冊,第569頁)
傳璋按:此則《正義》當原系于《史記·河渠書》“太史公曰……上姑蘇,望五湖”句下。檢《史記》三家注合刊本,此句下無注。唯《史記·夏本紀》“淮海維揚州……三江既入,震澤致定”句下有《正義》釋三江、五湖長注,凡497字(見中華本《史記》,第一冊,第59頁)。其中釋“五湖”云:“五湖者,菱湖、游湖、莫湖、貢湖、胥湖,皆太湖東岸五灣為五湖,蓋古時應別,今并相連。”宋人附刻《史記正義》于《史記集解索隱》時,因《夏本紀》之《正義》已有“五湖”釋文,故于此棄而不錄。幸《玉海》征引得以存世。又案:日人瀧川資言輯《史記正義佚存》,于《史記·三王世家》“五湖之間”句下所附《正義》佚文,與《玉海》征引的“又曰”云云文字相同(參見張衍田《史記正義佚文輯校》,第211頁)。《玉海》附刻的《小學紺珠》卷三“太史公曰:上姑蘇,望五湖”,引《史記正義》釋“五湖:游、莫、貢、、胥,并太湖東岸五灣”,與《玉海》所引“又曰”《正義》全同。
12.《玉海》卷二十四《地理·道涂·禹九道》
《史記·夏本紀》:禹“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
《正義》:通達九州之道路。(元刊《玉海》,卷二十四,第十一葉;合璧本,第一冊,第522頁;明刻《玉海》,卷二十四,第十一葉;《四庫全書》,第943冊,第601頁)
傳璋按:此則《正義》當原系于《史記·夏本紀》“開九州通九道”句下。《史記》三家注合刊本此下無注。宋人合刻時或以為“通九道”無須設注,故未錄此《正義》。瀧川資言《史記正義佚存》輯得此則《正義》佚文(參見張衍田《史記正義佚文輯校》之《夏本紀第二》“以開九州通九道”句下《正義》佚文,第6頁)。
13.《玉海》卷二十四《地理·關塞·漢武關》
《高紀》:秦三年“八月,沛公攻武關”。《注》:“應劭曰:‘武關,秦南關,通南陽。’文穎曰:‘武關在析西百七十里。’”
《史記正義》:《括地志》曰:“故武關在商州商洛縣東九十里,春秋時少習。”(元刊《玉海》,卷二十四,第二十葉;合璧本,第一冊,第526頁;明刻《玉海》,卷二十四,第二十葉;《四庫全書》,第943冊,第607頁)
傳璋按:《玉海》敘文所稱《高紀》,指《漢書·高帝紀》,《注》系顏師古《漢書注》。此則《史記正義》當原系于《史記·高祖本紀》“乃用張良計……因襲攻武關”句下。《史記》三注合刻本此句下有《索隱》而無《正義》。《索隱》曰:“《左傳》云楚司馬起(營所)[豐析]以臨上雒,謂晉人曰‘將通于少習’,杜預以為商縣武關也。又《太康地理志》武關當冠軍縣西,峣關在武關西也。”(見中華本《史記》,第二冊,第361頁)宋人附刻《正義》時,因《索隱》已注明武關位置,故舍棄《正義》。《史記·淮南衡山列傳》“陳定發(fā)南陽兵守武關”句下有《正義》:“故武關在商州商洛縣東九十里。春秋時。闕文。”(見中華本《史記》,第十冊,第3080頁;黃善夫梓《史記》三注合刻本引《正義》與今本同)與王應麟所引《正義》“春秋時”之前文字全同,《淮南王列傳》所引《正義》蓋為便于閱讀而重注。唯宋時《淮南傳》“武關”句下《正義》“春秋時”后文字殘闕,故以“闕文”二字標示。其實所缺者即《高祖本紀》“攻武關”句下《正義》“春秋時少習”句中“少習”二字。“少習”者,山名也。
14.《玉海》卷二十四《地理·關塞·臨晉關》
灌嬰定南陽郡,西入武關,從東出臨晉關擊降殷王。
《史記正義》:臨晉關即蒲津關也,在臨晉縣。今在同州。(元刊《玉海》,卷二十四,第二十一葉;合璧本,第一冊,第527頁;明刻《玉海》,卷二十四,第二十一葉;《四庫全書》,第943冊,第607頁)
傳璋按:此則《正義》當原系于《史記·樊酈滕灌列傳》“從東出臨晉關”句下。檢《史記》三注合刻本,此句下三注全無。(參中華本《史記》,第八冊,第2668頁)《史記·曹相國世家》“曹參從漢王出臨晉關至河內”句下有《正義》:“臨晉關即蒲津關也。在臨晉縣,故言臨晉關。”注文微有不同,故《玉海》所錄當為佚文。
15.《玉海》卷二十四《地理·關塞·靈關》
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曰:乃關沫若,徼柯鏤靈山。
《史記正義》:鑿靈山以通關也。(元刊《玉海》,卷二十四,第二十二葉;合璧本,第一冊,第527頁;明刻《玉海》,卷二十四,第二十二葉;《四庫全書》,第943冊,第608頁)
傳璋按:此則《正義》當原系于《史記·司馬相如列傳》“鏤零山”句下。三家注合刊本無注。瀧川資言輯得此則《正義》并附入《史記會注考證》卷一百十七《司馬相如列傳》“鏤零山梁孫原”句下(參見張衍田《史記正義佚文輯校》,第406頁)。
16.《玉海》卷二十四《地理·關塞·漢函谷關》
《史記》楚懷王攻函谷關。
《正義》:古函谷關在陜州桃林縣西南十二里。今屬靈寶縣。(元刊《玉海》,卷二十四,第二十五葉;合璧本,第一冊,第529頁;明刊《玉海》,卷二十四,第二十五葉;《四庫全書》,第943冊,第610頁)
傳璋按:此則《正義》當原系于《史記·楚世家》“十一年蘇秦約從山東六國共攻秦楚懷王,為從長至函谷關”句下(中華本《史記》,第五冊,第1722頁)。《史記》三家注合刻本此下無注,幸《玉海》收錄而得存此。呂祖謙撰《大事記解題》卷四亦征引此則《正義》。
17.《玉海》卷二十四《地理·關塞·隋榆關》
《史記正義》:今榆木塞也。在勝州北。王恢所謂“植榆為塞”也。顏師古曰:“在朔方,或謂之榆中。”(元刊《玉海》,卷二十四,第三十一葉;合璧本,第一冊,第532頁;明刻《玉海》,卷二十四,第三十一葉;《四庫全書》,第943冊,第614頁)
傳璋按:此則《正義》當原系于《史記·秦始皇本紀》三十三年“自榆中并河以東屬之陰山,以為四十四縣,城河上為塞”句下為“榆中”所作注解(中華本《史記》,第一冊,第253頁)。此句有裴骃《集解》:“徐廣曰:‘在金城。’”按:金城郡,漢昭帝始置,榆中縣亦當時新設,在今甘肅榆中縣西北。張守節(jié)不同意裴注,而認為蒙恬拓境建塞在上郡,當在唐時“勝州北”,即今內蒙古河套東北岸,故別出新注。宋人合刻《史記》三家注時棄此則《正義》,殊為疏失。張守節(jié)在《史記·趙世家》武靈王二十年“西略胡地至榆中”句下為“榆中”設注:“勝州北河北岸也。”(中華本《史記》,第六冊,第1811頁)與《秦始皇本紀》所注“榆中”同。“榆中”,《始皇本紀》始見,必設《正義》注明,而三家注本無有,幸《玉海》引錄而存留典冊。
18.《玉海》卷二十五《地理·標界·畿封》
《書·正義》:“陜縣,漢之弘農郡治,其地居二京之中,故以為二伯分掌之界。”
《史記正義》:《括地志》云:“陜原在陜縣西南二十五里。”分陜不因其城,乃從原為界。(元刊《玉海》,卷二十五,第一葉;合璧本,第一冊,第537頁;明刻《玉海》,卷二十五,第一葉;《四庫全書》,第943冊,第618頁)
傳璋按:此則《正義》當原系于《史記·燕召公世家》“其在成王時,召公為三公,自陜以西,召公主之;自陜以東,周公主之”句下(中華本《史記》,第五冊,第1549頁)。三家注合刊本有《集解》:“何休曰:陜者,蓋今弘農陜縣是也。”《正義》為《集解》補充說明周、召二伯分陜的標界,但宋人合刻時惜未收錄。
19.《玉海》卷二十八《圣文·黃帝書》
《史記》黃帝老子言。
《正義》曰:黃帝道書十卷蓋公善治黃老言。曹參治齊用黃老術。竇太后好黃老言。(元刊《玉海》,卷二十八,第十九葉;合璧本,第二冊,第590頁;明刻《玉海》,卷二十八,第十九葉;《四庫全書》,第943卷,第680頁)
傳璋按:此則《正義》當原系于《史記·孝武本紀》“會竇太后治黃老言”句下(中華本《史記》,第二冊,第452頁)。此句無《集解》、《索隱》注,此則《正義》亦未收。
20.《玉海》卷二十九《圣文·御制詩歌·三侯章》
《史記·樂書》高祖過沛,詩《三侯之章》,令小兒歌之。
《正義》:三“兮”也。(元刊《玉海》,卷二十九,第五葉;合璧本,第二冊,第603頁;明刻《玉海》,卷二十九,第五葉;《四庫全書》,第943冊,第695頁)
傳璋按:此則《正義》當原系于《史記·樂書》“高祖過沛詩《三侯之章》”句下。《史記》三家注合刻本有《索隱》:“按:過沛詩即大風歌也。其辭曰‘大風起兮云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xiāng),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是也。侯,語辭也。《詩》曰‘侯其祎而’者是也。‘兮’亦語辭也。沛詩有三‘兮’字,故云三侯也。”(中華本《史記》,第四冊,第1177頁)因《索隱》對此有詳注,且涵《正義》釋文辭義,故宋人合《史記正義》于《史記集解索隱》二注本時,未附刻此則《正義》。
21.《玉海》卷四十《藝文·古文春秋》
《自序》:“余聞之董生,《春秋》文成數(shù)萬,其指數(shù)千。”《注》:“張晏曰:《春秋》萬八千字。”
《正義》:左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余通,藏于秘府,伏而未發(fā)。漢武帝時,河間獻《左氏》及《古文周官》。成帝時,劉歆校秘書,見府中《古文春秋左氏傳》,大好之。《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詁而已。及歆引《傳》文釋《經》,轉相發(fā)明。(元刊《玉海》,卷四十,第三葉;合璧本,第二冊,第784頁;明刻《玉海》,卷四十,第三葉;《四庫全書》,第944冊,第107頁)
傳璋按:此則《正義》當原系于《史記·太史公自序》司馬遷答壺遂問難時所說“《春秋》文成數(shù)萬,其指數(shù)千”句下。《史記》三家注合刊本于此有《集解》(即《玉海》所引之《注》)及《索隱》(參見中華本《史記》,第十冊,第 3298-3299頁),而佚此則《正義》。
22.《玉海》卷四十《藝文·春秋五傳》
夾氏《漢志》: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
《史記正義》:《七錄》云:“建武中鄒、夾皆絕。”(元刊《玉海》,卷四十,第七葉;合璧本,第二冊,第786頁;明刻《玉海》,卷四十,第七葉;《四庫全書》,第944冊,第109頁)
傳璋按:此則《正義》當原系于《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及如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可勝紀”下,鄒氏、夾氏亦為“捃摭《春秋》之文以著書”者流,其書亡于東漢光武帝建武年間。
23.《玉海》卷四十《藝文·春秋·漢春秋決獄》
《前傳》:“淮南衡山反,使仲舒弟子呂步舒治淮南獄,以《春秋》之義顓斷于外,不請。”《注》:“應劭曰:‘仲舒居家,朝廷每有政議,遣廷尉張湯問其得失,于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言之詳矣。’”《繁露》曰:“《春秋》之聽獄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
《史記正義》:《七錄》曰:“《春秋斷獄》五卷。”(元刊《玉海》,卷四十,第十三葉;合璧本,第二冊,第789頁;明刻《玉海》,卷四十,第十三葉;《四庫全書》,第944冊,第112頁)
傳璋按:此則《正義》當原系于《史記·儒林列傳·董仲舒?zhèn)鳌分偈娴茏訁尾绞妗爸灵L史,持節(jié)使決淮南獄,于諸侯抎專斷,不報,以《春秋》之義正之,天子皆以為是”句下。《史記》三家注合刊本于此無《集解》、《索隱》,此則《正義》亦未收。《玉海》于《前傳》文后所稱之《注》,系指《前漢書》顏師古注。又按:瀧川資言所輯《正義》佚文,于《史記·儒林列傳·董仲舒?zhèn)鳌废掠腥纭队窈!匪洝啊镀咪洝吩?《春秋斷獄》五卷”一樣的文字(參見張衍田《史記正義佚文輯校》,第430頁)。
24.《玉海》卷四十六《藝文·正史·漢史記》
《司馬遷傳》:司馬氏世典周史。談為太史公,有子曰遷云云。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不敢缺。”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紬史記金匱石室之書。
《漢官儀》:司馬遷父談,世為太史。遷年十三,使乘傳行天下,求諸侯之史記。又見《西京雜記》。
《史記正義》:《博物志》云:“遷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元刊《玉海》,卷四十六,第十一葉;合璧本,第二冊,第902頁;明刻《玉海》,卷四十六,第十一葉;《四庫全書》,第944冊,第246頁)。
傳璋按:《史記》三家注合刊本《太史公自序》“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句下有《索隱》:“《博物志》:‘太史令,茂陵顯武里,大夫司馬遷,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三十字(見中華本《史記》,第十冊,第3996頁),而無《正義》此注。顯然是宋人將《史記正義》附刻于《史記集解索隱合刻本》時,見“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句下《正義》與《索隱》所引《博物志》相同,為避重復而削此則《正義》不用。而《玉海》于“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句下保存的這則《正義》,為解決司馬遷生年疑案提供了確切的文獻根據(jù)。又按:《玉海》卷一百二十三《官制·九卿》,太常屬官“太史令”目引《司馬遷傳》,在“談為太史公”句下,引“如淳曰”云云、“師古曰”云云之后,雙行夾注:“《史記》‘太史公掌天官’《索隱》曰:‘《博物志》:太史令司馬遷,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元刊《玉海》,卷一百二十三,第六葉;合璧本,第五冊,第2355頁;明刻《玉海》,卷一百二十三,第六葉;《四庫全書》,第946冊,第293頁)與《正義》佚文所引“遷年二十八”相同。
25.《玉海》卷四十六《藝文·正史·史記》
《司馬遷傳》:上記軒轅,下至于茲……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
《正義》:《史記》起黃帝,訖于漢武天漢四年,合二千四百一十三年。百三十篇,象一歲十二月及閏余也。《后漢》楊終受詔,刪《太史公書》為十余萬言。(元刊《玉海》,卷四十六,第十二葉;合璧本,第二冊,第902頁;明刻《玉海》,卷四十六,第十二葉;《四庫全書》,第944冊,第247頁)
傳璋按:此則《正義》當原系于《史記·太史公自序》“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為《太史公書》”句下(中華本《史記》,第十冊,第3319頁)。三注合刊本此下有《索隱》而無《正義》。《索隱》只釋司馬遷著作何以稱《太史公書》,而對“百三十篇”的含義未著一字。此則《正義》節(jié)自張守節(jié)《史記正義·論史例》(見中華本《史記》,第十冊,附錄第13頁)。按《論史例》當置于《史記正義》卷首,而上引《正義》在《史記正義》三十卷之末,首尾懸隔,有必要重注。瀧川資言《史記正義佚存》亦輯得此《正義》佚文(見張衍田《史記正義佚文輯校》,第476頁)。
26.《玉海》卷五十《藝文·譜牒》
《史記》太史公曰: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傳。……予觀《春秋》《國語》,其發(fā)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
《正義》:《大戴禮》及《孔子家語》篇名《索隱》同。(元刊《玉海》,卷五十,第四葉;合璧本,第二冊,第986頁;明刻《玉海》,卷五十,第四葉;《四庫全書》,第944冊,第344頁)
傳璋按:此則《正義》當原系于《史記·五帝本紀》太史公曰:“《五帝德》及《帝系姓》”句下。中華書局點校本(第一冊,第46頁)所據(jù)底本為清同治九年(1870)金陵書局刻成之《史記集解索隱正義合刻本》,此句下《正義》僅有“系,音奚計反”五字音注。檢南宋黃善夫所梓三注合刻本,此句下有“《正義》曰:系,音奚計反。《五帝德》及《帝系姓》,皆《大戴禮》文及《孔子家語》篇名。漢儒者以二書非經,恐不是圣人之言,故或不傳學也”,比金陵書局刻本多出整整40字。《玉海》所引《正義》正出于其中,顯為節(jié)略。黃善夫本于《史》文“儒者或不傳”句下又有“《索隱》曰:《五帝德》、《帝系姓》皆《大戴禮》及《孔子家語》篇名,以二者皆非正經,故漢時儒者以為非圣人之言,故多不傳學也”。宋人合刻三家注時,將二注并存,證明此條《正義》釋文是從單本《史記正義》原文中采輯的。清儒張文虎主持金陵書局校刻《史記》三家注時,誤以為《正義》為“系”字音注下,“原衍‘五帝德’云云四十字,乃《索隱》文,官本無”,抎自刪削《正義》四十字,大誤。而中華書局校點《史記》時,又誤從張文虎校勘札記。其實唐玄宗時,司馬貞與張守節(jié)同注《史記》,各自為書,不相為謀,亦互不相見文本,只因注書所據(jù)典籍基本相同,故注文相同或相近時有出現(xiàn),實屬正常。又按:《玉海》于上引《正義》“篇名”二字下,有雙行小字夾注“《索隱》同”三字,說明單本《索隱》亦有與單本《正義》相同的釋文;而此處王應麟以《正義》釋文為正解,以《索隱》為附錄,故曰“《索隱》同”。
27.《玉海》卷五十三《藝文·諸子·鬼谷子》
《唐志·縱橫家》:《鬼谷子》二卷蘇秦,又樂壹《隋志》云“樂一”注三卷,尹知章注三卷。
《史記正義》:鬼谷,谷名,在雒州陽城縣北五里。《七錄》有《蘇秦書》,樂壹注云:“秦欲神秘其道,故假名鬼谷也。”《鬼谷子》三卷,樂壹注。樂壹,字正,魯郡人。有《陰符七術》,有《揣》及《摩》二篇。《戰(zhàn)國策》云:“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為揣摩。期年,揣摩成。”按:《鬼谷子》乃蘇秦書,明矣。(元刊《玉海》,卷五十三,第二十一至二十二葉;合璧本,第二冊,第1059頁;明刻《玉海》,卷五十三,第二十一至二十二葉;《四庫全書》,第944冊,第429-430頁)。
傳璋按:此則《正義》當原系于《史記·蘇秦列傳》“東事師于齊而習之于鬼谷先生”句下。《史記》三家注合刊本此下有《集解》、《索隱》而無《正義》。瀧川資言《史記正義佚存》所輯《正義》佚文有《玉海》征引《正義》的前半部,自“鬼谷谷名”起,迄“樂壹,字正,魯郡人”(參見張衍田《史記正義佚文輯校》第225頁)。
28.《玉海》卷五十八《藝文·漢六經異傳》
《史記·自序》“厥協(xié)六經異傳。”《索隱》云:“如子夏《易傳》、毛公《詩傳》、韓嬰《詩外傳》、伏生《尚書大傳》之流也。”
《正義》:如左丘明《春秋外傳國語》。(元刊《玉海》,卷五十八,第六葉;合璧本,第二冊,第1153頁;明刻《玉海》,卷五十八,第六葉;《四庫全書》,第944冊,第536頁)
傳璋按:此則《正義》當原系于《史記·太史公自序》“厥協(xié)六經異傳”句下。《史記》三家注合刊本,此句有《索隱》長注(見中華本《史記》,第十冊,第3319頁),而無《正義》。上引《正義》宋人合刻時割棄。漢人以《左氏傳》為《春秋經》正傳,或稱《內傳》;而視《國語》為《春秋經》外傳,非正,故要“協(xié)”。
29.《玉海》卷五十八《藝文·漢列仙列士傳》
《隋志》:漢時阮蒼作《列仙圖》。劉向典校經籍,始作《列仙》、《列士》、《列女》之傳。
《史記正義》:《七略》云:“《列仙傳》二卷,劉向撰。”(元刊《玉海》,卷五十八,第八葉;合璧本,第二冊,第1154頁;明刻《玉海》,卷五十八,第八葉;《四庫全書》,第944冊,第537頁)
傳璋按:此則《正義》當原系于《史記·封禪書》始皇“求仙人羨門之屬”句下。《史記》三家注合刊本三家均無注。
30.《玉海》卷五十八《藝文·錄·越計然萬物錄》
計然者,濮上人也,博學無所不通,尤善計算。嘗南游越,范蠡卑身事之。其書則有《萬物錄》,著五方所出皆述之。事見《皇覽》及《晉中經簿》。
《史記正義》:《方物錄》。(元刊《玉海》,卷五十八,第十八葉;合璧本,第二冊,第1159頁;明刻《玉海》,卷五十八,第十八葉;《四庫全書》,第944冊,第544頁)
傳璋按:此則《正義》當原系于《史記·貨殖列傳》“昔者越王勾踐困于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計然曰:‘知斗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觀之。’”數(shù)句之下。《玉海》特提“越計然《萬物錄》”,意指這番言論出自計然的著作《萬物錄》中。元至正本、明初南監(jiān)本均作“方物錄”,《文淵閣四庫全書》亦作“方物錄”。“方”為“萬”之訛。蓋“萬”為“萬”字六朝以降的俗體,《正義》原本亦當作“萬”而不作“萬”。四庫館臣不明“萬物錄”的含義,或附會《國語》中有“民神雜糅不可方物”的成句,誤抄《萬物錄》為《方物錄》。
31.《玉海》卷六十二《藝文·論·漢素王妙論》
《史記·越世家》《注》:“太史公《素王妙論》云:范蠡本南陽人。”
《正義》:二卷。《七略》云:“司馬遷撰。”(元刊《玉海》,卷六十二,第一葉;合璧本,第二冊,第1225頁;明刻《玉海》,卷六十二,第一葉;《四庫全書》,第944冊,第622頁)
傳璋按:此則《正義》當原系于《史記·越世家》“范蠡事越王勾踐”句下,三注合刊本有《集解》,如上《注》說。《正義》又為《集解》補注。按《史記正義》注例,當先引《集解》說,后釋《素王妙論》篇卷,并誰氏所著。三注合刻本刪削此則《正義》,遂成佚文。
32.《玉海》卷八十五《器用·符節(jié)·黃帝合符釜山》
《史記》:帝修德振兵,未嘗寧居,東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峒,登雞頭;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葷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
《正義》:合符,謂合諸侯符瑞于釜山封禪也。猶禹會會稽玉帛萬國。《括地志》:“釜山在媯州懷戎縣北三里,上有舜廟。”郭子橫《洞冥記》稱:“東方朔云:‘東海大明之墟有釜山,山出慶云,應王者之符命。’”黃帝有黃云之瑞,故合符應于釜山也。(元刊《玉海》,卷八十五,第一葉;合璧本,第三冊,第1621頁;明刻《玉海》,卷八十五,第一葉;《四庫全書》,第945冊,第334頁)
傳璋按:此則《正義》當原系于《五帝本紀》黃帝“合符釜山”句下。《史記》三家注合刊本有《索隱》(見中華本《史記》,第一冊,第7頁),注文與此則《正義》基本相同,故宋人以《史記正義》附刻于《史記集解索隱》時,刪去與《索隱》重合的文字,而僅取《正義》所引《括地志》指明釜山所在的15字。《玉海》卻先征引《正義》全文,而以《索隱》附后,且僅節(jié)引“合諸侯符契圭瑞,而朝之于釜山,猶禹會諸侯于涂山然也”23字。可知王應麟以《正義》注文典正,故全取而不刪節(jié)。此事亦可證明所謂“《正義》疏通《索隱》”為無根之說。
33.《玉海》卷九十二《郊祀·漢九天祠》
《郊祀志》:高祖六年,長安置祠祀官,九天巫祠九天,皆以歲時祠宮中。《注》:“師古曰:九天者,謂中央鈞、東方蒼、東北旻、北元、西北幽、西方浩、西南朱、南炎、東南陽。其說見《淮南子》。一說:東旻、東南陽、南赤、西南朱、西成、西北幽、北元、東北變、中央鈞。”
《史記正義》:《尚書考靈曜》云:“東昊、東南陰”云云,同上。東蒼、東北閔、北元、西北幽、西昊、西南朱、南炎、東南陽。《太元經》云:中、羨、徒、罰更、晬、郭、咸、治、成天。(元刊《玉海》,卷九十二,第十五葉;合璧本,第四冊,第1746頁;明刻《玉海》,卷九十二,第十五葉;《四庫全書》,第945冊,第478頁)
傳璋按:此則《正義》當原系于《史記·封禪書》“九天巫祠九天”句下。《史記》三家注合刊本此句下有《索隱》,亦有《正義》(見中華本《史記》,第四冊,第1379頁)。但《正義》僅引《太玄經》,《玉海》所錄《正義》中的《尚書考靈曜》等全部刪削。不過《玉海》所引《正義》亦有節(jié)略,所謂“云云同上”者,指同上“一說”所引《尚書考靈曜》。這則《正義》佚文的全文當是:
《史記正義》:《尚書考靈曜》云:“東方昊天、東南陽天、南方赤天、西南朱天、西方成天、西北幽天、北方玄天、東北變天、中央鈞天也。”東蒼、東北閔、北玄、西北幽、西昊、西南朱、南炎、東南陽。《太玄經》云:“一中天、二羨天、三徒天、四罰更天、五晬天、六郭天、七咸天、八治天、九成天也。”
34.《玉海》卷九十二《郊祀·漢五》
《地理志》:扶風雍縣有五。
《史記正義》:西畤在秦州。《括地志》:三原在岐州雍縣南二十里。鄜,上、下畤并在此原上,因名三畤原,在吳山之陽。畦畤在雍州櫟陽縣東二十五里櫟陽故城中。晉灼云:“形如種韭一畦,畤中各一土封也。”張晏云:“漢祠五畤于雍丘,五里一烽火。”《括地志》云:“渭陽五帝廟,在雍州咸陽縣東三十里。”《宮殿疏》云:“五帝廟,一宇五殿也。”一宇之內設五帝各依其方帝,別為一殿,而門各如帝。(元刊《玉海》,卷九十二,第十九葉;合璧本,第四冊,第1748頁;明刻《玉海》,卷九十二,第十九葉;《四庫全書》,第945冊,第480頁)
傳璋按:此則《正義》當原系于《史記·封禪書》“西畤、畦畤祠如其故”句下。《史記》三家注合刊本此下無《集解》,亦無《索隱》(參中華本《史記》,第四冊,第1377頁)。此《正義》在宋人合刻三家注時亦未附刻,遂佚。
35.《玉海》九十二《郊祀·圜丘》
《郊祀志》:地貴陽,祭之必于澤中圓丘云。
《史記正義》:蓋在今寶鼎縣北圜丘上,祠后土是也。(元刊《玉海》,卷九十二,第二十葉;合璧本,第四冊,第1389頁;明刻《玉海》,卷九十二,第二十葉;《四庫全書》,第945冊,第481頁)
傳璋按:此則《正義》當原系于《史記·封禪書》“始立后土祠汾陰脽丘”句下。《史記》三家注合刊本此下有《集解》:“徐廣曰:元鼎四年。”(見中華本《史記》,第四冊,第1389頁)注出作后土祠的年份,此則《正義》為《集解》補注其所在。
36.《玉海》卷九十五《郊祀·唐虞五府》
《史記》:舜受終于文祖。
《正義》:鄭玄云:“文祖,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也。”《尚書帝命驗》云:“帝者承天立府,以尊天重象也。五府者,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玄矩,蒼曰靈府。”《注》云:“唐虞謂之天府,夏謂之正室,殷謂之重室,周謂之明堂:皆祀五帝之所也。文祖者,赤帝熛怒之府火精光明,文章之祖。周曰明堂。神斗者,黃帝含樞紐之府斗,主也。土精澄凈,四行之主。周曰太室。顯紀者,白帝招拒之府紀,法也。金精割斷萬物。周曰總章。玄矩者,黑帝光紀之府矩者。法也。水精玄昧,能權輕重。周曰玄堂。靈府者,蒼帝威靈仰之府。周曰青陽。”(元刊《玉海》,卷九十五,第三至四葉;合璧本,第四冊,第1790頁;明刻《玉海》,卷九十五,第三至第四葉;《四庫全書》,第945冊,第527頁)”
傳璋按:此則《正義》當原系于《史記·五帝本紀·舜本紀》“舜受終于文祖”句下。《史記》三家注合刻本此下有《集解》、《索隱》與《正義》注文(見中華本《史記》,第一冊,第23-24頁)。但合刻者刪去《正義》開首所引《集解》文,所引《尚書帝命驗》“五府者”以下脫奪“赤曰文祖,白曰顯紀,黑曰玄矩,蒼曰靈府”16字,所引注文“水精玄昧”,“昧”字又訛作“味”。
37.《玉海》卷九十五《郊祀·汶上明堂》
《武紀》: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水圜宮垣,為復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曰昆侖。天子從之入,以拜祀上帝焉。于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
《史記正義》:《括地志》云:“明堂故城在兗州博城縣東北三十里汶水上。”《漢書》云:“古時明堂處,明年秋乃作明堂。”(元刊《玉海》,卷九十五,第十八至十九葉;合璧本,第四冊,第1797-1798頁;明刻《玉海》,卷九十五,第十八至十九葉;《四庫全書》,第945冊,第535-536頁)”
傳璋按:此則《正義》當原系于《史記·封禪書》“于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句下(中華本《史記》第四冊,第1401頁)。《史記》三家注合刻本有《集解》:“徐廣曰:在元封二年秋。”而無《正義》。此則《正義》為《集解》補注所作明堂之所在。
38.《玉海》卷九十七《郊祀·宗廟·高廟》
《后百官志》:“高廟令,六百石。”《本注》曰:“守廟,掌按行掃除。無丞。”《注》:“《漢官儀》曰:員吏四人,衛(wèi)士一十五人。”
《史記正義》:《括地志》云:“高廟在長安縣西北十三里渭南。”(元刊《玉海》,卷九十七,第十三至十四葉;合璧本,第四冊,第1827頁;明刻《玉海》,卷九十七,第十三至十四葉;《四庫全書》,第945冊,第572頁)
傳璋按:此則《正義》當原系于《史記·劉敬叔孫通列傳》“衣冠月出游高廟,高廟,漢太祖”句下(見中華本《史記》,第八冊,第2725頁)。此句有《集解》引應劭釋“游衣冠”,引如淳釋高祖衣冠收藏處,而未注出高廟方位所在。此則《正義》為《集解》補注。宋人以《史記正義》附刻于《史記集解索隱》時割棄未用。又按:瀧川資言《史記正義佚存》輯得有此,系于“大孝之本也”句下(參見張衍田《史記正義佚文輯校》,第351頁)。
39.《玉海》卷九十七《郊祀·漢諸帝廟號》
景帝廟號德陽,中四年三月起。
《史記正義》:《括地志》云:“德陽宮,漢景帝廟,在雍州咸陽縣東北二十九里。自作之,諱不言廟,故言宮。”(元刊《玉海》,卷九十七,第十四葉;合璧本,第四冊,第1827頁;明刻《玉海》,卷九十七,第十四葉;《四庫全書》,第945冊,第572頁)
傳璋按:此則《正義》當原系于《史記·孝景本紀》“中四年三月置德陽宮”句下(中華本《史記》,第二冊,第445頁)。《史記》三家注合刊本有《集解》:“瓚曰:‘是景帝廟也,帝自作之,諱不言廟,故言宮。’《西京故事》云景帝廟為德陽宮。”而未注其廟所在。此則《正義》為《集解》補注德陽宮處所。宋人以《史記正義》附刻于《史記集解索隱》時,因其文與《集解》大致相同,故不附刻而亡佚。幸《玉海》征引而留存天埌。
40.《玉海》卷九十八《郊祀·封禪·漢武封禪》
《史記正義》:伍緝之《征記》曰:“漢武封壇廣丈三尺,高丈尺,下有玉籙書,以金銀為鏤,封以璽。”(元刊《玉海》,卷九十八,第九葉;合璧本,第四冊,第1581頁;明刻《玉海》,卷九十八,第九葉;《四庫全書》,第945冊,第599頁)
傳璋按:此則《正義》當原系于《史記·封禪書》“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祠太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祕”句下(中華本《史記》,第四冊,第1398頁)。《史記》三家注合刊本此下無注。《玉海》所引伍緝之“《征記》”,書名應為“《從征記》”,“征”上奪“從”字;“高丈尺”,據(jù)《史記》“丈”當為“九”之訛。又按:瀧川資言《史記正義佚存》于《史記·封禪書》“上于是乃令諸儒習射牛、草封禪儀”句下,輯有《正義》引伍緝之《從征記》,文字與《玉海》所引全同(參見張衍田《史記正義佚文輯校》,第63-64頁)。
41.《玉海》卷九十九《郊祀·周壽星祠》
《漢志》:秦于杜、亳有五社(《史記》作“三社”)主之祠、壽星祠,各以歲時奉祀。
《史記正義》:角、亢在辰為壽星。三月之時,萬物始生,春氣布養(yǎng),各盡其性,故壽。《爾雅》:“壽星,角、亢也。與老人別星。”(元刊《玉海》,卷九十九,第二十三葉;合璧本,第四冊,第1874頁;明刻《玉海》,卷九十九,第二十三葉;《四庫全書》,第945冊,第626頁)
傳璋按:此則《正義》當原系于《史記·封禪書》“杜、亳有三社主之祠、壽星祠”句下(中華本《史記》,第四冊,第1375頁)。《史記》三家注合刻本此句有《正義》曰:“角、亢在辰為壽星。三月之時,萬物始生建,于春氣布養(yǎng),各盡其性,不罹災夭,故壽。”部分佚失單本《史記正義》所引《爾雅》文,而《正義》引《爾雅》注出“壽星”與“老人星”非一星,甚有意義。
42.《玉海》卷九十九《郊祀·社稷·枌榆社》
《高紀》:后四歲,天下已定,詔御史令豐治枌榆社,常以時春以羊彘祠之。
《史記正義》:高祖里社也。(元刊《玉海》,卷九十九,第七葉;合璧本,第四冊,第1866頁;明刻《玉海》,卷九十九,第七葉;《四庫全書》,第945冊,第617頁)
傳璋按:此則《正義》當原系于《史記·封禪書》“詔御史令豐謹治枌榆社”句下。此句《史記》三家注合刊本無注。但前此有《史記》文“高祖初起,禱豐枌榆社”,其下有《集解》:“張晏曰:‘枌,白榆也。社在豐東北十五里。或曰枌榆,鄉(xiāng)名,高祖里社也。’”(中華本《史記》,第二冊,第1378頁)張守節(jié)因劉邦稱帝后特詔御史令豐邑“謹治枌榆社”,其事嚴重,故特于其下設《正義》點明此“枌榆社”非他,乃高帝“故里社”。宋人合刊時或因前文已有《集解》詳注,故棄此則《正義》不用。
43、44.《玉海》卷九十九《郊祀·漢雍諸星祠》
《志》:雍有日、月、參、辰、南北斗、熒惑、太白、歲星、填星、辰星、二十八宿、風伯、雨師、四海、九臣、十四臣之屬百有余廟。
《史記正義》:《漢舊儀》:“祭參、辰星于池陽谷口,夾道左右為壇。文王都豐,武王都鄗,二都有昭明祠。”《河圖》云:“熒惑星散為昭明。”《春秋傳》:“昭明起,有德如太白。”(元刊《玉海》,卷九十九,第二十五葉;合璧本,第四冊,第1875頁;明刻《玉海》,卷九十九,第二十五葉;《四庫全書》,第945冊,第627頁)
傳璋按:此則《正義》當原分系于《史記·封禪書》“雍有日月參辰”及“灃、滈有昭明”二句下(中華本《史記》,第四冊,第 1375-1376頁)。《史記》三注合刊本于“雍有日月參辰”句下有《索隱》:“案:《漢舊儀》云:‘祭參、辰星于池陽谷口,夾道左右為壇也。’”于“灃滈有昭明”句下有《索隱》:“案:樂產引《河圖》云‘熒惑星散為昭明’。”此二則《正義》釋文與《索隱》大同,故宋人將《正義》附刻于《史記集解索隱》本時,為避重復而未將《正義》附入。值得注意的是,王應麟著《玉海》,于此只取《正義》而棄《索隱》。
45.《玉海》卷一百一《郊祀·祠壇·魯雩壇》
《郊特牲·疏》鄭注《論語》云:“沂水在魯城南,雩壇在其上。”
《史記正義》:《括地志》云:“沂水,亦名雩水。衛(wèi)宏《漢舊儀》云:‘魯雩壇在城東南,引龜山水為沂,至壇西行曰雩水。’”(元刊《玉海》,卷一百一,第五至六葉;合璧本,第四冊,第1907頁;明刻《玉海》,卷一百一,第五至六葉;《四庫全書》,第945冊,第665頁)
傳璋按:此則《正義》當原系于《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浴乎沂風乎舞雩”句下(中華本《史記》,第七冊,第2210頁)。《史記》三家注合刊本此下有《集解》引包氏釋曾點語意,而不及雩壇位置。張守節(jié)《史記正義》為裴骃《集解》補注,惜宋人合刻時未收。
46.《玉海》卷一百二《郊祀·漢六祠》
《郊祀志》:諸所興如薄忌泰一及三一、冥羊、馬行、赤星,五,寬舒之祠官以歲時致禮。凡六祠,皆太祝領之。
《正義》:赤星即靈星。祠“五”者,謂太一、三一、羊、馬行、赤星,并令祠官寬舒致禮。“凡六祠”,謂后土兼上五為六。后土在汾陰,非寬舒領祠,故別言“凡六祠”。(元刊《玉海》,卷一百二,第二十七葉;合璧本,第四冊,第1936頁;明刻《玉海》,卷一百二,第二十七葉;《四庫全書》,第945冊,第700頁)
傳璋按:此則《正義》當原系于《史記·封禪書》“今天子所興祠……凡六祠皆太祝領之”句下(中華本《史記》,第四冊,第1403頁)。有《索隱》:“案:《郊祀志》云‘祠官寬舒議祠后土為五壇’,故謂之‘五寬舒祠官’。”司馬貞《史》文斷句有誤,故注文不知所云。張守節(jié)《正義》則對“五祠”、“六祠”注釋精準。又按:瀧川資言于《史記·封禪書》“凡六祠”句下,輯有《正義》佚文:“謂后土兼上五凡六祠也。后土在汾陰,非寬舒領祠,故別言‘凡六祠’。”(參見張衍田《史記正義佚文輯校》,第57-58頁)
47.《玉海》卷一百十一《學校·周辟雍》
《史記·封禪書》:豐滈有天子辟池。《索隱》曰:即周天子辟雍之地。
《正義》曰:周文、武豐、滈皆置辟雍,故秦立祠。(元刊《玉海》,卷一百十一,第十三葉;合璧本,第四冊,第2113頁;明刻《玉海》,卷一百十一,第十三葉;《四庫全書》,第946冊,第9頁)
傳璋按:此則《正義》當原系于《史記·封禪書》“灃、滈有昭明、天子辟池”句下(中華本《史記》,第四冊,第1375頁)。此下有《索隱》:“樂產云未聞。顧氏以為璧池即滈池,所謂‘華陰平舒道逢使者,持璧以遺滈池君’,故曰璧池。今謂天子辟池,即周天子辟雍之地。故周文王都酆,武王都滈,既立靈臺,則亦有辟雍耳。張衡亦以辟池為雍。”此則《正義》內容不及《索隱》豐富,但指出“天子辟池”為秦時神祠之一,可補《索隱》未及之義。惜被宋人合刻《史記》三家注者割棄。
48.《玉海》卷一百三十五《官制·詔封·漢十八侯位次》
《漢功臣表》……申之以丹書之信,重之以白馬之盟,又作十八侯之位次。
《史記正義》載姚察說同。(元刊《玉海》,卷一百三十五,第六葉;合璧本,第五冊,第2581頁;明刻《玉海》,卷一百三十五,第六葉;《四庫全書》,第946冊,第551頁)
傳璋按:《玉海》敘文所稱《漢功臣表》,指《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史記正義》載姚察說同”者,指同于《漢表》“又作十八侯之位次”句下顏師古為十八侯姓名及位次所作的注釋。姚察,《陳書》有傳,陳時任吏部尚書,領大著作,學兼儒史,所著《漢書訓纂》三十卷,見重于世。此則《正義》所引姚察說當原系于《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表首“侯第”欄。因與表首“侯第”欄《索隱》所引姚氏所敘十八侯位次文字全同,故宋人附刻單本《史記正義》于《史記集解索隱》者棄而不錄。現(xiàn)將《玉海》提而未錄的《史記正義》“姚察說”輯佚于下:
《史記正義》:按:姚察曰:“蕭何第一,曹參二,張敖三,周勃四,樊噲五,酈商六,奚涓七,夏侯嬰八,灌嬰九,傅寬十,靳歙十一,王陵十二,陳武十三,王吸十四,薛歐十五,周昌十六,丁復十七,蠱逢十八。
49.《玉海》卷一百三十五《官制·詔封·漢十八侯位次》
《史記正義》云:《楚漢春秋》無奚涓、薛歐,有韓欽、陳潰,而王吸為王崇,丁復為丁侵。(元刊《玉海》,卷一百三十五,第六葉;合璧本,第五冊,第2581頁;明刻《玉海》,卷一百三十五,第六葉;《四庫全書》,第946冊,第551頁)
傳璋按:此則《正義》亦當原系于《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之“侯第”欄首,張守節(jié)于先引姚察說后,再引所見陸賈《楚漢春秋》所載高祖功臣侯封的原初紀錄,作為“一說”備考。宋人合刊《史記》三家注時亦予割棄。
50.《玉海》卷一百三十五《官制·詔封·列侯位次簿》
《史記世家》:列侯畢已受封,及奏位次,皆曰:曹參第一。鄂千秋進曰云云,蕭何第一,曹參次之。
《史記正義》:顧胤云:“高祖止定十八侯,呂后令陳平終竟第錄。”按:高祖定十八侯,陳平定一百一十九侯,凡一百三十七人八人孝惠、高后封。功臣凡一百四十三人,一百二十九預侯第,十四人不預有罪及改封王。西漢列侯及建武而存者,平陽、建平、富平、爰戚、高昌、歸德、義成、長羅。(元刊《玉海》,卷一百三十五,第七葉;合璧本,第五冊,第2582頁;明刻《玉海》,卷一百三十五,第七葉;《四庫全書》,第946冊,第552頁)
傳璋按:此則《正義》當原系于《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之“功第”欄首引姚察說、《楚漢春秋》說之后。
51.《玉海》卷一百四十《兵制·兵法·呂尚七術》
《史記正義》:《六韜》、《三略》、《陰符》、《七術》之屬。《鬼谷子》有《陰符》、《七術》,有《揣》及《摩》二篇。(元刊《玉海》,卷一百四十,第六葉;合璧本,第五冊,第2697頁;明刻《玉海》,卷一百四十,第六葉;《四庫全書》,第946冊,第686頁)
傳璋按:此則《正義》當原系于《史記·蘇秦列傳》“得周書《陰符》”句下。此下有《集解》、《索隱》而無此《正義》。蓋宋人以《史記正義》附刻于《史記集解索隱》時為避復重而不取此《正義》。又按:瀧川資言所輯《史記正義佚存》在《史記·蘇秦列傳》“以出揣摩”句下有佚文《正義》:“《鬼谷子》有《揣》及《摩》二篇,言揣諸侯之情,以其所欲切摩,為揣之術也。按:《鬼谷子》乃蘇秦之書明矣。”(參見張衍田《史記正義佚文輯校》第226頁)
52.《玉海》卷一百四十四《兵制·講武·漢講武場》
《史記正義》:《功臣表》:《括地志》云:“故平縣城,在洛州偃師縣西北二十五里,有漢祖講武場。”《水經注》:“平縣有高祖講武場。”(元刊《玉海》,卷一百四十四,第十一葉;合璧本,第五冊,第2750頁;明刻《玉海》,卷一百四十四,第十一葉;《四庫全書》,第946冊,第750頁)
傳璋按:此則《正義》當原系于《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國名”欄“平”國下(見中華本《史記》,第三冊,第917頁)。平侯名沛嘉,以“兵初起,以舍人從擊秦,以郎中入漢,以將軍定諸侯,守洛陽,功侯”。《史記》三家注合刊本“平”下有《索隱》:“縣名,屬河南。”而無《正義》,蓋闕。考三注合刊本《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表首第一欄為“國名”,下有《正義》:“此國名匡左行一道,咸是諸侯所封國名也。”據(jù)此,再參照《玉海》所引“平國”《正義》,可知單本《史記正義》為此表“國名”欄所有漢時封國(縣)均按唐時地名對應設注解說。而宋人以《史記正義》附刻于《史記集解索隱》時,因行政區(qū)劃與唐時不同,地名亦甚多變化,張守節(jié)按唐時地名所對釋的漢時地名對宋人已無多大參考價值,故一概刪削不錄。幸王應麟《玉海》釋漢高祖講武場地望而征引了“平”國的《正義》,使我們得窺單本《史記正義》所作《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的舊貌。
53.《玉海》卷一百五十五《宮室·漢長樂官》
《紀》:高祖五年五月,車駕西都長安。后九月,徙諸侯子關中。治長樂宮。
《正義》:長樂宮,在長安縣西北十五里。(元刊《玉海》,卷一百五十五,第九葉;合璧本,第六冊,第2945頁;明刻《玉海》,卷一百五十五,第九葉;《四庫全書》,第947冊,第82頁)
傳璋按:此則《正義》當原系于《史記·高祖本紀》七年“長樂宮成”句下。三家注合刊本此下無《集解》、《索隱》,此則《正義》也未附刻。《史記·樗里子列傳》“樗里子葬渭南章臺之東。……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其下有《正義》:“漢長樂宮在長安縣西北十五里。”(見中華本《史記》,第七冊,第2310頁)與《玉海》“漢長樂宮”條下《正義》注同。《高祖本紀》“長樂宮成”,為“長樂宮”名首見,按《史記正義》注釋體例,應于其下設注。《史記》三家注本無《正義》注,蓋脫漏。《樗里子列傳》“長樂宮在其東”句下出《正義》,乃《史記正義》同一事典在不同篇卷重注例。
54.《玉海》卷一百五十五《宮室·漢沛宮》
《禮樂志》:孝惠時以沛宮為原廟,令歌兒習吹相和,以百二十人為員。
《史記正義》:《十三州志》云:“漢興四年,改泗水為沛郡,理相城,故以沛為小沛。”《括地志》云:“泗水亭,在徐州沛縣東一百步,有高祖廟。”(元刊《玉海》,卷一百五十五,第十八葉;合璧本,第六冊,第2949頁;明刻《玉海》,卷一百五十五,第十八葉;《四庫全書》,第947冊,第88頁)
傳璋按:此則《正義》當原系于《史記·高祖本紀》“為泗水亭長”句下。《史記》三家注合刊本此下有《正義》:“秦法,十里一亭,十亭一鄉(xiāng)。亭長,主亭之吏。高祖為泗水亭長也。《國語》有‘寓室’,即今之亭也。亭長,蓋今里長也。民有訟諍,吏留平辨,得成其政。《括地志》云:‘泗水亭在徐州沛縣東一百步,有高祖廟也。’”(見中華本《史記》,第二冊,第343頁)合刻本散佚“十三州志”云云24字。
55.《玉海》卷一百五十六《宮室·漢宜春宮》
《司馬相如傳》:臨曲江之隑州兮,望南山之參差張揖曰:隑,長也。苑中有曲江之象,中有長州。 師古曰:臨曲岸之州,今謂曲江。
《史記正義》:曲池,武帝造,周迴五里,在宜春苑中。(元刊《玉海》,卷一百五十六,第一葉;合璧本,第六冊,第9957頁;明刻《玉海》,卷一百五十六,第一葉;《四庫全書》,第947冊,第96頁)
傳璋按:此則《正義》當原系于《史記·司馬相如列傳》之《哀二世賦》“臨曲江之隑州兮”句下。此句《史記》三家注合刊本有《集解》與《索隱》(見中華本《史記》,第九冊,第3055頁),而無《正義》。此為宋人以《史記正義》附刻于《史記集解索隱》時割棄。
56.《玉海》卷一百六十二《宮室·臺·魯觀臺》
《史記》:魏伐宋,取儀臺。
《正義》:靈臺也。《莊子》:義臺,路寢。(元刊《玉海》,卷一百六十二,第八葉;合璧本,第六冊,第3078頁;明刻《玉海》,卷一百六十二,第八葉;《四庫全書》,第947冊,第241頁)
傳璋按:此則《正義》當原系于《史記·魏世家》“伐宋取儀臺”句下。此下有《集解》:“徐廣曰:‘一作義臺。’”有《索隱》:“按:年表作‘義臺’,然義臺見《莊子》,司馬彪亦曰‘臺名’,郭象云:‘義臺,靈臺。’”(見中華本《史記》,第六冊,第1844頁)而無《正義》。此則《正義》因與《索隱》涉同而割棄。又按:呂祖謙《大事記解題》卷二周顯王四年下有《史記正義》:“郭象曰:‘儀臺,靈臺也。’”當與《玉海》所引同一來源。
57.《玉海》卷一百六十二《宮室·臺·楚陽云之臺》
《子虛賦》:楚王乃登陽云之臺。
《正義》:言其高出云之陽。(元刊《玉海》,卷一百六十二,第九葉;合璧本,第六冊,第3079頁;明刻《玉海》,卷一百六十二,第九葉;《四庫全書》,第947冊,第241頁)
傳璋按:此則《正義》當原系于《史記·司馬相如列傳》“于是楚王乃登陽云之臺”句下。此下有《集解》:“徐廣曰:‘宋玉云楚王游于陽云之臺。’骃案:郭璞曰:‘在云夢之中。’”引郭璞釋陽云臺的所在方位(見中華本《史記》,第九冊,第3014頁),而無《正義》。《玉海》征引之《正義》釋此臺得名之由。宋人合刻時未附入而成佚文。
58.《玉海》卷一百六十二《宮室·漢鴻臺》
《史記正義》:甘泉有瑤臺。(元刊《玉海》,卷一百六十二,第十三葉;合璧本,第六冊,第3081頁;明刻《玉海》,卷一百六十二,第十三葉;《四庫全書》,第947冊,第243頁)
傳璋按:此則《正義》當原系于《史記·封禪書》“又作甘泉宮,中為臺室”句下(中華本《史記》,第四冊,第1388頁)。《史記》三家注合刊本此下無注。
59.《玉海》卷一百六十二《宮室·漢龍臺》
《司馬相如傳》:《上林賦》“登龍臺”。《注》:“張揖曰:‘觀名,在豐水西北,近渭。’”
《史記正義》:《三輔故事》云:“龍臺,高六丈,去豐水五里。漢時龍見陂中,故作此臺。”《括地志》云:“龍臺,一名龍臺觀。在雍州鄠縣東北三十五里。”(元刊《玉海》,卷一百六十二,第二十葉;合璧本,第六冊,第3084頁;明刻《玉海》,卷一百六十二,第二十葉;《四庫全書》,第947冊,第248頁)
傳璋按:此則《正義》當原系于《史記·司馬相如列傳》中《上林賦》“登龍臺”句下。此句有《集解》,如《玉海》敘文所稱之“《注》”。張守節(jié)嫌《集解》所引張揖《漢書音義》釋“龍臺”語焉不詳,故引《三輔故事》說明興建龍臺的原由,又引《括地志》指出其具體位置。此則《正義》是對《集解》的極好補充,正符《史記正義序》“引致旁通”的旨趣。又明刻《玉海》“故作此臺”句中“此”字訛作“比”字。
60.《玉海》卷一百六十四《宮室·樓》
漢井幹樓
《史記正義》:幹,司馬彪云:“井欄也。”《關中記》云:“宮北有井幹臺,高五十丈,積木為樓,言筑累方木,轉于交架如幹。”(元刊《玉海》,卷一百六十四,第二葉;合璧本,第六冊,第3113頁;明刻《玉海》,卷一百六十四,第二葉;《四庫全書》,第947冊,第283頁)
傳璋按:此則《正義》當原系于《史記·孝武本紀》作建章宮“井幹樓”句下。其下有《索隱》:“《關中記》:‘宮北有井幹臺,高五十丈,積木為樓。’言筑累萬木,轉相交架,如井幹。司馬彪注《莊子》云:‘井幹,井闌也。’又崔譔云:‘井以四邊為幹,猶筑墻之有楨幹。’又諸本作‘榦’。音[韓]。《說文》云:‘幹,井橋。’”(見中華本《史記》,第二冊,第483頁)此則《正義》釋文與《索隱》相近,而義無加進,故宋人以《史記正義》附刻于《史記集解索隱》者棄而不取。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王應麟在《玉海》中為漢井幹樓作注時只取《正義》而舍《索隱》,個中原由頗可玩味。又,《正義》“言筑方木”句中“方”字,當為“萬”字傳寫之訛。“萬”乃六朝“萬”字俗體,隋唐以降一直沿用,《索隱》亦作“萬木”可作參證。
61.《玉海》卷一百六十六《宮室·觀·漢甘泉四觀》
《史記》:甘泉更置前殿,始廣諸宮室。
《正義》:揚雄云:“甘泉本秦離宮,既奢泰。武帝增通天臺、迎風宮。近則有洪涯、儲胥,遠則有石關、封巒、鳷鵲、露寒、棠梨等觀。又有高華、白虎、溫德、相思觀,曾城、走狗、天梯、瑤臺等。”《黃圖》:“武帝先作迎風館于甘泉山,后加露寒、儲胥二館。建元中作石關、封巒、鳷鵲觀。”(元刊《玉海》,卷一百六十六,第二葉;合璧本,第六冊,第3143頁;明刻《玉海》,卷一百六十六,第二葉;《四庫全書》,第947冊,第318頁)
傳璋按:此則《正義》當原系于《史記·孝武本紀》“于是甘泉更置前殿,始廣諸宮室”句下(中華本《史記》,第二冊,第479頁)。《史記》三家注合刊本于此有《索隱》引“姚氏案:揚雄”云云,與本則《正義》注文同,唯未征引《黃圖》。宋人合刻三家注時,因上述《正義》與《索隱》泰半相同,而未附刻。
62.《玉海》卷一百六十六《宮室·漢延壽觀》
《史記》益延壽觀。
《正義》:《括地志》云:“延壽觀在雍州云陽縣西北八十一里,通天臺西八十步。”(元刊《玉海》,卷一百六十六,第三葉;合璧本,第六冊,第3144頁;明刻《玉海》,卷一百六十六,第三葉;《四庫全書》,第947冊,第318頁)
傳璋按:此則《正義》當原系于《史記·孝武本紀》“甘泉則作益延壽觀”句下(中華本《史記》,第二冊,第478頁)。《史記》三注合刊本此句下無注。《史記·封禪書》“甘泉則作益延壽觀”句下有《索隱》:“小顏以為作益壽、延壽二館。案:《漢武故事》云:‘作延壽觀,高三十丈。’”與上引《正義》不同。宋人合《史記正義》于《史記集解索隱》者,于《孝武本記》相應文句下未刻入《正義》,遂成佚文。幸《玉海》征引方得以重見天日。
63.《玉海》卷一百六十九《宮室·門闕·漢長安十二門》
《黃圖》:[長安城]北出西頭第一門曰橫門,門外有橋曰橫橋。《史記》曰:橫城門。
《史記正義》:秦興樂宮北門對橫橋。(元刊《玉海》,卷一百六十九,第二十二葉;合璧本,第六冊,第3201頁;明刻《玉海》,卷一百六十九,第二十二葉;《四庫全書》,第947冊,第385頁)
傳璋按:此則《正義》當原系于《史記·外戚世家》“褚先生曰:蹕道先驅旄騎出橫城門”句下。《史記》三家注合刊本此下有《集解》:“如淳曰:‘橫音光。《三輔黃圖》云北面西頭門。”有《正義》:“《括地志》云:‘渭橋本名橫橋,架渭水上,在雍州咸陽縣東南二十二里。’”(見中華本《史記》第六冊,第1982頁)與《玉海》所引《正義》不同,可相互補充。
64.《玉海》卷一百六十九《宮室·門闕·漢建章鳳闕》
《文選注》:魏文帝歌曰:“長安城西有雙圓闕,上有雙銅爵,一鳴五穀生,再鳴五穀熟。”《關中記》:“建章宮圓闕臨北道,鳳在上。閶闔門內東出有折風闕,一名別風。”
《史記正義》:《三秦記》云:“柏梁臺有銅鳳,因名鳳闕。”(元刊《玉海》,卷一百六十九,第二十六葉;合璧本,第六冊,第3203頁;明刻《玉海》,卷一百六十九,第二十六葉;《四庫全書》,第947冊,第387頁)
傳璋按:此則《正義》當原系于《史記·孝武本紀》“于是作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前殿度高未央。其東則鳳闕,高二十余丈”句下。《史記》三家注合刊本此下有《索隱》長注(見中華本《史記》,第二冊,第482頁),而無《正義》。《索隱》注引用《三輔黃圖》、《關中記》、《西京賦》、《三輔故事》以釋“鳳闕”,此則《正義》則引《三秦記》指出“鳳闕”即“柏梁臺”,可備一說,而宋人合刻三家注時未收錄。
65.《玉海》卷一百七十三《宮室·城·周公城》
《史記正義》:《括地志》云:“周公故城在岐山縣北九里,召公故城在岐山縣西南十里。此周、召之采邑也。”(元刊《玉海》,卷一百七十三,第八葉;合璧本,第六冊,第3272頁;明刻《玉海》,卷一百七十三,第八葉;《四庫全書》,第947冊,第467頁)
傳璋按:此則《正義》當原系于《史記·魯周公世家》“周公旦者,周武王弟也”句下。《史記》三家注合刊本此下有《集解》:“譙周曰:‘以太王所居周地為其采邑,故謂周公。’”有《索隱》:“周,地名,在岐山之陽,本太王所居,后以為周公之菜邑,故曰周公。即今之扶風雍東北故周城是也。謚曰周文公,見《國語》(見中華本《史記》,第五冊,第1515頁)。《玉海》所引《正義》指出周公城、召公城的具體位置,可補《集解》、《索隱》注文之不足,卻為宋人合刊三家注者所遺棄,殊為可惜。又按:瀧川資言于此句下亦輯得《正義》佚文:“《括地志》云:周公城在岐山縣北九里。”(參見張衍田《史記正義佚文輯校》,第84頁)
66.《玉海》卷一百七十三《宮室·榆谿舊塞》
《史記》云:按榆谷舊河塞。
《正義》:今榆林縣東四十里。(元刊《玉海》,卷一百七十三,第十六葉;合璧本,第六冊,第3276頁;明刻《玉海》,卷一百七十三,第十六葉;《四庫全書》,第947冊,第472頁)
傳璋按:此則《正義》當原系于《史記·衛(wèi)將軍驃騎列傳》“按榆谿舊塞”句下。《史記》三家注合刊本此下有《集解》:“如淳曰:‘案,行也。榆谿,舊塞名。或曰按,尋也。’”有《索隱》:“按榆谷舊塞。如淳云:‘按,行也,尋也。榆谷,舊塞名也。’案:《水經》云‘上郡之北有諸次水,東經榆林塞為榆谿’,是榆谷舊塞也。”(中華本《史記》,第九冊,第2924頁)《集隱》與《索隱》只引漢魏人舊注,《正義》則按唐時地名、方位重新作注。然宋人合刻者并不理會,徑行刪削。又,“今榆林縣”,《文淵閣四庫全書》作“經榆林縣”,因音同訛“今”為“經”。
67.《玉海》卷一百七十三《宮室·城·五原塞》
《匈奴傳》:是歲太初三年也。句黎湖單于立,漢使光祿徐自為出五原塞數(shù)百里,遠者千里,筑城障列亭。
《史記正義》:五原塞即五原郡榆林塞也。在勝州榆林縣四十里。《晉太康地志》:“自北地郡北行九百里得五原塞。”(元刊《玉海》,卷一百七十三,第二十葉;合璧本,第六冊,第3278頁;明刻《玉海》,卷一百七十三,第二十葉;《四庫全書》,第947冊,第474頁)
傳璋按:此則《正義》當原系于《史記·匈奴列傳》“漢使光祿徐自為出五原塞”句下。《史記》三家注合刊本此下有《正義》:“即五原郡榆林塞也。在勝州榆林縣四十里。”(見中華本《史記》,第九冊,第2916頁)而佚《玉海》征引《正義》所引《晉太康地志》文。
三、《玉海》征引《史記正義》佚文的價值
《玉海》征引的這批不為《史記》三家注合刻本收錄的六十余條《史記正義》佚文,對于司馬遷與《史記》研究具有重大價值。約略計之則有如下數(shù)端:
1.對深入理解《史》文大有裨益
匡補裴注,拾遺補闕。如第2條“堯刻漏”。《史記·五帝本紀》“日永,星火,以正中夏”、“日短,星昴,以正中冬”,上句下有《集解》:“馬融、王肅謂日長晝漏六十刻,鄭玄曰四十五刻。”下句下有《集解》:“馬融、王肅謂日短晝漏四十刻。鄭玄曰四十五刻,失之。”“日永”指夏至,白晝最長;“日短”指冬至,白晝最短。其長其短,古人以漏刻之數(shù)計之。馬融、王肅與鄭玄計數(shù)不同,裴骃認為鄭玄“失之”。《玉海》所引《正義》佚文,針對裴骃對鄭玄的指摘,作出按斷:“馬融以昏明為限,鄭玄以日出入為限,故有五刻之差。”指出二說有異,實因計時所取標準不同所致,鄭玄并未“失之”。佚文對裴注有補正之功。又如第18條“畿封”。《史記·燕召公世家》“自陜以西,召公主之;自陜以東,周公主之”,《集解》引漢何休說:“陜者,蓋今弘農陜縣是也。”而《正義》佚文在引“《括地志》:陜原在陜縣西南二十五里”后,明確指出周、召二公分治京畿的標界是“分陜不因其城,乃以原為界”。此注實有助于理解《史》文分陜之義。再如第23條“漢春秋決獄”。《史記·儒林列傳》載董仲舒弟子呂步舒持節(jié)裁決淮南王謀反大獄,“以《春秋》之義正之”。此“《春秋》之義”何指?今本三家注無一作出說明。而《正義》佚文于其下注引“《七錄》曰:《春秋斷獄》五卷”,讀者則可明瞭呂步舒秉承的“《春秋》之義”,實即其師董仲舒的大著《春秋斷獄》。
古典幽微,竊探其美。如第32條“黃帝合符釜山”《正義》佚文,先釋“合符”所為何事——“謂合諸侯符瑞于釜山封禪也”,次引《括地志》及《洞冥記》,點出釜山所在方位及其神異之處,最后說明為何黃帝合符必于釜山的原因。注解委曲詳明,可增進讀者對《史》文的理解。又如第46條“漢六祠”所引《正義》佚文,所釋《史》文長句錯綜復雜,頗不易解。《史記》三家注合刊本此下有《索隱》,司馬貞沒有讀懂《史》文,妄摘“五寬舒之祠官”五字為句,又節(jié)引《漢書·郊祀志》不相干之文,妄加比附:“案:《郊祀志》云‘祠官寬舒議祠后土為五壇’,故謂之‘五寬舒祠官’也。”簡直不知所云。而張守節(jié)《正義》佚文,在正確斷句、厘清文意的基礎上謹慎下注:“祠‘五’者,謂太一、三一、羊、馬行、赤星,并令祠官寬舒致禮。‘凡六祠’,謂后土兼上五為六。后土在汾陰,非寬舒領祠,故別言‘凡六祠’。”注文簡要精準,于后學大有裨益。
2.為古史疑難地名提供準確答案
張守節(jié)長于輿地之學。王應麟《玉海》征引《正義》佚文涉及古史地名者多達42條,占全部佚文的六成,大都為已成廢墟的秦漢宮觀、祠廟、關塞,或久已淤塞的上古河道。張守節(jié)征引《括地志》按唐時方位一一注明,或為《集解》補注,或為疑難古史地名提出探尋線索。
為解釋岐異的地名所在作出裁斷。如第6條“龍門山”。《集解》于《夏本紀》引《尚書·禹貢》孔安國注:“龍門山在河東之西界。”由此引發(fā)“龍門山在絳州龍門縣”的說法;《集解》于《太史公自序》“遷生龍門”下又引“徐廣曰:在馮翊夏陽縣”,則山又在河西,由此《括地志》稱“龍門,在同州韓城縣北五十里”,《索隱》亦主此說。河東、河西二說各有所據(jù)。《正義》佚文先兼引二說,然后根據(jù)龍門山兼跨冀、雍二州實際的山形走勢,指出“其山更黃河,夏禹所鑿者也”,予以調停,最后以“龍門山在夏陽縣”作出裁斷,為“遷生龍門”的龍門的確切所在作出結論。這條佚文亦足以破除后世以為司馬遷生于河東河津縣之惑。
為殘闕的古注提供補闕的原文。如今本《史記·淮南衡山列傳》“陳定發(fā)南陽兵守武關”句下有《正義》:“故武關在商州商洛縣東九十里,春秋時。闕文。”“春秋時”以下文字殘闕,南宋黃善夫合刻《史記》三家注時已然如此,故不得已以“闕文”二字標示,所闕何字、所闕多少,不得而知。而第13條《正義》佚文原當系于《史記·高祖本紀》“乃用張良計……因襲攻武關”句下。所引“《括地志》曰:故武關在商州商洛縣東九十里,春秋時少習”與《淮南傳》“武關”句下《正義》“春秋時”之前文字全同,唯多“少習”二字,昭示“少習”二字正是今本《史記·淮南傳》之《正義》所“闕”之“文”。“少習”,山名,因山勢置關曰“武關”。今后若整理《史記》三家注本,除應在《高祖本紀》“武關”下補上《正義》佚文,還應為《淮南衡山列傳》之《正義》“闕文”補足“少習”二字。又如《史記·河渠書》太史公“上姑蘇,望五湖”,何為“五湖”,歷來釋說紛紜,至有以“五湖”為“太湖”之異名者。第11條《正義》佚文,認為“五湖”系與太湖相連的五個小湖“游、莫、貢、、胥”的共名,“在蘇州西四十里”,實為“太湖東岸五灣”。按:姑蘇是蘇州西南的一座小山名,吳王闔閭、夫差曾在此山范圍內興建離宮別館,而山西太湖湖濱的“五湖”曾是春秋末期吳越水戰(zhàn)的戰(zhàn)場所在。太史公“上姑蘇,望五湖”的目的之一,當是考察吳越爭霸的史跡。張守節(jié)的這條《正義》佚文頗有助于古史考證。
為久已廢棄的秦漢關塞所在指點線索。第67條《正義》佚文,原當系于《匈奴列傳》“漢使光祿徐自為出五原塞”句下,《史記》三家注本此下有《正義》,與佚文《正義》前段相同:五原塞“即五原郡榆林塞。在勝州榆林縣四十里”。但唐代勝州在朔方邊地,不易尋訪。佚文《正義》征引《晉太康地志》“自北地郡北行九百里得五原塞”。北地郡郡治在唐代京師長安以北不足二百里處,自此為起點北行,就為尋覓考察五原古塞指明了方向和路徑。
3.《正義》佚文的發(fā)現(xiàn)有助于了解單本《史記正義》的舊貌
《史記》三家注合刻本《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表首首欄為“國名”,其下有《正義》:“此國名匡左行一道,咸是諸侯所封國名也。”然而今本每個侯國國名之下只有《索隱》據(jù)《漢書·地理志》、《晉書地道志》等注出封國所在縣邑名稱,而《正義》卻一無所有。這是否單本《正義》原貌呢?答案是否定的。且看《玉海》征引《正義》佚文第52條。《玉海》在“兵制”門之“漢講武場”目征引《史記正義》:“《括地志》云:‘故平縣城,在洛州偃師縣西北二十五里,有漢祖講武場。’”《玉海》點明此條《正義》出自《功臣表》。此表非他,乃太史公在《史記》中為漢王朝所制的第一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張守節(jié)征引《括地志》與《水經注》,為高祖所封第三十二位的平侯沛嘉的封國平縣所在作注。這條被《史記》三家注合刻者刪削的“平國”《正義》,卻透露了重要的信息。聯(lián)系《史記正義序》“郡國城邑委曲申明”的注例以及《功臣表》表首“國名”欄《正義》的提示,可以肯定,張守節(jié)《正義》單本必為高祖所封143侯侯國所在一一設注點明與漢邑對應的唐時縣名。
宋人將《正義》附刻于《史記集解索隱》二家注本時,因宋代的行政區(qū)劃與唐時不同,縣名也變化甚大,《正義》所釋與漢邑對應的唐時地名,對于宋人已無多大參考價值,為減少三家注本全書篇幅以降低成本,《功臣表》“國名”欄的所有《正義》注文一概削去不錄。出于同樣的原因,《惠景間侯者年表第七》所封93位侯國國邑《正義》、《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第八》所封119位侯國國邑《正義》、《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第九》所封162位侯國國邑《正義》,也一概刪削不錄。漢世侯者諸表被削去的侯國封邑《正義》,總數(shù)多達517條。
宋人合刻《史記》三家注時,不僅全部刪削了張守節(jié)為漢世侯國封邑所作的《正義》,而且《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表首“侯第”欄單本《史記正義》的注文也不予收錄。第48條《正義》佚文,系從陳隋間學者姚察《漢書訓纂》采輯的漢高祖所封十八侯姓名及位次,與《索隱》所引姚氏說,二者同源,宋人為避重復,不錄《正義》猶有可說;以下兩條《正義》的被刪,則反映了合刻者的淺識。第49條《正義》佚文,系錄自陸賈《楚漢春秋》關于十八侯姓名、位次的異說。據(jù)《后漢書·班彪傳》“漢興,定天下,太中大夫陸賈記錄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可知《楚漢春秋》作于天下初定不久之時。陸賈以當時人記當時事,自較此后陳平受命呂后所定列侯等列更為可信。又如第50條《正義》佚文,張守節(jié)先引顧胤說,然后加長“按”指出:高祖所定列侯數(shù),陳平所定列侯數(shù),總數(shù)多少,又自注其中“八人,孝惠,高后封”;功臣表總錄一百四十三人,預侯第者一百二十九人,不預者十四人,又自注不預的原因是“有罪及改封王”;最后點出高祖功臣一百四十三侯,到東漢光武帝建武年間而存者僅余平陽、建平等八侯。這條敘事詳明的《正義》,與高祖封侯之誓“使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寧,爰及苗裔”形成鮮明對照,可以幫助證明史事考證的《正義》亦被合刻者棄而不錄,殊為可惜。這些被刪削的《正義》佚文,可使后人復睹單本《史記正義》的部分原貌。
今后整理《史記》三家注合刊本時,《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侯第”欄被削的三條《正義》佚文或可恢復,而“國名”欄被刪削的517條《正義》,除“平”侯條可以增補外,其余516條恐怕是永遠消亡于天埌之間了。
4.為瀧川資言所輯《史記正義佚存》增加了可信度
日本學者瀧川資言從彼邦公、私所藏《史記》古板本、古鈔本匡郭內外標注輯得《史記》三家注合刻本所遺佚的《正義》一千余條,散入《史記會注考證》相應《史》文之下。這原本可稱之為二十世紀《史記》研究史上的重大發(fā)現(xiàn)。以程金造為代表的大陸學者,卻認為瀧川資言所輯得的《正義》佚文“只有十分之一二是可靠的,絕大部分是讀者的雜鈔和注解”。筆者十多年前曾針對程氏的“偽托說”作長篇《平議》予以辨析,本文“前言”業(yè)已提及。值得注意的是,《玉海》所征引的《正義》佚文,其 11、12、15、23、25、27、41、46、51、65,凡10條,瀧川資言《史記正義佚存》亦皆全部或部分輯得。然而瀧川資言輯佚《正義》及撰《史記會注考證》時,并未從王應麟《玉海》取資。這可以證明瀧川資言從日本存世的《史記》古板本、古鈔本匡郭內外標注抄錄的《正義》佚文,與《玉海》征引的《正義》佚文系出同源,皆過錄自張守節(jié)單本《史記正義》。這批輯自《玉海》的《正義》佚文的發(fā)現(xiàn),也為瀧川資言的《史記正義佚存》增添了可信度。
5.為考定司馬遷的生年提供了確鑿的文獻根據(jù)
司馬遷的生年,由于班固《漢書·司馬遷傳》失載,遂成千古疑案。自王國維于1916年發(fā)表《太史公系年考略》,史公生年疑案的澄清方現(xiàn)轉機。王先生從《史記·太史公自序》三家注本中發(fā)現(xiàn)兩則唐人古注:一為“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句下司馬貞《索隱》:“《博物志》:‘太史令,茂陵顯武里,大夫司馬遷,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一為下文“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句下張守節(jié)《正義》:“按遷年四十二歲。”若按《索隱》,元封三年(前108)司馬遷繼任太史令時“年二十八”,則當生于漢武帝建元六年(前135);若按《正義》,太初元年(前104)司馬遷始撰《太史公書》時“年四十二”,則當生于景帝中元五年(前145)。王氏認為《正義》與《索隱》同本張華《博物志》,但推算史公生年卻相差整整十歲,二者必有一錯。王氏以《正義》為是,而疑今本《索隱》“年二十八”乃“年三十八”之訛,理由是“三訛為二,乃事之常;三訛為四,則于理為遠”,從而得出結論:“史公生年當為孝景中五年,而非孝武建元六年矣。”
將近一個世紀以來,王國維的司馬遷生于景帝中元五年(前145)說,被譽為“方法正確、邏輯嚴密、引證可靠”而為中外諸多學者信而不疑。郭沫若先生曾于1955年發(fā)表《太史公行年考有問題》,提出司馬遷生于武帝建元六年(前135)說,但其論證邏輯并未脫離王國維數(shù)字訛誤說的窠臼,故難以服眾。
其實王國維的司馬遷生于景帝中元五年說存在致命的缺陷:并無任何文獻依據(jù),卻改字立說,有違考據(jù)學通則;其為史公行歷的排比,亦疏誤頻出。筆者于1988年向“全國《史記》學術研討會(西安)”提報論文《司馬遷生于武帝建元六年新證》(載《陜西師大學報·全國〈史記〉學術研討會論文專輯》,1988年增刊;又載《史記研究集成》第一卷,華文出版社,2005年第1版),另辟蹊徑,從《太史公自序》及《報任安書》中找到測算司馬遷生年的三個標準數(shù)據(jù):“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于是仕為郎中”、“待罪輦轂下二十余年”,和一個基準點:《報任安書》作于征和二年(前91),以史公關于自身行跡的自敘為本證,以《索隱》與《正義》為佐證,通過對史公移居茂陵、從學問故、壯游入仕、友朋交往等等方面行跡的清理,證實《索隱》所引《博物志》元封三年“年二十八”數(shù)字無訛,與史公自敘若合符節(jié),司馬遷實生于武帝建元六年(前135)而非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對于《索隱》與《正義》在史公生年上出現(xiàn)“十年”之差的原因,筆者在論文第五節(jié)“從書法史的角度看《正義》‘按遷年四十二歲’系‘按遷年丗二歲’之訛”,從書體演變的角度,通過對廿(二十)、丗(三十)、卌(四十)三個數(shù)字書寫形式變化軌跡的考察,運用大量實證作出了合理的解釋。筆者在該節(jié)中曾作如下推斷:
著錄有“太史令,茂陵顯武里,大夫司馬遷,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的寫本《博物志》,司馬貞作《索隱》時征引了,張守節(jié)也會見讀過,他據(jù)《博物志》所作的按語原作“按遷年丗二歲”。唐代《正義》單本與《索隱》并元“十歲”之差。差訛發(fā)生在由唐人寫本到宋人刻本的轉換期。
當然,這個判斷還需確鑿的文獻根據(jù)支撐。
1995年,筆者向“紀念司馬遷誕辰214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西安)”呈送論文《從書體演變角度論〈索隱〉、〈正義〉的十年之差——兼為司馬遷生于武帝建元六年說補證》(載臺灣《大陸雜志》第九十卷第四期,1995年4月出版;又載《司馬遷與〈史記〉論集》第三輯,陜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10月出版)、《太史公“二十歲前在故鄉(xiāng)耕讀說”商酌》(載臺灣《大陸雜志》第九十一卷第六期,1995年12月出版),共三萬余言,以更多的證據(jù)重申了1988年的觀點。筆者通盤檢點今本《史記》與《漢書》,發(fā)現(xiàn)其中“二十”與“三十”罕見相訛,這一事實使王國維的《索隱》年“二十八”系“年三十八”訛成的擬測成為無根之木;而“三十”與“四十”相訛卻頻繁出現(xiàn)的事實,又昭示了王國維的《正義》“年四十二”絕難由“年三十二”訛成的判斷難以立足。顯然,王國維立論的基石“數(shù)字訛誤說”并不具備“科學的基礎”,而據(jù)以考證太史公的生年,其方法自難稱正確,邏輯也談不上嚴密,司馬遷生于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實無成立的余地。按司馬遷生于武帝建元六年(前135)的結論,公元1995年應是太史公誕辰2130周年,而非2140周年。
值得今人慶幸的是,唐代《正義》單本與《索隱》并無“十年”之差的文獻依據(jù),在隱晦不彰六百余年后,終于浮出水面。趙生群于2000年3月3日在《光明日報》率先發(fā)表《從正義佚文考定司馬遷的生年》,披露他從王應麟所撰《玉海》中發(fā)現(xiàn)的一則《正義》佚文:
考《玉海》卷四十六載:“《史記正義》:《博物志》云遷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又《玉海》卷一百二十三載:“《索隱》曰:《博物志》:太史令司馬遷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
筆者往年在做《史記》版本源流、敘事起迄與主題遷變研究時,參閱相關文獻,也于《玉海》中發(fā)現(xiàn)了這兩則對于考定司馬遷生年彌足珍貴的史料(參見文末圖1及圖2)。
王應麟纂輯《玉海》,他所征引的《史記正義》與《史記索隱》,均為南宋館閣所藏的單行唐寫本,二者引用的晉張華《博物志》都確鑿無疑地記錄了司馬遷于武帝元封三年繼任太史時“年二十八”,亦與今本《史記》三家注錄入的《索隱》紀年吻合,從而為筆者往年所作的“寫本《博物志》,司馬貞作《索隱》時征引了,張守節(jié)也會見讀過”的判斷,提供了可信的文獻根據(jù),同時也否定了王國維疑今本《索隱》“年二十八”乃“三十八”之訛的臆測。
不僅如此,《玉海》收錄的這則《正義》佚文的發(fā)現(xiàn),也使筆者關于張守節(jié)“據(jù)《博物志》所作的按語原作‘遷年卅二歲’。唐代《正義》單本與《索隱》并無‘十年’之差”的推斷得以證實。因為《玉海》錄入的《索隱》、《正義》與今行三家注合刊本《史記》的《索隱》所征引的《博物志》,皆作“年二十八”,證明從古至今這個司馬遷的紀年數(shù)字從未發(fā)生訛變。《正義》據(jù)以推算,在“太初元年”下所作按語,只能是“遷年三十二歲”,而今本作“年四十二歲”必錯無疑。至于今本《正義》致誤的原因,筆者在前揭論文中,已從書體演變的角度,通過“廿(二十)”、“丗(三十)”、“卌(四十)”三個數(shù)字以及“世(丗)”字由唐入宋書寫形態(tài)的變化軌跡,作了詳盡的考論。
由于《玉海》收錄引用了《博物志》的《史記正義》佚文的發(fā)現(xiàn),使《史記·太史公自序》自“卒三歲”至“五年而當太初元年”一段《史》文的《正義》原本舊貌復原成為可能。張守節(jié)《史記正義序》述其注例有云:“次舊書之旨,兼音解注,引致旁通。”所稱“舊書”,指張氏以其為本的裴骃《集解史記》。張氏注例大意是說,他為《史記》作《正義》時,先編次裴骃注文,然后才是自己為《史》文注音釋字、推而廣之、擴而充之的注義。試遵張氏注例,為《史》文自“卒三歲”至“太初元年”的《正義》復原:

王應麟在征引《史記正義》所錄《博物志》時,文字有所節(jié)略,但基本數(shù)據(jù)已全部保存。
根據(jù)從《玉海》中發(fā)現(xiàn)的《正義》佚文、《索隱》與今本《史記》三家注中的《索隱》所征引的《博物志》,皆作元封三年“遷年二十八”,以及修正后的今本《史記》太初元年張守節(jié)按語“遷年丗二歲”推算,司馬遷必生于漢武帝建元六年丙午(前135)。
近聞陜西省司馬遷研究會受中國史記研究會委托,著手籌備于2015年在西安舉行“紀念司馬遷誕辰216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對誕辰絕對年代的確定,依然根據(jù)實難成立的王國維的司馬遷生于孝景中五年(前145)說。筆者祈望盛會主辦方慎重考慮,能否按太史公的真實生年——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將會標修正為“紀念司馬遷誕辰215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以免重蹈1995年國際盛會將司馬遷早生十年的失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