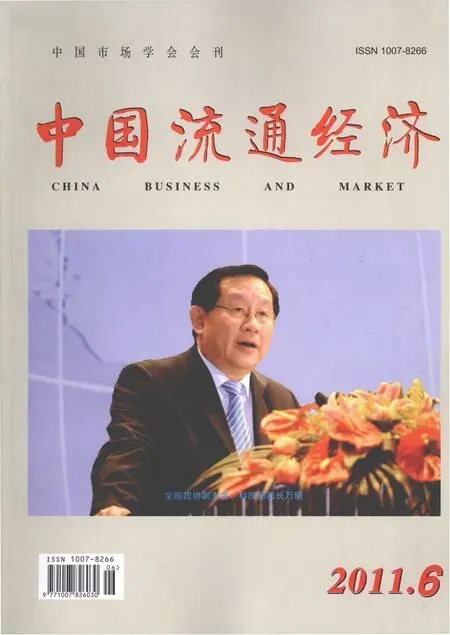國內外礦業稅費制度的比較及有效借鑒
王文娟,李京文
(1.中央財經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北京市 100081;2.北京工業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北京市 100022)
國內外礦業稅費制度的比較及有效借鑒
王文娟1,李京文2
(1.中央財經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北京市 100081;2.北京工業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北京市 100022)
礦業稅費制度是一國礦業政策重要的組成部分,制定合理而有效的礦業稅費制度對于更好地發揮礦業稅費制度應有的經濟與社會功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對比國內外礦業稅費制度,可以發現,國外通常把礦業作為一個獨立的產業來對待,其礦業稅費制度充分考慮礦業企業的特殊性和多樣性,對礦業企業形成了一個較為穩定、完善、有針對性的宏觀調控財政稅收制度;而我國把礦業統歸于第二產業,資源稅成為礦業稅費主要的內容,相關稅費制度的制定很難體現礦業企業的特殊性,存在原有資源稅不足、稅費體系不完善、優惠和補貼政策不明確等一系列問題。為進一步完善我國礦業稅費制度,應借鑒國外成熟礦業稅費制度成功經驗,立足我國實際,明確資源稅功能,完善礦業稅費體系,落實優惠和補貼政策。
礦業稅費制度;國際比較;借鑒
礦業稅費制度作為一國礦業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備受政策制定者和利益相關者的重視。一方面,作為工業原料和能源產品主要來源的礦產資源在性質上屬于不可再生資源,而隨著工業化、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對其的需求量日益增加,礦業成為國民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重要保障,礦業稅費制度不合理容易催生礦業企業粗放的生產方式,造成高污染、高能耗與資源浪費現象,不利于礦產資源的合理開發利用與保護;另一方面,礦業稅費制度的合理建立與完善對礦業企業的持續穩定發展、資源的合理開發利用、礦業的有效投資以及礦業的進出口貿易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1]因此,在建立礦產資源有償使用制度、研究我國現階段礦業稅費制度、全面理解我國礦業稅費制度不足的基礎上,借鑒國外相對完善的礦業稅費制度,幫助我國制定更加合理的礦業稅費制度是十分必要的。
一、我國現行礦業稅費制度概述
我國現行礦業稅費制度是1994年稅制改革后逐步形成的,主要由兩大部分構成:一是包括礦業企業在內的所有企業都適用的普通稅費制度,如所得稅、增值稅等;二是礦業企業所特有的稅費制度,如資源稅、礦產資源補償費、礦區使用費等。[2]
1.企業所得稅。當今世界幾乎所有國家都開征了所得稅,但計稅基礎、稅率設定、征稅方式等方面的具體規定存在差異。企業所得稅是我國最主要的稅種之一,目前的基本稅率為25%。企業所得稅一般按企業經營所得(銷售收入減去各項成本費用后的凈額)一定的百分比征收。
2.增值稅。增值稅的征稅對象為企業經營過程中的增值收入,是流轉稅主要的構成部分,在我國現行的礦業稅費制度下,礦業企業不僅需要繳納資源稅,同時也要就經營所得的增值收入繳稅,稅率已由13%的優惠稅率提高至17%的基本稅率。
3.資源稅。我國資源稅設置的初衷是體現國家對資源尤其是礦產資源的所有權,促進資源的合理開發利用,調節資源的級差收入。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以及資源和環境形勢的日益嚴峻,我國資源稅開征的功能定位也不斷變化,開始注重資源的有效開發利用,并希望通過內化外部成本達到保護自然環境的目標。1986年9月2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發布《財政部關于對煤炭實行從量定額征收資源稅的通知》,成為我國第一代資源稅的開端,當時的納稅對象局限于利潤率超過12%的采礦企業。1994年開始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資源稅暫行條例》規定在中國境內開采天然原油、天然氣、原煤、其他非金屬礦原礦、黑色金屬礦原礦、有色金屬礦原礦或者生產鹽的單位和個人,應當依法繳納資源稅。實行從量定額征收,采礦業具體適用的稅額,由財政部同國務院有關部門根據資源賦存狀況、企業開采條件、資源等級、地理位置等客觀條件的差異,在規定的稅額幅度內確定,征稅標準具體如表1所示。
4.礦產資源補償費。礦產資源補償費是礦業企業因開采不可再生的礦產資源而對作為資源所有者的國家給予的補償。1994年,我國通過并實施《礦產資源補償費征收管理規定》,費率一般為礦業企業礦產資源品銷售收入的1%~4%,按照礦產資源的種類分檔。礦產資源補償費收入由中央和地方共享,收入主要用于礦產資源的勘查與再開發。
5.礦區使用費。根據1989年開始實施的《開采海洋石油資源繳納礦區使用費的規定》和1990年開始實施的《中外合作開采陸上石油資源繳納礦區使用費暫行規定》,對在我國行使管轄權的海域內依法從事開采海洋石油資源的中國企業和外國企業以及在我國境內從事合作開采陸上石油資源的中國企業和外國企業征收礦區使用費,按年度或油氣總產量征收。
二、國外現行礦業稅費制度
國外現行礦業稅費制度歸納起來也主要由兩大部分構成:一是企業普遍適用的稅費制度,如所得稅、增值稅等;二是礦業企業特有的稅費制度,包括權利金、保證金、耗竭補貼、資源超額利潤稅、采礦業權租金、紅利等。
1.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一般以銷售收入扣除各項成本費用后的余額為計稅基礎,在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礦業與其他行業的所得稅稅率相同,但有些國家會針對礦業企業的特殊性制定一定的優惠政策,如允許礦業企業固定資產的加速折舊等。表2列舉了部分國家的企業所得稅稅率,據統計,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企業所得稅稅率均在30%以上。

表1 我國資源稅征稅標準
2.增值稅。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對礦業企業生產銷售礦產品既不征收增值稅,也不征收與增值稅性質類似的相關稅收,如銷售稅等。例如,美國、澳大利亞等國對礦業企業生產銷售礦產品不征收增值稅,但征收銷售稅;南非對礦業企業征收14%的增值稅,但出口零稅率;印度尼西亞和中國也對礦業企業征收增值稅。
3.權利金。權利金是礦產開采人因開采不可再生的礦產資源而向資源所有人支付的補償,它保護所有者對資源的所有權。20世紀末21世紀初,英美法系國家的礦業稅費大都采用了權利金制度,這一制度也逐漸成為了國際礦產資源開發的慣例。權利金主要包括從量權利金、從價權利金、凈離岸價權利金、凈利潤權利金等類型。權利金收入大多作為礦產資源勘探、開發和環境保護等活動的基金,各國的權利金費率大多在3%~8%之間,表3為世界部分國家的權利金費率。

表2 國內外企業所得稅稅率對比

表3 世界部分國家礦業權利金費率
4.保證金。礦產資源是關系人類生產、生活十分重要的不可再生資源,礦產資源的開采會不可避免地造成生態和環境的破壞。為解決礦業開采和生產帶來的環境問題,世界各國紛紛采取各種措施,部分國家設置了環境稅,如“黑肺稅”、“氰化物補償稅”等,[4]而礦地恢復保證金制度是其中效果比較顯著的措施之一,保證金制度以制度的形式明確了礦業企業治理環境破壞、恢復生態的義務,其收入用于環境破壞的治理和恢復,并對企業與環境保護相關的支出在計稅時準予扣減。
5.耗竭補貼。耗竭補貼又稱為負權利金,最早產生于1913年的美國。之所以稱之為負權利金,是因為它與權利金是基礎相同、性質相同卻又截然相反的兩個概念。礦產資源作為可耗竭的不可再生資源,必須加以合理開發利用,權利金是資源開發過程中經營者對所有者(國家)的補償,而耗竭補貼是對礦業經營者的補貼,用以鼓勵經營者積極勘察新資源或開發可替代資源。耗竭補貼作為一種對礦業經營者的補償,費率一般在14%~22%之間,從納稅人納稅年度的凈利潤中扣除,可以有效降低經營者的稅負,為企業積極勘探開發新資源提供動力。目前,世界上很多國家的礦業稅費都實施了耗竭補貼制度,表4為部分國家耗竭補貼制度的相關規定。
6.資源超額利潤稅。超額利潤稅是礦業稅費制度中為調節礦業企業級差收入而設置的,最早于1975年在澳大利亞提出,是對礦業企業獲取的超過常規投資收益以上的收益征收的一種稅,其目的在于通過國家干預,調節礦業企業間因自然條件等因素所造成的級差收入,但這一制度目前僅在極少數國家得以推行。
三、對比視角下我國現行礦業稅費制度的不足
對比國內外的礦業稅費制度,我們不難發現,其最根本的差異在于:國外通常把礦業作為一個獨立的產業來對待,因而其礦業稅費制度充分考慮了礦業企業的特殊性和多樣性,已經對礦業企業形成了一個較為穩定、完善、有針對性的宏觀調控財政稅收制度;而我國把礦業統歸于第二產業,資源稅成為礦業稅費的主要內容,相關稅費制度的制定很難體現礦業企業的特殊性,因而在管理實踐中與國際有效經驗相比還存在諸多不足之處。[5]本文將就以下幾個主要方面進行探討。
一是資源稅功能定位不明確,征稅稅額、征收范圍、計稅依據不科學。[6]在我國,資源稅是礦業稅費體系中最主要的稅種。設置資源稅最初的目的是為了調節礦業企業間因自然條件等差異而形成的級差收入,保證企業間的公平競爭,但1994年稅制改革后,我國的資源稅開始了既對非劣等資源征稅,又對劣等資源征稅的普遍征收方式,稅收間的級差相對于企業收入的級差而言顯得微乎其微,從而使得資源稅原有的調節級差收入的功能定位不再明顯。此外,與國際較為完善的礦業稅費制度相比,我國資源稅的設計缺乏對資源與環境保護的功能定位;稅額設計顯得過低,補償費率也不高,平均在1.18%左右,而國外則大多位于2%~ 8%之間;資源稅征收范圍主要集中于礦產品,顯得過于狹窄;資源稅在從量計稅方式下以銷售量和自用量作為計稅依據,容易助長礦業企業采富棄貧、采易棄難、采大棄小的行為。
二是礦業稅費制度中稅金重復設計,稅種設置不健全。總體來看,國外的礦業稅費制度經過幾百年的變遷,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已經比較成熟,形成了一個較為完善的稅費體系,這一體系既包括一般企業所普適的所得稅、增值稅等,也包括礦業企業所特有的權利金、保證金、耗竭補貼、超額利潤稅等,各個稅費的設置都有其自身的功能定位,能夠通過這一稅費體系對礦業生產進行較為全面、科學的宏觀調控。而我國的礦業稅費制度至今還未形成一個完善的體系,一方面存在稅金重復設計的問題,使得現有稅費各自應有的功能紊亂,難以正常發揮作用。例如,對于礦業企業,國際普遍征收礦業相關稅費,如資源稅、權利金、保證金等,一般不再征收增值稅或者給予一定的增值稅優惠,而我國不僅對礦業企業征收資源稅,也征收增值稅,同時還存在資源稅與礦產資源補償費重復征收的現象,2006年出臺征收的石油特別收益金也存在資源稅重復設計征收的問題等。另一方面,還存在很多應稅領域未設置相應稅費的情況,使得對這些領域的稅收調控缺失。例如,資源耗竭補貼已經成為國際礦產資源開發利用過程中的國際慣例,而我國目前還沒有耗竭補貼,也沒有保證金等稅費項目,礦業稅費體系還不是很成熟。

表4 部分國家礦業耗竭補貼制度規定
三是礦業稅費制度中優惠、補貼政策不到位、不明確、不完善。稅收優惠和減免是稅收制度中一個十分重要的組成部分,市場經濟發達的國家大都對煤礦等礦產資源的開發利用實行保護性的稅收政策,包括稅收優惠、稅收減免、稅額抵扣等,而我國目前對于礦產品開發利用的稅收減免政策還有待完善。國外有關礦業企業的稅費種類一般較少,而優惠政策較多,目前最重要的優惠體現在前期優惠措施方面,特別是在礦業企業前期勘察與開發支出的稅收政策方面,如準予加速折舊、稅前扣除、資本化等,這些政策鼓勵并推動著礦業企業積極勘探新資源,開發替代性資源,在降低礦業企業有效稅賦方面發揮著積極作用。此外,很多國家普遍實行的耗竭補貼、對煤炭生產和經營企業的結構調整、對衰老礦區轉產實行補貼等措施都有力地推動著一國礦業的發展。而我國礦業稅費制度缺乏有效的前期優惠和后期補貼政策,使得新企業難以進入并發展壯大,已有企業缺乏勘察開發新資源與可替代資源的動力,面臨著資源接替的壓力。[7]
四、完善我國礦業稅費制度的有效借鑒
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我國的礦業稅費制度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存在諸多不足之處,相比之下,國外的礦業稅費制度經過幾百年的發展變遷已經逐漸完善,有很多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的地方。因此,我們應該在借鑒國外成熟礦業稅費制度的基礎上,立足我國實際,明確我國礦業稅費制度未來的發展方向。
1.明確資源稅的功能定位。即要明確資源稅的功能定位,科學合理地設計征稅稅額、征稅范圍和計稅依據。首先,我們要確定資源稅到底是以調節級差收入為主要目標還是以保護環境、合理利用資源為目的。筆者認為,新形勢下資源稅的立稅目的應更加偏向于環境保護,通過資源稅將企業的外部環境成本內化,完善我國環境稅收體系的建設。其次,針對新時期我國資源稅存在的征稅稅額、征稅范圍、計稅依據等方面的問題,筆者認為,礦產的資源稅稅額設計可以根據各個礦業企業在自然條件、礦產質量、企業所處生命周期、贏利水平等方面的具體情況進行具體分析,在給定的稅額幅度內分別加以確定,現有稅額幅度應適當放大以體現稅收的差異調節作用;而征稅范圍窄問題主要是針對所有自然資源而言的,就礦產資源而言,要盡量將一些應征稅而未征稅的礦產資源納入征稅范圍,使資源稅發揮更加全面的調控作用;就計稅依據而言,筆者認為,應將按銷售量和自用量征稅改為按實際開采量征稅,避免不必要的資源浪費。[8]
2.完善礦業稅費制度的體系建設。即要完善現有礦業稅費制度的體系建設,合并已有重復設計的稅費,增加缺失的相關稅費。根據1994年頒布的《礦產資源補償費管理規定》,我國征收的礦產資源補償費調整的是礦產資源所有者(國家)與經營者之間的關系,這與國外普遍征收的權利金相類似,但其費率卻明顯低于各國的權利金,不能真正發揮應有的作用。鑒于此,筆者認為,可以考慮將之與資源稅合并征收,并在合并后適當調高資源稅稅率,而對于其他存在重復征稅的方面,也要重新設計稅目,改變重復征稅的問題。另外,為了完善我國現有的礦業稅費制度,筆者認為,我國也應在借鑒他國成功經驗的基礎上建立起保證金制度和資源耗竭補貼制度,通過保證金制度實現代內公平和代際公平,改變我國企業普遍存在的粗放型增長方式,從而更加合理有效地利用資源,更好地保護環境,使“誰開發、誰保護,誰污染、誰治理,誰破壞、誰恢復”的原則落到實處。同時,我們還要借鑒國外的耗竭補貼制度,從礦業企業的利潤中提取部分資金留作企業尋找接替資源之用,也可用于企業的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改善我國大部分企業只顧生產不顧未來發展的現狀,推動企業可持續發展。
3.完善礦業稅優惠政策。即要完善和明確礦業稅費制度中的優惠政策、補貼政策,并將之落實到位。針對我國礦業稅費制度中優惠政策、補貼政策不完善、不明確、不到位的現實,筆者認為,一方面,要著重關注對礦業企業的前期優惠政策,在發展初期,應給予企業盡可能多的優惠條件,如允許企業采取加速折舊方法,允許相關費用的稅前扣除,允許勘察開發費用的資本化等,通過這些優惠措施促使處于發展初期的企業不斷成長,實現規模發展,保證資源更加合理有效的利用,同時推動發展中的企業不斷壯大;[9]另一方面,要學習借鑒國外礦業稅費制度中的補貼政策,將各項補貼收入用到實處,努力改變我國礦業企業普遍存在的粗放型增長方式,改變礦業企業高污染、高能耗、浪費嚴重的現狀,將補貼資金作為企業尋找新能源、實現產業升級和結構調整的基金,實現經濟、社會與環境的和諧發展。
[1]James Otto,Craig Andrews,Fred Ca-wood.Mining Royalties:A Global Study of Their Impact on Investors,Government and Civil Society[M].Washington D.C.:The World Bank,2006:27-28.
[2]張新安,魏鐵軍.現代市場經濟國家礦業稅收制度研究[M].北京:地震出版社,1997:45-46.
[3]何國家.澳大利亞煤炭工業的稅收和租賃費[J].中國煤炭,1999(12):37-38.
[4]宋國明.我國周邊國家的礦業稅費制度[J].國土資源情報,2002(7):31-35.
[5]陶樹人.對我國礦山企業經濟和稅收政策的研究[J].中國礦業,2001(4):11-14.
[6]林芝.試析我國資源稅費制度的不足[J].經濟論壇,2009(6):63-64.
[7]郭淑華.我國生態稅收存在的問題及對策研究[D].北京:中國石油大學,2009:23-24.
[8]洪水峰,楊昌明.中國礦業稅費改革方向初探[J].中國國土資源經濟,2004(11):18-20.
[9]楊志安.現行資源稅與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偏差及其矯正[J].稅務研究,2008(5):42-43.
Comparison and Effective Reference on Mining Tax System at Home and Abroad
WANGWen-juan1and LIJing-wen2
(1.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Beijing100081,China;2.Bei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Beijing100022,China)
Mining tax system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components of national mining policy.Formulating the rational and effective mining tax system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role of mining tax system.By comparing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mining tax system,we can find that,in other countries,the mining industry is usually treated as an independent industry and the tax system for this industry is usually a stable,perfect and suitable macro control financial tax system.While in China,this industry is treated as the secondary industry and resource tax is the most important components of mining tax.There are some problems with China's mining tax system.As a result of that,the spatiality of mining enterprises can not be embodied in the related tax system.To further improve China's mining tax system,we should learn from the mature mining tax system of other countries,clarify the role resource tax plays,improve the mining tax system and clarify and implement preferential and subsidy policy.
mining tax system;international comparison;effective reference
F810.422
A
1007-8266(2011)06-0099-05
王文娟(1965-),女,山西省大同市人,中央財經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師,管理學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為公共政策和組織行為學;李京文(1933-),男,廣西壯族自治區陸川縣人,技術經濟學家及數量經濟學家,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學部主席團成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北京工業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院長,中央財經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第七屆、第九屆全國政協委員,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第八屆全國人大代表,我國技術經濟和工程管理理論的開拓者之一,主要研究方向為科技進步、生產率、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工程項目技術經濟評估、工程管理、資源與環境、可持續發展和區域規劃等。
陳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