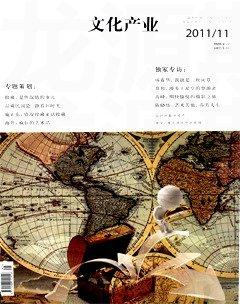育邦:漫步于星空的悠游者
梁雪波
“讀書就是游蕩。”育邦在介紹法國作家帕斯卡·基尼亞爾的小說時如此說道。對于育邦來說,閱讀就像林中漫步,有一種“不尋求達到目的的等待”,在漫無目的的碎步中充滿了探秘的沖動、未知的發(fā)現(xiàn)、相遇的喜悅,充滿無限的可能性。
作為一個癡迷于閱讀的“悠游卒”,育邦對古今中外的文學大師有著深入的考察與理解,加繆、貝克特、佩索阿、巴別爾……他沉溺其間,感受、思考、呼吸,書籍成為他進行自我觀照的隱秘的鏡像。從這個角度說,育邦是一個有著多重靈魂的人。
作為一位年輕的作家,育邦在詩和小說之間游走多年,他的小說寫作“致力于中國小說的革新,致力于對閱讀經(jīng)驗和生活經(jīng)驗的雙重超越”。在最近完成的“虛構(gòu)之詩”中,他通過對經(jīng)典文本的模擬、仿寫、戲謔性的混淆。表達自己對詩歌與世界的感受,以圖達到以假亂真的寫作“預謀”。
與育邦交談,讓人不由地產(chǎn)生“重新做一個讀者”的沖動。他說自己喜歡那種無所事事的閱讀時光,他認為文學在當代的功用之一,就是“能讓我們意識到自身的匱乏,還有生活中那些已經(jīng)削弱我們并正在讓我們氣喘吁吁的東西”。
《徒步者隨錄》的作者、文體考究的散文家鐘鳴曾經(jīng)有過這樣的自我評價:“太少的人生經(jīng)歷和太多的幻想”。這句話用在70年代出生的人身上似乎更加契合。畢竟,50年代出生的鐘鳴還當過兵、做過知青,經(jīng)歷過文革、
80年代的文化熱潮等等。而對于“70后”,比如育邦來說,生活的軌道仿佛早早地就鋪設好了,他不再是“迷惘的一代”,也不屬于“垮掉的一代”,在政治喧囂退潮后的轉(zhuǎn)型社會,他與時代保持著一種若即若離的關系,在物質(zhì)世界與內(nèi)心真實之間游移往返。
1976年,育邦出生于位于蘇北的灌云縣,父親在鄉(xiāng)政府工作,一家人就居住在鄉(xiāng)政府院子里,這里還有一座不大不小的文化站。小時候的育邦性格文靜、內(nèi)向、不愛說話,勤勞能干的母親對他一直寵愛有加,家庭氛圍和諧安寧,父母對他也沒有嚴苛的管束。育邦還記得,當年鄉(xiāng)文化站里有一個圖書館,因為都是熟人,他經(jīng)常去玩,圖書館其實并不大,藏書也十分有限,但對于一個小孩子來說,那小小的屋子和花花綠綠的圖書就包孕著整個世界,神秘而無窮。
“從小我就對未知的事物充滿渴望,并且保持濃烈的興趣。”育邦認為這種對知識異乎尋常的熱情,是一種延續(xù)至今的慣性。讓他記憶深刻的是,小學二年級的時候,他得到了一個萬花筒,“這是我一生中最感興趣的玩具。”他常常把它帶在身邊,甚至在上學的路上也要玩一玩,弄一弄。“我那好奇的眼睛一睹到萬花筒的筒口時就會睜得更大,我的瞳孔一定也倒影出繽紛絢麗的色彩。那一刻,我——一個膽小的孩子,驚訝遠遠地超出了羞澀。這是一個多么美妙的世界啊l我曾見到和未曾見到、我能想象的和不可想象的色彩旋轉(zhuǎn)著,悸動著,跳躍著……一個立體的迷幻世界……”童年的鄉(xiāng)村生活對育邦來說,是短暫的易逝的,猶如萬花筒中的碎片。
三年級時,育邦就轉(zhuǎn)到鎮(zhèn)上的小學讀書了。回望小學生活,他印象最深的是朱老師。朱老師博學優(yōu)雅,為人剛正不阿。教他時已經(jīng)快五十歲了,還只是個代課教師。“他依稀有一些白頭發(fā),整個頭發(fā)都是根根直豎,很能讓人想起魯迅先生。”育邦喜歡上他的語文課,至今還能歷歷記得他講的紀曉嵐,徐文長的故事,那些充滿智慧的古代文士給育邦以無限的憧憬,“他講了很多古代文人墨客的故事,這在我幼小的心靈里種下一顆種子。今天說來,這顆種子就是對于文學和語言的尊敬,對于純粹知識分子的尊敬和向往。”朱老師還寫得一手好字,他常常用“溫暖而寬大的手掌”握著育邦的小手,輔導他練習書法。對朱老師,育邦至今仍持有一份尊崇和感激之情,他說:“朱先生是那個貧乏時代里的鄉(xiāng)村知識分子,貧困卻清靜。他的影響在貧瘠的鄉(xiāng)村里代表著一種無形的道德力量。在我的生命維度里,他占據(jù)著與陶淵明,孟浩然,徐文長等這些古代杰出知識分子一樣重要的位置,并且他的坐標確定著其他人的坐標。”
關于小學的讀書生活,很多年之后,育邦在他的小說《身份證》里,有過一段“煽情”的描述——“那是很久以前的事,從小學三年級就開始了,你那時就學會了早起,早晨五點半就起床了,不管是嚴寒還是酷暑,起床后鍛煉身體,活動活動筋骨跑跑步,更主要的是讀書。先是背誦語文課文,你能背下當時課本上所有的課文,你現(xiàn)在還能記得那些熟悉的課文的名字,《爬山虎的腳》、《故鄉(xiāng)的楊梅》、《游擊隊之歌》,《神筆馬良》,《凡卡》,《小抄寫員》,《踢鬼的故事》,《最后一課》……多么動聽悅耳的名字啊,就像山澗的甘泉滋潤了一個因急速趕路而干涸疲憊的人。你甚至想再找來你當時讀的小學語文課本,一個字一個字一幅插圖一幅插圖從頭到尾慢慢地閱讀品味,仿佛一個老酒鬼碰到五糧液或茅臺,他不敢大口地喝,只是一小口一小口地啜飲,留下更多的時間和空間來回味,品評。……”
小時候的育邦,懂事,乖巧,學習上基本不需要父母操心,因此也頗得老師的喜愛。他喜歡讀課外書,這對他的作文產(chǎn)生著,了潛移默化的影響。他記得,小學五年級的時候?qū)戇^一篇作文,這篇作文他沒有按照通常的要求(記敘文要真人真事)來寫,而用了一種虛構(gòu)的方式,甚至還用了“象征主義”的手法,其中寫到了“花”和“傘”這兩個意象,寓意老師和同學的關系,寫得很美。老師為此表揚了他,并用毛筆把這篇“美文”抄下來,貼在黑板上,當作范文。育邦說,其實當時自己也不懂什么意象啊象征啊,可能是課外書讀得多,自然而然模仿出來的。后來上初中、上高中,他也寫過許多所謂的優(yōu)秀作文,但都沒有留下印象,唯獨這篇作文讓他難以忘記。
在鎮(zhèn)子上讀完初中,然后以優(yōu)異的成績考上縣中,父親工作調(diào)動伴隨著母親焦灼的呵護之心,于是一家人都搬到了縣城。那段讀書歲月,也許正如育邦筆下的文字:“時光與世事在這里迅即流過,帶來無盡的惆悵和思考。”
1994年,育邦考上南京師范大學,一路風塵地來到了省城。南京屬于亞熱帶溫濕性氣候,魚米豐饒,歷史悠久,文人墨客輩出。而20世紀90年代正是先鋒小說異軍突起之時,當年在南京活躍的年輕小說家就有蘇童,葉兆言,韓東、朱文等一大批。在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也有兩位小說家魯羊、郭平,兩位都是育邦的老師。受他們的影響,在大學二年級的時候,育邦開始嘗試寫小說,因為他覺得自己和文學的關系更為密切,而當時認為成為一名作家的主要方式就是寫小說。前期的寫作,以仿作為多。育邦發(fā)現(xiàn),其實法國文學中就有仿作的傳統(tǒng),很多好的作家在年輕的時候都有模仿前輩作家、優(yōu)秀作家的經(jīng)歷,然后慢慢再形成自己的風格。“當時自己也讀到了很多好的作品,但還沒有找到合適的方式賦予作品以生命,這個時候模仿是最好的手段。更多的意義上是一種練筆吧。”
大三的時候,有一次魯羊在課上讀了一段發(fā)表在《譯林》雜志上的作品,那是葡萄牙大詩人費爾南多·佩索阿的隨筆集《惶然錄》片段,當時該書還沒有出版中譯本。育邦聽了之后非常喜歡,還把那期《譯林》借來復印了,然后就期待著《惶然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