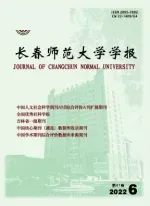人民幣升值對珠三角經濟結構的影響效應分析
許罕多,吳海嶺
(1.山東大學經濟學院,山東濟南 250100;2.中國海洋大學經濟學院,山東青島 266100)
2003年以來,美國認為人民幣幣值低估是導致中美貿易不平衡的重要原因,要求人民幣升值以改善美國的巨額貿易赤字。另一方面,20世紀90年代開始,中國國際收支就呈現出經濟項目和資本項目都為順差的局面,尤其是2000年以來,伴隨中國經濟高增長的持續,中國出口導向型的發展方式不斷固化,進出口總額在G DP中的比例已經達到70%左右,外匯儲備余額不斷增加,這些因素也成為推動人民幣升值的因素。在此背景下,分析人民幣升值對中國經濟的影響成為一個重要問題。改革開放以來,珠三角已經成為中國工業化的典范。隨著2007年以來世界經濟環境的轉變,珠三角經濟的未來發展也面臨挑戰。研究人民幣升值對珠三角經濟的影響,分析人民幣升值同珠三角經濟結構調整之間的關系有助于預測中國經濟的未來走向。
一、貨幣升值對經濟影響的相關研究回顧
人民幣升值對經濟的影響,國內外學者已經做了很多相應的研究。尹翔碩 (2004)對日本1981年以后的匯率變動與貿易收支進行了回歸分析,結果顯示匯率并不是影響一國貿易收支長期變動的主要因素,更基本的因素是儲蓄與投資。余永定 (2007)通過建立中國國際收支的理論框架,分析“雙順差”的本質及其與宏觀經濟的關系,強調中國“雙順差”主要受國內制度缺陷、相關政策調整滯后的影響。徐穎 (2008)針對人民幣兌美元匯率進入“6時代”給我國出口企業造成的很大影響 (特別是出口依存度較高的珠三角地區),提出了一些應對策略。張斌等 (2006)建立了一個貿易、非貿易兩部門模型,理論上證明在保持實際匯率不變與國內物價水平穩定的貨幣政策組合下,貿易部門相對于非貿易部門更快的全要素生產率進步會造成工業服務業產業結構扭曲并阻礙農村勞動力向城鎮轉移。以上研究主要從理論上分析了匯率變化對經濟結構的影響,而沒有進行實證檢驗。
Akhtar Hossain(1997)的研究發現孟加拉國的實際匯率升值是由經濟增長提高了對不可貿易品的需求引起的。Frenkel(2004)運用線性回歸模型研究了實際匯率對阿根廷、巴西、智利和墨西哥四國的影響,得出實際匯率的變動對就業有顯著影響,且實際匯率變動對失業率變動影響有滯后效應等結論。Burgess(1998)根據G7國家的數據,利用非線性最小二乘估計方法分析了匯率波動對就業的影響,結果顯示不同國家的反應程度不同。盧鋒 (2006)研究了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兩部門勞動生產率、工資增長、單位勞動成本等實際匯率基本因素變動,發現20世紀80年代前后兩部門的勞動生產率相對增長與美國及13個OECD國家平均水平比較分別下降了40%和30%左右;進入90年代后這一指標開始上升,90年代中后期以來增速加快,到2004年累計增長一倍左右。
二、人民幣升值對珠三角地區的歷史影響
1994年1月1日,人民幣官方匯率與外匯調劑市場匯率并軌,實現了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匯率。這一時期絕大多數國內企業的外匯收入必須結售給外匯指定銀行,同時中央銀行又對外匯指定銀行的結售周轉外匯余額實行比例幅度管理。在這一制度下,銀行持有的結售周轉外匯被限定在一定的比例范圍內,超過這一范圍上限的銀行必須通過銀行間外匯市場出售,反之則必須從該市場購進。在匯率并軌后,人民幣匯率便不斷升值,對外貿易、外商投資等都受到嚴峻的考驗。但人民幣升值幅度的加大,表明我國經濟開放程度的加大,有助于有管理的浮動機制的完善,進而在條件成熟的情況下,使人民幣逐步走向自由兌換。
珠三角以外向型的高新技術制造業和勞動密集型的加工型產業為主導,這種發展模式妨礙了工業化的深化,整個經濟體系的內生增長動力不強。特別是在資源約束、勞動力價格上升和人民幣升值三重效應下,經濟發展的成本不斷上升,珠三角地區可持續發展受到制約。1994年以來,人民幣升值對珠三角經濟的影響可以分為幾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994—1998年,由于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人民幣重新盯住美元,人民幣升值促使珠三角結構調整的壓力也消失了。2000年以后,中國經濟增長加速,珠三角地區的加工產業生存環境惡化,加工企業內部面臨同行的激烈競爭,同時整個加工行業經常受到來自美國和歐盟的反傾銷訴訟,出口產業的升級壓力加大。第二個階段是1998—2005年,中國一直實行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這個時期,珠三角產業內部出現了一些新的變化,一方面一些產業開始自創品牌,例如家電行業、打火機行業;另外一方面是產業內部的壟斷性在加強,產業內部兼并趨勢顯著,很多規模小的加工企業或者被收購,或者倒閉。第三個階段是2005年以后,這一階段人民幣匯改重啟,人民幣重新開始對美元小幅、持續升值。2007年美國金融危機爆發對中國宏觀形成較大沖擊,珠三角很多加工型企業倒閉,這一情況在2009年隨著美國經濟的復蘇開始緩解。
三、實證模型
本文將利用VAR模型 (向量自回歸模型)來說明匯率對珠三角地區經濟結構的影響,經濟結構變化用對外貿易凈流量、制造業的固定資產投資額和制造業勞動就業量來說明。
1.數據來源及轉換
對數據進行自然對數轉換,使其趨于線性化,不僅能夠消除時間序列中的異方差現象,同時也不改變原有的協整關系。本文所有數據都進行了對數化處理。對外貿易凈流量是利用1994到2008年珠三角地區的出口額與進口額的差得到的,這一時期的匯率也是從1994年到2008年,分別記為lnjlc和lnhl1;制造業固定資產投資數據從1994年到2009年,對應的匯率也是從1994年到2009年,分別記為lntz和lnhl2;制造業勞動就業量數據從1978年到2008年,對應匯率也是從1978年到2008年,分別記為lnjy和lnhl3。所有數據來源于各年中國統計年鑒和新中國50年統計資料匯編。
2.向量自回歸 (VAR模型)估計
本文采用協整理論分析珠三角地區匯率與凈出口、制造業的固定資產投資和勞動就業量的關系,即從時間序列的非平穩性分析入手,探求非平穩變量間蘊含的均衡關系,避免了傳統的線性回歸對非平穩的經濟時間序列進行簡單回歸時產生的偽回歸現象。協整關系表達的是若干個由單位根過程所生成的數據的變量,若存在一種線性組合,使這一組合的殘差由穩定過程所生成,則這種組合即為變量間的協整。它度量了這幾個變量間的長期穩定性,其經濟意義在于對于各自具有長期波動規律的變量,如果存在協整關系,變量間也就具有長期的均衡關系。一次沖擊只能使協整變量在短時間內偏離均衡位置,在長期中會自動回復到均衡位置。
對經濟變量進行協整分析前,要對時間序列及其差分序列的平穩性進行檢驗,確定變量的單整階數;其次是檢驗變量間的因果關系;再次檢驗變量間的協整關系,建立協整方程,說明具體的長期均衡關系;最后建立協整變量與均衡誤差之間的誤差修正模型。
3.平穩性檢驗
由于許多經濟變量是非平穩的時間序列,如果使用傳統的計量經濟學方法分析,容易產生“偽回歸”問題。協整的前提是各序列都是平穩性的時間序列,所以第一步對序列作平穩性檢驗。

表1 各變量的ADF檢驗結果
如表1所示,根據單位根檢驗,lnhl1、lnjlc和lnhl3、lnjy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是平穩的,說明他們都是零階單整序列,即I(0);而lnhl2和lntz在各個顯著性水平下都是不平穩的,其一階差分也是非平穩序列,但是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其二階差分平穩,說明lnhl2和lntz是二階單整序列,即I(2)。
4.格蘭杰因果檢驗
前面已經檢驗出各個序列的平穩性,下面用Granger模型來估計各個變量間的因果關系,最優滯后期通過VAR模型檢驗。滯后階數為3時AIC和SC最小,因此滯后階數選擇3。檢驗結果如下表所示。

表2 lnhl1和lnjlc的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結果

表3 lnhl2和lntz的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結果

表4 lnhl3和lnjy的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結果
由以上表格所知,對于lnhl1不影響lnjlc的原假設,拒絕它犯第一類錯誤的概率是010085,表明匯率升值影響凈出口的增加,而凈出口的增加對匯率的影響不大,即匯率升值和凈出口增加之間是從匯率升值到凈出口增加的單向因果關系。同理可得制造業的固定資產投資的增加影響匯率的升值,而匯率的升值對制造業固定資產投資的影響關系不顯著;對于制造業的勞動就業量與匯率間的關系,可以看出匯率的升值影響制造業勞動就業量的增加,而就業量的增加對匯率升值的影響不顯著,即匯率升值和制造業勞動就業量增加之間是從匯率升值到勞動就業量增加的單向因果關系。
四、結論
通過對珠三角地區隨著匯率變化經濟構成的分析,以及匯率與貨物和服務凈流出、制造業固定資產投資和勞動就業量的實證檢驗,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第一,匯率升值和凈流出是單向因果關系。數據表明匯率升值伴隨著貨物和服務凈出口額的增加。根據彈性理論,雖然匯率升值會導致出口下降,進口增加,但由于珠三角很多加工型產業屬于來料加工,人民幣升值對進出口凈值影響不大。另外,由于珠三角出口產品的需求彈性較小,升值帶來的出口緊縮相對較弱。
第二,匯率和制造業固定資產投資的關系。如果人民幣升值,制造業的投資量將會減少,而從長期看,固定資產投資會增加。所以目前人民幣升值確實導致大量制造企業的破產倒閉,但是只有經過這次沖擊的重新洗牌,低層次、低附加值的產品才會逐步退出珠三角地區,從而實現經濟結構的調整。
第三,珠三角現有制造業吸收了大量的勞動力,也加速了農村勞動力的轉移,但是長期內匯率與就業量負相關的關系不會改變。這需要實施必要的人力資本政策,提升勞動力的技能和素質,培養新型的科技人才。勞動力的質量比數量更為重要,如果缺乏對勞動力的投資,就很難獲得人力資本的增值,進而也就難以獲得人力資本所帶來的外部效應,因而在政策制定上要優先發展基礎教育和職業培訓政策。
[1]徐穎.淺析人民幣升值對珠三角區域經濟的影響[J].湖北經濟學院學報,2008(5).
[2]魏巍賢.人民幣升值的宏觀經濟影響評價[J].經濟研究,2006(4).
[3]張曙光.人民幣匯率問題:升值及其成本-收益分析[J].經濟研究,2005(5).
[4]張斌,何帆.貨幣升值的后果——基于中國經濟特征事實的理論框架[J].經濟研究,2006(5).
[5]巴曙松,吳博,朱元倩.匯率制度改革后人民幣有效匯率測算及對國際貿易、外匯儲備的影響分析[J].國際金融研究,2007(4).
[6]巴曙松,王群.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對我國經濟影響的實證研究[J].財經問題研究,2009(4).
[7]尹翔碩.論匯率變動與貿易收支的決定因素[J].世界經濟研究,2004(2)
[8]古克鑒,余劍.匯率變化與中國產業結構調整研究[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
[9]余永定.2009年中國宏觀經濟面臨的挑戰[J].國際金融研究,2009(1).
[10]高樂詠,王孝松.美國逼迫人民幣升值的深層原因探討——政治經濟學視角[J].南開學報,2008(4).
[11]Devarajan,Shantayanan,Jeffrey D.,Lewis,and Sherman Robinson.External Shocks,Purchasing Power Parity,and the Equilibrium Real Exchange Rate[J].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1993,7(1):45-63.
[12]Akhtar Hossain.The Real Exchange Rate,Production Structure,and Trade balance:The Case of Bangladesh.[J]journal Of Indian Economic Review,1997(2).
[13]Frenkel Rober.Real Exchange Rate and Employment in Argentina Brazil Chile and Mexico[D].Paper prepared for the Group of 24 Washington D.C.,September 2004.
[14]Sinon M.Burgess,Michael M.Knetter.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of Employment Adjustment to Exchange Rate Fluctuations[J].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986(1).
[15]David E.Lebow.Import Competition and Wages:The Role of the Nontradable Sector[J].The Review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93,7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