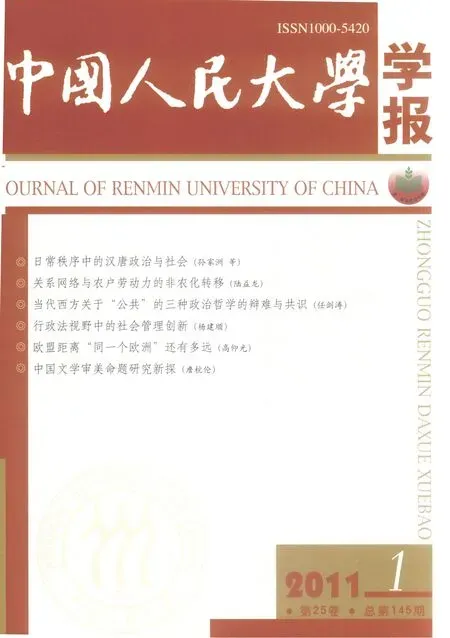對馬基雅維利的重釋:基于《曼陀羅》的文本分析
陳華文
對馬基雅維利的重釋:基于《曼陀羅》的文本分析
陳華文
馬基雅維利形象在無數學者的詮釋下頗為分裂對立,而致力于做出統一解釋的努力總顯得理據不足。這都與解釋者局限于馬氏的政治著作文本有關。《曼陀羅》作為一個形式上直接處理現實生活的戲劇文本,傾向于表達普遍性的問題,這就提供了一個避開文本分歧的可能性。借助于戲劇行動,馬基雅維利充分闡發了一個人應該如何審慎行事的見解。在政治與戲劇這種并行結構中,人們會發現馬基雅維利學說的核心并不是共和主義,也不是愛國主義,而是關于一個人應該如何生活的普遍性教誨。他對于這個問題的回答與古代倫理和現代道德的進路都有所不同。我們需要從這里出發,重新理解馬基雅維利的思想及其與現代政治、現代倫理的關系。
馬基雅維利;《曼陀羅》;審慎;現代政治
一、馬基雅維利的問題
馬基雅維利不僅在歷史上備受訾議,而且近些年來在無數學者的詮釋下,其形象更具分裂性。這可以從一篇對1969年以來西方學界對馬基雅維利的研究綜述中略窺一斑:“對于近期的研究而言,馬基雅維利是現代政治科學、形而上政治學與國家理性之父……他是共和自由的愛國者導師,同樣也是專制君主制、恐怖主義以及絕對主義的導師……”[1]。導致馬基雅維利形象出現分裂的部分原因與其作品在對于邪惡毫不諱言的同時也提出了一些略顯崇高的政治價值 (例如國家統一與公共福祉等)有關。馬基雅維利在其政治著述,尤其是《君主論》中,直截了當地提出了一些“邪惡”主張:君主必須懂得如何善用野獸之道,當遵守信義反而對自己不利的時候,英明的統治者絕不能夠、也不應遵守信義;施恩應細水長流,而傷害則應干脆利落……對于這些在他之前的古典思想家假他人之口隱秘表達的信條,馬基雅維利不僅以自己的名義公開宣示,甚至欣然自得。①施特勞斯指出,馬基雅維利并不是第一個表達類似觀點的人,這種觀點由來已久。柏拉圖也曾借用其筆下人物卡里克勒斯和特拉西馬庫斯,闡發這些邪惡的政治信條;修昔底德則是借古代雅典的戰爭使節來宣揚同樣的主張。施特勞斯特別指出,只有馬基雅維利敢于在他名下無所忌憚地闡發這種信條。見Strauss.Thoughts on Machiavelli.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9,p.10。哪怕是在今天,馬基雅維利的這些說辭,還會使得讀者震驚。
對于馬基雅維利的研究者來說,如果不打算僅僅停留在道德高度一味盲目責罵的話,那么就必須認真面對馬基雅維利的“邪惡”學說,直接深入其最令人震驚的地方,如此方能做出切中肯綮的解讀。對此,人們需要知曉關于馬基雅維利的突兀評價。一方面,有研究者為其“邪惡”學說予以辯護。《君主論》最后一章,以及貫穿《李維史論》始終的、對于意大利統一的激情呼告,使得一些辯護者以為找到了馬基雅維利作為一名抱有共和理想的愛國者形象。黑格爾指出:“一個人在讀《君主論》的時候,必須既要考慮馬基雅維利以前的若干世紀的歷史,也要考慮他所處時代的意大利歷史。”[2](P151-152)循此脈絡,《李維史論》后來才成為劍橋學派探尋共和主義德性概念與自由概念的思想源泉。而另一些辯護者在其政治著述里找到了作為一名保持價值中立的政治科學家形象。盡管馬基雅維利本人沒有使用過“政治科學”這樣的詞匯,但由于他似乎強調審慎 (prudence)與技藝 (art)在奪取政治權力或者治理國家 (無論是君主國,還是共和國)時的重要性,因此被辯護者們視為政治科學之父。總的說來,辯護者或力圖揭示出一個為國家統一或共和福祉而冷峻思考的馬基雅維利,或將他塑造成在不同價值間保持中立的形象。另一方面,有論者仍然堅持抨擊馬基雅維利的立場。施特勞斯就重申馬基雅維利作為邪惡導師的說法,認為不管是將馬基雅維利視為愛國者抑或政治科學家,都是一種混淆視聽的誤解。[3](P10-11、80)
可見,馬基雅維利形象在學者們的詮釋下愈加分裂對立,但也有不少研究者致力于給出一個統一的馬基雅維利形象。例如斯金納認為《君主論》與《李維史論》的政治教訓如出一轍,兩書可統一為馬基雅維利的一個基本論點:“任何人‘無論采取何種異乎尋常的行動,只要對于組成一個王國或締造一個共和國有幫助’,都不能加以譴責,否則就是不近情理。”①斯金納:《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礎》上卷,284-285頁,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斯金納在《李維史論》最后一卷結尾處發現了馬基雅維利將國家的生存與自由置于首位,而一切其他的考慮則應束之高閣。具體論述詳見斯金納:《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礎》上卷,第六章。另外,曼斯菲爾德認為:“較之《君主論》給人的第一印象,以及在那些認為兩書相互對立的普通看法下它所享有名聲而言,它有著更多的共和主義因素;同樣,與《李維史論》給人的第一印象及其據此所得的名聲相比,它也有著更多的君主制甚或專制政體的因素。”[4](Pxxii)然而,斯金納和曼斯菲爾德的兩種解釋并不足以提供一個完整的馬基雅維利形象。前者仍然是以愛國主義為圭臬,并力圖將馬基雅維利的德性 (virtù)詮釋成共和德性,從而建立起一個正大光明的馬基雅維利形象。劍橋學派的這種做法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馬基雅維利的邪惡主張給人帶來的道德張力,但實際上有論者認為這是對馬基雅維利的誤讀,因為馬基雅維利從來就沒有提過什么共和德性。②曼斯菲爾德對共和主義的解讀進路予以了強烈的反對,他認為馬基雅維利并非如常人所言是共和德性的信徒,哪怕他的確認為共和國要優于君主國。見Harvey C.Mansfield.Machiavelli's Virtu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6,p.23.不過,至于曼斯菲爾德的“其A中有B,B中有A”的解釋進路,有可能忽視了A和B所共有的東西。實際上,為什么會有分裂的馬基雅維利形象?斯金納或曼斯菲爾德為統一的馬基雅維利形象所作的解釋為何不夠?這兩個問題都與文本選擇僅局限于政治著作有關。目前關于馬基雅維利思想的研究過多集中在其政治著述當中,尤其是《君主論》與《李維史論》的關系當中。實際上,馬基雅維利除了在思想史上留下厚重的政治著述,還創作和翻譯了幾部充滿嬉笑怒罵的詼諧戲劇,《曼陀羅》是其中最具原創性的一部。
那么,這些戲劇能否為我們提供理解馬基雅維利政治思想的新資源?我們注意到,馬基雅維利在給圭恰迪尼的一封信里,署名為“馬基雅維利,歷史學家,喜劇家與悲劇家”[5](P371)。戲劇和歷史是馬基雅維利表達的兩個主要方式。根據亞里士多德的論述,較之歷史,戲劇所表達的內涵更具有普遍性——“詩是一種比歷史更富哲學性、更嚴肅的藝術,因為詩傾向于表現帶普遍性的事,而歷史卻傾向于記載具體事件。”[6](P81)從這個意義上看,馬基雅維利在戲劇里所表達的意涵較之其歷史作品和政治著述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理解成由古代典范及其所處時代佛羅倫薩的事例構成)更具有普遍性。因此,施特勞斯強調馬基雅維利學說的普遍適用性的解釋方向[7]有其合理性,辯護者的說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舒緩其學說給人們帶來的緊張,但它們畢竟沒有直接面對馬基雅維利對于邪惡的處理,因此反而有可能丟失其學說中真正重要的東西。相反,馬基雅維利的戲劇《曼陀羅》作為反映現實生活的文本,其對普遍問題的揭露,有可能向我們展示出一個完整的馬基雅維利形象,從而為我們提供重釋其“邪惡”學說的新視角。
二、戲劇與政治:馬基雅維利的兩個舞臺
從戲劇作品出發,理解馬基雅維利的政治思想,首先會遇到這樣的質疑:馬基雅維利的政治思想在其政治著述里已得到完全的展現,并不需要訴諸其他作品,尤其是文學作品。《蠢驢》和《曼陀羅》“這兩部作品對于理解馬基雅維利的思想并沒有提供什么新的東西。它們不過是通過詩歌和戲劇技巧,對那些在其政治著述中已得到完好發展的理念予以強調”[8](P6)。這類意見認為馬基雅維利的所有思想都可以在其兩部政治著述當中找到。
但這種詮釋進路因沒能注意到馬基雅維利的世界的雙重性,而把握不到馬基雅維利學說的核心。馬基雅維利在給維托里的一封信里寫道:“不管是誰,看到我們的信,那些相對體面的,還有其他的,可能都會感到驚訝,因為我們乍一看都像是那么正經的人,討論重大事件,那些不夠正直和崇高的想法從來都不會在我們的頭腦里出現。但幾頁過后,他們馬上會發現,我們,同樣的一個我們,竟是如此卑劣、薄情、放蕩,總是如此不帶遮攔地談論荒誕不經之事。”[9](P312)而馬基雅維利認為,他和維托里不應該因此遭受譴責,反而應該受到贊揚,因為他們如實地模仿了本性 (nature)本身的方方面面。馬基雅維利文學作品及通信集里所顯現出的輕與重,乃是對本性的模仿。[10](Px-xi)若僅僅閱讀其政治著述,只能看到馬基雅維利世界的一部分。
馬基雅維利投入文學創作與他在政治生活中的跌宕經歷密切相關。關于馬基雅維利具體什么時候開始寫作 (包括其政治著述和文學作品),研究者們并沒有取得一致的看法。他們也很少懷疑,如果馬基雅維利仍維持著他以前的那份工作,他就不可能創作影響如此深遠的文學作品。[11](P135)美第奇家族復辟后,曾作為佛羅倫薩共和國外交秘書的馬基雅維利遭受放逐。他向維托里描述了自己在這些日子里是如何生活的。他不僅談到夜里與古代政治家縱橫捭闔,還提到早晨有愛情詩歌相伴。[12](P262)事實上,馬基雅維利獻書洛倫佐以求重返政治舞臺的希望落空后,他日益將自己視為一名文人。[13](P98-99)1517年他在給朋友的一封信里,表達了對于同時代著名詩人阿里奧斯托 (Ariosto)在其作品《憤怒的奧蘭多》(Orlando Furioso)中沒有將自己歸為詩人行列的耿耿于懷。“我最近讀了阿里奧斯托的《憤怒的奧蘭多》,這部詩歌總體可謂精美,不少段落奇妙無比引人入勝。如果他和你在一起,那么代我問候并轉告他,我唯一的抱怨是他提到了如此之多的詩人,卻單獨撇下了我。不過,在我的《蠢驢》中,我是不會落下他的。”[14](P318)在這段尖酸刻薄的評論里,馬基雅維利將自己當做一名詩人予以自嘲,同時也暗諷阿里奧斯托像驢子一樣愚笨。這充分表明馬基雅維利有能力且迫不及待地想加入文學的圈子當中。
戲劇對于馬基雅維利來說,是他離開政治舞臺后唯一的出路,在這里他能扛住命運,使得他慘淡的生活稍有樂趣。[15](P10)但是,馬基雅維利創作文學作品并不只是為了消遣時日或滿足時下墮落的品味,而是需要通過抒情詩、敘事文與戲劇來體現理解現實生活的不同表達方式。關于喜劇與現實生活的關系,有兩種主要的觀點:一種是古典的,認為喜劇是現實的模仿,是自然、習俗和家庭私人生活 (domestic affairs)的一面鏡子①代表人物莫過于亞里士多德,他指出喜劇和悲劇都是對生活的模仿,“二者 (指索福克勒斯與阿里斯多芬)都模仿行動中的和正在做著某件事情的人們”。見亞里士多德:《詩學》,43頁,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這也是文藝復興時期的喜劇學家所支持的觀點;另外一種則出自當代喜劇理論家,他們認為古典喜劇源自狂歡節,舞臺上的這一天所呈現的是對現實的顛覆。②Marvin Herrick.Comic Theor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64;同樣參見Douglas Radcliff-Umastead.The Birth of Modern Comedy in Renaissance Italy.Chicago&London: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9,introduction.馬基雅維利并沒有將喜劇視為現實生活的反面,而是私人生活的一面鏡子。盡管喜劇兼具文雅與逗人發笑的語詞,但是那些帶著享樂的迫切心情來欣賞喜劇的人們只有
在回到私人生活之后、在當下現實之中才能慢慢咀嚼出當中的有用鑒戒。[16](P188)戲劇是對現實生活的模仿,行動作為戲劇的主要對象,是對人性以及人的思想、人的目的最清晰、最有表現力的揭露。黑格爾認為戲劇的創作主體首先要徹底洞察到人的目的、斗爭及其終局是以內在普遍的力量為根據的。推動人動作的情欲和個性,在詩人那里應是了然于胸的。普通眼光所視為黑暗、偶然和混亂統治著的東西對于詩人卻顯示著絕對理性在實在界的自我實現。[17](P247-248)因而,唯有借助其戲劇里所描述的世界,我們才能懂得馬基雅維利的學說是關于人類普遍事務的,而不是局限于某個時代某個國度甚或某個群體。盡管戲劇并不是一個強大的庇護所,但可以給他機會表達自己的想法。[18](P173)訴諸戲劇舞臺,馬基雅維利表達了自己對于那些影響人類行動的情感與野心的關注。因此,我們完全可以接受這樣一個觀點:“對話體給予柏拉圖的機會,猶如戲劇之于馬基雅維利。”[19](P338)
三、《曼陀羅》的隱喻式解讀及其批評
《曼陀羅》是馬基雅維利最具原創性的一部戲劇。與《君主論》和《李維史論》比較而言,這部戲劇在馬基雅維利還活著的時候就為他贏得了名聲。根據喬萬尼 (Giovanni Manetti)1526年初寫給馬基雅維利的一封信,《曼陀羅》與普勞圖斯的《孿生兄弟》同一個晚上在威尼斯上演,羅馬喜劇雖然得到優美的吟誦,但與《曼陀羅》相比,卻仍然被認為“毫無生機”[20](P379)。馬基雅維利本人在與圭恰迪尼的通信里,也多次提起這部戲劇,并為好友能從中得到愉悅而甚覺快樂。[21](P164)可見,《曼陀羅》不僅獲得別人的贊譽,馬基雅維利本人對《曼陀羅》也甚為滿意。
不少評論家給予《曼陀羅》一種重要的地位,認為它與馬基雅維利的思想尤其是政治思想有著密切的聯系,從而對之進行直接的政治解讀。解讀的方式基本上是將戲劇情節與政治進行隱喻式的對照與比附,主要有以下兩種具體進路:
第一,現實政治的隱喻:陰謀政治。這種思路強調從戲劇的形式出發來進行理解,認為戲劇是歡迎解釋的,因而致力于探幽索隱、力圖發現潛藏在文學作品當中的隱喻,并且相信馬基雅維利對于文學作品里的隱喻傳統是非常熟悉的。“馬基雅維利肯定認為他的觀眾或多或少熟悉中世紀的隱喻寫作傳統,以及諸如但丁和薄伽丘等人在文學寫作中使用隱喻所表達的主張。馬基雅維利本人就寫過《蠢驢》這樣一首隱喻味道非常濃烈的詩歌。”[22](P807)持有這種解釋進路的學者如阿蘭桑多·巴隆基 (Alessandro Parronchi)、桑伯格 (Sumberg)和卡勒斯 ·羅德 (Carnes Lord)。他們受到馬基雅維利是一名政治家的身份影響,利用劇本人物關系與歷史背景的分析,認為《曼陀羅》里存在著關于現實政治的隱喻。巴隆基把《曼陀羅》看做美第奇家族回歸的寓言。①Alessandro Parronchi.“La prima rappresentazione della‘Mandragola’”.L a Bibliof ilia.64(1962),37-86。原文“allegoria del ritorno dei Medici in Firenze”,也即“關于佛羅倫薩美第奇家族回歸的寓言”。桑伯格認為這部戲劇表面上的缺陷以及庸俗景象下的隱性情節 (hidden plot)隱藏著一些馬基雅維利政治教誨的危險因素。他指出,馬基雅維利演繹了密謀推翻腐化國家的新科學,并預示著一場針對腐化的佛羅倫薩的陰謀。[23](P320-340)卡勒斯同樣認為,《曼陀羅》當中包含著精心編制的隱喻,這種隱喻為馬基雅維利在佛羅倫薩參與的政治活動,他在文章里詳盡細膩地分析了劇中人物與1504年左右佛羅倫薩政治人物的對應關系。[24]強調《曼陀羅》是陰謀政治的隱喻,這種思路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馬基雅維利政治著述當中對陰謀的精心討論的影響。馬基雅維利在《李維史論》篇幅最長的一章里詳細討論了陰謀[25](P218-235),包括陰謀的重要性、君主防范陰謀的舉措以及參與陰謀的私人公民應如何行動,等等,而這些近似于《曼陀羅》中的過程。這些認為劇中隱喻著陰謀政治的解讀鉤沉索隱,想象力豐富且極富創造性,但是除了挖掘出馬基雅維利在寫作上所展現出的審慎技藝外,它們對于理解馬基雅維利的思想并沒有實質性的意義。
第二,政治理念的比附:新君主典范與馬基雅維利式人物的尋找。在這種進路中,闡釋者將《曼陀羅》劇中人物與馬基雅維利政治理念世界當中的新君主典范進行關聯分析。另外,這種進路往往也會尋找劇中的馬基雅維利。這類文獻比較豐富。總體而言,研究者普遍認為,李古僚像是馬基雅維利,而卡利馬科則是馬基雅維利在《君主論》中所設想的領導者。[26](P272)不過,也有文章認為,恰好就是看起來很愚蠢的尼恰,充分展現了馬基雅維利作為一名愚人大師的德性。[27](P99-115)也有評論家指出,劇中的每個男性角色都被理解成為馬基雅維利本人的自我表現。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合理的,因為我們對人物的刻畫本身就蘊含著自我表露的因素。在一個對自我做出最有效介紹才有利于獲得成功的社會里,這種可能性就更有依據。對于馬基雅維利來說,在離開政治舞臺的那些年月里,一直帶有重返政治舞臺的想法,那么,追求刻畫一個全新的自己就顯得理所當然。不管是就政治和外交方面進行著書立言,還是對自己所可能的樣子予以戲劇或詩歌形式的嘲諷,這些都有可能為他回歸政治舞臺或者重建人脈提供幫助。[28](P153)借助于劇本里的人物角色與政治著述中的歷史典范的比附,可以在馬基雅維利的戲劇作品與政治著述之間建立起更為緊密的關系,但這樣的結果是導致其戲劇作品淹沒在政治著述業已構建起的理論框架當中,而看不到戲劇形式本身對于馬基雅維利思想的重要性。
總而言之,把《曼陀羅》與政治直接聯系起來,這種解讀進路有其合理之處。“當政治行動對于馬氏而言沒什么可能時,他轉向文學作品,因而其詩歌、書信以及戲劇里重復著他作為一名政治行動者被壓抑的關懷,這并不是一件令人很驚訝的事。”[29](P265)這種進路注意到了馬基雅維利在戲劇當中或針砭時弊、或冷嘲熱諷。這既符合馬基雅維利的能力和個性——他本人在《曼陀羅》的開場白當中毫不諱言,尖酸刻薄也是他最為擅長的技藝[30](P11),也與其時代的作風基本保持一致——“‘目光銳利、口舌刻薄’是對于這個城市 (指佛羅倫薩——筆者注)的居民的描寫。對每件事和每個人都隨便加以蔑視大概是當時社會上流行的風氣。”[31](P175)然而,盡管這種進路注意到《曼陀羅》與馬基雅維利政治著述中的一致性,卻得出了一個夸張而草率的結論:“《曼陀羅》并不是一部普通的喜劇,它所呈現出的事件歸根到底不是關于‘私人生活’的,而是對‘政治領域’的分析。”[32](P810)于是,這種進路使得戲劇僅僅成為馬基雅維利表達政治思想的一個載體,卻忽視了戲劇本身作為一部獨立作品所具有的思想深度。因而,有研究者反對把《曼陀羅》視為挖掘政治寓意的素材。黑爾抱怨說,人們過度解釋馬基雅維利的文學作品,總是要用這些文學作品來撐起馬基雅維利作為政治、軍事或者歷史作家的名譽,或者用來說明馬氏某些不為人知的人格特征,而很少把他們視為藝術作品,亦即源自豐富的文學靈感、語言激情以及寫作過程的作品。他懇求人們應該把馬基雅維利的文學作品看做獨立的藝術作品,而不是視為挖掘政治意涵的材料。他認為勉強從《曼陀羅》中挖掘政治意涵,是對馬基雅維利的一種掠奪。[33](Pxi)
綜上所述,文學作品固然歡迎隱喻式解讀,而馬基雅維利既是政治家又是戲劇家的身份也鼓勵人們對其作品探幽索隱。但是,將馬基雅維利的戲劇與其政治著述或現實政治進行簡單的比附,然后得出結論認為馬基雅維利的戲劇是政治的,這種觀點與認為馬基雅維利的思想在其政治著述中已完全展現的說法一樣,都是對馬基雅維利文學作品的輕視,從而一起陷入了馬基雅維利為其觀眾所設下的局。[34](P10)政治領域與戲劇世界對于他來說,都是同等重要的,也只有在這種并行結構下,真正的馬基雅維利才能得以彰顯。
四、一個人應當如何生活:馬基雅維利的審慎
《曼陀羅》里的戲劇行動圍繞著這樣一個具體問題展開:為了達成一個既定目標,應該如何去容忍惡與利用善。在《曼陀羅》所描述的私人生活里,這個目標是卡利馬科勢不可擋的情欲,以及盧克萊西亞與其丈夫尼恰想要一個孩子的欲望。卡利馬科生于佛羅倫薩,后被送往巴黎,在那兒寄居多年。某日,他偶聞家鄉有一位當今世上最美麗的女人,便不顧意大利戰火繚繞,毅然返鄉。驅使他置生死于度外的,是對于盧克萊西亞的占有欲望。與國家統一或者共和福祉這樣的目標比較而言,情欲的實現既不高尚、也不詩意。但在馬基雅維利看來,它是符合人性的。在馬基雅維利的世界里,既有著沉重的政治問題、軍事事務,也有著輕飄的感情與欲望。在他的生活與著述中,人們會看到他處理嚴肅的外交問題,會知曉他對于共和政治的偏好,也會讀到他與友人討論些不那么正經的事情。馬基雅維利接受包括情欲在內的各種欲望所指向的任何目標,而不僅僅是為了國家或者公共福祉這些高尚的目的。然而,這位讓卡利馬科銷魂奪魄的女人已為人婦,而且看起來端莊、虔誠。她的身份和表面上所呈現出的傳統德性將戲劇行動置于沖突之中,自然欲求的實現遭遇到了道德對行動的限制。卡利馬科在掙扎之后,情欲支配他勢必“要籌劃干點兒事情,哪怕像畜生一樣殘忍、冷酷、可恥”[35](P17)。
在這里,我們所遇到的就是在本文開篇所提到的那個馬基雅維利,即傳授邪惡教誨的馬基雅維利。借用卡利馬科的憂慮和行動,馬基雅維利揭露出自然欲望的要求與道德的要求之間的緊張態勢。為了達成個人所覬覦的目標,完全可以采取邪惡的行動,如同劇中為情欲所控的卡利馬科一樣。他在食客李古潦的主導下,訴諸一連串的欺騙,利用盧克萊西亞丈夫尼恰的輕信以及他們想要得到一個孩子的欲望,成功實現了目標。可見,馬基雅維利的戲劇告訴我們,國家統一或共同福祉不能為他的邪惡教誨開脫,他的邪惡教誨同樣為自然欲求服務。[36](P284-286)在后來,馬基雅維利應圭恰迪尼的邀約為《曼陀羅》上演所添加的獻歌部分里,開篇就指出,那些生活在憂慮和苦楚當中的人們,不懂得這世間的騙局。言下之意,馬基雅維利旨在通過這部戲劇,向人們揭橥這世間的騙局。這個意圖與其《君主論》當中最具影響力且備受爭議的一章所揭示的甚為一致。“人們實際上怎樣生活同人們應當怎樣生活,其距離是如此之大,以至一個人要是為了應該怎樣辦而把實際上是怎么回事置諸腦后,那么他不但不能保存自己,反而會導致自我毀滅。”[37](P73)在這里,馬基雅維利認為其寫作的目的在于論述事物的真實情況,而不是想象的方面。但是,如果據此認為馬基雅維利的作品僅僅是對人們實際上如何行事的觀察與描述,那么必將難以發現馬基雅維利的深刻,而且與其作品里所蘊涵的思想也不相符。事實上,馬基雅維利的著述自始至終都在向人們傳達“應當”如何生活的主張。
借助于反映現實生活的戲劇行動,馬基雅維利充分闡發了對于一個人應該如何審慎行事的見解。在他的世界里,支配世事的并不是道德、上帝或者傳統,而是必需 (necessity)。卡利馬科為了實現其自然欲求,必須訴諸適宜的手段。一開始,卡利馬科希望能通過改變盧克萊西亞的本性 (nature),在她面前展現自己的慷慨以吸引她。不過,李古潦認為這個計策不一定能達到目的,從而提出另一個主張。這個計謀主要依賴于欺騙,這是一個按照古典德性生活的人所不會采取的卻是有保障的妙計。在他看來,道德、宗教給人們所營造出的是一種幻象。在生活中,蕓蕓眾生 (people)寧愿“相信”這些“謊言”,而甚少能夠憑借理智去“判斷”,去看清這世間的真實 (effectual truth)。如同戲劇所指出的,只有祛除此種幻象的人,其行動的可能性才不會受到道德的限制,才能獲取其所欲求的東西。但是,在戲劇里,李古潦洞察到卡利馬科的澡堂計劃不能保障目標的實現,從而提出以曼陀羅為藥方。這說明在馬基雅維利的世界里,并不是每個人都具有判斷力和據以審慎行事的德性。又或者說,馬基雅維利是在向人們建議,人應該審慎行事,他們需要充分洞察這種必需,而不被道德幻象所迷惑。也就是要能夠洞察世事、深諳人性,以冷峻的意志扛住命運,做到順勢而為,包括容忍惡與利用善,而且能夠“表現出”具有傳統或習俗所尊崇的美德,從而達成既定目標。對于目標本身道德與否,馬基雅維利不予置評——在他的作品中,我們所看到的目標,既包括國家統一,也包括共和國的創建,同樣還有本能的情欲。可見,馬基雅維利在洞察世事的基礎上,提出關于人應當如何生活的訓諭。他悉心教誨人們的是,為了達成既定目標,應該采取怎樣的行動。他在《李維史論》中對此毫不諱言:“我以為或能多有所成,俾可給他人達到既定目標提供一條捷徑。”[38](P6)不過,戲劇形式更能彰顯出其學說的普遍性。《曼陀羅》作為一部戲劇,其主要注重的是行動,馬基雅維利能夠將其對審慎行事的理解,巧妙地與戲劇形式結合起來,表明應該如何生活;而馬基雅維利的政治著述所討論的只是其中一些具體的情勢。一旦我們發現,在政治或軍事上的真理可以轉化成反映私人生活的戲劇,或者說在政治與戲劇的并行結構之中,我們會發現馬基雅維利學說的核心并不是共和主義,也不是愛國主義,而是關于一個人應該如何生活的普遍性教誨。
關于這個問題,馬基雅維利的回答與古代倫理和現代道德的進路都有所不同。前者以亞里士多德為代表,從行動者的美德出發,關注人的完善以及道德德性的實現;而后者則是從行動的普遍規則出發,圍繞各種義務展開,例如霍布斯對確定政治義務的不懈努力,康德主義將道德責任視為道德哲學的根本問題,功利主義旨在捍衛普遍福利最大化的原則。至于馬基雅維利,一方面,他關注德性,強調審慎行動的能力,尤其是具有洞察情勢的判斷力和扛住命運的男子漢氣概。但他并沒有像亞里士多德那樣具體討論行動者應該具有哪些美德。他不把道德德性作為行動的目的,反而認為審慎行事不僅要有作惡的能力,也需要偽善的本事。另一方面,他并沒有對究竟應該如何行動提出具體規則,也不像現代道德理論那樣對行動規則進行理論化。可見,他對一個人應該如何生活的回答,既不同于古代倫理又不同于現代道德。
我們正需要從這種區別當中去重新理解馬基雅維利與現代政治乃至現代倫理的關系。伯林認為,馬基雅維利所處理的乃是對兩種不可調和的生活理想的區分,因此也是對兩種道德的區分,一方面是基督教的道德,另一方面是異教徒的道德。人們必須在這兩種生活方式中做出抉擇,選擇一種,放棄另外一種。伯林力圖闡明,馬基雅維利選擇了一種相悖于基督教道德觀的目的王國。分析起來,馬基雅維利的學說的確具有規范意義,不是簡單地玩弄技巧。但這種規范意義并不像伯林所說的那樣,屬于一種以共同目標為最高價值的希臘城邦倫理。馬基雅維利的審慎概念,拒絕將道德德性視為行動的終極目的。[39](P43-58)論者認為馬基雅維利是在兩種道德之間選擇了其中一種,這種說法同樣也是淺薄的。它沒有注意到馬基雅維利的戲劇里對于這兩種道德 (古典的道德德性與基督教的道德)的利用。馬基雅維利并不是在兩種道德之間進行選擇,而是提出了一個超越兩種道德的新范式。
《曼陀羅》還有可能讓我們審視馬基雅維利涉及的古今問題。施特勞斯注意到了馬基雅維利利用愛國主義情結來服務于一個更隱秘不宣、諱莫如深的目的。他認為,馬基雅維利實際上是在提出新的啟示,一個新的法規準則的啟示,一個新的基督教十誡的啟示。[40](P83)但是,他將馬基雅維利簡單地置于古今之爭當中并認為他屬于“今人”或現代性的開創者也是有問題的。他的確洞察到馬基雅維利與前人的斷裂。但是,馬基雅維利的審慎概念與現代倫理并不相同,同時他也沒有開創出一種現代政治理性概念。不同于霍布斯的是,馬基雅維利的審慎概念缺乏一種現代政治理性所具有的普遍性。他的審慎德行只為部分人所擁有,蕓蕓眾生更多是“相信”而非“判斷”。至少,從這個意義上看,我們很難認為馬基雅維利是現代政治的開創者。因而,馬基雅維利在戲劇行動里對審慎的理解,為我們重新審視其在思想史上的地位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1] John H.Geerken. “Machiavelli Studies Since 1969”.J 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1976,37.
[2] 黑格爾:《新的歷史中的國家理性的理念》,1925。轉引自卡西爾:《國家的神話》,北京,華夏出版社,2003。
[3][7][36][40] Strauss.Thoughts on Machiavelli.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9.
[4][25][38] Machiavelli.Discourses on Livy.translated by Harvey C.Mansfield and Nathan Tarcov.Chicago&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6.
[5][9][12][14][20] James B.Atkinson and David Sices.Machiavelli and His Friends:Their Personal Cor-respondence.Dekalb: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96.
[6] 亞里士多德:《詩學》,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
[8] Joseph V.Femia.Machiavelli Revisited.University of Wales Press,2002.
[10] Vickie B.Sullivan.The Comedy and Tragedy of Machiavelli.Yale University Press,2000.
[11] 邁克爾·懷特:《馬基雅維利:一個被誤解的人》,長春,東北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
[13] 斯金納:《馬基雅維利》,北京,工人出版社,1986。
[15][30][34][35] Machiavelli.Mandragola.Translation,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Mera J.Flaumenhaft.Illinois:Waveland Press,Inc.,1981.
[16][21][33] J.R.Hale.The Literary Works of Machiavelli.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1.
[17] 黑格爾:《美學》第三卷 (下),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
[18] Salvatore Di Maria.“Machiavelli on stage:MandragolaandClizia”.inSeeking Real Truths,ed.by Vilches Patricia and Seaman Gerald,Brill Academic Pub,2007.
[19][23] Theodore A.Sumberg.“L a Mandragola:An Interpretation”.The Journal of Politics.Vol.23,No.2,1961.
[22][24][32] Carnes Lord.“On Machiavelli's Mandragola”.The J ournal ofPolitics.Vol.41,No.3,1979.
[26][29] Susan Behuniak-Long.“The Signification of Lucrezia in Machiavelli's‘L a Mandragola’”. The Review ofPolitics.Vol.51,No.2,1989.
[27] Michael Palmer. “The Master Fool:The Conspiracy of Machiavelli's Mandragola”.inMasters and Slaves.Lanham,Lexington Books,2001.
[28] Ruggiero Guido.Machiavelli in Love.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7.
[31] 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37] 馬基雅維利:《君主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
[39] Isaiah Berlin.“The originality of Machiavelli”.Nigel Warburton,Jon Pike,Derek Matravers(ed.).Reading Political Philosophy:Machiavelli to Mill.London:Routledge,2000.
(責任編輯 林 間)
Rethinking of Machiavelli:Based on the Reading ofMandragola
CHEN Hua-wen
(School of Government,Sun Yat-sen University,Guangzhou,Guangdong 510275)
There are many faces of Machiavelli hidden in the literature,some of which are even contrary to one another.However,the approaches that try to fix the gap are not convincible enough.The reason is that they are limited simply in Machiavelli's political writings.Mandragolatends to deal with a problem of the universal.In the light of the drama action,Machiavelli presents his understanding of how one should live,which constructs the core of his teaching.The answers he provides are different from the approaches of ancient ethics and modern morality.Thus,we can rethink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chiavelli and modern politics or modern eth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Mandragola.
Machiavelli;Mandragola;prudence;modern politics
陳華文: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 (廣東廣州5102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