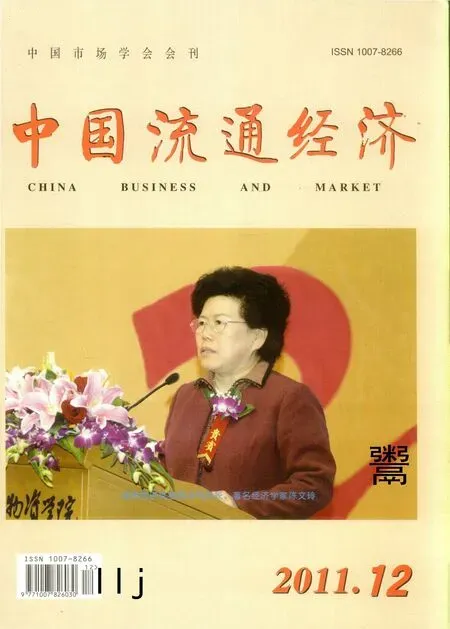產(chǎn)品內(nèi)貿(mào)易、分工與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升級(jí)關(guān)系研究
安歌軍,趙景峰
(西北大學(xué)經(jīng)濟(jì)管理學(xué)院,陜西 西安 710069)
借助第三次科技革命帶來(lái)的生產(chǎn)力的巨大飛躍,產(chǎn)品內(nèi)分工成為當(dāng)代國(guó)際分工的典型形態(tài)。基于產(chǎn)品內(nèi)分工的貿(mào)易稱為產(chǎn)品內(nèi)貿(mào)易,產(chǎn)品內(nèi)分工方式出現(xiàn)以后,中間投入品貿(mào)易成為國(guó)際產(chǎn)業(yè)交換的主要形式。在跨國(guó)公司產(chǎn)品內(nèi)分工的全球生產(chǎn)價(jià)值網(wǎng)絡(luò)中,我國(guó)長(zhǎng)期專業(yè)從事低端加工,逐漸出現(xiàn)了被跨國(guó)公司“邊緣化”的趨勢(shì)。因此,在新時(shí)期跨國(guó)公司爭(zhēng)相沿著產(chǎn)品生產(chǎn)價(jià)值鏈逐步攀升尋找新的核心競(jìng)爭(zhēng)力的背景下,我國(guó)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的升級(jí)顯得尤為必要。
一、跨國(guó)公司產(chǎn)品內(nèi)貿(mào)易的發(fā)展
1.跨國(guó)公司產(chǎn)品內(nèi)貿(mào)易的興起與發(fā)展
跨國(guó)公司產(chǎn)品內(nèi)分工與貿(mào)易的興起和繁榮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jié)果。首先,科技革命造成的生產(chǎn)力的巨大飛躍使技術(shù)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技術(shù)進(jìn)步所帶來(lái)的產(chǎn)品生產(chǎn)工序的可分離性為產(chǎn)品內(nèi)分工與貿(mào)易的發(fā)展創(chuàng)造了有利的前期條件。其次,各國(guó)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不平衡性與資源稟賦的差異,為跨國(guó)公司產(chǎn)品內(nèi)分工與貿(mào)易提供了極為有利的現(xiàn)實(shí)條件。由于缺乏資金、技術(shù)實(shí)力,發(fā)展中國(guó)家不得不承接發(fā)達(dá)國(guó)家的產(chǎn)業(yè)轉(zhuǎn)移,嵌入跨國(guó)公司全球產(chǎn)品內(nèi)分工價(jià)值鏈,在產(chǎn)業(yè)轉(zhuǎn)移中分享已經(jīng)被發(fā)達(dá)國(guó)家瓜分過(guò)的極為有限的利潤(rùn)空間。同時(shí),產(chǎn)品內(nèi)分工與貿(mào)易的蓬勃發(fā)展還得益于世界市場(chǎng)上各個(gè)地理單位資源稟賦的差異性,由要素稟賦差異形成的比較優(yōu)勢(shì)為參與產(chǎn)品內(nèi)分工與貿(mào)易的各國(guó)取得分工與貿(mào)易利益,提供了現(xiàn)實(shí)的可能性。再次,跨國(guó)交易中商流、信息流、資金流與物流等交易成本的下降,有力地促進(jìn)了跨國(guó)公司產(chǎn)品內(nèi)分工與貿(mào)易的發(fā)展,如遠(yuǎn)洋、航空運(yùn)輸成本的大幅降低以及新舊通信手段之間的相互滲透與融合,使產(chǎn)品內(nèi)分工與貿(mào)易進(jìn)一步深化。最后,全球范圍內(nèi)貿(mào)易自由化的發(fā)展與各國(guó)鼓勵(lì)加工貿(mào)易的政策變化對(duì)產(chǎn)品內(nèi)分工與貿(mào)易發(fā)揮了積極的促進(jìn)作用。
2.跨國(guó)公司產(chǎn)品內(nèi)貿(mào)易對(duì)國(guó)際產(chǎn)品內(nèi)分工的影響
壟斷資本主義資本輸出的發(fā)展讓跨國(guó)公司出現(xiàn)在人們的視野中,生產(chǎn)的跨國(guó)經(jīng)營(yíng)使跨國(guó)公司得以在全球范圍內(nèi)盡可能地提升資源配置效率,由生產(chǎn)力所推動(dòng)的社會(huì)分工的細(xì)化也為跨國(guó)公司獲益最大化提供了現(xiàn)實(shí)的途徑,由產(chǎn)業(yè)間分工到產(chǎn)業(yè)內(nèi)分工,再到當(dāng)前盛行的產(chǎn)品內(nèi)分工,跨國(guó)公司的全球生產(chǎn)價(jià)值鏈在地域上不斷趨于分散化,跨越多個(gè)國(guó)家的垂直價(jià)值鏈不斷延長(zhǎng),跨國(guó)公司的中間產(chǎn)品貿(mào)易持續(xù)增加。跨國(guó)公司之所以能夠主導(dǎo)國(guó)際產(chǎn)品內(nèi)國(guó)際分工,依靠的是其強(qiáng)大的由技術(shù)優(yōu)勢(shì)、企業(yè)規(guī)模、組織管理能力及融資能力組成的所有權(quán)優(yōu)勢(shì),在跨國(guó)公司的控制下,國(guó)際產(chǎn)品內(nèi)分工生產(chǎn)價(jià)值鏈得以在各地比較優(yōu)勢(shì)的引導(dǎo)下進(jìn)行合理的配置,然后各國(guó)通過(guò)中間產(chǎn)品的貿(mào)易進(jìn)行國(guó)際交換,在不同層次的國(guó)家之間形成一種工序型的國(guó)際分工新格局。
在以跨國(guó)公司為主導(dǎo)的產(chǎn)品內(nèi)國(guó)際分工與貿(mào)易中,各國(guó)的分工地位是不平等的,因而獲益是不均衡的。跨國(guó)公司憑借自身強(qiáng)大的所有權(quán)優(yōu)勢(shì)與內(nèi)部化優(yōu)勢(shì),依據(jù)發(fā)展中國(guó)家的區(qū)位優(yōu)勢(shì)與資源稟賦特點(diǎn),將自己處于成熟階段與標(biāo)準(zhǔn)化階段的產(chǎn)品分布于全球各個(gè)地理區(qū)域,自身長(zhǎng)期占據(jù)附加值較高的高端價(jià)值鏈戰(zhàn)略性增值環(huán)節(jié)。而發(fā)展中國(guó)家則長(zhǎng)期處于簡(jiǎn)單的加工裝配等低附加值環(huán)節(jié),其優(yōu)勢(shì)的取得只能依靠產(chǎn)品價(jià)值鏈轉(zhuǎn)移過(guò)程中的技術(shù)外溢與知識(shí)擴(kuò)散效應(yīng),從而長(zhǎng)期處于被動(dòng)“被鎖定”的狀態(tài),逐漸在新型的國(guó)際分工中被發(fā)達(dá)國(guó)家邊緣化,失去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優(yōu)化和升級(jí)的內(nèi)在動(dòng)力。在各地域之間比較優(yōu)勢(shì)的瞬息萬(wàn)變中,發(fā)展中國(guó)家還面臨跨國(guó)公司撤資后造成的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空心化”帶來(lái)的威脅。因此,在由跨國(guó)公司主導(dǎo)的產(chǎn)品內(nèi)國(guó)際分工中,發(fā)展中國(guó)家在參與分工和貿(mào)易的同時(shí),必須清醒地認(rèn)識(shí)到,本國(guó)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的優(yōu)化升級(jí)才是長(zhǎng)遠(yuǎn)之計(jì)。
二、中國(guó)參加國(guó)際產(chǎn)品內(nèi)分工與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升級(jí)分析
產(chǎn)業(yè)鏈的全球鋪展形成了產(chǎn)品生產(chǎn)工序在空間上的分離,中間投入品貿(mào)易由此獲得了長(zhǎng)足的發(fā)展。發(fā)達(dá)國(guó)家憑借其強(qiáng)大的競(jìng)爭(zhēng)實(shí)力,在由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基本競(jìng)爭(zhēng)規(guī)則決定的分工中長(zhǎng)期占據(jù)著進(jìn)入壁壘較高的環(huán)節(jié)和區(qū)段,而廣大發(fā)展中國(guó)家則只能依托產(chǎn)業(yè)轉(zhuǎn)移過(guò)程中的技術(shù)與知識(shí)外溢來(lái)獲得發(fā)展與提升的可能性空間,我國(guó)參與對(duì)外貿(mào)易的實(shí)踐充分說(shuō)明了這一點(diǎn)。
1.我國(guó)參與國(guó)際產(chǎn)品內(nèi)分工的現(xiàn)狀
跨國(guó)公司全球價(jià)值鏈的縱向整合極大地降低了產(chǎn)品價(jià)值供應(yīng)體系的運(yùn)行風(fēng)險(xiǎn)和成本,在資源充裕的地區(qū)設(shè)立密集使用該種資源要素的增值環(huán)節(jié)。以勞動(dòng)力資源豐富廉價(jià)而著稱的中國(guó),參與國(guó)際產(chǎn)品內(nèi)分工與貿(mào)易的主要形式就是能密集使用這一資源的加工貿(mào)易。加工貿(mào)易是我國(guó)參與國(guó)際產(chǎn)品內(nèi)分工與貿(mào)易的主要方式,也是我國(guó)對(duì)外貿(mào)易的主體,主要涉及汽車、電子等專業(yè)化分工程度較高的行業(yè)。我國(guó)的加工貿(mào)易是一種典型的垂直型產(chǎn)品內(nèi)貿(mào)易,被稱為“三角貿(mào)易”,即從以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為主的東亞國(guó)家(地區(qū))進(jìn)口資本品和技術(shù)含量較高的中間產(chǎn)品,充分利用我國(guó)的勞動(dòng)力和土地資源成本優(yōu)勢(shì)進(jìn)行組裝加工,然后將一部分出口至這些國(guó)家(地區(qū)),一部分出口至歐美國(guó)家的貿(mào)易狀態(tài)。在這種加工貿(mào)易方式中,東亞各國(guó)將中國(guó)視為制造基地和出口平臺(tái),我國(guó)則處于東亞國(guó)際生產(chǎn)網(wǎng)絡(luò)的低端,從事加工裝配工作,所獲得的利益僅限于微薄的勞務(wù)加工費(fèi),長(zhǎng)期以來(lái)這種加工貿(mào)易方式成為我國(guó)對(duì)外貿(mào)易順差的主要來(lái)源。
進(jìn)口中間投入品,經(jīng)加工組裝后再出口的生產(chǎn)與貿(mào)易活動(dòng),使我國(guó)中間產(chǎn)品的貿(mào)易發(fā)展迅速。根據(jù)胡小娟的研究結(jié)果,1995~2004年我國(guó)中間產(chǎn)品出口的年增長(zhǎng)率為34.43%,中間產(chǎn)品進(jìn)口的年均增長(zhǎng)率為17.5%。其中,半成品的年均增長(zhǎng)率為7.21%,零部件的增長(zhǎng)率為26.03%。1995年以來(lái),中間產(chǎn)品進(jìn)口始終占進(jìn)口總額的50%以上,中間產(chǎn)品的進(jìn)口來(lái)源地為以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為首的東亞,中間產(chǎn)品的出口地為西歐和北美等地,中間產(chǎn)品貿(mào)易的迅速發(fā)展是我國(guó)承接國(guó)際產(chǎn)品內(nèi)分工的主要體現(xiàn)。在國(guó)際產(chǎn)品內(nèi)分工與貿(mào)易中承擔(dān)加工貿(mào)易,而且在加工貿(mào)易進(jìn)出口企業(yè)中,外資企業(yè)占據(jù)很高的比重,這充分反映了我國(guó)在國(guó)際產(chǎn)品內(nèi)分工與貿(mào)易中所占據(jù)的低端加工裝配環(huán)節(jié)和對(duì)外資的嚴(yán)重依賴。
2.產(chǎn)品內(nèi)貿(mào)易和國(guó)際分工的發(fā)展要求提升中國(guó)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層次
參與國(guó)際產(chǎn)品內(nèi)分工的深度與現(xiàn)實(shí)已經(jīng)使我國(guó)不能再忽視跨國(guó)公司產(chǎn)品內(nèi)貿(mào)易的存在了。無(wú)疑,跨國(guó)公司通過(guò)產(chǎn)品內(nèi)分工將大量先進(jìn)的技術(shù)與設(shè)備帶入中國(guó),通過(guò)技術(shù)外溢與知識(shí)外溢有力地促進(jìn)了我國(guó)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與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的調(diào)整,但同時(shí)也應(yīng)該看到,通過(guò)加工貿(mào)易過(guò)程中的技術(shù)與知識(shí)外溢來(lái)發(fā)展本國(guó)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方式,存在巨大的局限性,缺乏可持續(xù)性。
從功能上看,全球價(jià)值鏈上的每一個(gè)環(huán)節(jié)都是產(chǎn)品內(nèi)國(guó)際分工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是產(chǎn)品得以順利生產(chǎn)的保障。然而,各產(chǎn)業(yè)鏈之間的收益和影響力具有明顯的非對(duì)稱性,只有某些特定的高附加值的價(jià)值環(huán)節(jié)才能憑借其巨大的影響力獲得高額的收益,而這些戰(zhàn)略環(huán)節(jié)長(zhǎng)期以來(lái)都被發(fā)達(dá)國(guó)家所占據(jù),與發(fā)展中國(guó)家的非戰(zhàn)略環(huán)節(jié)形成了鮮明的對(duì)比。發(fā)達(dá)國(guó)家在全球范圍內(nèi)尋求資源配置的最佳方式,而發(fā)展中國(guó)家吸引發(fā)達(dá)國(guó)家投資的比較優(yōu)勢(shì)具有極強(qiáng)的不穩(wěn)定性,一旦出現(xiàn)比較優(yōu)勢(shì)的變遷,跨國(guó)公司就會(huì)迅速地將其生產(chǎn)工廠遷至比較優(yōu)勢(shì)較大的地區(qū),從而使原生產(chǎn)基地的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面臨“空心化”的困境,南美地區(qū)經(jīng)濟(jì)發(fā)展過(guò)程中這種非戰(zhàn)略環(huán)節(jié)的不穩(wěn)定性表現(xiàn)得尤為明顯。在諸多因素的作用下,在承接國(guó)際產(chǎn)品內(nèi)分工的過(guò)程中,我國(guó)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面臨著巨大的風(fēng)險(xiǎn)。[1]
首先,通過(guò)產(chǎn)業(yè)轉(zhuǎn)移“空間分割”,我國(guó)作為跨國(guó)公司全球價(jià)值鏈的一個(gè)布點(diǎn)被納入全球生產(chǎn)價(jià)值鏈體系,從事產(chǎn)品單一環(huán)節(jié)的生產(chǎn),往往不能形成整體的競(jìng)爭(zhēng)優(yōu)勢(shì),面臨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被鎖定在低端環(huán)節(jié)的風(fēng)險(xiǎn),同時(shí)前后向的產(chǎn)業(yè)聯(lián)系被弱化,難以對(duì)本國(guó)產(chǎn)業(yè)形成整體的拉動(dòng)作用。其次,跨國(guó)公司往往偏向于利用我國(guó)的靜態(tài)比較優(yōu)勢(shì),僅僅利用我國(guó)的優(yōu)惠條件和低廉的要素成本,并將這種比較優(yōu)勢(shì)固定下來(lái),使其難以升級(jí),使我國(guó)經(jīng)濟(jì)發(fā)展失去自主動(dòng)力。再次,發(fā)達(dá)國(guó)家依據(jù)技術(shù)的不斷進(jìn)步將產(chǎn)品生產(chǎn)中已經(jīng)或即將處于比較劣勢(shì)的環(huán)節(jié)轉(zhuǎn)移至發(fā)展中國(guó)家,而自身卻不斷加大研究開發(fā)力度,沿著產(chǎn)品生產(chǎn)的價(jià)值鏈向高端發(fā)展,這使我國(guó)產(chǎn)業(yè)的發(fā)展從一開始便面臨被“邊緣化”的風(fēng)險(xiǎn)。最后,我國(guó)的勞動(dòng)力比較優(yōu)勢(shì)具有很強(qiáng)的替代性,面臨著與其他國(guó)家的競(jìng)爭(zhēng),而跨國(guó)公司從發(fā)達(dá)國(guó)家轉(zhuǎn)出的均是一些勞動(dòng)密集型產(chǎn)業(yè)環(huán)節(jié),對(duì)要素的要求較低,一旦各國(guó)的比較優(yōu)勢(shì)發(fā)生動(dòng)態(tài)變化,這些產(chǎn)業(yè)必將進(jìn)行轉(zhuǎn)移,這種“候鳥型”的產(chǎn)業(yè)轉(zhuǎn)移極易造成我國(guó)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的“空心化”,給經(jīng)濟(jì)的長(zhǎng)期穩(wěn)定發(fā)展和產(chǎn)業(yè)安全帶來(lái)隱患。
在產(chǎn)品內(nèi)分工全球價(jià)值鏈體系結(jié)構(gòu)極度不穩(wěn)定的客觀現(xiàn)實(shí)下,價(jià)值鏈上的每一個(gè)企業(yè)都處于“逆水行舟,不進(jìn)則退”的競(jìng)爭(zhēng)環(huán)境中,因此在全球價(jià)值鏈體系之中沿著價(jià)值鏈增值路徑提升產(chǎn)業(yè)發(fā)展層次是每個(gè)企業(yè)的生存法則。
三、從產(chǎn)品內(nèi)貿(mào)易和分工看實(shí)現(xiàn)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升級(jí)的路徑選擇
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的合理化與高級(jí)化是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調(diào)整的兩個(gè)基本要素。在跨國(guó)公司產(chǎn)品內(nèi)分工與貿(mào)易條件下,雖然我國(guó)在某些產(chǎn)業(yè)的規(guī)模和成本上具有一定優(yōu)勢(shì),但由于發(fā)達(dá)國(guó)家對(duì)全球價(jià)值鏈的強(qiáng)大控制力,我國(guó)被迫承接處于低端的勞動(dòng)密集型、價(jià)值增值能力低的加工裝配環(huán)節(jié),國(guó)內(nèi)各產(chǎn)業(yè)之間的比例和相互協(xié)調(diào)能力以及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的升級(jí)均受到牽制。在跨國(guó)公司產(chǎn)品內(nèi)分工與貿(mào)易條件下,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升級(jí)不再僅僅局限于由勞動(dòng)密集型向資本、技術(shù)密集型轉(zhuǎn)變,而且還包含同一生產(chǎn)價(jià)值鏈內(nèi)部勞動(dòng)密集型環(huán)節(jié)向資本、技術(shù)密集型環(huán)節(jié)的轉(zhuǎn)變。[2]
首先,優(yōu)化產(chǎn)業(yè)組織結(jié)構(gòu),提升企業(yè)能力。跨國(guó)公司產(chǎn)品內(nèi)分工與貿(mào)易的發(fā)展,使全球生產(chǎn)價(jià)值鏈呈現(xiàn)“片段化”,使我國(guó)生產(chǎn)組織結(jié)構(gòu)趨向分散化,這對(duì)于企業(yè)更深層次融入跨國(guó)公司全球價(jià)值鏈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制約,也阻礙了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的調(diào)整。因此,要提升產(chǎn)業(yè)集中度與企業(yè)規(guī)模水平,注重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的合理化,切實(shí)調(diào)整各產(chǎn)業(yè)之間的比例,不斷優(yōu)化產(chǎn)業(yè)的組織結(jié)構(gòu),增強(qiáng)產(chǎn)業(yè)之間的協(xié)調(diào)發(fā)展能力。企業(yè)要抓住跨國(guó)公司產(chǎn)品內(nèi)分工的切入點(diǎn),積極參與其中,充分利用現(xiàn)有的比較優(yōu)勢(shì),積累資本、技術(shù)和勞動(dòng)力素質(zhì),同時(shí)利用跨國(guó)公司產(chǎn)品內(nèi)分工與貿(mào)易過(guò)程中的技術(shù)與知識(shí)溢出效應(yīng),通過(guò)“干中學(xué)”不斷積累經(jīng)驗(yàn),追求動(dòng)態(tài)比較優(yōu)勢(shì),爭(zhēng)取向具有較高附加值的戰(zhàn)略性環(huán)節(jié)挺進(jìn)。
其次,發(fā)揮產(chǎn)業(yè)集群的輻射和帶動(dòng)作用,加快產(chǎn)業(yè)整體升級(jí)。當(dāng)前在跨國(guó)公司產(chǎn)品內(nèi)貿(mào)易條件下,參與國(guó)際分工的產(chǎn)業(yè)集群絕大多數(shù)處于國(guó)際產(chǎn)品內(nèi)分工的低端,創(chuàng)新能力不強(qiáng),同時(shí)由于過(guò)度依賴外資,導(dǎo)致產(chǎn)業(yè)集群抗風(fēng)險(xiǎn)能力較差,“路徑依賴”現(xiàn)象嚴(yán)重,產(chǎn)業(yè)集群能力弱小的客觀現(xiàn)實(shí)要求我國(guó)在加快諸多產(chǎn)業(yè)集群建設(shè)的同時(shí),加快產(chǎn)業(yè)集群內(nèi)部各個(gè)產(chǎn)業(yè)鏈條的完整化,形成上下游產(chǎn)業(yè)鏈間的相互拉動(dòng)效應(yīng),提升產(chǎn)業(yè)集群的能力,通過(guò)產(chǎn)業(yè)集群的集體行動(dòng)與跨國(guó)公司各廠商之間建立密切平衡的關(guān)系,通過(guò)集群內(nèi)學(xué)習(xí)與集群間學(xué)習(xí),加快產(chǎn)品與工藝創(chuàng)新,獲得集群的持續(xù)性動(dòng)態(tài)競(jìng)爭(zhēng)優(yōu)勢(shì),推動(dòng)集群企業(yè)在全球工序分工中不斷“入鏈”,發(fā)揮集群內(nèi)各企業(yè)優(yōu)勢(shì),形成協(xié)力生產(chǎn)體系,加快資本與技術(shù)積累,實(shí)現(xiàn)產(chǎn)業(yè)集群在國(guó)際產(chǎn)品內(nèi)分工中的升級(jí)和產(chǎn)業(yè)的持續(xù)升級(jí)。
最后,提升產(chǎn)業(yè)技術(shù)結(jié)構(gòu),發(fā)揮技術(shù)的帶動(dòng)作用。從產(chǎn)品內(nèi)分工角度講,促進(jìn)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升級(jí)應(yīng)以掌握核心技術(shù)為中心展開,“干中學(xué)”的學(xué)習(xí)效應(yīng)對(duì)技術(shù)水平的提升具有重要的促進(jìn)作用,但更為重要的是要加大自主技術(shù)的研究與開發(fā)。因此,應(yīng)建立以企業(yè)為主體,以市場(chǎng)為導(dǎo)向,產(chǎn)學(xué)研相結(jié)合的技術(shù)創(chuàng)新體系,堅(jiān)持原始自主創(chuàng)新、集成創(chuàng)新與引進(jìn)消化吸收再創(chuàng)新相結(jié)合的路徑是我國(guó)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優(yōu)化升級(jí)的必由之路,加快創(chuàng)新體制的建立是關(guān)鍵,要營(yíng)造有利于創(chuàng)新的氛圍,完善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保護(hù)制度,激發(fā)全社會(huì)的創(chuàng)新積極性,并適時(shí)向產(chǎn)業(yè)鏈條的研發(fā)設(shè)計(jì)、品牌營(yíng)銷等高端環(huán)節(jié)滲透,逐步擺脫被發(fā)達(dá)國(guó)家“邊緣化”的困境,提高我國(guó)在國(guó)際產(chǎn)品內(nèi)分工中的地位。
[1]華德亞,董有得.跨國(guó)公司產(chǎn)品內(nèi)分工與我國(guó)的產(chǎn)業(yè)升級(jí)[J].國(guó)際經(jīng)貿(mào)探索,2007,23(8):55-59.
[2]陳曉紅,胡小娟.跨國(guó)公司FDI與我國(guó)中間產(chǎn)品貿(mào)易實(shí)證分析[J].國(guó)際經(jīng)貿(mào)探索,2007(7):62-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