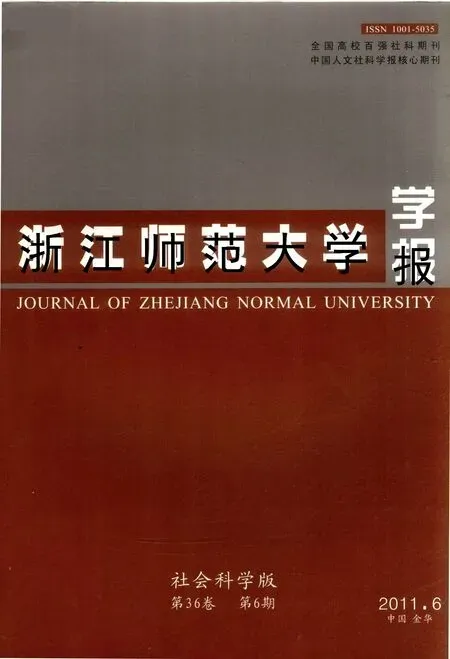藝術“突圍”與文化“暴動”
——20世紀80年代文學思潮和“五四”文化啟蒙關系再梳理*
邵向陽, 楊荷泉
(浙江師范大學人文學院,浙江 金華 321004)
20世紀中國經歷了兩次影響深遠的思想文化變革,第一次是世紀初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在中國古老而傳統的思想文化史上,這場狂飆突進的思想“嘩變”無疑是一場慘烈的文化“暴動”。第二次是世紀末期的80年代思想解放運動,這場因政治解禁而引發的藝術“突圍”,催生了20世紀80年代中國文學對西方文學藝術的模仿和創新,為中國當代文學史留下了一道永遠亮麗的風景線。
關于20世紀80年代文學思潮與“五四”文化啟蒙之間的密切關系,是學術界一個業已形成廣泛共識的話題。大多論者往往認為,以“傷痕文學”為起點的新時期文學就是“重回五四起跑線”。不可否認,20世紀80年代文學在某些方面、在某種程度上重新走上“五四”文學的道路,諸如重拾“五四”的啟蒙理想、重現“五四”的“文學復興”,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然而,由于社會背景、思想氛圍等條件大不相同,20世紀80年代文學思潮不可能完全重復“五四”時期的道路。隨著藝術“突圍”的激情冷卻,它很快被20世紀90年代的物質主義解構成一場藝術模仿表演秀。
一、80年代:第二個“五四”
20世紀80年代初期,隨著“文革”的結束,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狀況發生了重要變化,中國文學壓抑多年的能量與激情似乎也在一夜間爆發,呈現出多元共存的局面。相對于20世紀50年代以來的“十七年文學”、“文革文學”,20世紀80年代的文學出現了令人振奮的嶄新現象。無論是揭露“文革”歷史創傷的“傷痕文學”,還是尋找失落人性的“反思文學”,抑或是探索開拓的“改革文學”等等,無不包含了破舊立新的激情和樂觀主義的人文理想,“一切都令人想起五四時代。人的啟蒙,人的覺醒,人道主義,人性復歸,……都圍繞這感性血肉的個體從作為理性異化的神的踐踏蹂躪下要求解放出來的主題旋轉。‘人啊,人’的吶喊遍及各個領域各個方面。這是什么意思呢?相當朦朧;但有一點又異常清楚明白:一個造神造英雄來統治自己的時代過去了,回到五四時期的感傷、憧憬、迷茫、嘆息和歡樂。但這已是經歷了六十年之后的慘痛復歸”。[1]
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然而,有著類似時代背景的不同時代,也可產生相通的文學主題。作為20世紀80年代文學思潮開端的“傷痕文學”發軔之作,《班主任》發出了“救救被‘四人幫’坑害了的孩子”的時代呼聲,充滿了強烈的啟蒙精神,與魯迅在《狂人日記》中發出的“救救孩子”的呼聲遙相呼應,使我們聽到了和五四文學相同的吶喊聲。這不由得使我們想起那個新舊思潮激烈交戰、東西方思想文化融會撞擊的“五四”時代,“五四”先賢先哲們將解放“自我”、張揚“個性”作為人性解放的一種手段,高揚民主和科學的旗幟,直接投身到文學啟蒙的偉大實踐中。以反封建、人性解放的啟蒙理想作為核心價值觀念的“五四”文學,自誕生之時,就將通過啟蒙手段達到個性解放、民主自由、將人從長期的封建思想禁錮中解放出來,作為一己的道德使命,充滿著人道主義關懷的“五四”啟蒙精神。遺憾的是,“十七年文學”所要著力表現的是集體主義的“大我”“英雄”,人道主義被放逐,“文革文學”里稍有一點人情人性的作品,就有被打成“毒草”的危險。20世紀50年代以來,長達近三十年的政治運動,使得“五四”啟蒙被迫中斷,以民主和科學作為核心精神的“五四”精神漸行消退,甚至消失殆盡,以致釀出一場反科學反民主的鬧劇和悲劇,致使整個國家遭殃、思想文化隔絕封閉、億萬民眾落難、人身人格備受摧殘和侮辱,也使得“五四”啟蒙精神蒙受奇恥大辱。
在結束“文革文學”進入20世紀80年代文學之際,人們要告別一種舊話語而創造一種新話語,必然要借助一些思想資源。由于“文化大革命”被廣泛看作是一場喪失人道主義的封建文化專制運動,是一股建立在反啟蒙基礎上的文化思潮,因此,面對20世紀中國文學史,他們選擇了“五四”,并且特別青睞于“五四”的啟蒙思想,他們高喊著“回歸五四”、“回到魯迅那里去”的口號,重新發現了“五四”的啟蒙理想,接續了“十七年文學”、“文革文學”期間中斷已久的啟蒙運動。伴隨著改革開放的春風,“五四”精神才終于回歸它的發祥地,并重新煥發出新的活力,迎來了“五四”啟蒙精神的全面復蘇和回歸。而20世紀80年代文學的發展也被視為類似于“五四”文學那樣的“復興”。“‘復興’的提出,又通常與‘五四’啟蒙文學相聯系,看成是對‘五四’的‘復歸’。在八十年代初,人們最為向往的,是他們心目中‘五四’文學的那種自由的、‘多元共生’局面”。[2]從20世紀80年代前期的中心問題來看,所要“復興”的,主要是“五四”文學所提倡的“民主”和“科學”的啟蒙精神,和以“五四”為旗幟、在20世紀50-70年代被視為“異端”和“毒草”而遭到否定乃至批判的文學思潮。20世紀80年代文學和五四文學在“啟蒙”這一點上產生了共鳴,這就標志著20世紀80年代文學接通了“五四”以來被阻斷隔絕了30年的啟蒙思潮,也實現了當代文學與“五四”文學的鏈接。可以毫不夸張地說,20世紀80年代的思想解放在某種程度上是對五四精神的繼承和發展,是新時期新的思想啟蒙。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20世紀80年代被看作是“第二個‘五四’時期”,開啟了以“五四”啟蒙思想為主導的“新啟蒙”運動階段。
二、“五四”啟蒙:“啟蒙”的悲哀
“五四”新文化運動“本質上是一場企求中國現代化的思想啟蒙”,[3]與之相伴而生的“五四”文學革命,也因此具有濃郁的啟蒙色彩。“五四”文學先驅們秉承了中國知識分子傳統的憂患意識與使命意識,他們以啟蒙為己任,大力倡導“民主”和“科學”的啟蒙精神,鮮明提出“人權、平等、自由”的啟蒙思想,并試圖以自己的思考和創作實踐喚醒人們關于個性解放、人道主義等意識的思考。從整體上來看,“五四”啟蒙運動的根本動因和任務,就是側重于“人”的徹底解放和覺醒。因此,“人”的發現可以看作是“五四”啟蒙的最大收獲。
作為“人的自然的呼聲”的“五四”文學,將“表現自我”、“個性解放”作為自覺的文學追求,周作人在《人的文學》中提出的“人的文學”,可以作為“五四”啟蒙文學的基本口號。在這一口號的感召下,個人獨立、個性解放成為“五四”時期鮮明的時代特征,出現了一大批抒寫個人生活和情緒的個人化色彩極為濃厚的文學作品,此外,家庭、愛情婚姻等問題在“五四”文學中也或多或少都有所反映。而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魯迅等先驅者以西方的自由平等、民主科學等精神為參照,試圖運用思想啟蒙的手段,來改造在長期的封建社會中積淀而成的國民劣根性,從而推動“五四”啟蒙的歷史進程。魯迅在30年代談及自己的創作時曾說:“說到‘為什么’做小說罷,我仍抱著十多年前的‘啟蒙主義’,以為必須是‘為人生’,而且要改良這人生。我深惡先前的稱小說為‘閑書’,而且將‘為藝術的藝術’,看作不過是‘消閑’的新式的別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4]正是從這樣的“啟蒙主義”文學觀念出發,魯迅的作品往往熱衷于表現一系列的病態社會里的人的精神病苦。在魯迅的影響下,以魯彥、彭家煌、蹇先艾等為代表的鄉土小說作家群則深刻地描繪了封建宗法社會中落后、愚昧、野蠻的農村生活圖景。在“五四”時期的特定環境下,“五四”文學先驅者堅信自己人道主義的精神立場,進行深刻的思想啟蒙,做出了種種艱苦卓絕的努力。無論是以白話文取代文言文為當時的思想啟蒙運動提供了必要的工具,還是周作人的“人的文學”的呼吁、魯迅“救救孩子”的“吶喊”、郭沫若的“鳳凰”的吟唱等等,都是時代的最強音、啟蒙的最強音。
“五四”啟蒙作為中國文學史上較為激進的一股反封建思潮,具有極其樂觀的主觀設想:回顧過去的歷史,為辛亥革命之前遠未完成的“人”的解放與覺醒,進行了歷史的補課;瞻望未來前景,“是從這種人性的得到解放,以及民主主義秩序的得到確立,向著社會主義民主理想,以及人類全面和徹底的解放過渡,由一般意義上的啟蒙主義發展成為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啟蒙”。[5]然而,無論是回顧過去歷史的補課,或是瞻望未來前景的發展,這兩個方面都還遠遠沒有完成。就前者而言,當時的國民并沒有從那種激進的“啟蒙”思潮中清醒過來,在愚昧麻木的“被啟蒙者”眼里看來,“啟蒙者”的一切啟蒙理想全都是毫無意義的“表演”,甚至將“啟蒙者”當作了閑聊的“談資”。這是“啟蒙者”和“被啟蒙”者之間不可避免的隔膜,是啟蒙的悲哀。實際上,“五四”啟蒙陷入一種“啟而尚蒙”的尷尬局面。此外,“在‘五四’前期,現實急需的是直接服務于當時思想啟蒙運動的‘啟蒙文學’,而不是對文學自身進行啟蒙的‘文學啟蒙’”,[6]也就是說,“五四”啟蒙走上了政治啟蒙先行的道路,五四文學淪為了為政治服務的工具。“20年代末啟蒙高潮的自動衰減,成了啟蒙運動失敗的明顯標記,在啟蒙意識被不斷涌來的革命文學、救亡運動遮沒覆蓋、瓦解的同時,胡適走向了學術,陳獨秀走向了革命,周作人走向了閑適,只剩下魯迅孤獨地、始終不懈地堅持自己懷疑的啟蒙精神”。[7]然而,全國解放以后的文學發展趨勢并不是向“人性的解放”邁進,“文化大革命”更是把批判和禁錮人性的趨勢推向了極端。總之,由于“五四”啟蒙所要試圖解決的艱巨任務并未能得到完成,所以“五四”啟蒙并不能算是一次成功的嘗試。
然而,歷史是絕不會跳躍前進的,歷史在哪里斷裂,歷史就會在哪里重演。任何一個可能會產生重大歷史作用的文學命題,只要在前一個時代的任務還沒有完成,那么它就會在后面一個嶄新的時代中被再度提出來。“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后,“人”的解放和覺醒、獨立和自主、價值和尊嚴等問題被重新提出來,20世紀80年代作為一個新時期所肩負的歷史使命,就是繼續未竟的“五四”啟蒙的任務。既然“五四”所開啟的反封建任務沒有完成,那么80年代所面臨的首要任務就是如同“五四”時期打破封建傳統那樣,將深受“現代迷信”毒害的人們從“文革”的禁錮中解放出來。
三、“新啟蒙”:“五四”的回歸與偏離
“救亡壓倒啟蒙”是李澤厚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在一篇題為《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的文章中提出的著名觀點,在這篇文章中,李澤厚以“啟蒙”與“救亡”兩大性質不相同的思想史主題來建構中國現代史,認為在中國現代史的發展過程中,民族危亡的嚴峻現實迫使知識分子放棄啟蒙理想而走向民族救亡,“反封建”的“五四”啟蒙任務被民族救亡主題中斷,而且被封建主義傳統的“集體主義”意識形態悄悄地改頭換面,最終造成了封建主義在20世紀50年代中后期直至“文化大革命”期間的泛濫成災。李澤厚將“文化大革命”發生的原因歸結為“封建傳統”的全面復活,其原因是“五四”提出的反封建任務沒有完成。李澤厚不僅解釋了“救亡壓倒啟蒙”的過程,而且把它看作是20世紀80年代回到“五四”的根本動因,“這種對‘文革’產生原因的解釋成為1980年代知識分子的廣泛共識,以致有學者稱它為80年代知識界的‘元話語’”。[8]作為對20世紀80年代“新啟蒙”發生原因的一種闡釋,李澤厚的“救亡壓倒啟蒙論”無疑成為了新時期的重要思想理論資源。在“新時期”文學史敘事中,“十七年文學”和“文革文學”常常被理解為“五四”啟蒙精神在此期間中斷的兩個文學史階段,這就是影響至深的“斷裂論”。“‘斷裂論’之所以成為影響深遠的文學史敘述,不能不說和20世紀80年代的‘新啟蒙’話語有著直接的關系”,[9]既然“五四”啟蒙的任務沒有完成,那么20世紀80年代作為一個新的歷史時期的使命,就是繼續被中斷的“啟蒙”精神,“救亡壓倒啟蒙”作為“元話語”,促使“啟蒙”成為20世紀80年代文學思潮的主導聲音。
以1985年前后為界,20世紀80年代文學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由于“文革”被普遍認為是“封建主義”的“全面復辟”,因此在紛雜的思想文化“輸入”的20世紀80年代前期,人道主義的啟蒙精神成為反叛“文革”模式的話語資源。在這一時期,出現了一大批對“文革”批判、反思的具有啟蒙精神的文學創作。就小說而言,出現了“傷痕文學”和“反思文學”的潮流。20世紀80年代的“新啟蒙”以“傷痕文學”的代表作《班主任》為開端,作品所傳達出來的那聲原始的現代性吶喊,振聾發聵地撼動、喚醒并復蘇了人們內心深處反封建的現代人性欲望。事實上,“傷痕小說”就是人的心靈拷問的文學表達過程,“傷痕小說”發軔的初衷,就是掙脫“文化專制”的枷鎖、更新全民族觀念的啟蒙過程。隨后,“反思文學”繼承了“傷痕文學”的衣缽,從建國以來的歷史事實中尋找反人道、封建專制的根源,試圖尋找失落的人性基點。詩歌創作的主要成就,體現在青年一代的“朦朧詩”創作和“復出詩人”的“歸來的歌”。舒婷、北島、顧城等青年一代朦朧詩人以思想啟蒙為創作的基點,以表現“自我”和張揚“個性”為時髦和責任;艾青、公劉等“歸來”的詩人用他們非凡的勇氣與膽量,對十年浩劫進行了痛苦而深刻的反思,寫出了一系列引人共鳴的優秀詩篇,成為啟蒙的利器。此外,這一時期的戲劇也承接了“當代”的傳統,以與“文革”有關的“社會問題劇”為主。可以說,20世紀80年代前期的“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朦朧詩歌”、“歸來的歌”等文學思潮都屬于廣義范疇的啟蒙文學。
20世紀80年代中期,文學界積聚的革新力量開始得到釋放,迎來了文學創新的“高潮”,涌現出了一大批與“傷痕文學”、“反思文學”的藝術形態不同的作品:《系在皮繩扣上的魂》(扎西達娃)、《古船》(張煒)、《透明的紅蘿卜》(莫言)、《爸爸爸》(韓少功)、《你別無選擇》(劉索拉)等等,此后便有“尋根文學”、“現代派文學”的提出。到了80年代中后期,“回到文學自身”和“文學自覺”成了熱門話題。在這一文學命題的感召下,對文學“形式”問題的關注、對文學承擔過多的社會責任的清理、對文學只關注社會政治層面問題的反省等問題,引起了當代作家的重視。他們開始探索語言和敘述的可能性,開始嘗試遠離社會政治問題的“日常生活”寫作、“個人寫作”,諸如馬原的《岡底斯的誘惑》、洪峰的《極地之側》、格非的《迷舟》、孫甘露的《信使之函》、方方的《風景》、池莉的《煩惱人生》等等,此后又有“先鋒小說”、“新寫實小說”的提出。縱觀20世紀80年代中期及中后期的文學創作,“文學啟蒙”的口號已經成為疑問:“尋根文學”表現出的“復古”傾向,會導向對批判反思的“傳統文化”的回歸;“現代派文學”所引起的“現代派問題”之辯與“偽現代派”之辯,“實際上就是堵死了一個人文啟蒙的探索通道”;[10]“先鋒”作家們只注重追求諸如卡夫卡、馬爾克斯等一系列西方現代派大師的形式表現,卻忽略了他們作品中深層次的人文思想內涵;“新寫實小說”所謂“還原”生活的“零度敘事”模式使得文字中人文價值的判斷顯得模糊難辨,最終與現代啟蒙的精神漸行漸遠。
縱觀整個20世紀80年代的文學創作,前期“傷痕文學”、“反思文學”還在努力繼續“五四”時期未竟的“啟蒙”任務,然而,啟蒙主義思潮的內涵在80年代中期和中后期卻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即思想內核由啟蒙主義向著存在主義的蛻變”。[11]無論是 80年代中期的“尋根文學”、“現代派文學”,還是80年代中后期的“先鋒小說”、“新寫實小說”,啟蒙思想的含量顯得愈加稀薄:“尋根文學”致力于對傳統意識、民族文化心理挖掘,清晰可見地透露出對文化保守主義觀念的堅守;“現代派文學”將西方現代文學資源作為獲取靈感的渠道,潛隱地對啟蒙已經構成了某種有力的威脅;“先鋒小說”在吸納西方現代主義觀念的同時,也在進行著對現實的消解,將文學導向了虛無主義的道路;“新寫實小說”看似褒揚“日常生活”的背后,隱藏的是對啟蒙精英意識的顛覆。不可否認,單單從文學本位的角度來看,80年代中期以及中后期的“尋根文學”、“現代派文學”、“先鋒小說”、“新寫實小說”的文學價值遠遠超過了80年代前期的“傷痕文學”和“反思文學”等文學思潮,然而前者在啟蒙上的缺失也是顯而易見的。同樣,不可避免地,20世紀80年代的“新啟蒙”同“五四”啟蒙一樣,最終陷入了“式微”的悲劇宿命。
關于“啟蒙”,德國哲學家康德有一個經典的說法:“啟蒙運動就是人類脫離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狀態。不成熟狀態就是不經別人的引導,就對運用自己的理智無能為力。當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經別人的引導就缺乏勇氣與決心去加以運用時,那么這種不成熟狀態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Sapere aude!(要敢于認識!)要有勇氣運用你自己的理智!這就是啟蒙運動的口號。”[12]在康德看來,啟蒙遭遇的最大問題不是理性、理智的問題,而是道德問題,是大量“懶惰和怯懦”之人對于安逸的“不成熟狀態”的一味沉溺。因此,如果我們僅僅以那些“人道主義”、“自由”、“尊嚴”等抽象的啟蒙理念作為評判的準則,就果斷地把“五四”時期和80年代統稱為“啟蒙的時代”,無疑是在很大的程度上降低了啟蒙的標準。從嚴格意義上說,“五四”時期的啟蒙和20世紀80年代的“新啟蒙”都遠未能真正實現。
20世紀80年代試圖延續“五四”時期未完成的啟蒙任務,這一出發點固然充滿著積極的樂觀主義理想,但隨著“新啟蒙運動”在80年代末期的戛然而止,又把一場演化為“動亂”的激進運動掩埋在我們歷史的記憶里。因此有學者在20世紀80年代末發出了“啟蒙已經終結”的斷言。同時,“啟蒙尚未終結”的呼聲也此起彼伏,發生于1993年至1995年間“關于‘人文精神’的那場大討論就是在濾去了‘革命’激情之后的‘再啟蒙’”。[13]盡管五四文學存在著一些固有的缺陷,并沒有完成它應有的“啟蒙”使命,但無疑也是那個時代的光榮與輝煌,值得文學史永遠紀念。盡管20世紀80年代以來掀起的“新啟蒙”運動也很快銷聲匿跡了,對于當代文學的發展來說,作為一個彌足珍貴的人文思想武器,“啟蒙”仍然是一個繞不開、永遠也不會過時的話題,啟蒙的路仍要走,即使是在艱難曲折中負重前行。
[1]李澤厚.二十世紀中國文藝一瞥[M]//李澤厚.中國現代思想史論.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251.
[2]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241.
[3]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修訂本[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4.
[4]魯迅.我怎么做起小說來[M]//魯迅.魯迅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512.
[5]林非.對“五四”啟蒙與“文學革命”的反思[J].中州學刊,1989(3):3-9.
[6]洪峻峰.五四文學革命的啟蒙意義[J].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1(1):61-68.
[7]尚水英.五四啟蒙文學的理想與現實效應[J].甘肅農業,2006(2):198-198.
[8]趙黎波.1980年代文學批評啟蒙話語的現代化特征[J].文藝爭鳴,2010(12):114-119.
[9]趙黎波.“重返八十年代”與“十七年文學”研究[J].理論與創作,2010(2):42-46.
[10]丁帆.八十年代:文學思潮中啟蒙與反啟蒙的再思考[J].當代作家評論,2010(1):4-18.
[11]張清華.“80年代文學”論略:一個文學史的考察[J].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7):34-43.
[12]康德.答復這個問題:“什么是啟蒙運動”[C]//康德.歷史理性批判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90:22.
[13]樊星.從“新啟蒙”到“再啟蒙”——紀念“五四”九十周年[J]. 文藝爭鳴,2009(2):92-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