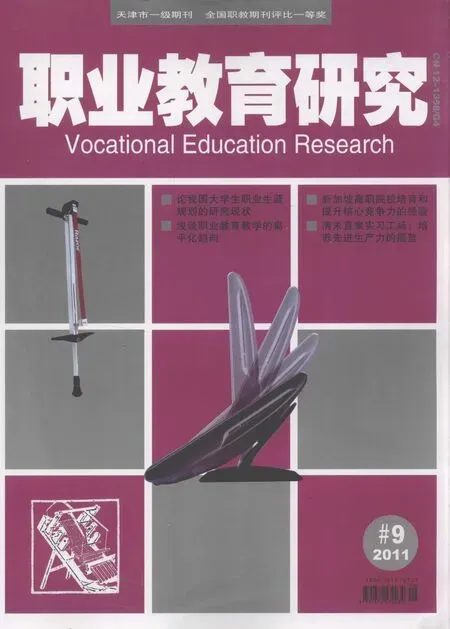清末直隸實習工場:培養先進生產力的搖籃
陳凱
(天津師范大學 天津300074)
清末直隸實習工場:培養先進生產力的搖籃
陳凱
(天津師范大學 天津300074)
在清末“新政”時期,直隸工藝總局為振興全省實業發展,創辦了實習工場,培訓工匠,以滿足新興工業的需要。此舉的目的是為民眾謀生計,它以實訓操作為主,兼授以書、算普通知識,同時也生產產品,是早期職業教育的一種有益的探索。
清末;直隸實習工場;先進生產力;實業強國
上世紀初,清王朝經歷了甲午、庚子之變,在衰敗的道路上繼續向下滑落。當時的中國雖有百日維新、洋務運動,以圖強國,但基本上仍處于農耕社會,不多的近代工業主要集中于軍火制造方面。在中國共產黨誕生之前,已有一些先進的中國人向東西方發達國家尋求救國、強國之道,認為唯有發展近代工業才是有效的方法。朝廷為維護其統治,也不得不提出實行“新政”,振興實業,發展工商業即為晚清“新政”的一項重要內容。
直隸是當年推行“新政”的模范省。1902年,時任北洋銀元局總辦等職的周學熙(1866~1947)受直隸總督袁世凱指派,東渡日本考察“工商幣制”,目睹了近代資本主義的繁盛,從而得出了“日本維新最注意者,練兵、興學、制造三事”①的深刻觀感。返國不久,便呈準袁督,創建直隸工藝總局,并受命出任總辦。由周學熙主持的工藝總局,在天津先后創辦了高等工業學堂、考工廠(商品展覽館)、實習工場、教育品制造所、勸業鐵工廠等多個單位,并推動了全省的工業建設事業。其中,“規模最大,收效最宏”②的當屬設于天津的直隸實習工場。
在生產力諸要素中,有知識、有技能的勞動者是首要能動的因素。在一個世紀前,具有淺近文化知識、略知近代理化原理、能操作簡單機械的工匠(技術工人),無疑應屬于先進生產力的代表。當年,以“儲各項公司工匠之才”為宗旨的實習工場,應當說是培養先進生產力的搖籃。
實習工場成立于1904年10月,其申辦呈文表明,它是“以推廣民間生計為主……俟練習有成,擬合紳商開辦各項公司,使學者得所用”,期以“風氣日開,民生日裕”③。在其《試辦章程》中規定:“以提倡制造,培養民生,儲各項公司工匠之才,成本局學堂學生之藝為宗旨。”工場專辟講堂,“工徒每日須分班講習書課一點鐘”。同時明確工場“與工業學堂聯絡一氣,兼以工場為工業學生試驗之所,而學堂各科教習即可為工場工徒講課之師,相輔而行”④,取名“實習”,意即為學生、工徒實地練習工藝之場所。依朝廷《學堂章程》要求,“高等工業學堂應附設實習工場”,以供學生實習之用,但實際上又是一個相對獨立的培養工匠的單位。一些相關史料的不同說法也證明了這一特質,如“設實習工場以練習其技能”⑤,“為培養工匠之才以興實業”⑥,“實以技術之傳授為主”⑦,“以更番傳習,養成各項工師之人,格振興實業,補救漏卮為宗旨”⑧,等等。用今天的話語概括,就是培養造就實用型人才,為振興實業服務。創辦實習工場的首任“管理”(場長),由高等工業學堂庶務長、后成為天津四大書法家之一的趙元禮兼任。
辦場計劃獲準后,因陋就簡,先以教養局移交房屋數十間,修葺使用,撥付開辦經費銀五千兩。約一年后即行移址擴建,再加上材料成本支出,又撥付銀三萬二千五百兩。遂即雇聘向工徒傳授技藝的工匠、工師,除高等工業學堂教習兼課之外,聘漢文教習、圖畫教習各一名,又先后聘日本籍木工模型、機織提花、彩印、化學工師4名來現場傳藝任教。另配備監理、總稽查、稽查、采辦等管理人員十余名,監工若干名。招收工徒主要來自本省,也有奉天、蒙古、山東、山西乃至四川、廣東等外省籍青少年。官費工徒約占七成,自費工徒約占三成。工場之設與通常作坊習藝、師父帶徒弟最大的不同之處在于,對工徒“每日須分班講習書課”,包括文化課和技術專業課。
1905年末,實習工場遷入河北窯漥舊右營擴建的新址,從現今存留的該場平面圖看,規劃有序,布置規整,專設東、西講堂兩處,具有相當規模。至1907年,已擁有房舍500余間,開設科目有織布、織巾、染色、彩印、木工、砑光、制皂、窯業、制燧(火柴)、圖畫、刺繡、提花等10多個,在場工徒近700名,僅機織工(織布、織巾)即有400余名,成為當年頗具規模的“儲各項公司工匠之才”⑩的重要基地。
工場制成品多屬紡織、輕化工業物品,以機織各色斜直紋布袍面、被面、褥單,大小毛巾,各色布匹、紗線漂白等為多,也有化學類的火柴、黃白條皂,手工制作的洋式木工桌椅,日用瓷器,繪制扇面、鏡心屏幅,刺繡花卉禽鳥等。用今天的眼光看,這一切都屬于初級工業產品乃至手工藝品,而在當年,則是向近代工業進軍的成果。值得一提的是,實習工場的產品不但曾受到農工商部頒發“匾額”的獎勵,有的還曾“進呈御覽”,得到“上意甚為嘉悅”的評價。遺憾的是,受到獎勵和贊許的產品,雖“巧思獨運,花樣翻新”,但僅是“繡竹”和“繡鷹”而已,均為手工刺繡,此類稱之為“最精貨品”,但全然沒有近代工業的影子,這也是時代使然罷了!
1906年10月,實習工場舉辦了第一次“縱覽會”。據時任工場管理員(場長)、縣丞(副縣職)陳秉鑒呈報稱:“東西洋諸文明國,工業進步速若電芒,其原動力之所在不外理化之研究日精,社會之鼓蕩日劇,故能月異而歲不同。”此次“縱覽會”的功能,就是發揮“社會鼓蕩(宣傳)之力”,從而使“人人知工業為富強根本”。“縱覽會”十分隆重,總局員司到場,總辦周學熙蒞會講話鼓勵,并以“在事諸人各盡義務,精益求精,勿以小成而自滿足,勿以困難而生懈怠”誡勉。來賓天津縣學董李家禎致祝詞,贊賞“場中出品之精美”,更盼“冀我祖國之工業駕駛東西洋而上”云云。隨后,依次參觀各科產品,稱織布廠“所織各色布五色繽紛”,“花樣新鮮”;織巾科“所織各巾勻密堅致”;染科兼彩印科“布置得法,染法、印法亦均敏妙”;刺繡科“花卉翎毛鮮艷飛動”;制燧科“分桿、蘸藥、裝匣分用手搖機,靈捷巧速”,總之備加贊賞。“縱覽會”會場有多支樂隊吹奏助興,“各官紳、工商庶眷屬,陸續來觀,車馬喧闐,幾至途為之塞”,稱“天津從來開會之特色無逾其是者”,五天會期內,共接待參觀者達五萬數千人,且當場便有“本邑諸巨紳”提出“擬即行創開工廠,以通風氣而興實業者數家”,足見“其影響于闔邑紳商工業之思想甚非淺鮮”。因此,決定以后每年舉辦“縱覽會”一次。直隸總督袁世凱對此也做了批示,稱“觀聽所傾,成效已著,仰仍督飭切實考校,力求進步”,“嗣后準于每年秋間開會一次,俾眾觀感”云云。
至1907年,實習工場已畢業工徒近七百名 (自費回籍者未計),均授予文憑,“分投各屬傳習”,或留場效力,或下派省屬州、縣服務。可以說,他們為當年起步不久的民族工業提供了人力和技術支撐,實現了辦場宗旨規定的“儲各項公司工匠之才”的目標。
為適應直隸全省紡織業發展的需要,1906年,實習工場還開設了一家“織染監工傳習所”,招收20~40歲“書算精通,文理明白,身健品端,且無家事之累”者30人,作為期3個月的培訓,滿足了各府、州、縣對織染監工的需要。如同今天的短期技術培訓,做到了需要什么人才,就及時培訓什么人才。
在此期間,直隸工藝總局屬下的工商研究總所還曾對實習工場的經營管理作過專題研究,提出了“各科分別各計盈虧”,“盈余酌給花紅”,工料與出產成品掛鉤、比較,以提高工效等措施。可以說,這是早期的經濟核算,是對于按貢獻給予獎勵,以提高生產效率的有益探索。
1910年,實習工場經過五六年的實踐,根據需要,對該場《章程》又做了一次“續訂”,稱為《續訂實習工場章程》,計六章、二十條。除重申辦場宗旨外,科目設置增添了紙工;招收工徒取消了12~15歲的“幼童”,改為招收16~25歲“體壯性純,粗知書算者”;明確了織染、胰皂、織巾4科,培訓期為6個月,其他各科為1年;還規定了實行月考、季考和大考以及紀律、賞罰等條款。
基于上述情況采用定性分析與定量監測相結合的方式對兩種方式對環境的實際影響進行評價分析.首先設計實驗,研究廁紙入下水道對水體的污染情況.
綜觀實習工場的創建與發展,有如下幾個特點:
第一,興工藝以強國,辟工場以濟民生。由于清王朝統治者的昏庸腐敗,中國錯失了近代工業革命的機會,使得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大大落后于東西方經濟發達國家。“落后就要挨打”,清朝統治下的中國成了任列強掠奪宰割的對象,國弱民窮,尤其是沒有土地的城市貧民更是生計無著。因此,從中國實際出發,行“振興實業”之策,不但是強國所需,也是為貧民謀生計的一條重要出路。1904年,《大公報》就載有一篇短文稱:“實業可以救貧”,“有子弟的,萬不可錯主意,趁機會教他學一份手藝,將來就不愁沒飯吃了。待工藝大興之后,國家也就不愁貧窮了。”實習工場的創辦,正是適應了這一要求。
第二,技能培養與素質培養兼顧。實習工場以造就工匠為目標,但不同于傳統的工場作坊師傅帶徒弟的模式,只以掌握操作技能為滿足。在注重實地練習的同時,專設講堂,“課以修身、漢文、歷史、地理、算學、體操等淺近課程,俾得略具普通知識”,“期得成才”。其“聰穎者”更可參加“工業學堂所有之各項科學,量材施教”。如總辦周學熙在一次視察時所說:工場系為“造就人才”,而非“平常木匠鋪收徒”。工徒培訓結束就業,凡“技藝超格異常勤奮者,可漸升副匠目、正匠目,以至副工師、正工師”。如果沒有文化、道德(修身)素質的培養,僅是造就單純的勞動力,這一目標則是難以實現的。
第三,實習工場為追趕和掌握近代先進技術,不惜重金,聘請外籍工師來場傳授技藝。如1905年,聘日本籍化學工師中澤政太,月支銀150兩,數倍于本國教習,并付給來往“川資”(旅費)各150兩。與之相應的是,對高薪聘來的洋工師也有嚴格、具體的要求,如需聽從場方管理員(場長)、總教習之命令,與“共事之華人,均應和衷共濟”,對學生、匠徒“不得自行打罰,及諸無禮舉動”,要做到“盡心傳授”,使匠徒、學生六個月畢業時“均可自行制造,考驗如法”,等等。
第四,學用一致,實習工場培養的工徒為推廣近代工業起到了儲備人才和示范作用。在“振興實業”的大氣候下,這一時期工藝總局又倡導天津城鄉建民立工場及藝徒學堂十余處,北京小學堂工場兩處,外府州縣工藝局廠六七十處。最有學以致用意義的,當屬省內高陽土布業的發展。為提倡工藝,工藝總局曾行文各縣,高陽李氏積極響應,派人來實習工場實習機織,并購置天津勸業鐵工廠仿造的鐵輪織機,逐年推廣,遂“造成河北省高陽土布之巨大工業”民國后則更加興盛。時至今日,高陽仍具有河北省“紡織之鄉”、“紡織強縣”的聲譽。
作為向近代工業進軍,培養先進生產力的實習工場,經過一段時期的繁榮,終因起步較晚,產品水平落后,敵不過質高價低、洶涌進入中國市場的各種洋貨,致使產品滯銷,日見虧累,于辛亥革命成功不久便結束了自己的使命。它在歷史上留下的足跡,今天已少有人知,乃至完全被遺忘。但幸有留存的一些珍貴文獻史料可以追尋。當我們重新審視它的時候,會發現它的一些經驗,如關注民生、學用一致、重金引進人才等等,至今仍有一定的啟示意義。
注釋:
⑥⑩周爾潤:《直隸工藝志初編》,北洋官報局出版(北京首都圖書館制網絡版),第136,190頁
⑧甘厚慈:《北洋公牘類纂續編(工藝卷)》,北洋官報局出版
G718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5727(2011)09-0179-02
陳凱(1936—),男,北京市人,天津師范大學副教授(已退休),研究方向為天津近代史。
(本欄責任編輯:王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