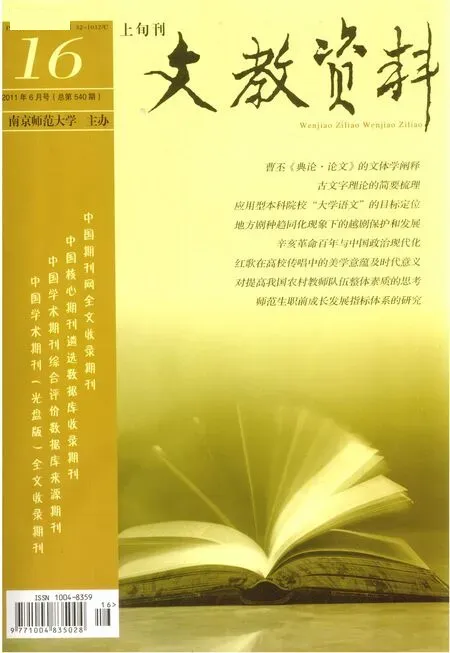柔弱的靈魂——對契訶夫短篇小說《窩囊》的會話與功能分析
吳曉雷
(貴州師范大學 外國語學院,貴州 貴陽 550001)
一、引言
倘如伍爾夫所言,靈魂是安東·契訶夫小說關注的焦點,那么對白就是契訶夫表現人物靈魂的主要手段。無論在其早期還是后期作品中,契訶夫小說中的對白,分量都彌足輕重,作為一種敘事手法而言,或許可以看作源自其戲劇創作的影響,但究其根本,還在于其對人類心靈的關注。“他對于心靈極感興趣;他是人與人關系的最精巧微妙的分析者”[1]。而人物之間的交談,正像契訶夫在其《出診》(1898)中所述一樣,更能反映出人物的所思所慮,反映出當下社會的改變帶給人們的憂思和困擾。《窩囊》①,是契訶夫寫于1883年的早期作品,小說中的對白來自僅有的兩個主人公:男主人和女家庭教師,寥寥千字的小說幾乎只包含了兩人的對白,巧妙地將主與仆、強者與弱者之間的巨大反差呈現在讀者面前,也體現出了作者對強權之下的俄羅斯人民,尤其是“小人物”生存狀況的深切關懷,和其“怒其不爭”的悲憫之情。而契訶夫細致入微的觀察和冷靜、客觀的描寫,更是將隱藏在小人物內心的奴化、異化了的靈魂通過其語言揭示出來,讓讀者看到了弱者不幸的根源,不僅在于強權與體制的壓迫,更在于弱者對自身人格的放棄。本文即以會話分析的方法對《窩囊》一文中的對白進行梳理,并以韓禮德的功能語法為理論基礎,對人物對白進行深入分析,揭示這篇小說中的對白語言是如何暴露人物心靈深處的扭曲的。
會話分析是20世紀60年代美國社會學家哈維·薩克斯在分析日常會話時采用的一種民俗學方法,話輪、相鄰對等概念被用于分析會話的結構,總結日常會話中的規律,以期研究日常會話背后反映的社會秩序。文學語言在本質上是對生活語言的高度模仿和提煉,文學語篇中的對白與日常會話的基本結構和特征也并無二致,在文學評論中,會話分析的方法也取得了豐厚的成果。和強調會話過程中體現出的社會規范性、體制性不同,功能語言學更關注交際過程中語言使用者的個體差異,譬如對語言概念功能的分析,即可以探析“語言使用者對主客觀世界的認識和反映”[2]。而韓禮德(2000)對語言的交際功能,也是從會話入手進行分析,和會話分析不同的是,會話分析更側重于規律性呈現的會話結構,而功能語法則著眼于會話中具體的小句,通過對小句中語氣等系統的分析,將語言使用者如何通過語言傳情達意的過程還原出來。論文將利用會話分析中的話輪、話輪轉換對《窩囊》一文中的對白進行初步分析,在分析總體結構后,再選擇其中典型的相鄰對,對其優選等級進行分析,試圖對小說對白中的體制性特征進行說明;功能語法中的人際功能、語篇功能則將用于分析小說女主角的部分言語,以進一步解釋女主人公體制化言語后的心理機制。
二、會話分析
話輪(turn),按照萊文遜(1983)的說法,是指“a time duringwhich asingle participantspeaks,within a typical,orderly arrangement in which participants speak withminimal overlap and gap between them”[4](一次典型、有序、會話參與者同時發言和間隔較少出現的交談中,單一的參與者發言的時間)②。而話輪的分配,總是通過發言人有意識地選擇下一發言人,或發言者的自我選擇實現的,在這種交談中,參與者有意無意地交替發言而完成的話輪轉換(turns-taking)最終保證了交談的順利進行。在會話分析中,會話參與者在談話中對話輪的控制被用來反映參與者對交談的控制,也反映出了會話參與者之間的人際關系,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參與者不同的心理表現和性格特征。在契訶夫的《窩囊》中,交談發生在男主人“我”和女家庭教師尤麗雅·瓦西里耶芙娜之間,下表對整篇小說話輪總數、二人各自話輪數和長度之間的關系進行了統計說明,籍此來分析二人在談話中體現出來的人際關系。

表1
小說中“我”和尤麗雅·瓦西里耶芙娜間的對白總共有19次話輪,其中“我”占了11次,尤麗雅占8次。單純從數量上并不能看出作為男主人的“我”與作為家庭教師的尤麗雅之間有任何強者與弱者的差距,而從話輪的分配方式來看,尤麗雅4次是通過有意識地主動發言來奪得話語權,占了其話輪總數的一半,并沒有明顯地在談話中處于弱者的地位。然而一旦考慮到話輪的長度,可以發現,男主人的強勢地位昭然若揭,其話輪長度幾乎是家庭教師話輪長度的8倍。從表中可以看出,雖然尤麗雅在話輪數量上并沒有處于明顯的弱勢地位,但在整個交談的過程中,幾乎都是男主人在發話,聽不到尤麗雅的聲音,幾次主動的發言也并沒有持續很長時間,從男主人的話輪分配方式來看,11次話輪都是主動有意識地奪得話語權,由此可以看出,尤麗雅在奪得話語權之后,既沒有充分表達自己的意見,也無力與強者進行抗爭,短短數語之后,就又喪失了自己的話語權。
通過對《窩囊》中話輪數、話輪長度及話輪分配方式的簡要分析,我們可以看出“我”和尤麗雅之間強者與弱者懸殊的地位差距。亦有學者曾指出二人身份地位的懸殊導致了“話語權利的失衡”[3],但從對白中所表現出的話輪分配情況來看,尤麗雅的“柔弱”并不體現在其爭取話語權的主觀性上;相反,話輪分析表明,在對話語權的爭奪中,尤麗雅并非無法戰勝強者,而是多次通過自己有意識地主動發言奪得了話語權。這種對話語權的爭奪與失衡,是否是強者與弱者之間力量懸殊的爭斗在交談中的結果呢,還是可以作出另外一番解釋?純粹的結構分析在勾勒出簡單的人際關系之后,還需要對具體的言語進行深入細致的考察。會話分析中的相鄰對(adjacency pair)和優選等級(preference organization)便提供了這樣一把放大鏡,可以對小說中這種表面的矛盾作進一步的分析。所謂相鄰對,指的是“會話中不同的交談者發出的兩個語句組成的序列”[5]。相鄰對中的兩個部分,通常以提問、請求和相應的答復組成,而相鄰對中的第二部分,由于文化、環境、政治等原因,在特定的語境下,會存在一種答復優于,或更見于另外可能出現的答復的情況,這就是所謂的優選等級。優選等級是說話人在進行答復時進行的選擇,選擇通常分為合意與不合意的兩種,合意的應答通常是無標記性的,更直接,沒有較長的延時或明顯的停頓出現,反之,不合意的應答則是標記性的,常常出現停頓等語言特征。一般而言,合意性應答通常更能保證交談的順利進行,因此也常常具有抽象化和體制化的明顯特征。
例1 T1 I:The tenth of January Igave you ten rubles...(我:一月十日您在我這兒拿去十個盧布……)
T2 Julia:You didn’t! (尤麗雅:我沒拿過!)
T3 I:But Imadeanoteof it.(我:可是我這個本子上記著嘛)
T4 Julia:Well...all right.(尤麗雅:哦,算了,……好吧。)
例2
T1 I:Here itis!(我:拿去吧!)
T2 Julia:Merci.(尤麗雅:謝謝。)
這兩個例子是《窩囊》中較為典型的相鄰對。例1中的T2是尤麗雅對男主人宣稱事實的反駁,T3是男主人對尤麗雅所作反駁的否定,而T4則是尤麗雅對這種否定的接受。在T3、T4這對相鄰對中,T4話輪開始時,話語標記語Well的出現,表明了這一話輪的標記性特征,而延遲后的回答是對T3中男主人否定的接受,具有明顯標記性特征,屬于典型的不合意應答。“不合意應答的種種特征表明它的發出者意識到,所發出的應答是不合意的”“交際者在無法遵守有關的規則時仍然要表明他們知道存在著這些規則,并樂意接受它們的指導”[6]。在T4中,Well表示出了尤麗雅對于男主人否定不愿接受的心理,而其后的延遲反映出了她對自己的調整,選擇了避免爭執的方式,順從地接受了男主人對自己的否認。這種不合意應對的特征,體現了尤麗雅從猶豫過渡到順從的微妙變化。從優選等級的角度來看,例1中的T2雖然是一種自覺地爭取話語權的嘗試,但合意性的應對,體現了尤麗雅遵從交談中規則的做法,高度體制化的應答抹去了爭辯的主體性。經過T3、T4的交際之后,主體性在尤麗雅身上消失了。而例2是一種典型的“提議—認可/拒絕”性的相鄰對。尤麗雅對于男主人提出的11盧布不假思索地接受了,毫無猶豫,語言上也沒有再出現任何標記性特征,是典型的合意性應答,也是高度體制化,抽象化的應答,完全摒棄了個人的主體因素在內。從上述的兩個例子來看,尤麗雅的應答呈現出了一種高度體制化的特點,而例1中的兩對相鄰對突出了一個特征,即雖然尤麗雅有意識地爭取自己的發言權,卻不能利用這種權利,而是很快地陷入了一種體制化要求的失語中去。也許,對體制化無聲息的服從,這才是話語權力失衡的真正原因。在其言語體現出的柔弱之下,我們看到的,是一個不去表達自己的悲哀的靈魂。
如萊文遜(2001)所說,優選等級體現的更是一種結構性概念,而非心理因素。從會話分析對《窩囊》中對白的結構性分析得到的結論是否有其心理真實性,還有待進一步地分析。
三、功能分析
韓禮德(2000)認為,對話從本質上來講,是一種“交換”,而交換之物無外乎(1)物品和服務或是(2)信息。當語言被用于交換物品和服務時,韓禮德稱之為建議;用于交換信息時,陳述。而在“我”和尤麗雅之間的對白中,61個小句中只有5句是“建議”。因此,我們可以說,在《窩囊》這篇小說中,人物對白基本上是用于交換信息的。韓禮德(2000)指出:“When language isused to exchange information,[…]It becomes something that can be argued about——something thatcan beaffirmed ordenied,and also doubted,contradicted,insiston,...etc.”(當語言被用于交換信息時,……就可以進行爭論了——可以確認或否認,也可以懷疑、反駁、堅持,……)。“In order forsomething to bearguable,ithas tobe specified forpolarity:either itisso,or itisn’tso”(而若(語言)可供爭論,其歸一性必須明確:非是即非)。而歸一性 (polarity)并不僅只是限定成分(finite)的屬性,小句中的語氣 (mood)和剩余成分(residue)均可以具備歸一性的特征,只是在實現小句所表現的語言爭議性時,不同的語法成分具備了不同的功能,譬如,在語氣系統中,時態通常提供的是作出判斷的參照,情態則表明了語言使用者對事物事態的認識和判斷,而主語則指出了責任的歸屬。
在這篇小說中,應付工資的數目是二人對白中爭論的核心內容,以下選取的例子都是圍繞這一核心爭論的對白,試以功能語法中歸一性等相關概念進行分析。
例3 T1 I:Now then,weagreeon thirty rublesamonth...(我:好,以前我跟您說定每月三十盧布……)
T2 Julia:Forty.(尤麗雅:四十)

表2
例4 T1 I:Now then,you’ve been here twomonths,so...(我:喏,您在我們這兒工作了兩個月。……)
T2 Julia:Twomonthsand fivedays.(尤麗雅:兩個月零五天。)

表3
例5T1 I:The tenthof January Igaveyou ten rubles...(我:一月十日我給了您十盧布……)
T2 Julia:You didn’t.(尤麗雅:您沒有。)
T3 I:But Imadeanoteofit.(我:可是我這個本子上記著嘛)
T4 Julia:Well...all right.(尤麗雅:哦,算了,……好吧。)
T5 I:Take twenty-seven from forty-one——that leaves fourteen.(我:四十一減掉二十七,還剩下十四盧布。)
T6 Julia:Onlyoncewas Igiven anymoney,and thatwas byyourwife.Three rubles,nothingmore.(尤麗雅:只有一次,您太太給過我三盧布,此外再沒有了。)
在例3和例4兩個相鄰對中,T2話輪都是對T1的否定,然而在其省略形式中,很難看出歸一性的所在,所以通過表2和表3對T1話輪中的人際功能進行分析,來理解T2的歸一性體現在何處。從表2表3來看,兩例都是對小句中剩余成分的否定,在例3中,是對補語的否定,例4,環境附加語,而這兩處,恰恰是小句中無從表達主觀意志和個人感情之處。例5中,T2話輪對T1的否認,表面上看極易理解為對于限定成分的否定,但將T6中尤麗雅闡述的事實一并考慮在內后,我們可以看出,這兒的否定實際上是由主語承載的。如韓禮德(2000)所說“the subjectspecifies the’responsible’element”(主語使責任部分明確),在例5中,爭議所在并非在于尤麗雅有沒有從主人這兒得到錢,而在于從誰那兒得到的錢。面對“我”所捏造的事實,強加給尤麗雅的“罪名”,尤麗雅并沒有足夠的意志和意愿去抗爭,在T4中,尤麗雅甚至接受了這樣一種虛假的指控,而不去反駁。T6話輪所提供的信息更是讓尤麗雅陷入了被男主人進一步盤剝克扣的困境。通過對這幾個例子的人際功能分析,我們可以看到,尤麗雅的言語表現出另外一個特征,即尤麗雅每一次的發言,雖然看起來是爭奪到了話語權,但這種話語權并沒有用來表達尤麗雅自己的主觀愿望和感情,而僅只局限在對客觀事物的簡單描述上,一旦這種“客觀性”受到了別人的否定,缺乏主體個人意志支撐的話語立即失去了力量,尤麗雅似乎并不能支配一種可以完整表達自己意愿的語言,即使在占有話語權的時候,這種權利也并不能在言語中得到正常的行使。下面將從語言的語篇功能出發,透過二人的對白,對《窩囊》中展現出的人物心理進行進一步分析。
主位,“is thatwith which the clause is concerned”(就是小句關注的內容),在陳述小句中,通常是由主語占據著主位的位置,而非主語主位就成了標記性主位。正像韓禮德(2000)分析指出的,標記性主位總是由前景化了的小句成分擔任,因而成為了信息關注的焦點。而《窩囊》一文中,尤麗雅的8次發言中,有7次都選擇了標記性主位,唯一一次非標記性主位由主語“you”承擔。
例6T1 I:Why this“merci”?(我:您干嗎道謝?)
T2 Julia:Inmyotherplacestheydidn’tgivemeanything atall.(尤麗雅:在別的地方,人家連一個錢也沒給過我。)

表4
例6中尤麗雅的言語頗具代表性,非人稱的小句成分:環境附加語占據了通常以人稱為主位的位置,而該句的主語則為第三人稱復數的人稱代詞。如上文所述,小句的主位是信息關注的焦點,而主語是責任的所在,而尤麗雅在發言時,不僅沒能表達出自己的情感和意愿,而且總是從被關注的位置逃開,避免成為負責任的主體,將責任交付于他人,而不為自己負責任的同時,也將自己的命運交付給了他人,徹底失去了自身主體的身份和地位。這種言語中反映出的心理特征,與會話結構分析的結果正相一致,反映出了尤麗雅早已喪失了自己為人的主體性,習慣于體制強加于她的弱者身份。就像人際功能系統所揭示的一樣,語篇功能同樣也印證了尤麗雅人格中的弱點。
短篇小說《窩囊》的對白中,另一個值得注意的語言現象是男主人“我”的言語。小說中,男主人的言語可以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集中克扣工錢的問題上,第二部分是在質疑尤麗雅軟弱的表現。下表統計了兩部分對白中的標記性主位的數量。

表5
從表5可以明顯地看出,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中,無標記主位和標記主位的數量差距甚大。如我們所知,標記性主位都是非人稱的,在第一部分中,男主人故意表現出冷冰冰的態度,欺騙、盤剝尤麗雅的工錢,因此對白中的小句均以標記性主位開始,而第二部分中,“我”不再偽裝,而是向尤麗雅道出實情,原來這只是場玩笑,而“我”的對白也處處流露出了男主人真實的感情和對尤麗雅窩囊表現的同情和憤怒,自然會選擇非標記性的主位。然而玩笑雖然是開了,或許并不想男主人想象的那樣,會有任何教益,體制化的言語在尤麗雅的心靈深處已盤根錯節、真正柔弱的,不是尤麗雅的社會地位,而是在她柔弱的身體里扭曲了的靈魂。這才是小說結尾那句:“將世間的弱者碾碎竟是如此容易!”哀嘆的由來。
四、結論
論文利用會話分析和功能語言學的理論成果,對小說中二人對白進行了從會話結構到對白小句,從宏觀到微觀,從外到內、由表及里的分析。一層層剖析了小說所揭示的殘酷無情的社會現實,看到了短篇小說《窩囊》中的女家庭教師,在高度體制化的社會中表現出的“窩囊”,看到了一顆被體制扭曲、奪去力量的蒼白的靈魂,看到了柔弱的個性,在好心的強者留下機會時,也早已習慣了屈服,而不知、不會、不愿去表達自己的意愿和要求,這才是被扭曲了的靈魂的可悲之處,也看到了契訶夫精湛的技藝和深邃的洞察力,通過尤麗雅,將弱者靈魂深處的悸動與無力展現在讀者的面前。失去了靈魂的軀殼,不過是一部高度程式化的機器而已,而所謂話語的失衡,不過是被體制化了的靈魂所患的失語癥,真正的可怕,不是無力反抗帶來的絕望,而是在希望面前不去反抗帶給人的悲哀。
注釋:
①汝龍譯.契訶夫文集.論文所引契訶夫小說譯文皆參照上海譯文出版社.部分譯文稍作改動,1999.
②論文所引萊文遜譯文皆為作者自行譯出.
[1]伍爾夫,弗吉尼亞.“俄國人的觀點”.論小說和小說家[A].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9.
[2]Halliday,M.A.K.An IntroductiontoFunctionalGrammar[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Edward Arnold(Publisher)Limited,2000.
[3]趙雪瑩.“柔弱的人:由悲憫到質疑的超越”.開封大學學報[J].2005,(12).
[4]Levinson,Stephen C.Pragmatics[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and Research Press,2001.
[5]劉運同編著.會話分析概要[M].上海:學林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