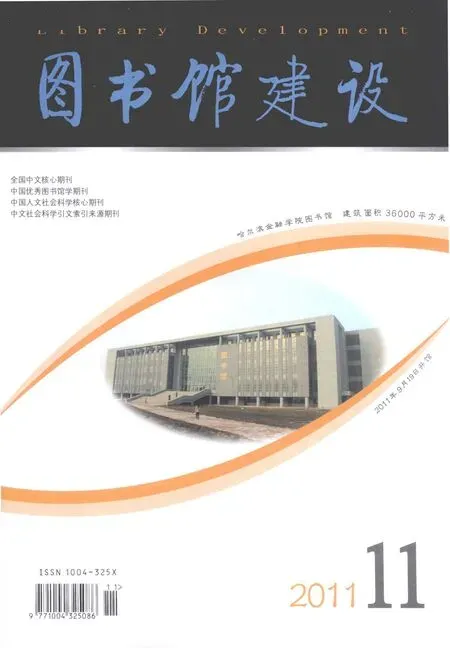電子書版權保護與最終用戶利益的平衡──對亞馬遜刪除電子書事件的思考
李 云 (新鄉學院圖書館 河南 新鄉 453003)
有學者認為,預計到2020年,電子書的銷售規模將超過紙質圖書[1]。發展電子書必然要涉及版權問題,雖然利益平衡仍然是解決電子書版權矛盾的基本原則,但是在利益的守衡與失衡中,失衡往往成了常態。因為版權不斷擴張導致的“數字鎖定”①[2]損害甚至是剝奪了圖書館、讀者等最終用戶②的利益[3]。2009年7月,在美國發生的“亞馬遜刪除電子書事件”就是典型的例證。該事件引起美國國內和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和爭論,并被eWeek資訊網站列為“2009年度最不受公眾歡迎的九大事件”之首[4]。透過該事件的表象探討其本質,對于厘清電子書涉及的版權關系以及創構與維系電子書生產、傳播和使用中的利益平衡機制、保障最終用戶的利益是非常有意義的。
1 亞馬遜刪除電子書事件及其爭議
1.1 事件的梗概
2009年7月,美國B2C(Business to Consumer,商家對客戶)巨頭亞馬遜公司(以下簡稱亞馬遜)接到版權人的抗議,稱亞馬遜圖書館(Amazon Library)的由英國著名作家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撰寫的兩部作品——《1984》和《動物農場》(Animal Farm)未經授權。這兩部電子書是由數字出版社Mobile Reference通過亞馬遜圖書館平臺的自動添加服務提供的。雖然有不少讀者已經付費并下載了這兩部電子書,但是為了避免版權糾紛和承擔法律責任,亞馬遜竟然在沒有事先告知讀者的情況下,通過技術手段將讀者手持閱讀器Kindle中的相關內容刪除[5]。為了平息讀者的不滿情緒,亞馬遜的CEO(Chief Executive Officer,首席執行官)杰夫·貝索斯(Jeff Bezos)在Kindle論壇上撰文向讀者道歉,稱擅自刪除電子書內容的做法非常不妥且“愚蠢之極”,并表示將接受教訓,保證不會再次發生此類事件。隨后,亞馬遜為讀者提供了補償的辦法:①將免費向讀者賠送刪除的圖書及讀者在電子書中所作的注釋;②讀者可以選擇獲得價值30美元的亞馬遜購物券或者30美元的支票;③如果讀者不選擇重新獲得被刪除的圖書,同時購買《1984》與《動物莊園》兩部小說的Kindle讀者將獲得價值60美元的補償[5]。但是,亞馬遜的補救措施并未獲得讀者的原諒與好感,這一事件逐漸“發酵”開來,在社會上掀起軒然大波,再次引發了數字時代版權人利益和公眾利益保護與平衡的爭論。
1.2 不同的觀點
Kindle是亞馬遜精心打造的品牌手持閱讀器,它在版權保護上的最大突破是亞馬遜可以通過數字版權管理技術(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簡稱DRM)控制和修改終端用戶的閱讀權限。一方面,亞馬遜能夠任意設置用戶格式協議條款,賦予自己合法進入用戶終端刪除電子書的權利 ;另一方面,當亞馬遜發現用戶終端有侵權電子書時,可以遠程刪除電子書,確保Kindle上保存的電子書的非盜版性。這種繞開了兼容性與跨平臺的通過特定設備對版權進行的保護具有較高的技術可行性,而且DRM本身受到版權法的保護。因此,如果不對DRM的應用加以限制,那么DRM就可能在法律的庇佑下損害最終用戶的利益。針對亞馬遜刪除電子書事件,各國學者的觀點大相徑庭。芝加哥大學法學教授Randal C. Picker認為,亞馬遜刪除有權利瑕疵的電子書的做法是正確的,因為透過這樣的技術系統可以更有效地執行版權法的規定,為規范版權使用創造了新的機會[6]。但是更多的是對亞馬遜刪除電子書的反對之聲。《洛杉磯時報》編輯David L.Ulin和自由軟件基金會的Holmes Wilson都表示,只要版權商擁有刪除電子書的方法,就不得不令人擔憂其總有一天會因種種緣故而故意使用這一功能[7]。哈佛大學法學院教授Jonathan Zittrain認為,像Kindle、TiVo和iPod這樣的設備會成為監管者的工具,使他們有機會隨意操作、修改讀者的電子書,達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7]。亞馬遜刪除電子書事件發生后,總部設在波士頓的自由軟件基金會征集了來自圖書館管理員、出版商和重要作者共同簽名的請愿書并將其遞交給亞馬遜,要求亞馬遜放棄對Kindle中載入圖書的控制權,重新考慮對DRM軟件的使用[7]。可見,對于亞馬遜刪除電子書事件爭論的核心在于,版權在DRM的保護下和在為DRM提供版權保護的法制條件下,最終用戶在版權利益鏈條中的地位是否被弱化,其利益怎樣落到實處。
2 亞馬遜刪除電子書事件相關問題的分析
2.1 內容與載體的可分離性
針對亞馬遜刪除電子書事件,《Slate》的技術專欄作家Farhad Manjoo就紙質圖書與電子圖書的侵權后果進行了比較,認為如果讀者擁有的紙質圖書存在侵權問題,版權人很難將該書收回,因為讀者可以拒絕交出圖書;而對于侵權的電子書,版權人或者閱讀器制造商可以輕而易舉地通過技術手段將其刪除[8]。這其中的重要原因是,紙質圖書的物質載體和文本內容合二為一,讀者購買紙質圖書是對物質載體與文本內容的“雙重購買”,在圖書進入流通領域后,版權人無法借助對物質載體的控制達到管理版權的目的;相比之下,電子圖書的物質載體和文本內容是可以分離的,讀者購買了電子閱讀器并不意味著同時就獲得了文本內容的閱讀權。不僅如此,即使讀者享有的合法的電子書的閱讀權,也是囿于DRM的允許限度之內的,而且是可以在DRM的監管下削弱與喪失的。亞馬遜刪除電子書事件正是利用了電子書內容與載體相分離的技術特征。
2.2 首次銷售原則的適用性
亞馬遜刪除電子書事件使理論界重新聚焦于“首次銷售原則”(the first sale doctrine)是否適用于網絡環境這樣一個重要的版權問題。“首次銷售原則”又稱“權利窮竭原則”,是指當作品復制件經過市場交易后其物權實現了轉移,版權人不再享有控制該復制件流轉的權利[9]。“首次銷售原則”的合理性在于,消除了版權的專有性對作品自由流通產生的負面影響。正是基于“首次銷售原則”,圖書館可以合法地向讀者出借館藏圖書,讀者也可以將其擁有物權的圖書以出售、出借、捐贈等形式進行處理[9]。然而,“首次銷售原則”在網絡環境中遇到的挑戰來自于立法與技術兩個方面:一是目前國內外版權法幾乎都對此問題持否定態度;二是DRM使“首次銷售原則”在網絡環境下根本無法得到貫徹。例如,即使讀者通過手持閱讀器閱讀完電子書后愿意在轉讓后立即刪除自己閱讀器中的“原件”,也無法轉讓給他人閱讀[9]。另外,DRM使電子書無法建立“二手市場”,當讀者的閱讀器丟失后若還想閱讀某種電子書,只能同時再次購買閱讀器和該電子書。針對這種狀況,美國圖書館界希望通過立法的形式適當延展“首次銷售原則”在網絡環境下的法律效力,認為只要作品通過閱讀器傳輸給另外的讀者后刪除“原件”,就可以適用該原則,并強調讀者處理作品的傳統權利應該在網絡環境中有條件地得到保留。
2.3 版權保護技術的平衡性
有學者認為,技術進步對版權是一種威脅,但另一方面,正是通過技術進步,版權才得以繼續存在[10]。這種觀點不僅體現技術本身所具備的功能,而且表明技術措施確實已經在當代法律制度中享有了合法的版權地位。然而,版權保護技術的發展與對技術的版權保護對最終用戶享有的傳統利益構成了嚴重的威脅。對此,法國國家圖書館館長弗雷德里克·巴爾比耶說:“信息工具的技術含量增大,無法保證讀者能自主地控制系統。”[11]美國圖書館學會指出,圖書館正被迫屈從于“一招制百式”的單一技術,使讀者服務的多個層面受到全面壓抑[12]。因此,需要在技術創新中找到版權人利益和最終用戶利益的平衡點。例如,為了擺脫刪除電子書事件的陰影,亞馬遜自2010年12月30起開始允許讀者通過Kindle互相借閱電子圖書。這種變化一方面說明技術的發展已經能夠使亞馬遜對Kindle上各種格式的數字內容實施全面、精細化的版權管理;另一方面亞馬遜認識到有必要使最終用戶的權益在網絡空間得到延伸,以取得雙贏的結果。
2.4 應用豁免規則的責任性
在亞馬遜刪除電子書事件中,存在權利糾紛的圖書是由內容提供者通過亞馬遜圖書館平臺的自動添加功能上載的,亞馬遜起到的只是“傳輸管道”的作用,刪除電子書是亞馬遜按照1998年美國《跨世紀千年版權法》(Digital Millennium Copyright Act,簡稱DMCA)設定的“避風港”原則規避版權責任的本能反映,很難從法律上找出其過錯[13]。按照DMCA的規定,作為“傳輸管道”的網絡服務提供者在不知情的條件下不為其傳輸的侵權內容承擔賠償責任,但是應當在接到版權人的“通知”后刪除侵權內容或者阻斷與對應內容的鏈接[13],否則服務提供者就要在承擔停止侵權責任的同時承擔賠償責任。我國《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也有類似的規定,但是其中“避風港”原則涉及的只是網絡服務提供者和版權人的關系問題,沒有充分考慮到最終用戶的利益。亞馬遜刪除電子書事件之所以在社會上引起強烈反響,是因為讀者事前已經為電子書“埋單”。雖然亞馬遜后來進行了道歉并作了經濟補償,但是這好比一個人在未經別人允許的情況下潛入其房間偷走了圖書后留下讀者原本付出的購書費。盡管讀者可以通過法律途徑尋求公道,但是讀者為此付出的時間代價、經濟代價、精神代價如何補償呢?況且,亞馬遜的行為在法定規則內,讀者能否勝訴還是個未知數。
3 電子書版權保護與最終用戶利益平衡的思考
3.1 強調用戶利益在版權法中的重要地位
法律離不開利益,法律由利益決定[14]。法律之要義是利益平衡,利益平衡同樣是版權法奉行之圭臬。在版權利益關系中,公共利益具有“法益優先價值”。從根本上講,創設版權制度源于對公共利益的考慮,版權制度從公共利益角度對版權原則進行了定義和定位。法律保護版權是希望社會能從這種保護中得到實惠,其基本方法就是以適度受限的版權人的個人自由換取社會公眾廣泛的能夠自由接近作品的權利。因此,版權制度歷來視圖書館、讀者等主體為最終用戶,即使版權法對這些主體有所涉及,也多是從限制版權、保障圖書館和讀者利益的角度來規定的[3]。在數字技術條件下,圖書館、讀者的版權地位不應有所改變。雖然版權擴張是一種總的態勢,但是每增加一種版權權能,就需要在這個新的權能層面上實現版權人和圖書館、讀者等最終用戶之間的權利與義務的平衡。版權人新的專有權利必須受到以最終用戶為代表的公共利益需求的制約。
3.2 正確把握技術措施保護版權的強度
亞馬遜刪除電子書事件暴露出一個發人深省的問題——在技術不斷創新和日臻完善的背景下,如何把握通過技術措施保護版權的強度。但是在實踐中,要在技術上將電子書等數字化作品的合法借閱與非法盜版區分開來并非易事,需要在法定層面上作出判斷。因為自從人類社會有了法律,法律對技術的態度就是促進加限制,其出發點是對比版權更優先的社會價值觀的關照[15]。所以,健全法規是保障圖書館、讀者利益的當務之急。例如,圖書館信息網絡傳播權的例外就不在我國《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設定的4種豁免情形之中,如果版權人采取了控制復制的技術措施,即使作品滿足合理使用的條件,圖書館仍然不得破解該技術措施,這導致圖書館的合理使用權無法實現。對于法律沒有詳細規定的關于最終用戶權益的保護,則需要依靠版權人和技術提供商的社會良知,在運用新的技術成果為其攫取利潤時,應保持對社會道德與社會責任的敬畏之心,并分擔法律的另一重要任務——對社會利益的維護。
3.3 不斷探索和創新數字版權授權模式
完善電子書的版權授權模式可以從兩條路徑入手 :(1)電子書制造商從版權人處獲得授權。這種授權從表面上看似乎無涉于最終用戶,但實質上卻與最終用戶利益有重要的關系。據報道,我國大約80%的圖書的電子版權直接為作者所掌握[16]。電子書制造商從版權人處得到的合法權利越多,最終用戶閱讀的圖書內容就越廣泛,而且可以避免承擔版權連帶責任等法律風險。對此,電子書制造商應加強與版權集體管理組織的合作,如2009年4月漢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同中國文字著作權協會達成內容數字化版權采購協議,成為中國文字著作權協會管理的數字版權的團體使用者。同樣,應建立“準法定許可制度”,即為擬使用作品設置一定的公告期,可以使用公告期滿、權利人無異議的作品,但是最終用戶應向權利人支付報酬或者通過版權集體管理組織轉付報酬。而對于公告期滿、權利人提出異議的作品,應立即將對應的作品刪除或阻斷鏈接。(2)最終用戶從電子書制造商處得到授權。例如,電子書制造商可以在閱讀器中設定讀者能夠制作電子書復制件的有效期,期滿后復制件自動被刪除,這樣既保障了讀者臨時復制的權利,又防止了復制件被不合理地擴散。再如,把讀者的賬號同電子書閱讀器捆綁在一起,若讀者不慎丟失了閱讀器,可以向電子書制造商申請更換閱讀器,從而避免讀者為閱讀同種電子書重復支付費用。
3.4 積極打造豐富的電子書版權內容平臺
在電子書業界歷來有“刀片”和“刀架”的比喻,即將閱讀器形容成“剃須刀架”,將電子書的內容比作“刀片”[8]。最終用戶除了體驗電子閱讀器本身的功能外,主要希望通過閱讀器閱讀盡可能多的內容,沒有內容的閱讀器只是擺設。如此一來,內容版權就成為重要的籌碼。掌握和運用內容版權不僅成為電子書制造商普遍采取的競爭策略,而且成為能否給最終用戶帶來實際利益的關鍵問題。這就是為何在“電子書=內容+技術+服務”的營銷模式中“內容”被放在首位。例如,亞馬遜的Kindle能夠占據美國電子書市場60%的份額、構建龐大的讀者群體的成功秘訣之一是其背后有強大的正版書庫支持;Nook的內容平臺Barnes&Noble可以提供超過70萬種電子書;Sony Reader與谷歌合作,其內容平臺可為用戶提供超過100萬種圖書。然而,我國電子書除盛大Bambook電子書網站外,內容資源普遍貧乏。一項針對國內44種電子書產品的調查表明,內容資源低于1萬種的內容平臺占到了42.9%[17]。2010年10月,新聞出版總署發布的《關于發展電子書產業的意見》提出了搭建電子書內容資源投送平臺的戰略目標[18]。據報道,我國在“十二五”發展期間將建立8~10個這樣的國家級平臺[18]。
3.5 協調與整合電子書版權鏈的利益關系
就電子書等數字出版物而言,最終用戶權利的保護必須著眼于整個產業鏈利益關系的協調與整合。因為在電子出版中原有的主體類型、主體之間的法律關系發生了重大變化,去中間化的結構打破了固有的利益分配模式,加劇了作者、傳統出版社、唱片公司、影視制作商、服務平臺、網絡運營商、終端制造商等主體之間的矛盾沖突,這其間利益損失最大的是最終用戶。例如,在亞馬遜和美國知名出版集團麥克米蘭公司的版權糾紛中,由于最初的談判未果,亞馬遜刪除了Kindle中麥克米蘭公司擁有版權的電子書,但是隨即就有讀者在微博中寫道,“告訴麥克米蘭,我想在Kindle上看這本書。”[19]
平衡電子書產業鏈中各主體之間版權利益最重要的方法就是加強彼此的合作,實現利益共享。例如,亞馬遜目前給出版社的利潤份額是70%,而谷歌給出版社的利潤份額是63%,為此許多出版商(包括數字出版商)加入到Kindle DX試驗計劃[20]。在國內,目前漢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方正集團有限公司、中國移動通信集團公司分給作者和出版社的利潤總額分別是80%、40%、40%[21]。由此可見,合作的效果是非常明顯的。
注 釋:
①數字鎖定是指權利人應用技術措施對版權進行超強保護,使用戶失去了利用版權的相關權利。
②版權法意義上的最終用戶可以是自然人(如讀者),也可以是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如圖書館、檔案館等公益性單位)。
[1]譚曉婷.出版社應成為電子書產業的主導者[J].中國出版,2010(6):56-59.
[2]朱 理.格式合同、技術措施與利益平衡[J].中國版權,2007(7):11-13.
[3]韋 之.著作權產品最終用戶的法律責任探討[J].著作權,2000(4):10-12.
[4]2009年度最不受用戶歡迎的九大事件[EB/OL].[2011-05-18].http://blog.sina.com.cn/s/blog.664142b70100h7au.htm.
[5]黃晨霞.Kindle刪掉了什么?[EB/OL].[2011-05-18].http://finance.com.cn/1011/2009912/03496740293.shtml.
[6]亞馬遜刪除電子圖書事件紛爭未平[EB/OL].[2011-05-18].http://it.sohu.com/20090727/n265523991.shtml.
[7]刪書事件持續發酵,亞馬遜激怒用戶引發爭議[EB/OL].[2011-05-18].http://www.cnbeta.com/articles/90143.htm.
[8]郭 品.國產電子書陷版權困局,改變現狀非一日之功[EB/OL].[2011-05-18].http://media.nfdaily.cn/content/201008/17html.
[9]王 遷.論網絡環境中的“首次銷售原則”:上[EB/OL].[2011-05-18].http://blog.sina.cn/s/blog46a2dlf5010004f5.html.
[10]勒帕熱.數字環境下版權例外和限制概況[J].劉板盛,譯.版權公報,2003(1):3-19.
[11]史歷峰.規范技術標準,用版權助推電子書大蛋糕[EB/OL].[2011-05-18].http://www.lawtime.cn/info/23cq/gnzscqdt 12010090844712.html.
[12]趙秀玲.數字環境下版權和鄰接權限制與例外:國際圖書館界的觀點[J].版權公報,2003(2):1-21.
[13]薛 虹.網絡時代的知識產權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138.
[14]馮曉青.知識產權法前沿問題研究[M].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4:66.
[15]韋 之.知識產權法與技術的另外一種關系[J].中國版權,2007(7):5-9.
[16]馬海力,張 波.電子書背后的著作權困惑[J].出版參考,2010(6):16-17.
[17]胡詩瑤.國產電子書內容平臺建設調查分析[J].出版發行研究,2011(1):50-54.
[18]蘇江麗.電子書產業版權保護機制創新研究[J].新聞界,2011(1):92-94,84.
[19]逸 飛.亞馬遜因定價分歧撤下出版商所有電子書[EB/OL].[2011-05-18].http://tech.163.com/10/0131/12/5UBUSKU 0000915BF.html.
[20]鄧文雷.電子書價格戰出版商贏得定價權,消費者需多花錢[EB/OL].[2011-05-18].http://www.chinanews.com/cul/news/2010/0225/2138523.shtml.
[21]黃國榮.內容版權授權直接制約電子書產業的發展[EB/OL].[2011-05-18].http://tech.163.com/11/0103/116PFHM3 TV000915BD.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