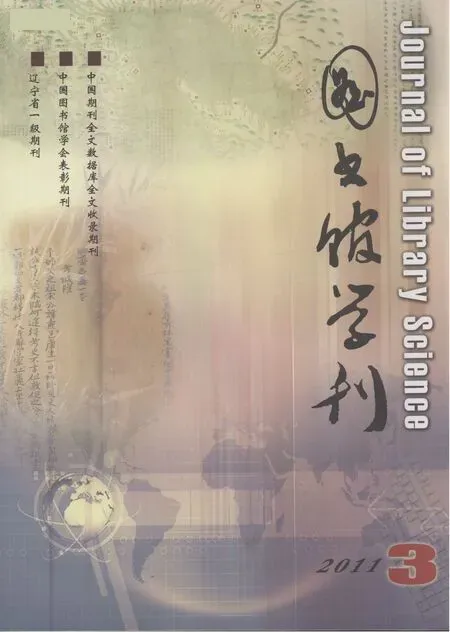新中國圖書館學研究對象爭鳴六十年
馬恒通 黃 閩
(河北師范大學圖書館,河北 石家莊 050016)
圖書館學的研究對象是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國際上對此問題特別關注,我國也不例外。
新中國成立60年來,我國圖書館學者對圖書館學研究對象問題進行了廣泛、深入、持續的探討和爭鳴,獲得了重要突破和進展。學界對此問題的討論大致可分為兩大類,即“非本質說”和“近似本質說”。前者是指對圖書館學整體的抽象的認識,是未接近“本質”的認識,大約有50余種。后者為“近似本質說”,即對圖書館的認識仍沒有達到本質認識的層次,只是在不同程度上接近了本質性認識的層次,約40余種[1]。為推動圖書館學繼續深入發展,對新中國60年圖書館學研究對象(“對象說”)的研究顯得非常必要。因篇幅所限,現擇其代表性觀點綜述之。
1 非本質說
1.1中國圖書館學研究對象諸“非本質說”及爭鳴——基于個案的視角
20世紀50年代至21世紀初,我國學者關于圖書館學研究對象的認識,先后推出了“要素說”、“規律說”、“關系說”、“層次說”、“系統說”、“活動說”、“互動說”和“圖書館說”等“對象說”。
1957年,劉國鈞先生發表《什么是圖書館學》,該文認為,圖書館事業由“圖書、讀者、領導和干部、建筑與設備、工作方法”5項要素組成。明確指出“圖書館學所研究的對象就是圖書館事業及其各個組成要素”[2]。這個觀點當時被錯誤認為是“要素說”。之后對劉先生的觀點展開了長時期的討論和爭鳴。1957年,北京大學圖書館學系在一次“科學討論會”上,首次討論劉先生的上述文章。同年,《北京大學學報》報道了朱天俊的關于此“討論會”的情況和一些同志不同意劉先生觀點的“發言”[3-4]。
從此至今,我國絕大多數學者都把劉國鈞先生作為新中國創立“要素說”的代表。于鳴鏑(1981)、朱建亮(2002)、吳慰慈(2004)等肯定了“要素說”,有的還指出其不足[5-7]。
然而,20世紀末至21世紀初,我國許多學者認真分析了劉國鈞的上述文章后,否認“劉國鈞是‘要素說’代表人物”的提法。茅振芳(1996)、邱五芳(1999)、王子舟(2000,2003)、王續琨、羅懷遠(2002)、胡萍(2003)、陳源蒸(2006)等先后撰文,一致認為,劉先生所指“圖書館學所研究的對象就是圖書館事業及其各個組成要素”,就是把“圖書館”作為圖書館學研究對象。劉國鈞先生是提出“圖書館學研究對象是‘圖書館’的第一人”,而非“要素說”的代表[8-14]。
1960年,北京文化學院圖書館學研究班認為,“圖書館事業和它的全部活動規律”是圖書館學的研究對象,首次推出了“規律說”[15]。1961年、1981年,武大、北大文化學院和圖書館學系分別在編著的兩部專業教材中支持“規律說”[16-17]。1981年、2004年,薛新力、于鳴鏑、劉長發各自推出了“關系說”。薛新力(1981)認為,“圖書館學研究對象就是圖書、讀者、圖書館組織、圖書館方法等要素構成圖書館事業之關系,研究這種關系的發生、發展和變化的科學”[18]。于鳴鏑(1981)認為,圖書館及其內部關系和外部關系是圖書館學研究對象[5]。劉長發(2004)則指出,圖書館學研究對象是由“圖書館與環境”、“各圖書館之間”和“圖書館內各要素之間”等多種要素組成的系統,系統中每個要素之間構成一種互動關系,研究它們之間的互動關系就構成了圖書館學的研究對象。推出了另一種“關系說”[19]。1982年,張欣毅和劉迅指出,圖書館學對象就是由“客觀實體對象層次”、“抽象認識對象層次”、“科學具體對象層次”這3個層次構成。首次推出“層次說”[20]。李惠珍(1997)認為,圖書館學研究對象是由“客體具體層次”、“科學抽象層次”和“思維具體層次”3個層次構成,指出“圖書館學研究對象就是多層次綜合整體的圖書館活動”。推出了與上述張、劉類似的“層次說”——“實體綜合層次說”[21]。郭星壽與那春光等分別提出了“系統說”。郭星壽(1982)認為,“現代圖書館學的研究對象是圖書館系統”[22]。那春光等(1992)將“圖書館藏書系統”作為圖書館學研究對象[23]。1985~2004年,沈繼武、郭星壽、王續琨分別推出“活動說”。沈繼武(1985)認為,“圖書館學的研究對象是圖書館活動”,其理由是:“圖書館活動是一個完整的社會現象”,“圖書館是一種社會實踐活動”[24]。郭星壽(1992)在其所著一書中指出,“圖書館及其活動”是圖書館學的研究對象[25]。王續琨、羅懷遠(2002)認為“圖書館活動”是圖書館學研究對象。指出,“所謂圖書館活動,是指以圖書館為依托的各個層面上的社會活動和物流、信息流”[11]。2004年,張踐明認為“圖書館實質是研究讀者與圖書館資源互動關系及其規律的科學”,推出“互動說”[26]。
建國之初至今,持“圖書館說”(“事業說”)的人較多。一種傾向性觀點認為,圖書館學研究對象就是“圖書館”(或“圖書館事業”)。劉國鈞(1957)是新中國提出“圖書館說”的第一人,已如上述。周文駿(1957)、黃宗忠(1960,2003,2006)、吳慰慈與邵巍(1985)、金恩暉(1988)、茅振芳(1996)、白光田(2001)、吳慰慈和董焱(2002)、吳慰慈(2004)、蔣鴻標(2004)、周九常(2006)、王淑華(2008)、湯樹儉(2009)等先后發文或著書,都認為圖書館學的對象是“圖書館”或“圖書館事業”[27-35],[7],[36-38],相繼推出“圖書館說”。當然,這里所指的圖書館不是具體的實體圖書館,而是一個歷史的集合體,是概括化和抽象化的圖書館。他們有的(如金恩輝)明確指出,如果“圖書館學不研究圖書館,它也就不成其為圖書館學了”。有的(如黃宗忠)強調,“研究對象的本質自然在圖書館之內,不應在圖書館之外”,“如果不以圖書館作為研究對象,就不屬于圖書館學的研究范圍”。有的(如白光田)認為此“圖書館說”一是反映了大部分人的觀點;二是也有久遠的歷史;三是可為圖書館學的生存與發展奠定不可動搖的基礎;四是能清晰地確定圖書館學的研究內容,有效遏制其研究范圍的隨意擴張。
叢全滋(2009)認為,“圖書館的本質”是“收藏、揭示和傳遞文獻”,并指出這樣就“把圖書館與社會上的其他機構明確地區分開來”[39]。這實質上是把“收藏、揭示和傳遞文獻”作為“圖書館學的研究對象”,推出“藏用說”。
上述各“說”都立足于圖書館,以圖書館為前提,皆以或近似于以“圖書館”為研究對象,統稱“館內說”或“內圖書館說”。由于這些“對象說”均未準確揭示圖書館的本質,所以我們稱其為“非本質說”。
1.2中國圖書館學研究對象諸“非本質說”及爭鳴——基于集中評論的視角
1993~2009年,一些學者對上述諸“對象說”進行了集中評判。
趙媛(1993)撰文評判了上述一些“對象說”。關于“規律說”,趙認為,它“只反映了圖書館學研究對象的一個側面”,“圖書館界所談的‘規律說’”,所談之內容“實質上是一種工作規律,而非圖書館特殊矛盾的運動規律”。關于“事業說”,趙指出,“圖書館事業”并不能完全代表圖書館這一客體,它僅僅是其中的一個方面,故將其視為“對象說”“很不全面,存在著極大的局限性”。關于“圖書館說”,趙認為它“最大貢獻有兩點”:第一,“它找到了圖書館的特殊的、本質的矛盾,即藏與用的矛盾”,“它將圖書館學與其他學科區別開來”;第二,“它與過去其他學說的區別在于,它是站在整體的系統的高度來看待圖書館,而不是局限于其中的某一點、某一側面。也就是說,它用一個最簡的概念,即‘圖書館’限定了圖書館這一整體,包括圖書館所有方面、所有關系、所有過程”。其觀點支持“圖書館說”[40]。
馬恒通(2000,2007)兩次發文集中對上述諸“對象說”進行了評判。指出上述諸“對象說”由于都未準確揭示出圖書館的本質,因此不是圖書館學的研究對象[41-42]。其詳細內容請參見此兩文。
王續琨、羅懷遠(2002)認為上述“要素說”、“系統說”、“關系說”、“規律說”皆不是圖書館學研究對象,因為這些“對象說”都是圖書館學的研究內容[11]。
趙益民(2009)兩次發文指出,“過去許多‘對象說’均因未能完全準確地區分圖書館與其他公關文化機構而沒有取得廣泛的共識”,因而都不是圖書館學研究對象[43-44]。
總之,新中國成立60年來,我國學者對圖書館學研究對象“非本質說”的認識相繼提出了“要素說”、“規律說”、“關系說”、“層次說”、“系統說”、“活動說”、“互動說”、“圖書館 (事業)說”等“對象說”。盡管這些“非本質說”未真正探尋到“圖書館學對象”,但它的學術價值不可低估。因為人們對圖書館的認識需要一個由淺入深的過程,我們不能脫離當時實際情況(時代背景、圖書館事業發展狀況以及當時人們的認識水平等)而憑空想象。下述“近似本質說”正是在“非本質說”的基礎上和啟發下通過爭鳴而產生的。可以這樣說,沒有“非本質說”的建立,也就沒有“近似本質說”的建立、深化和發展。
2 近似本質說
2.1中國圖書館學研究對象諸“近似本質說”及爭鳴——基于個案的視角
2.1.1 “知識說”
20世紀80年代初至今,我國學者不斷深入探索圖書館的本質,對“圖書館學研究對象”提出了不同的“知識說”——一種“近似本質說”(“對象說”)。
1981、1988、1992年,彭修義3次撰文,指出“知識”是圖書館學的“四大研究對象”之一。強調“必須將知識作為圖書館學的一種研究對象”,首次推出“知識說”[45-47]。1984年,宓浩和黃純元在一次基礎理論研討會上首次提出“知識交流說”,并在其專著(1988)中更明確地指出:圖書館是“促進社會知識交流的社會機構”。認為圖書館學研究對象是“知識交流”[48-49]。20世紀末,劉洪波(1991)、王知津(1998)、蔣永福(1999)等撰文探討了知識組織、知識揭示與圖書館學的關系,認為圖書館學(情報學)的研究對象是“知識組織”,相繼推出“知識組織說”[50-52]。金勝勇等(2007)指出,“圖書館學的研究對象是基于信息檢索需要的信息組織”,提出“信息組織說”[53]。這實質上也是一種“知識組織說”。梁燦興(1998)強調,“圖書館學要研究解決的核心問題是,如何才能保證文獻群中知識單元的可獲得性”,認為“文獻群中知識單元的可獲得性是圖書館學的研究對象”,推出了“可獲得性論”[54]。之后他多次發文完善這一學說并引起爭鳴。王子舟(2000)認為,圖書館的研究對象應轉向“知識集合”,知識集合就是指用科學方法把客觀知識元素有序組織起來,形成提供知識服務的人工集合。指出“知識集合”是圖書館學的研究對象。創立了“知識集合論”[55],并引起爭鳴。吳慰慈、羅志勇(2000)指出,在信息時代,“管理知識內容恰巧是圖書館的優勢”,“圖書館學研究必須果斷地參與到知識管理領域中去”。首推“知識管理說”[56]。孟廣均(2003)指出,圖書館學的研究對象就是“對整個文獻信息系統的運動和發展進行有目的、有意義的控制,使整個環境和所有對象有序化、確定化、科學化”。從而推出新的“管理說”,這也是一種“文獻信息管理說”[57]。盛小平(2003)認為,知識信息的組織、傳播與利用是現代圖書館學的研究對象[58]。陳耀盛(2005)強調,圖書館學情報學的研究對象是顯性知識活動和隱性知識活動,即知識管理[30]。他們相繼推出“知識管理說”[59]。周久鳳(2001)認為,“圖書館本質特征就是知識存取”,“知識存取”是圖書館學的研究對象,推出“知識存取論”[60]。王京山(2002)認為,“圖書館的本質屬性是信息的組織與傳播”,“信息組織與傳播才是圖書館學的研究對象”。提出了“信息組織與傳播說”[61]。蔣永福(2003)強調,“圖書館學的研究對象是客觀知識、圖書館和人之間的相互關系和相互作用”,推出“客觀知識說”[62]。龔蛟騰等(2003)指出,“圖書館的實質是公共知識中心”,“圖書館學研究對象是公共知識管理學”,提出“公共知識管理說”[63]。此“說”引起強烈反響,張踐明3次發文與龔蛟騰就此“說”展開激烈爭辯,反對與維護者都據理力爭,仍未達成統一認識[26],[64-66]。2004年,伊鴻博和常青、熊偉分別提出了“知識功能說”和“知識共享說”。伊鴻博認為“圖書館學的研究對象是圖書館的知識功能”[67]。熊偉認為圖書館的存在在于滿足人類共享知識的需求,指出圖書館學研究(本質)對象是“人類共享知識的實現體系”[68]。李林(2006)指出,將“知識信息的傳遞與服務”作為圖書館學的研究對象能夠最準確地反映圖書館活動的本質,真正確立自己的學科地位,推出“知識信息傳遞服務說”[69]。馬恒通(2007)指出,“圖書館的本質是圖書館館藏知識的傳播”,“圖書館學的研究對象是館藏知識的傳播”,首推“知識傳播論”[42]。吳海波、黃立冬(2008)認為,“交流說”中的文獻信息“超出了圖書館學的本質所在,所以用文獻知識來代替它”。“圖書館學就是研究文獻知識交流的一門學科”,從而推出了“文獻知識交流說”[70]。
2.1.2 其他“近似本質說”
1960年,黃宗忠等指出,圖書館事業中藏與用這對特殊的矛盾是圖書館學的研究對象。首推“矛盾說”[28]。1978年北大圖書館學系編的一書認為,“收藏”與“提供”的矛盾是圖書館學的研究對象[71]。曾浚一(1980)認為,“管理與利用”的矛盾是圖書館學研究對象[72]。
我國學者在不同時期還推出了不同的“交流說”。主要有“文獻交流說”、“知識交流說”、“文獻信息交流說”、“文獻知識交流說”4種觀點。“文獻交流說”以周文駿為代表。他于1983年和1986年分別發文和著書,明確指出“圖書館學的理論基本上是利用文獻進行情報交流工作的經驗的結晶”[73-74]。“知識交流說”如上述。“文獻信息交流說”則以倪波、荀昌榮(1986)為代表。他們指出,“文獻信息交流是圖書館工作的出發點和歸宿”,“圖書館學的研究對象是文獻信息交流”[75]。1986年黎盛榮認為“文獻信息的開發與利用”是圖書館學研究對象[76]。此種觀點實質上也是一種“文獻信息交流說”。吳慰慈和高波于2000年推出新“文獻信息交流說”。認為圖書館學的研究對象就是文獻信息流(信源)、圖書館(信道)、讀者(用戶)(信宿),“三者共同完成了文獻信息的交流過程”[77]。“文獻知識交流說”如上述。“交流說”一出臺,就受到多人質疑和否定。劉茲恒、管計鎖(2002)指出,“‘交流說’現在看來確實存在不足,比如‘文獻信息交流說’能否涵蓋數字圖書館?社會其他領域的文獻信息交流現象是否屬于圖書館學的范疇?盡管它表達了圖書館與知識、知識交流的相互關系,卻未能揭示圖書館內部的本質和機理,即忽略了知識組織問題”[78]。
鄭金山于1997年首次推出“符號信息說”。他指出:“符號信息(“文獻信息”、“語言信息”、“態勢信息”和“信號信息”等)是圖書館學研究的基本對象”[79]。1997年、1999年,張錦發文兩篇,推出“控制論”。他認為“圖書館的本質是人類社會信息控制系統”,圖書館學的研究對象是“研究社會信息及過程之控制”[80-81]。
1998年,丁國順、葉鷹分別推出“公共信息流通說”、“信息時空說”。丁國順認為,“圖書館是一種公共信息的特殊流通形態”,“公共信息流通則是圖書館學的研究對象”[82]。葉鷹將圖書館定義為:“有序化信息相對集中的時空”。抽象圖書館學的研究對象是“有序化信息時空”[83]。
徐引箎和霍國慶(1998)、柯平(2004)、許西樂(2006)先后推出不同的“資源說”。徐引箎和霍國慶借鑒美國圖書館學家切尼(B·E·Chernik)的“資源說”,認為“圖書館學的研究對象是圖書館,圖書館是一種動態的信息資源體系,所以,圖書館學的研究對象是動態的信息資源體系”,推出“信息資源說”[1]。柯平(2004)強調,“圖書館學的研究對象是知識資源”。“知識資源也就是與知識有關的所有資源”,包括知識、知識人、知識工具、知識活動4個要素[84]。從而推出“知識資源說”。許西樂(2006)指出,圖書館學的研究對象是“文獻信息資源的整序與傳遞過程”,從而推出“文獻信息資源論”[85]。
2000年于鳴鏑認為,圖書館學的研究對象是對文獻信息進行合理的組織并有效地通過讀者完成信息的轉化(包括物化成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從而推出“轉化說”[86]。王睿與張開鳳(2003)認為,“圖書館學的研究對象是圖書館與讀者在知識傳播中的有機結合”。從而推出“結合說”[87]。蔣鴻標(2004)認為,“結合說”不是圖書館學研究對象[35]。2004年,黃權才指出,既然“大家的研究對象都是本質”,“都是把圖書館的本質作為研究對象”,那么,把圖書館的研究對象確定為“圖書館的本質和運行規律”,“也就沒有必要再爭圖書館的哪一種本質是圖書館的研究對象了”。從而推出“本質說”[88]。2006年,王學進指出,只有圖書館能夠為讀者(用戶)提供文獻信息的三大保障:“數量、質量保障”,“揭示和檢索保障”,“空間和時間保障”,因此,圖書館學的研究對象是“圖書館為需求提供文獻信息保障的全過程及其相互關系”,其首推“保障說”[89]。
以上“近似本質說”也可稱為“外圖書館說”,但它們仍未準確揭示出圖書館的本質,只是在不同程度上接近了本質性認識的層次。
2.2中國圖書館學研究對象諸“近似本質說”及爭鳴——基于集中評論的視角
1993~2009年,一些學者對上述諸“對象說”進行了集中評判。
趙媛(1993)認為,“矛盾說”只“側重于事物間的特殊矛盾,而忽略了事物內部的特殊矛盾”,不能“充分體現圖書館與社會中的其他子系統及社會大系統的關系”。趙還指出,“知識交流說”無法與同樣進行著知識交流的情報部門、書店、學校等區別,“知識交流”只是圖書館的功能中的一部分,因此“不能成為圖書館學的研究對象”[40]。
曾建(1993)指出,“‘交流說’(筆者注:指“知識說”、“文獻交流說”、“文獻信息交流說”、“知識交流論”)由于忽視了對圖書館現象的認識,著重于圖書館外界環境的研究,即知識在社會中的產生和傳遞過程的研究,難以扣緊圖書館自身整體,盡管它理論抽象性較強,但對圖書館具體工作的指導是不夠的”[90]。
茅振芳(1996)認為,“矛盾說”對于圖書館無特殊性、專指性、唯一性,不是圖書館學研究對象。“交流說”(包括“情報交流說”、“知識交流說”)只能說明圖書館工作的性質、任務和功能作用,不能將其與圖書館學研究對象混同起來。關于“知識說”,茅指出,“知識”“是圖書館學研究的內容(不是全部內容)”,“但絕對不是圖書館學研究對象”[8]。
徐引箎、霍國慶(1998)認為,這3種觀點,即“矛盾說”、“交流說”(包括“文獻交流說”、“知識交流說”和“文獻信息交流說”)和“新技術說”也都有著明顯的缺陷:“矛盾說未能理清圖書館的所有關系”,“交流說普遍超越了圖書館學的學科范圍”[1]。
馬恒通(2000、2007)兩次發文,集中對上述2005年之前的大部分“對象說”進行了評判。認為這些“對象說”都把研究對象擴大到包括圖書館在內的所有與知識有關的機構(事業)或組織中,都因無專指性而未能揭示出圖書館的本質,當然也不是圖書館學的研究對象。筆者提出的“知識傳播論”也只是一種“近似說”,詳見參考文獻[41-42]。
王子舟(2001)指出,“知識交流說”“未能很好地解釋圖書館內部活動的根本機制”。“‘知識組織說’作為‘知識交流說’的補充,無疑是克服了上述缺陷,但所刻畫的是圖書館內部活動過程的本質,忽略了知識受眾,其哲學特征屬‘方法’而非‘本體’層次,不是以某種‘社會現象’當成圖書館學研究對象,而一門學科的研究對象往往是由一種有‘本體’意義的‘社會現象’來充任的”[91-92]。
周久鳳(2001)指出,“‘知識交流論’把研究重點放在圖書館與社會的聯系上,而較少關注圖書館的內部活動”。“‘知識組織論’強調的重點在于(知識)整序的‘過程’,即關注的是知識的‘存’,忽略了知識的‘取’”[60]。
王續琨、羅懷遠(2002)指出,“矛盾說”是圖書館學的研究內容,而非研究對象。還指出,上述“知識說”、“知識交流說”、“符號信息說”、“信息資源說”等,“由于知識、文獻、符號、信息資源等作為研究對象,對圖書館而言不具有專指性”,因而皆非圖書館學研究對象[11]。
儲流杰(2002)對上述諸“說”進行批判,指出“矛盾說”、“交流說”、“資源說”、“信息時空說”、“知識可獲得性說”、“知識集合論”、“知識組織說”等“都在一定階段、一定層次、一定程度上存在著經驗性、技術性、片面性、非本體性、神秘性等認識偏差”,這些“對象說”中除了“知識組織說”“反映的不夠全面”外,其余諸“說”“不僅概念過于寬泛,沒有專指性,不能揭示圖書館的本質,而且遠遠超出了圖書館學的規定性”,或“理論本身還不太完善”[93]。
黃宗忠(2003)指出,有人說“圖書館學研究對象是信息、是知識、是文獻”,我認為“這些說法都不夠準確。我們承認知識、信息、文獻都是圖書館不可分離的因素,但不是圖書館專有的研究對象”[29]。2006年他又指出,當前出現的“‘信息資源’、‘知識資源’、‘知識組織’、‘知識集合’、‘知識管理’、‘知識單元的可獲得性’等都是含義廣泛、涉及領域眾多,為多個學科共有、通用或不是圖書館學專有、專指的對象,是上位類學科或相關學科的內容,如果圖書館學以這些為研究對象,必然丟去或淡化主體,走上泛泛議論、不解決實際問題、無針對性的‘空殼學科’”[30]。
陳源蒸(2006)認為,“知識集合論”,“是書、人、法三要素新的闡述”。關于吳慰慈、高波推出的新“文獻信息交流說”,他認為,“關于文獻信息的產生,另有所屬學科,讀者則是圖書館的一個組成要素。此論層次不清,與確立學科的基本原則不符”。他指出,“關于‘資源說’的闡述,只是較為深入地討論了圖書館學的一個方面,不能作為整體的圖書館學”[14]。
趙益民(2009)兩次發文,指出“過去許多‘對象說’均因未能完全準確地區分圖書館與其他公共文化機構而沒有取得廣泛的共識”,“縱觀已有的‘知識交流’、‘知識集合’、‘知識組織’、‘知識管理’、‘知識傳播’、‘知識共享’等相關概念,如果將它們視作為圖書館學的研究對象和圖書館工作的實質,難免有所缺漏或存在認識上的偏頗”,“‘知識資源論’力圖解決這個問題”。并將“知識傳播論”與“知識資源論”對比分析,反對“知識傳播論”,支持“知識資源論”[43-44]。
總之,新中國成立60年來,我國學者在不同時代條件下,由于受人們的認識水平、圖書館的發展變化和客觀環境變化等多種因素的影響,人們對圖書館學研究對象的“近似本質”的認識也不盡相同,這是必然的。“近似本質說”盡管仍未找到圖書館的本質,但它對準確認識圖書館的本質,進而探尋出圖書館學的準確研究對象,對進一步推動圖書館學深入發展和圖書館事業發展,不僅具有重要的奠基作用,而且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
3 結語
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認為,人們是通過現象而把握事物的本質的,而現象是逐步展開的,因此,人們對事物的認識就有一個由表及里、由淺入深、由不完全到完全的發展過程。毛澤東同志指出:“客觀實際是錯綜復雜的,不斷發展變化的。我們的頭腦、思想對客觀實際的反映,是一個由不完全到更完全、不很明確到更明確、不深入到更深入的發展變化過程”。“人的思維不可能完全確切地反映客觀實際。人類只能在認識事物的過程中逐漸克服認識的不足”[95]。
新中國成立60年來,我國學者受主客觀多種因素的影響和制約,人們對圖書館學研究對象的認識呈現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空前繁榮和快速發展的新局面。在“百家爭鳴”中,大致經歷了表象的具體的認識階段、整體的抽象的認識階段、本質的規律的認識階段、深入的整合的認識階段,經歷了從圖書館層面到文獻層面,再到信息層面進而到知識層面的認識階段,經歷了這樣一個由零星到系統,由局部到整體,由實用到理念,由封閉到開放,由靜態到動態,由非本質到近似本質的探索過程。不同階段反映了不同的時代要求。
盡管“對象說”至今仍眾說紛紜,見仁見智,沒有達成共識,但每一個觀點都是向本質層次的步步逼近,反映了對圖書館學研究對象認識的不斷深入和進步。
中國圖書館學發展史已經并將繼續證明,圖書館學“研究對象”的爭鳴,有效地促進了圖書館學理論的進步和圖書館事業的發展。“真理是由爭論確立的”[94]。筆者堅信,“對象說”之謎必將在未來的“百家爭鳴”中解開!“對象說”的不斷爭鳴,必將不斷推動圖書館學和圖書館事業可持續健康發展,走向美好的未來!
[1] 徐引箎,霍國慶.圖書館學研究對象的認識過程:兼論資源說[J].中國圖書館學報,1998(3):3-13.
[2] 劉國鈞.什么是圖書館學[J].中國科學院圖書館通訊,1957(1):1-5.
[3] 朱天俊.北京大學圖書館學系1957年科學討論會上關于“什么是圖書館學”一文的討論情況[J].北京大學學報,1957(3):102-105.
[4] 北京大學圖書館學系1956級《什么是圖書館學》批判小組.批判劉國鈞先生“什么是圖書館學”[J].圖書館學通訊,1958(3).
[5] 于鳴鏑.圖書館學研究對象之管見[J].圖書館工作與研究,1981(2):24-27.
[6] 朱建亮.早期圖書館學理論流派“要素說”今評[J].圖書館,2002(4):21-23.
[7] 吳慰慈.圖書館學基礎[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33.
[8] 茅振芳.圖書館學研究對象新探[J].中國圖書館學報,1996(6):20-24.
[9]邱五芳.歷史回顧與現實思考——重讀《什么是圖書館學》[G].北京大學信息管理系等.一代宗師——紀念劉國鈞先生百年誕辰學術論文集.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
[10] 王子舟.圖書館學研究對象的歷史誤讀[J].圖書館,2000(5):1-4,27.
[11] 王續琨,羅懷遠.圖書館學研究對象辯析[J].圖書館建設,2002(4):10-12,17.
[12] 王子舟.圖書館學基礎教程[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3:2,77.
[13] 胡萍.圖書館學研究對象的歷史軌跡[J].圖書館理論與實踐,2003(3):51-53.
[14] 陳源蒸.關于“要素說”及圖書館學的研究對象J].中國圖書館學報,2006(4):87-90.
[15] 北京文化學院圖書館學研究班編印.社會主義圖書館學概論[M].1960:1-35.
[16] 武漢大學圖書館學系,北京大學圖書館學系,北京文化學院編印.圖書館學引論[M].1961:1-30.
[17] 北京大學圖書館學系,武漢大學圖書館學系.圖書館學基礎[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3-7.
[18] 薛新力.圖書館學定義初探[J].四川圖書館學報,1981(1):20-23.
[19] 劉長發.圖書館學研究對象的互動關系[J].現代情報,2004(3):4-10.
[20]張欣毅,劉迅.層次說——我們對圖書館學研究對象的認識[J].圖書館學刊,1982(3):1-5.
[21] 李惠珍.圖書館學研究對象新論[J].中國圖書館學報,1997(4):86-89,81.
[22] 郭星壽.淺談現代圖書館學的結構[J].圖書館界,1982(3):10-14,22.
[23] 那春光,董穎.圖書館學研究對象是圖書館藏書系統[J].圖書館建設,1992(5):14-16.
[24] 沈繼武.關于圖書館學若干理論問題的思考[J].圖書情報知識,1985(1):21-26.
[25] 郭星壽.現代圖書館學教程[M].太原: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1992:48-56.
[26]張踐明.“公共知識管理學”解構——兼與龔蛟騰等同志商榷[J].大學圖書館學報,2004(4):76-79.
[27] 周文駿.我國圖書館學的對象和內容管見[J].學術月刊,1957(9).
[28] 黃宗忠,郭玉湘,陳冠忠.關于圖書館學的對象和任務.圖書館學通訊,1960(5):28-36.
[29] 黃宗忠.關于圖書館學研究對象、定義、功能的新思考(上)[J].圖書館論壇,2003(6):4-12,25.
[30] 黃宗忠.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的再探討.圖書館論壇,2006(6):3-10.
[31] 吳慰慈,邵巍.圖書館學概論[M].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5:5-11.
[32] 金恩暉.圖書館學引論[M].北京:學苑出版社,1988:138-139.
[33] 白光田.圖書館學的研究對象統一論[J].圖書館建設,2001(5):18-20.
[34] 吳慰慈,董焱.圖書館學概論.修訂本[M].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2:10.
[35]蔣鴻標.“結合說”不是圖書館學研究對象[J].情報雜志,2004(9):130.
[36] 周九常.圖書館學對象研究的審問與批判[J].大學圖書館學報,2006(2):24-28.
[37]王淑華.試論圖書館的本質與定義方法——兼評圖書館學研究對象某些定義的不足[J].圖書館雜志,2008(11):6-9,12.
[38] 湯樹儉.圖書館學的研究對象離不開圖書館[J].圖書館學研究,2009(4):5-8
[39] 叢全滋.圖書館的本質:收藏、揭示和傳遞文獻[J].圖書館雜志,2009(2):17-20.
[40] 趙媛.建國以來圖書館學研究對象主要觀點評述[J].畢節師專學報,1993(3):31-39.
[41] 馬恒通.新中國圖書館學的研究對象爭鳴50年[J].圖書館,2000(1):18-23,33.
[42]馬恒通.知識傳播論——圖書館學研究對象新探[J].圖書館,2007(1):15-21.
[43]趙益民.是“知識傳播”還是“知識資源”?——就圖書館學研究對象問題與馬恒通先生商榷[J].圖書館,2009(1):12-14,48.
[44] 趙益民.圖書館學視野下的知識資源新定義[J].圖書館,2009(2):7-9,12.
[45] 彭修義.關于開展“知識學”研究的建議.圖書館學通訊,1981-88.
[46] 彭修義.圖書館學基礎理論淺見.湖北高校圖書館,1988(2):1-7.
[47] 彭修義.圖書館學理論研究的知識方向.圖書館,1992(4):37-40,33.
[48] 宓浩,黃純元.知識交流和交流的科學.見吳慰慈,邵巍編.圖書館學概論教學參考文選.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5:20-38.
[49] 宓浩.圖書館學原理.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88:215-220.
[50] 劉洪波.知識組織與知識社會化過程.中國圖書館學報,1991(1):24-29.
[51] 王知津.知識組織的研究范圍及發展策略.中國圖書館學報,1998(4):3-8.
[52]蔣永福.圖書館與知識組織——從知識組織的角度理解圖書館學.中國圖書館學報,1999(5):19-23.
[53] 金勝勇,劉志輝.圖書館學研究對象新論[J].圖書館理論與實踐,2007(1):4-7.
[54] 梁燦興.圖書館學的核心問題和研究對象新見.圖書館,1998(5):10-11,18.
[55]王子舟.知識集合初論——對圖書館學研究對象的探索.中國圖書館學報,2000(4):7-12.
[56] 吳慰慈,羅志勇.面向21世紀圖書館學研究的新趨向[J].中國圖書館學報,2000(6):3-6.
[57]孟廣均.關于圖書館學研究對象的隨想錄——從IFLA 2003年年會的主題談起.圖書館論壇,2003(6):33,72.
[58] 盛小平.知識管理對現代圖書館學研究對象的創新.圖書情報工作,2003(9):51-56,66.
[59]陳耀盛.圖書館學情報學的持續發展——走向知識管理.圖書館論壇,2005(4):11-14.
[60]周久鳳.知識存取論——對圖書館學研究對象的認識.晉圖學刊,2001(3):37-40.
[61] 王京山.圖書館學新思維:試論“大圖書館學”的建立.圖書情報工作,2002(1):49-53.
[62]蔣永福.客觀知識、圖書館、人——兼論圖書館學的研究對象.中國圖書館學報,2003(5):11-15.
[63]龔蛟騰,候徑川,文孝庭.公共知識管理學——關于圖書館本質的思考.大學圖書館學報,2003(6):2-6.
[64]張踐明.“公共知識中心”說詰難——與龔蛟騰等同志商榷.圖書情報工作,2005(7):131-134.
[65]龔蛟騰,候徑川,文孝庭.《“公共知識管理學”解構》何解之有?大學圖書館學報,2005(3):79-83.
[66] 張踐明.解構只是為了澄明.大學圖書館學報,2005(4):91.
[67] 伊鴻博,常青.關于圖書館學基礎理論問題的思考.四川圖書館學報,2004(1):2-4.
[68]熊偉.廣義本體論導論——圖書館學研究對象體系的重建.圖書與情報,2004(5):2-6.
[69] 李林.圖書館學的研究對象探討.圖書館論壇,2006(4):249-251.
[70]吳海波,黃立冬.文獻知識——圖書館學之本質研究對象.圖書館雜志,2008(11):10-12.
[71] 北大圖書館學系編印.圖書館學概論.1978:1-30.
[72] 曾浚一.對圖書館學研究對象的初步探索.見中國圖書館學會主編.周文駿,吳慰慈編.圖書館學情報學基本理論論文選.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2:85-97.
[73] 周文駿.概論圖書館學.圖書館學研究,1983(3):10-18.
[74] 周文駿.文獻交流引論.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6:3.
[75] 倪波,荀昌榮.理論圖書館學教程.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86:36-70.
[76] 黎盛榮.現代圖書館學的特點及其研究對象.圖書館工作與研究,1986(1):30-33.
[77] 高波,吳慰慈.信息技術對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的影響.江蘇圖書館學報,2000(3):6-12.
[78] 劉茲恒,管計鎖.對中國圖書館學研究對象的審視與展望.圖書情報工作,2002(1):45-48,98.
[79] 鄭金山.圖書館學研究對象新探.成都大學學報:社科版,1997(2):52-53.
[80]張錦.圖書館學基本問題再認識——論社會信息控制說.四川圖書館學報,1997(3):16-18.
[81]張錦.圖書館學研究對象評述——兼論控制說.圖書情報工作,1999(8):6-9.
[82] 丁國順.從圖書館的形態研究看圖書館學的研究對象基本概念.圖書館學研究,1998(4):1-5.
[83] 葉鷹.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的抽象建構.中國圖書館學報,1998(3):86-88.
[84]柯平.知識資源論——關于知識資源管理與圖書館學的研究對象.圖書館論壇,2004(6):58-63,113.
[85] 許西樂.對圖書館學研究對象的再認識.青海民族學院學報:社科版,2006(1):146-148.
[86] 于鳴鏑.轉化說:圖書館學研究對象的新探討.江蘇圖書館學報,2000(6):7-11.
[87]王睿,張開鳳.關于圖書館學的研究對象的再思考——兼與王子舟先生商榷.情報雜志,2003(5):103-104.
[88] 黃權才.在“本質”的紛爭中認識圖書館學研究對象.四川圖書館學報,2004(2):8-10.
[89] 王學進.究竟什么是圖書館學的研究對象.圖書館學研究,2006(3)2-6.
[90] 曾建.試評“知識文獻交流說”.成都大學學報:社科版,1993(4):9-11.
[91]王子舟.中國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的艱難重建——紀念《圖書館學基礎》出版20周年.圖書館,2001(3):1-6,20.
[92]王子舟.中國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的艱難重建(續)——紀念《圖書館學基礎》出版20周年.圖書館,2001(4):1-7.
[93] 儲流杰.對圖書館學研究對象認識的分析.圖書館學研究,2002(5):11-13.
[94]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1卷.北京:三聯書店,1957:567.
[95] 毛澤東.毛澤東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7,65-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