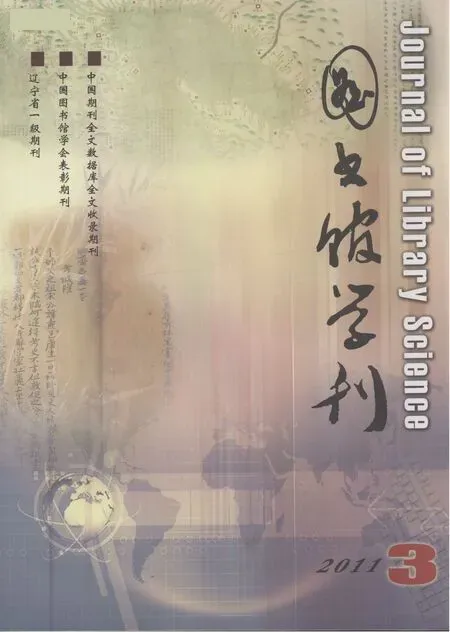何其芳藏書考
馮 佳
(中國傳媒大學圖書館,北京 100024)
何其芳在文學創作和文學評論方面有很高的成就。何其芳的成就與他熱愛圖書、收藏大量圖書、閱讀與評點圖書有著密切的聯系。
何其芳藏書有3萬余冊;收書質量很高,有許多難得的古籍珍本(如清曾衍東的《小豆棚》,光緒六年版本),也有不少版本價值和學術價值都很高的平裝毛邊本、初版本。
筆者在中國傳媒大學古籍室負責何其芳藏書的整理及借閱工作,就何其芳先生熱愛圖書的故事和充滿傳奇色彩的藏書經歷,及其所藏圖書種類和特色等進行了整理與研究,現將幾年的研究成果加以梳理與分析。
1 何其芳簡介
何其芳,原名何永芳,重慶萬州(原四川萬縣)人,生于1912年,卒于1977年。著名詩人、散文家、文學評論家、紅學家和藏書家、藏書室名“無計為歡室”。20世紀30年代他與卞之琳、李廣田組成中國現代文學史上著名的“漢園三詩人”。1938年到延安參加革命,歷任魯迅藝術學院文學系主任、中國作家協會書記處書記、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文學評論》主編。
何其芳一生著述頗豐。著作主要有散文集《畫夢錄》(1937年獲《大公報》文藝獎金)、《還鄉雜記》(又名《還鄉日記》)、《星火集》、《星火集續編》、《一個平常的故事》;有詩集《預言》、《夜歌》(又名《夜歌和白天的歌》);有小說、戲劇等合集《刻意集》;有論文集《關于現實主義》、《西苑集》、《論紅樓夢》、《關于寫詩和讀詩》、《詩歌欣賞》、《文學藝術的春天》。另有與卞之琳、李廣田合著詩集《漢園集》。
《何其芳全集》8卷本于2000年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收入何其芳自30年代以來寫作的詩歌、散文、小說、文藝論文、序跋以及翻譯作品、書信、日記等,約270萬字。
何其芳藏書約3萬5千冊,整理這些藏書發現何其芳兩枚藏書印:“何其芳”白方和“無計為歡室所藏圖書”朱方。夫人牟決鳴同志對“無計為歡室所藏圖書”藏書印這樣解釋:“其芳同志大半生從事文學事業。平日除工作、讀書、寫作外,無暇顧及其他游樂。”[1]何其芳鈐印十分謹慎,蓋有藏書印的圖書不及全書的千分之一。
2 何其芳藏書之來源
2.1 書肆購書
何其芳的藏書十之八九都是買來的,其余為贈書。這有書中所夾發票及書底所貼或蓋的價簽為證,大多是東安市場舊書店、中國書店的價簽紙片或印章。何其芳嗜書如命,晚年曾用詩歌的形式表達他對書的癡迷,如“一生難改是書癖,百事無成徒賦詩”(《憶昔》),“喜看圖書陳四壁,早知糞土古諸侯”(《偶成》),“大澤名山空入夢,薄衣菲食為收書”(《自嘲》)等。何其芳以文學事業為終生的職業,在他眼里書比功名利祿更重要,他為了購書更是可以“薄衣菲食”。
當年的何其芳家住東單,離王府井的東安市場較近,據說每到禮拜日,何其芳就去逛東安市場的書肆,天黑時他才拉上滿滿一平板車的書回家。還有著名的琉璃廠、西單商場、隆福寺等處,舊書店鱗次櫛比,何其芳常流連于這些地方。作為老主顧,他常與琉璃廠的舊書鋪約好,每星期給他送書。
上世紀50年代是更新換代的年代,也是舊書店、舊書攤交易的鼎盛時期。從何其芳所購線裝書的發票或封底價簽上的時間可以看出,所購線裝書大多是在這個時期。
“文革”后,何其芳開始自學德語,翻譯德國文學作品。為此,他常去舊西書鋪子淘書,并且頗有淘書心得。1974年5月9日何其芳致詩人方敬的一封信:“北京舊西書鋪有些收縮的樣子,西城的已和東城的合并了,只此一家……未合并以前,(西城那家)收了兩個人死后的西書,一個章士釗,文學書很少,一個是盛澄華的,主要是紀德和象征派詩人的作品。我去的可能遲了一些,有名的大家作品沒有怎么買到,只買了司湯達的三卷作品集,葆華來見到,說是法文書的好版本了。其實也不過印度紙精裝而已,仍是普及本,算不上豪華本。詩集多是小家的集子,只買到凡爾哈侖的詩集七種,算是一次較豐富的收獲。不過查書目,這個作者的作品還有好幾種,盛澄華大概也沒有買全……回想起來,那是錯過了一次機會,堆得地下都是書,不少人都挑著選,李健吾也去了……”[2]我們從何其芳上世紀70年的書信中,了解到他常常給自己和方敬買西文書,其外文書基本都購買于此時。方敬也是一位詩人。何其芳與方敬的友誼始于中學時代,與何其芳不同,方敬的性格比較外向活潑,曾經影響過何其芳的性格,使他也變得開朗起來。后來,方敬成了何其芳的妹夫,兩個人成了終生的好朋友。
何其芳出差到外地或外國,也是每到一地必到舊書鋪買書若干。如1952年夏天,何其芳訪問捷克、東德、蘇聯,他在6月17日的日記中記載:“逛一舊書鋪,買雨果的《歐那尼》一本,價僅十二克朗,書鋪有一曾在中國生活三十年的捷克老頭兒,自言曾做過北京五星啤酒廠技師,但中國話說得并不好。”[2]6月25五日的日記中記載:“陰雨天,上午逛了一陣舊書鋪。”[2]同年秋天,何其芳陪蘇聯作家去中南訪問途經武漢、長沙、廣州,在這三處的舊書店都有購書。如“漢口書兩包;長沙書三包;廣州書六包”[2];“1952年11月23日廣州文德路買舊書”[2]。何其芳在武昌舊書店購書的過程,令當時的陪同者曾立慧印象深刻,曾撰文《珍貴的往事——回憶何其芳同志》[3]記錄了這段經歷,這也是今天能見到何其芳購書細節的最完備的文字記載,從中能領略到何其芳對書的癡迷精神及他對后學無私提攜的長者風范。
何其芳購書范圍很廣,除文學外,政治、經濟、哲學、歷史方面的都在搜尋之列,這主要是因為何其芳所處學術環境很特殊。當時,何其芳的研究課題基本上都是政治任務,比如1953年屈原被列為世界文化名人,何其芳被指定做屈原研究;紀念馬雅可夫斯基誕生60周年,何其芳又做馬雅可夫斯基研究等。為了適應研究課題的需要,何其芳盡可能全面地買書,可能此時用不上,彼時就用上了,所謂“書到用時方恨少”,多多益善。
2.2 朋友贈書
何其芳在文學界擔任要職,身處主流文學的中心地位,圍繞在他身邊的都是成名的文學大家。何藏有109種贈書,贈書者都是中國現當代文壇上著名的作家,他們是卞之琳、李瑛、呂劍、聞捷、嚴辰、李廣田、郭小川、陳山、馮至、唐弢、王運熙、曹禺、沙汀、沙鷗、方敬、魏巍、臧克家、蘇金傘、力揚、田間、何家槐、李健吾、曹葆華、王瑤、游國恩、余冠英、巴金、俞平伯、嚴文井等近90位名家。
2.3 機構贈書
何其芳贈書中有130種研究機構或者出版社贈書,一般都蓋著機構的印章。出版社有作家出版社、解放軍文藝出版社等;研究機構有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中國戲劇家協會等。
3 何其芳藏書贈送中國傳媒大學
何其芳對藏書非常愛惜,買來的書籍,因為怕弄臟,一般連子女們都不讓看,而是專門給他們買復本。何其芳的書庫也不輕易讓人打開。曾經何其芳被下放到河南息縣東岳公社干校勞動,聽說大女兒三雅要帶走一些他的復本書,很是焦慮,趕緊囑咐夫人不讓女兒到書庫隨便找書。
何其芳珍惜自己收藏的每一冊書,是希望藏書能物盡其用,他生前曾自負地說:“我的這些書,供文學研究工作者用,是足夠了。”[4]何其芳逝世后,遵照生前“藏書不分散”的遺囑,3萬5千冊藏書集中捐贈給了中國傳媒大學(原北京廣播學院)。
據知情人透露,何其芳另有四大箱子資料寄托在親戚家,至今下落不明。目前所見到的何其芳藏書中幾乎沒有他本人的著作(除《刻意集》、《還鄉日記》為朋友贈書外),也沒有手稿,有可能這些比較私人的資料都珍藏在這四大箱子里。因為珍愛反而導致它們不見天日,這肯定不是何其芳的初衷,這也是何其芳研究的重大損失。
中國傳媒大學圖書館接受何其芳藏書之后,非常重視,特設何其芳古籍閱覽室以妥善收藏,并配備專門的人員進行整理。線裝書大多統一配上六面全部包裹的全包式、厚紙板外裱以藍布的函套,少數圖書保留了原有函套;按《中國圖書館分類法》分類,并配備中圖法、著者音序法和書名音序法3種卡片目錄,供讀者查閱;編有《何其芳古籍藏書目錄》一書;目前正在做機讀編目數據。平裝書按《中國圖書館分類法》分類,編有機讀目錄。
4 何其芳藏書的內容
何其芳藏書主要分3大類:古籍、中文平裝書及外文圖書,約9千多種、3萬5千余冊。
4.1 古籍
中國傳媒大學圖書館編有《何其芳古籍藏書目錄》一書,所收圖書以線裝書為主(除兩三冊經折裝圖書和蝴蝶裝圖書),由此可見,該書作者是將線裝書等同于古籍的,這也代表了一部分人的看法,顯然這種觀點是不科學的。這里有必要厘清古籍與線裝書的區別。中國傳統的圖書裝幀形式有線裝、蝴蝶裝、卷軸裝、經折裝、旋風裝等,自宋代以后,線裝書成為圖書裝幀的主要形式,至今仍有一些出版社采用線裝形式裝幀圖書。所謂古籍,在時間上有上限和下限的界定。目前學術界對古籍的上限和下限的劃定有一致的觀點,一般認為春秋末戰國時編定撰寫的經、傳、說、記、諸子書等是古籍的上限,下限則一般劃到1911年辛亥革命。也就是說中國境內產生于1911年以前的具有中國傳統裝幀形式的圖書一定是古籍。
當然,古籍的這個下限仍舊是粗線條的。辛亥革命以后出版的線裝圖書要視具體情況分析是否為古籍,目前學術界已大致量化為3種情況:一用線裝書形式出版的原古籍線裝書的影印本、重新雕版刷印本、重排本、縮印本應作為古籍收錄,因這它們只是原線裝書的“翻版”,沒有改變原線裝書的內容和外形,還完全是古籍的范疇。如《四部備要》、《四部叢刊》等。二用線裝書形式出版的原古籍線裝書的點校本、注釋本、賞析本、白話文譯本等,它們已改變了原線裝書的內容,失去了“古籍”的內涵,只保留了原線裝書的“外殼”,成為現代人的著作,故不能再作古籍之列。三用線裝書形式出版的現代人著作,無論其內容如何都不是古籍。學術界一般稱辛亥革命以后出版的古籍為“新印古籍”或“新版古籍”。
何其芳藏線裝書主要是清版本、民國版本及少數明刻本。很顯然清版本、明刻本屬于古籍;經過仔細考察,其所藏民國版本、少數新中國成立后的版本絕大多數是新印古籍。據統計,何藏古籍文獻2020余種、共2萬7千余冊;《中國古籍善本總目》所收善本35種;有54種帶有其本人的批注。經、史、子、集、叢收藏具備,其各類古籍文獻的收藏情況如下:
其一,經部。何藏經部古籍有110余種,新印古籍有40余種,其中善本3種。經部詩經類藏書最多,有60余種。《詩經》是我國的第一部詩歌總集,這些珍貴的古籍文獻對于詩經學研究具有極其重要的參考價值。
其二,史部。何藏史部古籍有260余種,新印古籍有90余種,其中善本兩種。何藏史部類目齊全,對廣大讀者研究我國歷史可提供較豐富的史料。
其三,子部。何藏子部古籍有360余種,新印古籍有110余種。其中小說類就有近220余種。其他如道家、法家、兵家、農家、醫家以及雜家類、宗教類等藏書均有。
其四,集部。何藏集部古籍有600余種,新印古籍有200余種,善本有30種。各朝代的重要作品集都有收藏,這些豐富的典藏為研究我國文學史提供了多方面的參考資料。
古籍叢書有130余種,新印古籍叢書有120余種,其中有少數叢書收書不全,比如《四部叢刊》全套是502種,何藏有413種。
4.2 中文平裝書
中文平裝書指民國圖書及新中國時期的圖書,具體到何其芳逝世即1977年所收圖書。
何藏平裝書約有7千余冊,有約500種帶有本人的批注。按照《中國圖書館分類法》分類整理,社會科學各類基本上都有,但以文學類為主,占總冊數的一半以上。何藏民國時期書刊約有兩千余冊,其中民國時期叢書有17種、共836冊,所收叢書都不全,主要有萬有文庫、叢書集成、澤林小說叢書等。
4.3 外文圖書
何藏外文圖書約有905種,其中德文圖書有463種,英文圖書有420種,法語和俄文圖書共有22種。
何藏德文圖書多是詩歌集,當時何其芳是一邊學德語,一邊開始翻譯詩歌。何其芳曾就讀于清華大學的外文系,有英語和法語基礎,他卻舍近求遠選擇了德國文學。這是因為他當時對德國詩人維爾特和海涅的詩歌很感興趣,他們的原文作品也比較好找;還有一點,是考慮到自己的身份和當時的時代背景,翻譯英美文學也許會授人以柄,而翻譯德國作品,至少可以以學習馬克思、恩格斯著作作為搪塞。何其芳一直沒有對外吐露自己的真實原因,只說是為了要讀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只有在親密的朋友面前,何其芳才敢袒露自己的真實打算。何其芳是借翻譯外國文學作品以解不能直接創作之苦,是曲線救國,足見他對文學的熱愛。
5 何其芳藏書的特色文獻
5.1《紅樓夢》及各種續紅樓藏書
在何藏中,《紅樓夢》及各種續紅樓的版本較多,計19種。作為紅學家,何其芳對《紅樓夢》和各種續紅樓的版本收藏相當重視,某種程度上,也是其研究的一個側面。以下是《紅樓夢》及各種續書版本概況:
《紅樓夢》120卷120回,(清)曹雪芹著,(清)高鶚著,(清)王希廉評,清道光壬辰(1832)上浣刻本。
《紅樓夢》40卷120回,(清)曹雪芹著,(清)高鶚著,(清)張新之評,清光緒辛巳(1881)臥云山館本。
《增評補圖石頭記》120卷120回、卷首,(清)曹雪芹著,(清)高鶚著,(清)王希廉評,(清)姚燮加評,鉛印本。
《國初鈔本原本紅樓夢》8卷80回,(清)曹雪芹著,民國上海有正書局石印本。
《紅樓夢八十回校本》,曹雪芹著,王惜時參校,俞平伯校訂,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2月第1版。
《戚蓼生序本石頭記》8卷80回,曹雪芹著,人民文學出版社1975年6月。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80回,(清)曹雪芹著,(清)脂硯齋評,1955年11月北京文學古籍刊行社朱墨影印本,
《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16回16卷,(清)曹雪芹撰,(清)脂硯齋評,民國五十年(1961)臺灣商務印書館等朱墨影印本。
《后紅樓夢》4卷30回,卷尾附刻吳下諸子和大觀園菊花社原韻詩和補題詩2種,(清)逍遙子著,宣統元年(1909)上海有益齋精校石印本。
《后紅樓夢》30回,卷尾附刻吳下諸子和大觀園菊花社原韻詩和補題詩2種,記第31卷、第32卷,(清)逍遙子著,文德堂石印本。
《后紅樓夢》30回,卷尾附刻吳下諸子和大觀園菊花社原韻詩和補題詩2種,記第31卷、第32卷,(清)逍遙子著。
《紅樓夢影》24回,(清)西湖散人撰,初刊于清光緒丁丑(1877)京都聚珍堂活字本。
《紅樓真夢》64回,郭則沄撰。此書初刊于1939年。何藏為1940年侯官郭氏鉛印本。
《繡像紅樓夢補》4卷48回,(清)歸鋤子撰,上海圖書集成局清光緒已亥年(1899)鉛印本。
《紅樓夢補》48回,(清)歸鋤子著,上海申報館鉛印本。《續紅樓夢》40回,(清)海圃主人撰,尚友堂本。
《續紅樓夢》30卷,(清)秦子忱撰,東瀛書館鉛印本。
《紅樓復夢》100回,(清)陳少海編輯,(清)陳詩雯校訂,上海申報館清光緒2年(1876)鉛印本。
《紅樓復夢》100回,(清)陳少海編輯,(清)陳詩雯校訂。
《增評補圖石頭記》、《國初抄本原本紅樓夢》、《脂硯齋重評石頭記》、上海有益齋精校石印本《后紅樓夢》和《紅樓夢八十回校本》這5種版本中帶有他本人約兩萬多字的批語。仔細考察何其芳的這些批語,主要分6大類:一是版本考證;二是故事情節介紹;三是人物分析;四是作品思想性分析;五是作品藝術性評價;六是后40回寫作手法評價。
5.2 現代作家作品集
中國文學史稱1919年五四新文化運動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這個階段為現代文學。何其芳自己就是活躍在現代文學文壇上的一員虎將,當年憑借《畫夢錄》力挫群雄,與曹禺(戲劇《日出》)和蘆焚(小說《谷》)共同獲得“大公報文藝獎金”。何其芳收藏現代作家作品集,一定程度上體現了他對身處其中的文學圈子的一種評判,這一點是值得學界深入探討的。
何藏現代作家作品集有60余種,現代文學史上的重要作家的作品都有收藏,主要有魯迅、周作人、聞一多、徐祖正、韋叢蕪、許欽文、柳亞子、臺靜農、綠漪女士、章衣萍、野渠、蔣光慈、蒲風、廢名、長虹、康白情、許地山、郁達夫、辛笛、郭沫若等人的作品集。
何藏現代作家作品集版本珍貴,初版本及毛邊本較多。毛邊本是一種特殊的裝幀形式,就是圖書印制過程中,未經最后一道裁切工序,保持折疊原狀,書邊稍有參差的書籍,又稱毛邊本或者毛裝本、未切本、留邊書。毛邊書在魯迅的大力提倡下,備受新文學名家的推崇,成為新文學出版物的一個標志。據說,毛裝本是魯迅從西方的裝幀形式借鑒過來的,其實我國古代線裝書就已有了這種裝幀形式,俗稱毛本。毛邊書出版量極少,普通讀者沒有機會接觸,當今受到收藏界熱捧。周作人兄弟翻譯出版的《域外小說集》毛邊書,在北京海王村2007秋季拍賣會上以29.7萬元天價拍賣成交。何藏有74種毛邊書,其中有22種現代作家作品集的毛邊本,這些書比一般的善本書更集中地體現了歷史文物性、學術資料性、藝術代表性。何藏初版本現代作家作品集有38種。初版本的關鍵價值在于學術價值和版本價值。初版本和以后的各版本比較,其修改情況一目了然,通過版本的研究指出作品前后異同,對于研究作家創作思想的演變是非常有益的。如何藏周作人作品集有12種,幾乎全是初版本,它們分別是《談虎集》(1928年初版和1929年第3版,毛邊本)、《過去的生命》(1929年初版,毛邊本)、《周作人書信》(1933年初版,毛邊本)、《雨天的書》(1934年第8版,毛邊本)、《藥味集》(1942年初版)、《書房一角》(1944年初版)、《夜讀抄》(1935年初版)、《藥堂語錄》(1941年初版)、《永日集》(1929年初版)、《苦竹雜記》(1936年初版和1941年再版)、《知堂文集》(1933年初版)、《秉燭后談》(1944年初版)。
新文學版本的出版非常重視書籍的裝幀設計,在封面或插圖設計方面形成獨特風格的大家主要有陶元慶、司徒喬、錢君匋、豐子愷、葉靈風、聞一多等。何藏現代作家作品集中就有3種出自名家設計的封面或插圖,它們是:豐子愷漫畫《蹤跡》書衣,朱自清著,上海亞東圖書館1924年12月初版;聞一多自已設計《死水》封面,1928年1月初版,新月書店出版;司徒喬作4幅插圖、葉靈鳳作兩幅插圖本《綠天》,綠漪女士著,北新書局,1928年7月再版。名家設計封面的版本,因其獨特的藝術價值,有點類似名人畫作,目前受到收藏界的熱捧。
5.3 名家簽名本
何藏109種簽名本贈書,幾乎全是新中國成立后的版本。何藏簽名本扉頁或題名頁上大多是“其芳同志教正”或“其芳同志指正”或“送給其芳同志”等簡短的題簽,但因為是朋友所贈,體現了濃濃的人文情懷;又因為是名人手跡,也具有極高的版本收藏價值。
何藏簽名本中題簽字數較多的是唐弢校訂魯迅的《門外文談》和天藍譯亞里士多德的《詩學》這兩種書。《門外文談》,人民出版社1974年5月初版,題名頁有“:此書開注于一九七二年,越二月,內部印過一次,一九七三年六月出試印本,八月定稿,至今將公開發行。全集此備注四十一條,現為一百二十五條。在此過程中,多謝你的鼓勵和支持。其芳同志唐弢一九七四年九月。”《詩學》,新文藝出版社1953年3月初版。題名頁有:“其芳同志:這本小小的譯作是得過你珍貴的幫助的,當它再版的時候,特送上以留紀念。天藍23//1953。”唐弢和天藍兩位作者在題簽中都表達了對何其芳幫助的感謝,唐弢的題簽還另有對此書寫作情況及出版情況的簡介,是作者對出版源流的親筆描述,具有極高的學術史料價值。
何藏贈書中有朋友贈給他自己發表的作品集《刻意集》和《還鄉日記》:《刻意集》,文化生活出版,民國二十七年(1938)十月初版。《還鄉日記》,靳以編輯,現代散文新集,上海良友復興圖書印刷公司印行1939年8月初版。《刻意集》是摯友卞之琳所贈,此書第一張扉頁上記:“一九四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其芳在延安收到。”第二張扉頁上“:書出版了兩年才見到,想著北更未曾寓目,特購寄西北,愿路上順延。之琳九月,一九四○,昆明。”此書上有何其芳和卞之琳兩位名家的簽名,實屬難得。何其芳還對全書進行了校改,作家自己校改作品的版本,更是難得,從中可以研究其創作思想的流變,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何其芳和卞之琳的友誼始于他們的大學時代,他們曾與李廣田組成“漢園三詩人”,出版詩集《漢園集》,后來他們又一起到革命勝地延安,他們之間的友誼深刻而長久。所以,也只有卞之琳這樣的朋友才會心系何其芳,惦記著何其芳在延安不能得到自己出版的作品的無奈,于是親自買來寄給何其芳。這本贈書是兩位文學大師深厚友誼的見證。《還鄉日記》的扉頁上有何其芳朱筆記“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三日收到鄭克從浙江寄來”,說明此書是鄭克所贈。何其芳在此書目錄頁后空白頁有墨藍筆批注:“遺失下列四篇:我們的城堡(發表于國聞周報十四卷十二期)私塾師 老人 樹陰下的默想。”何其芳的批注有利于我們把握《還鄉日記》版本的演變情況。
6 結語
何其芳藏書1978年捐贈給中國傳媒大學,當時及以后的一段時間內,我國出版業處于枯水期,館藏圖書貧乏,何其芳的這些藏書就成為莘莘學子們爭相借閱的讀物。據說當時要借閱何其芳藏書必須早早地趕到閱覽室,否則就借不到,只能掃興而歸了。曾經有學者提到何其芳藏書就激動不已,還利用回到母校講學的機會,重訪何其芳藏書,稱當時就是因為受何其芳藏書的影響而使他走上了文學研究的道路,這足以證明何其芳藏書是澤被過幾代學人的。在文化資源豐富的今天,如何更有效地開發利用何其芳藏書是我們需要積極思考的課題,比如整理何其芳批注出版,為何其芳研究者提供第一手研究資料,推動何其芳研究發展,與出版社合作再版一些珍稀版本等等。
[1]馬靖云.大澤名山空入夢,薄衣菲食為收書——何其芳藏書介紹.衷心感謝他——紀念何其芳同志逝世十周年.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7:334.
[2] 何其芳.何其芳全集.第8卷.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41-42,352,356,190,393.
[3]曾立慧.珍貴的往事——回憶何其芳同志.衷心感謝他——紀念何其芳同志逝世十周年.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7:149,152-153.
[4]馬靖云.大澤名山空入夢,薄衣菲食為收書——何其芳藏書介紹.衷心感謝他——紀念何其芳同志逝世十周年.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7:3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