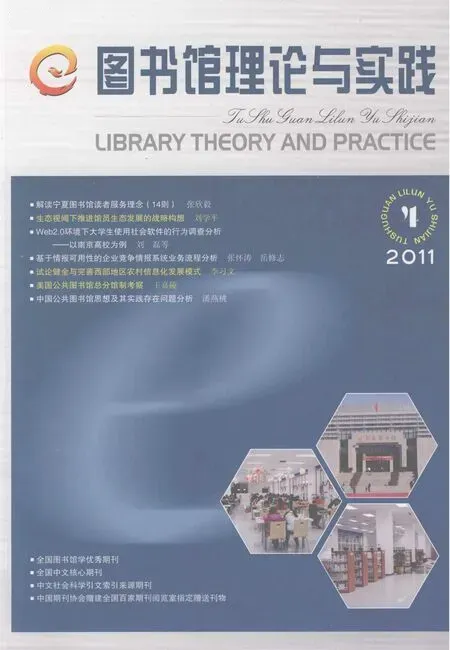金代的女真文和契丹文閱讀
●王 龍(包頭師范學院 歷史文化與管理學院,內蒙古 包頭 014030)
女真文和契丹文是金代前期在女真人,特別是上層女真貴族中除漢文外普遍使用的兩種文字。這兩種文字雖然使用范圍不很廣泛,時間不長,讀物也不算多,但它們作為特定歷史時期的產物,在儒家經典的翻譯及其閱讀活動中,對金代乃至整個中華民族的文化以及社會發展都曾產生過重要的影響和作用。
1 女真文閱讀
女真原無文字,刻木為契,部落內部傳令時以“信牌”為之。后來用了遼的大臣,才借用契丹字,書寫公文,“與鄰國交好乃用契丹字。”建國后,隨著政治、經濟發展的需要,金太祖阿骨打命完顏希尹創制女真文字。“希尹乃依仿漢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國語,制女真字。天輔三年八月,字書成,太祖大悅,命頒行之”。“其后熙宗亦制女真字,與希尹所制字俱行用。希尹所撰謂之女真大字,熙宗所撰謂之女真小字”。[1]女真文字頒行后,成為金代官方通用的文字。它便于金統治者各項命令的發布和執行,特別是便于女真民族學習其他民族先進的文化和技術,促進女真民族文化水平的提高以及女真社會的發展。所以女真字的頒行,在突顯女真的民族性,提升其民族自豪感的同時,也有益于其閱讀活動的發展。也使女真字、契丹字和漢字一起成為金代并存的3種文字,多文字閱讀也成為金代閱讀的一大特點。
1.1 女真文的翻譯及其閱讀
用女真文撰寫的著作保存下來的極少。從保存下來的由漢文翻譯成女真文著作的目錄來看,除了儒學經典外,絕大多數譯著是有關漢民族治國方略和兵法等內容的。這說明,金代統治者通過給女真人提供這樣的讀物,目的是讓他們了解漢文化和漢族倫理道德規范,提高他們的文化素養,使官吏們學習和掌握政治和軍事知識,增長治理國家和帶兵打仗的才干,完全出于統治者利益的考慮。而對于純文學作品及小說則翻譯的較少。但不管怎么說,金代的翻譯活動比起遼代和后來的元代都更具規模。
金代的皇帝,尤其是金世宗積極推進尊孔崇儒,倡導讀書興學,并大量地翻譯漢文典籍。自此,不僅漢文閱讀進入繁榮期,而且女真文閱讀也欣欣向榮。史載,“大定四年,詔以女真字譯書籍。五年,翰林侍講學士徒單子溫進所譯《貞觀政要》、《白氏策林》等書。六年復進《史記》、《西漢書》,詔頒行之。”[2]大定十五年(1175年),世宗又詔譯諸經。[2]大定二十三年(1183年),“譯經所進所譯《易》、《書》、《論語》、《孟子》、《老子》、《楊子》、《文中子》、《劉子》及《新唐書》”。世宗對宰臣說:“朕所以令譯《五經》者,正欲女真人知仁義道德所在耳。”[3]可見,金世宗倡導譯經的目的,就是要對女真人進行儒家思想教育。到大定二十八年(1188年),《五經》中已譯出《書》《易》《春秋》,尚有《詩》《禮》在翻譯中。此外,史料所記載的明昌二年(1191年),學士院所進的26種唐宋文集,它們是否是女真文譯本,還無法確定。還有早已無存的明正統時北京文淵閣著錄過的女真文《盤古書》《孔夫子書》《姜太公書》《孫臏書》《伍子胥書》《黃氏女書》《百家姓》《哈答咩兒子》《千字文》《女真字母》等18種書籍,[4]也是迄今所知的女真文讀物。
由上面提到的翻譯為女真文的書籍可看出:第一,女真統治者重視的是史書的閱讀,并以盛唐之治為其楷模,而首先翻譯了《貞觀政要》來教育女真人。其中包括白居易的79篇考試范文選《白氏策林》,也是以解決社會現實問題為題材的、頗具實用性的讀物。它們都反映了女真人經世致用的閱讀觀念;第二,女真人是以儒家經典為核心來進行文化教育,提高其文化素質,構建其知識結構的。正如元好問所言:“有天地,有中國,其人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孔,其書則《詩》、《書》、《易》、《春秋》、《論語》、《孟子》。”[5]可見,儒家思想永遠是中華各民族的文化資源和精神紐帶。
大定二十三年(1183年),參知政事梁肅奏曰:“漢之羽林,皆通《孝經》。今之親軍,即漢之羽林也。臣乞每百戶賜《孝經》一部,使之教讀,庶知臣子之道,其出職也,可知政事。”世宗聽后曰:“善,人之行,莫大于孝,亦由教而后能。”[6]于是“以女真字《孝經》千部付點檢司分賜護衛親軍。”[3]一是說明金朝對推行儒家倫理道德教育的重視;二是女真文《孝經》的閱讀曾在女真人中很普及;三是女真文印刷業亦很發達。此后,章宗也執行了同樣的規定。泰和四年(1204年),“詔親軍三十五以下令習《孝經》、《論語》”。[7]
1.2 女真文閱讀的衰落
在大批女真人南遷并與漢族人雜居相處后,由于漢民族在經濟、文化上的先進性對少數民族有著極大的吸引力,因此,在女真和漢族長期接觸、互相學習的過程中,女真人學習漢語,并在風俗習慣和文化各方面的漢化也成為歷史發展的必然。早在遼代,黃龍府(吉林農安)一帶的多民族地區,漢語已成為各民族的共同語言。“凡聚會處,諸國人言語不通,則各為漢語以證,方能辨之”。[8]即使在女真的故地會寧,在世宗時期已有許多女真人不懂女真的語言文字,甚至女真的歌也不會唱了。[3]南遷到華北的猛安謀克戶和漢族雜居共處,接觸頻繁,語言的漢化更普遍。到世宗時,更有多數女真人已不能熟練地操用本民族語言了。世宗在全局上雖然重視經濟文化的發展,并取得了顯著效果,但他從女真民族性發展的角度考慮,對女真人的漢化和封建化非常不滿。他不但倡導東北女真人保持原有的古樸民風,而且對那里的農耕和狩獵經濟也非常贊賞。為了保持自己的民族性,世宗時曾有規定,“凡承襲人不識女真字者,勒令習學”。[9]大定九年(1169年),樞密使思敬上疏論五事,其中第五件是:“親王府官屬以文資官擬注,教以女真語言文字”。[10]世宗采納了這個建議。大定十四年(1174年),世宗下令:“應衛士有不閑女真語者,并勒習學,仍自后不得漢語。”[11]大定二十五年(1185年),世宗又說:“大抵習本朝語為善,不習,則淳風將棄。”[3]同一年,完顏璟(后來的章宗) 由金源郡王進封為原王,判大興府事。完顏璟入以女真語謝,世宗大喜,且為之感動,并對宰臣說:“朕嘗命諸王習本朝語,惟原王語甚習,朕甚嘉之。”[12]可見,女真貴族中普遍以漢語為交際工具,女真語已很少使用了。不過,金朝也向來把漢文和女真文學習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如宣宗和章宗在少年時就由太子侍讀完顏匡教以漢字和女真字。然而隨著漢化程度的提高,女真文讀者逐漸減少。而且,社會的發展,也對女真人的文化素質不斷提出了要求。于是,大定二十六年(1186年),親軍完顏乞奴言:“制猛安謀克皆先讀女真字經史然后承襲。”對此,世宗評論道:“但令稍通古今,則不肯為非。爾一親軍粗人,乃然言此,審其有益,何憚而不從。”[3]這里所反映的是,從一個普通女真官員到皇帝對閱讀女真文經史,提高女真官員文化素質的高度認識。
女真文閱讀一直延續到明朝前期,此后便無人可識,漸成死文字。用女真文翻譯的書籍多已失傳,今天所能見到的只是一些碑拓殘片。明永樂年間編撰的《女真譯語》集中保存了大量女真語常用詞匯、文字資料和歷史檔案,是研究女真族歷史、語言、文字、風俗、習尚等的珍貴資料,也成為認讀女真文字的一把鑰匙。
2 契丹文閱讀和契丹讀者
2.1 契丹文在金代的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
除漢文和女真文之外,女真人從建國前到金章宗明昌二年(1191年) 十二月“詔罷契丹字”,[12]普遍地使用契丹文。就是說,在金朝的大部分時間里是3種文字并行使用的。而且契丹文也是女真人最早接觸的文字之一,甚至是從接觸契丹文開始了他們的閱讀活動。“女真初無文字,及破遼,獲契丹、漢人,始通契丹、漢字,于是諸子皆學之”。[13]說明皇上的兒孫們最初都跟契丹、漢人學習契丹文和漢字,并在后來學會了女真文。
實際上,金代作為在遼代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王朝,其政治、經濟和文化是在遼代的基礎上建立和發展的,而遼文化的影響更是根深蒂固。所以在金建國后的七八十年時間里,上自皇室,下至普通女真官員,有不少人是諳熟契丹文的。就是說,他們都是多文字閱讀者。而且,金代也將漢文、女真文和契丹文作為同等重要的文字來對待。如天眷元年(1138年) 金朝廷規定:“百官誥命,女真、契丹、漢人各用本文,渤海同漢人。”[14]在金代的國史館中,契丹字也始終被使用著。正隆元年(1156年),金代對國史院書寫官的選拔要求是:“女真書寫,試以契丹字書譯成女真字,限三百字以上。契丹書寫,以熟于契丹大小字,以漢字書史譯成契丹字三百字以上,詩一首,或五言七言四韻,以契丹字出題。”[15]世宗在談到猛安、謀克承襲者時,也說到:“自今女真、契丹、漢字曾學其一者,即許承襲。”[9]而且,世宗雖然是一個極力維護女真民族傳統的皇帝,但他也頗贊許契丹字的表現力,而懷疑女真文的實際用途。他說:“契丹文字年遠,觀其所撰詩,義理深微,當時何不立契丹進士科舉。今雖立女真字科,慮女真字創制日近,義理未如漢字深奧,恐為后人議論。”[16]實際上,在女真人的閱讀方面,契丹文起了很大的作用。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它一直成為漢族文學向女真人傳播的媒介。漢文著作被翻譯或轉寫成契丹文,然后再從契丹文譯成女真文。直到明昌二年(1191年) 四月,“諭有司,自今女真字直譯為漢字,國史院專寫契丹字者罷之”。[12]十二月,“詔罷契丹字”。并且在明昌五年(1194年) 三月,“置弘文院,譯寫經書”。[17]可見,這是專門翻譯漢文為女真文的機構。
2.2 女真中的契丹文讀者
許多女真的上層官員都是契丹文的積極學習者與優秀的作者和讀者。如康宗長子宗雄,好學嗜書。一次陪皇上打獵,誤中流失,為免于罪及射者,即拔去其矢,讬疾歸家,臥兩月,因學契丹大小字,盡通之。此時金尚未滅遼,國事尤重,戎馬倥傯,宗雄能在養傷兩月內學會契丹字,并能閱讀寫作,效力于國政,可謂女真貴族中好讀勤學之士的杰出代表。其子阿鄰亦“穎悟辯敏,通女真、契丹大小字及漢字。”[18]女真中的杰出學者徒單鎰,七歲習女真字,后又在女真學者溫迪罕締達指導下,學會了契丹大小字及漢字,該習經史。完顏勗,好讀書,國人呼為秀才,能以契丹字作詩文。其子宗秀“涉獵經史,通契丹大小字”。[13]世祖之孫斡璋,多勇略,通女真、契丹、漢字。[13]此外,《金史》中所記載的通女真、契丹和漢字者還有斡論、宗憲、徒單克寧、石古乃、完顏兀不喝、紇石烈胡剌、夾谷謝奴、胡十門、布輝、孛術魯阿魯罕、夾谷查剌、溫迪罕締達等,他們都是女真中多文字閱讀的典型,反映了當時女真貴族對多文字學習的重視。
2.3 金代的契丹人讀者
在金代的讀者中,契丹人占據著相當的數量。由于他們漢化程度很深,所以他們不僅通曉契丹文也兼通漢文,甚至有些人還懂女真文。他們繼承了遼代契丹人尊孔崇儒,熱愛漢文化的傳統,讀書明志,重道尚節,以其良好的儒學修養為金代文化的發展與繁榮作出了重要貢獻。有關這些讀者的情況,史料中也有一些記載,這里略陳數例,以證之。
遼東丹王突欲七世孫移剌履,為元初著名文士耶律楚材的父親。移剌履家學淵源,博學多藝,善屬文。“世宗方興儒術,詔譯經史,擢國史院編修官,兼筆硯直長”。[19]世宗在閱讀《貞觀政要》時,曾召問移剌履為什么近世沒有出現魏征式的忠嘉之士。他說:“忠嘉之士,何代無之,但上之人用與不用耳。”章宗為金源郡王時,喜讀《春秋左氏傳》,聞移剌履博學該洽,于是召質所疑。移剌履曰:“左氏多權詐,駁而不純。《尚書》、《孟子》皆圣賢純全之道,愿留意焉。”[19]章宗很高興地采納了他的建議。大定二十六年(1186年),移剌履任翰林修撰時,向世宗表進司馬光《古文孝經指解》曰:“臣竊觀近世,皆以兵刑財賦為急,而光獨以此進其君。有天下者,取其辭施諸宇內,則元元受賜。”[19]可見,出身于書香世家的移剌履,不僅飽讀經史,深得儒學要旨,而且以自己的博學洽聞在金代的文化建設和政治舞臺上發揮了重要作用。
蕭永祺,本名蒲烈,少好學,通契丹大小字。耶律固奉詔譯書時,他被辟置門下,因盡傳其業,深通漢文典籍。耶律固死后,蕭永祺繼之撰《遼史》,作紀三十卷、志五卷、傳四十卷。移剌粘合,“契丹世襲猛安也,兄弟俱好文,幕府延致名士。初帥彭城,雷希顏在幕,楊叔能、元裕之(元好問)皆游其門,一時士望甚重”。[20]移剌慥,契丹虞呂部人,通契丹、漢字。正隆年間,掌管契丹、漢字兩司都事。
3 結語
綜上所述,女真人雖然崛起于東北的白山黑水間,并且為了突顯和保存自己的民族文化,創造了女真文,同時也在使用契丹文,但他們所閱讀的內容仍然是儒家經典,其文化源淵也與中原文化一脈相承。可見,金代的文人學士,無論是女真、契丹,還是其他民族,同中原士人一樣,飽讀儒家經典,深受漢文化熏陶,既從政治國,也為文傳道。他們都是中華民族中的杰出讀者和儒家文化的優秀傳播者。
[1](元)脫脫,等.金史 卷73完顏希尹傳[M].北京:中華書局,1975:1684.
[2](元) 脫脫,等.金史 卷99徒單鎰傳[M].北京:中華書局,1975:2185,2186.
[3](元) 脫脫,等.金史 卷8世宗 下[M].北京:中華書局,1975:184互185.
[4]張秀民.遼、金、西夏刻書簡史[J].文物,1959(3):11互16.
[5](金) 元好問.遺山先生文集 卷32博州重修學記[M].北京:商務印書館,1937:427.
[6](元) 脫脫,等.金史 卷89梁肅傳[M].北京:中華書局,1975:1984互1985.
[7](元) 脫脫,等.金史 卷12章宗 四[M].北京:中華書局,1975:270.
[8](德) 馬克思.不列顛在印度的未來結果[C]//馬克思恩格斯選集 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70.
[9](德) 馬克思,恩格斯.費爾巴哈[C]//馬克思恩格斯選集 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81.
[10](宋)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證.大金國志校證卷40[M].北京:中華書局,1986:568.
[11](元) 脫脫,等.金史 卷73宗尹傳[M].北京:中華書局,1975:1675.
[12](元) 脫脫,等.金史 卷70思敬傳[M].北京:中華書局,1975:1626.
[13](元) 脫脫,等.金史 卷7世宗 中[M].北京:中華書局,1975:161.
[14](元) 脫脫,等.金史 卷9章宗 一[M].北京:中華書局,1975:208.
[15](元) 脫脫,等.金史 卷66始祖以下諸子[M].北京:中華書局,1975:1558.
[16](元) 脫脫,等.金史 卷4熙宗 紀[M].北京:中華書局,1975:73.
[17](元) 脫脫,等.金史 卷53選舉 三[M].北京:中華書局,1975:1182.
[18](元) 脫脫,等.金史 卷51選舉 一[M].北京:中華書局,1975:1141.
[19](元) 脫脫,等.金史 卷10章宗 二[M].北京:中華書局,1975:1232.
[20](元) 脫脫,等.金史 卷73宗雄傳[M].北京:中華書局,1975:1680.
[21](元)脫脫,等.金史 卷95 移剌履傳[M].北京:中華書局,1975:2099.
[22](金) 劉祁.歸潛志 卷6[M].北京:中華書局,1983: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