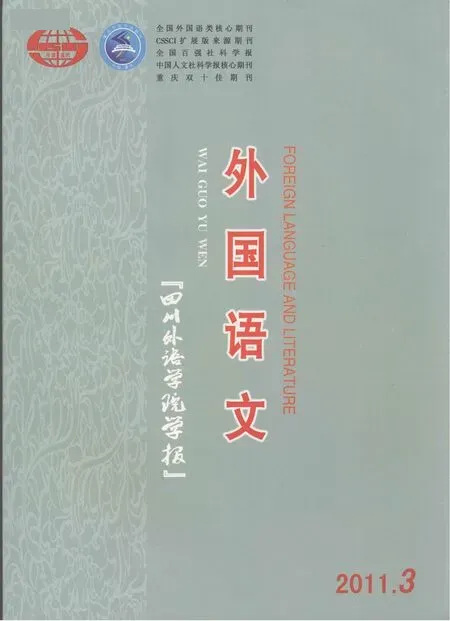論闡釋學理論和現象學意向性原則對譯者主體性發揮的啟示
廖文麗 譚 云飛
(湖南警察學院,湖南 長沙 4 10138)
1.引言
在傳統的翻譯理論中,譯者的角色和地位被定位為依附與被動的,如“譯者,舌人也”,“譯者是職業媒婆”,“譯者是戴著鐐銬的舞者”,等等。這既提出了翻譯的特點和難點,也體現了作為主體的譯者在翻譯中一直處于邊緣地位。20世紀70年代以來,西方翻譯界提出了翻譯的“文化轉向”問題,尤以蘇珊·巴斯內特(Susan Bassinet)的《翻譯、歷史與文化》(Translation,History and Culture)為代表。之后,翻譯研究從單純的語言學角度進入到語境、歷史、文化的宏觀大環境中。法國的安托瓦納·貝爾曼(Antoine Berman)在《翻譯批評論:約翰·唐》一書中指出,譯論批評必須以譯者為主體和基本出發點,并提出了“走向譯者”的口號。
現代闡釋學主張,“任何主體不是孤立的,主體既是歷史的載體,也是通往未來之橋梁,因此主體是一個綜合體,是歷史、個人和時代境域的合一”(張世英,2001)。闡釋學作為一種方法論,否認了接受主體的被動性與消極性。以此關照翻譯之主體,必然將重點落在譯者身上。隨著對翻譯理論中闡釋學的深入研究,人們也加深了對譯者主體性的肯定,譯者的主觀能動性得以強調。
現象學意向性原則注意到了意向對象不是一個被知覺的實體,而是一個在知覺方式中的“實體”,它隨著它的被意向方式而定,意識的意向性表現意識的基本性質。同樣的東西,在不同的意向中具有不同的意向對象。文學翻譯作品也是一個在知覺方式中存在的“實體”。一千位讀者,一千個哈姆雷特,同樣,一千位譯者一千個風格迥異的哈姆雷特。譯者作為整個翻譯實踐的主導因素,具有許多不依賴原文客體而存在的獨立性。他必須根據自己的主觀能動性、自身的潛能對意向對象——原文,進行創造性發揮。
2.闡釋學理論與現象學意向性原則
闡釋學(Hermeneutics)是20世紀60年代后盛行于西方分哲學和文化思潮,是一種研究意義的理解和闡釋的理論。它最初指的是探索詞句或作品文本的意義。其理論代表人物施萊爾馬赫明確了闡釋學的基本范疇:對文本的解釋和說明。他堅持在人類文化中能動的“自我”(ego)這個絕對的精神主體的創造性。闡釋學最重要的貢獻是其創造性地把理解本身作為研究對象、反思了主體對客體的認識和理解過程。海德格爾把闡釋學從方法論和認識論層次提高到了本體論性質的研究上來。赫伽達默將人的歷史性和人的理性綜合考慮,把闡釋學發展為系統的現代哲學闡釋學。西方現代闡釋學從主體參與入手,把人和現象看作是人的主體參與,經過主體投入再加以了解,這就是作為人文科學方法的闡釋學意義。現代闡釋學的建立是為了更有效地理解和解釋文學藝術作品,這與翻譯研究有著共同之處,即承擔解釋角色的譯者必須準確把握文學作品的內涵。從闡釋學入手研究翻譯自古有之。勒內(Frederick M.Rener)就認為:“從西塞羅到泰特勒,闡釋學的觀點貫穿整個西方傳統的翻譯理論,與其說翻譯是語言的操作,還不如說是闡釋翻譯的過程。”(李文革,2004:272)
現象學是關于哲學的基本思考,是20世紀最重要的哲學思潮之一。現象學這個詞有兩個組成部分:現象和邏各斯。二者都可以上溯到希臘術語:顯現者與邏各斯。意思是:顯示著自身的東西,顯現者,公開者。因此,“現象”一詞的意義就可以確定為:就其自身顯示自身者,公開者。胡塞爾(E.Edmund Husserl),20世紀現象學學派的創始人,把存在的哲學轉到認識論上來,并對意識認識論構造出方法論的端倪,以其思想活力開啟了不同于傳統哲學的某些新方法。其基本精神之一就是徹底打破傳統哲學關于主客對立的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這種形而上學是把世界分成現象界與本體界,以主客的絕對分離為前提,以現象與本質、具體與抽象、個別與一般為基本范疇。現象學探討的是呈現在意識中的世界,在這一視域中沒有脫離主體的客體,也沒有脫離客體的主體。現象學哲學關注的不是脫離了人的抽象物質世界,也不是脫離物質的抽象的精神世界,而是生活的世界才是關注的理論重點。(朱狄,1994:58)
胡塞爾的現象學是意識現象學。他認為現象就是意識中的現象。現象學是研究意義意向與意義現實之間的關系。其內涵是認識不能限于思維而要現實于直觀。但胡塞爾的意識不是人們通常理解的作為個人心理事件總和的“實在之物”的意識,而是人們的意向性的體驗,這種體驗具有對對象的指向性或意向性。意向性乃由意向行為(Noesis)和意向對象(Noema)兩個成分組成,但意識關系不是指這兩個存在著的相關部分之間的關系,而是意識行為和意識對象共同構成了意識的基本結構——意向性。因為意識的意向性構成總是有所指向,總是把自身指向某內容,因而意識總是有所意識的意識,總是在自身中帶著自己的“所意識”。
在胡塞爾看來,“意向性”是指人的主體的一種能力,這種能力能使得一切進入到人的意識中的現象能被構成為某種本質性的東西。那么,為什么“意向性”能有如此的能力呢?在具體的“意向性”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到“意向性”的能力決不是偶然的,而是有著根本的規定性。在胡塞爾看來,人類以前的知識有一個根本性的缺點,那就是將外物作為某種自明性的存在。
在現象學的意向性視野中,作為實物的對象與意向對象是嚴格區別的。例如,商人和藝術家面對同一塊木頭的時候,在不同的意向行為作用下就會形成不同的意向對象。商人可能會把這塊木頭看成能賣成多少錢的木頭,而藝術家可能將這塊木頭看成能雕刻成什么藝術品的木頭。雖然這塊木頭本是沒有任何改變,但是這塊木頭所形成的意向對象確實在變化。現象學認為,作為意識基本特性的意向性由意向行為與意向對象這一基本結構組成,意向對象不是一個實體,它隨意向行為方式的變化而變化。對此,胡塞爾提出一個著名的命題:“意識總是關于某物的意識”(1998:36)。這也意味著,意識就是意向體驗。意向性標志著所有意識的本己特性。
闡釋學理論與現象學意向性原則殊途同歸,都強調了翻譯過程中譯者的主觀能動性的發揮。
3.翻譯中譯者的主體性
目前譯者主體性成為國內外翻譯界關注的重點和研究的熱門話題之一。人們在談論翻譯主體性的時候,卻對翻譯主體這一問題認識上還存在歧義。但譯者在翻譯過程中的重要性卻是不爭的事實。作為翻譯主體及民族文化及其意象構建的參與者,譯者在翻譯過程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長期以來,譯者對原文以及原作者的忠實被視為翻譯的“金科玉律”。以原文為絕對標準,翻譯被看成是對原文的復制品,否認譯者在翻譯過程中的主觀能動性發揮的重要性。在傳統的翻譯理論中,譯者的角色和地位被定位為依附與被動的。作為翻譯活動中的一個重要主體,譯者的對象性活動的客體是原作,為把原作譯介紹為目的語讀者,就要充分發揮其能動性。譯者在進行翻譯之前,要充分調動自己的主觀能動性對原文進行認真解讀;在翻譯過程中,要充分發揮自己的文學鑒賞力和分析能力,力圖保持譯作與原作的平衡。對譯者來說,要使譯文無論在內容還是形式上都完全忠實于原文是不可能的。譯者應在理解原文內容和洞悉原文作者寫作意圖的基礎上,突破原文語言結構限制,力求找到目的語去表達原文信息的最佳形式。一名合格的譯者除了應具備一般作者所應具備的對生活的感悟外,還需要通曉兩種文字,對兩國迥然不同的文化背景與傳統有充分的了解。與作者不同,譯者翻譯時不僅要受到自身因素的制約,而且還要受到作者因素與讀者因素的共同制約,受到作者、譯者、讀者之間的時空關系因素的制約。
譯者的主體性在翻譯過程中是客觀存在的。文學翻譯是藝術的再創作。在原著面前,譯者必須發揮自身的藝術才能和主觀能動性,同時不能脫離原作。譯者是翻譯活動的主體,發揮能動性,經歷一個艱辛的過程,才能為讀者呈現出一個別樣的世界。譯者的主體性貫穿翻譯過程的始終,不僅體現在譯者對作品的理解、闡釋和語言層面上的藝術再創造,也體現在對文本的選擇、翻譯目的、翻譯策略的選擇等方面。譯者在具備相當的語言素養,文學素養和藝術素養之后,在尊重原作的基礎上,深入發掘自身主體意識能動作用和創作功能,以便譯出既對原著負責又對譯著讀者負責的文學作品。
4.闡釋學理論和意向性原則對譯者主體性發揮的啟示
闡釋學理論和意向性原則與譯者主體性發揮的啟示首先體現在譯者選材的主體性上。選材是必須既了解自己又了解作品,不善說理的人不必譯理論書,不會作詩的人千萬不要譯詩。選材之后,動筆之前,譯者應該充分了解原作者,了解其所處的時代背景、家庭背景、個人生活經歷、寫作意圖、寫作風格等。從整體上領悟原作的潛在思維邏輯,透過語言現象弄清語言形式意義的性質,從而更加準確的傳達原文信息。其次表現在翻譯創作過程中主體性的發揮。根據現代闡釋學和意向性原則的觀點,文本的意義是不確定的。一個文本完成之后,其意義取決于讀者對它的理解。這與傳統翻譯研究中追求作者原意的思想大相徑庭。譯者根據自己的理解將作品內容傳達給讀者。原作者的原意根本無處可尋,那么譯者努力忠實的便是作品本身,而并不是原作者。譯者追尋作者的本意并把作者的本意作為譯作的根本是徒勞的,也是不可能的。胡塞爾認為人類主體都有進行“意向活動”的能力并必然要求著某種意向性結論。“意向性”的第一特征是“懸擱”,即對外物的存在,擱置不進行討論,只專注于進入腦海中的各種意識現象,進而將這些意識現象在頭腦中進行各種處理以得到某種本質。這就說明譯者在翻譯過程中有很大的再創作空間,會有意無意地受自己的審美情趣、生活經驗、文化修養甚至政治態度等影響。翻譯既是一門科學又是一門藝術。翻譯既要準確地表達原文,也需要譯者在翻譯過程中體會原作者的感情,同時投入自己的感情,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向讀者傳達原文的信息。這就像人們對《紅樓夢》的解讀一樣,有的人看到的是賈寶玉與林黛玉的愛情悲劇;有的人看到的是官場上的勾心斗角;有的人看到的是官宦階級窮奢極欲的生活。以下是我國翻譯界幾位名家對莎士比亞戲劇中《王子復仇記》中哈姆雷特的一句著名臺詞的不同翻譯。
To be or not to be—that is a question.
(1)活下去還是不活,這是問題。(卞之琳譯)
(2)生或死,這就是問題所在。(王佐良譯)
(3)死還是不死,這是個問題。(許淵沖譯)
我們從這三位名家對這句名句的翻譯可以看出,如果讀者設身處地,假設自己就是哈姆雷特,他會怎么樣自問?王佐良先生的譯文,有點像哲學家的思考,其風格不太吻合舞臺劇。對比第一句和第三句翻譯,我們不難看出,他們的側重點不一樣。前者側重于活,后者側重于死;前者想活的念頭強烈點,后句想死的念頭強烈些。筆者認為,許先生的翻譯更加適合當時的語境。
最后,對翻譯方法選擇時主體性的發揮的啟示。翻譯是一種跨文化交流,從根本上說,就是向本土文化意識形態輸入異域文化意識形態。翻譯不是簡單的語言轉換,而是通過語言轉換進行文化溝通。韋努蒂(Lawrence Venuti)于1995年提出了“歸化”與“異化”的理論。前者是以目的語文化為中心,把一切不符合譯文讀者口味的異樣表達法改變成地道的目的語表達法。譯者盡可能讓讀者安居不動,而是讓翻譯作品盡量接近讀者,用目的語中富于文化色彩或內涵的意象來代替原語中特有的由于不同文化、風俗習慣、宗教、歷史、地域的差異形成的獨有意象。后者是以源語文化為中心,盡量保留原文寫作風格,使讀者感受源語語言及文化的差異。由于個人和社會因素,及長期的翻譯實踐、探索和翻譯經驗的積累,譯者會逐漸形成自己的翻譯特性和風格。譯者在特定的歷史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思想情感、審美情趣、性格氣質、翻譯水平等都會在翻譯中顯現出來。從譯者的主體性來看,譯者的修養、興趣愛好、審美等對譯作起重要作用。從而影響翻譯策略,譯者對外來文化如果采取開放態度,意在介紹外來文化,通常采取異化為主的翻譯策略。如果旨在向外傳播本民族文化,則通常采取歸化為主的翻譯策略。
5.結語
譯者的主體性在翻譯過程中是客觀存在的。文學翻譯是藝術的再創作。在原著面前,譯者必須發揮自身的藝術才能和主觀能動性,同時必須盡量忠實于原作。譯者是翻譯活動的主體,譯者發揮能動性,經歷一個艱辛的過程,方能為讀者呈現出一個別樣的世界。文學翻譯又是雙語之間的轉換,受譯者意識的影響并在意識的指導下進行。譯者在特定的歷史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思想情感、審美情趣、性格氣質、翻譯水平等都會在翻譯中顯現出來。闡釋學理論和現象學意向性原則為譯者的主體性發揮提供了哲學基礎,譯者可以充分的發揮自己的創造性。
[1]張世英.哲學導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2]李文革.西方翻譯理論流派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3]朱狄.當代西方藝術哲學[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4]胡塞爾.邏輯研究[M].倪梁康,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