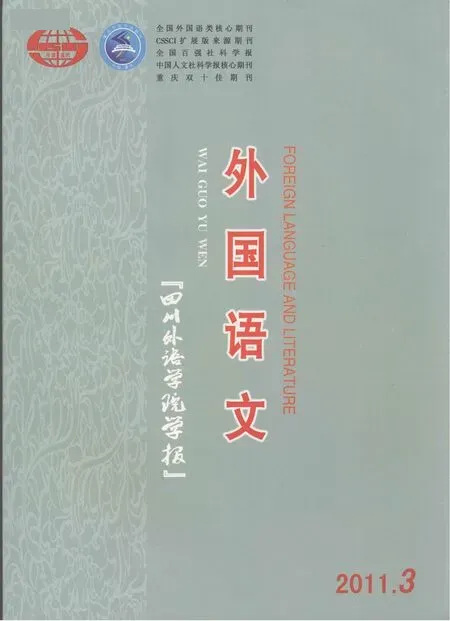轉喻的圖式及其例示的語言差異——以英漢名詞動用為例
譚業升
(上海外國語大學《外國語》編輯部,上海 200083)
1.引言
語言對比研究的基本問題是,如何將語言的多樣性與語言能力的共性聯系起來,怎樣既能夠保證不同語言有可變量從而具有個性,同時又能確保語言能力的一致性。從純語言學的角度看,這就是不變量和可變量的元語言表征的問題;從認知角度看就是要回答是否語言將我們囿于一種“世界觀”(world view)之中,或者說不同語言形成的表征是否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或者至少提供了跨越點(crossover points)。能否設想一些不變的語義特征來解釋這些相互關聯點,如果是這樣,這些特征是怎樣的,又如何來界定它們?認知語言學為我們研究這些問題提供了新的視角。它主張語言是一種創生于認知的普遍機制的屬性,與其它的認知活動(包括感知)有同種異體關系。認知語言學將語言表征和認知表征等同起來,將語言的認知表征看作是語言中的有意義的構造以及存在于這些構造的構建、功能和使用之下的認知過程;不同于將句法置于中心地位的生成語言學,它將語義等同于概念化,并放在突顯的中心位置來審視;通過具有概括性的底層的認知結構來描述一些具體概念領域的語言表征(Fuchs& Robert,1999:viii-x;8-10)。Kemmer(2008)指出,似乎存在一個人類認知概念結構的認知廣譜,從直接反映人類共有經驗的概念結構,到在一定意義上由文化特有經驗塑造的并表現出明顯的跨語言差異的概念結構。在多樣化的語言運作之上,存在著一系列具有共性的一般認知機制。對于這種共性認知機制和個性概念化之間的相互作用有待于進一步研究。本文將以名詞動用為例,以其涉及的轉喻圖式—例示關系為基礎,來對這種相互作用關系進行具體的探討,為揭示一般概念結構和語言特有概念結構的聯系,以及為探索一般認知過程(general cognitive processes)與個體語言概念化過程(language-specific conceptualization)的關系提供啟示。
2.名詞動用的認知轉喻基礎
名詞動用現象在過去的語言學研究中受到了很多關注,對于其性質和分類有了較多的了解。不過,隨著認知語言學的發展,人們對名詞動用的認知發生和理解機制產生了興趣,并取得了一定的認識。國內如高芳、徐盛桓(2000a:7-14;2000b:13-20)從關聯理論和含意本體論角度以常規關系為基礎對名詞動用理解的語用推理機制進行了探討,而劉正光(2000:335-339)則考察了名詞動用中的隱喻思維。在國外,Dirven(1999:275-288)指出,轉性(包括名詞動用)是以事件圖式為基礎的轉喻,并對轉性進行了重新分類。而Ruiz de Mendoza&Díez Velasco(2001:321-357)則將名動轉用定性為一種再范疇化,稱其為語法轉喻。他們都認為,名動轉用的認知基礎是轉喻。從認知語言學的視角看,轉喻并不僅僅是語言表達的替換,而是激活一個概念框架——不同的稱謂有理想認知模式(ICM)、圖式、場景(scenario)、腳本(script)等——的認知過程。Radden&K9vecses(1999:21)給轉喻下的定義是:轉喻是經由一個概念實體(載體)通達同一理想認知模式下的另一個概念實體(目標體)的認知過程。即載體為目標體提供了心理可及性。名詞動用中所涉及的轉喻大多以行為場景為基礎,是場景的組成要素與場景事件的動作行為間的激活關系。場景中的“動作對象”(如放置的物體)、位置、延續時間、施事、體驗者、目的、材料來源、工具等,因為與事件行為本身的規約化聯系①這種聯系也就是高芳、徐盛桓(2000a、b)所說的常規關系。,可以激活動作行為本身。與此種轉喻認知過程相伴隨的語言過程是語言載體即原生名詞的再范疇化,從而產生了Clark&Clark(1979)所列出的九大類名源動詞。轉喻是一種普遍的認知方式,一種一般的認知過程,它是我們古、現代漢語,英語以及其它語言中存在名詞動用的認知基礎。
劉正光(2000:335-339)詳細探討了名詞動用過程中的隱喻過程。我們認為,名詞動用的認知本質是轉喻,而隱喻則是在轉喻過程中附帶的次要認知過程。名詞動用的發生,可以是先轉喻再隱喻,也可以先隱喻再轉喻。請看以下各例:
(1)事情想蓋也蓋不住。
(2)他貓下身子,藏在土墻后面
(3)他在屋角猴著。
(4)母親都寶貝自己的兒子。
(5)他秧了一池魚。(選自劉正光,2000;竟成,1985)
在例(1)中,從歷時的角度看,“蓋”首先從名詞經轉喻變為動詞,即其對應的概念在行為圖式中,從指稱“動作行為使用的工具”經轉喻而激活“動作行為”概念,然后再在此基礎上形成隱喻轉換(“蓋”住抽象的事物)。在例(2)和例(3)中,貓和猴的某種形體特征先隱喻為“人”的形體特征,然后再經轉喻指稱與這種身體形態相關聯的動作行為。例(4)和例(5)中的“寶貝”和“秧”都是無生命的,但是經過隱喻來分別說明生命體的特征,然后再經過轉喻,用來指稱形成這些特征的行為。在這些例子中,與名詞動用再范疇化直接相關的都是轉喻過程。
3.轉喻的圖式——例示與英漢名詞動用的差異
Finley(2003)在論述名源動詞的產生和理解機制時指出,名源動詞的派生大致可以分為兩類:規則派生(rule derivation)和個體派生(individual derivation)。下面我們將分別探討它們與轉喻的聯系。
Finley(2003)認為,規則派生的名源動詞,其原生名詞隸屬相同語義范疇,可以按照一定的規則派生具有某種解釋或意義的動詞。如隸屬工具、處所、方式、結果范疇的原生名詞,可以系統性的再范疇化為動詞。
我們認為,這里的“規則派生”,有著強制性意味,是不太準確的說法,因為并不存在一般情況下要遵守的所謂“規則”,轉用與不轉用較大程度上取決于言語使用者的選擇,在一般情況下都有替換表達法。
Langacker(1997)指出,規則不能被看作是建構句子或從底層結構推導句子的包含一系列步驟的指令。認知語法的規則只能是從實際使用的構成言語使用事件的形式和意義中通過抽象而產生。規則是圖式模板,其中包含著在一些列表達中觀察到的有關它們結構的各個方面的共性。語法規則,是對象征復雜的表達(可以分解為更小的符號組件)的圖式化。在性質上看,這些規則(構式圖式)是直接與它們圖式化的表達平行的,只是在具體化程度上不同而已。Langacker提倡的以使用為基礎的語言觀或語言模式(usage based model)具有三個特征:語言知識與語言使用(說和理解語言)相關聯;語言系統具有動態性、語境適應性和社會交互性;語境影響言語使用事件(usage event),復現的言語使用事件又會影響語言系統。在語言系統網絡中,圖式、例示和言語使用事件三個層次交互作用。
語言知識是以實際使用為基礎的,是使用事件的概括性知識。語言知識(具體包括音系結構知識、語義結構知識和符號結構知識)可能是非常具體的低層次的知識,也可以是比所遇到的表達更抽象的、甚至是抽象得很遠的知識,記憶中有抽象圖式,也有具體的例示和例子,其中一部分知識之間會形成一個“圖式—例示”的級階。

名詞動用的派生規則其實質是產生轉喻的認知圖式,如工具—行為;處所—行為;結果—行為;方式—行為圖式等。轉喻作為一種基本的認知方式適用于任何經驗域,并且在具體概念的創生過程中起著基本作用。就具體的名詞動用個例而言,其所包含的具體轉喻過程是轉喻認知圖式的例示,而所謂“規則”應用也就是例示的過程。
語言使用者有關名詞動用的語言知識會涉及到轉喻的“圖式—例示”級階,在此可以借用Blank的轉喻類型圖來簡單描繪:

該圖的第一層提供了轉喻鄰接關系的兩個總的框架,第二層和第三層的關系就是潛在的產生轉喻的鄰接關系與實現了的具體轉喻之間的例示關系①當然,我們還可以假設,鄰接關系本身也存在不同的抽象等級(或曰上下義范疇等級),彼此間也是一種例示關系。。一個概念框架中不是所有的鄰接關系都能實現為具體轉喻,換句話說,在一個具體情景中,什么樣的鄰接關系用來激活一個大的概念框架取決于主體的識解。某類鄰接關系能否通過名詞動用的語言形式來實現為具體的轉喻,取決于識解的過程和條件。因此,比“規則派生”更準確的說法應該是,存在促使名詞系統性地派生動詞的轉喻認知圖式。
以圖式—例示級階為基礎探討語言的差異可以從兩方面考察:一是例示的種類差異,二是例示的頻率差異。一般說來,某圖式的例示種類多,例示頻率高,則說明此圖式的固化程度高,例示能力強,而例示的種類少且頻率低,則反映此圖式的固化程度低,例示能力弱。轉喻認知圖式在不同語言中的例示在兩方面都有可能表現出不同。
3.1 名詞動用的規則派生與轉喻圖式—例示級階
某些以轉喻為基礎的名詞動用在英漢兩種語言中表現出系統的差異。在英語中,名詞以轉喻圖式為基礎派生動詞的能力較強。如以“工具/方式—行為”轉喻圖式為基礎派生動詞的名詞,其范疇下還可以劃分出一定數量的小名詞類,如交通工具類、舞蹈類和佐料類。換句話說,“工具/方式—行為”轉喻圖式在英語中存在這三類不同的例示,例如:
(6)the cargo is trucked across the country(boat,truck等交通工具,用作動詞時具有travel by X的動詞義)
(7)the chef peppered the onions[作料用作動詞時具有add X to(給……添加佐料)的意義]
(8)We discoed/waltzed/tangoed/polkaed the night away[舞蹈名稱詞用作動詞時具有dance X(跳……舞)的意義]
而進入這些不同類范疇的新名詞也都有轉用作動詞的能力,如:交通類里新出現的交通工具Megalev(磁懸浮列車),剛流行的舞蹈(hip-hop)和印度佐料等。
相反,以上幾類名詞在現代漢語中一般不轉用作動詞,也就是說以上述三種方式例示“工具/方式—行為”轉喻圖式的能力很弱。例如:
(9)我從市區摩托車到浦東機場。
(10)我從市區磁懸浮到浦東機場。
如果沒有突顯自己的交通工具的意圖的話,一般不會使用以上的用法,這也可以從例(10)的可接受性高于例(9)看出,因為磁懸浮作為新生事物,目前來說的確是應該突顯的交通工具。需要注意的是,在古代漢語里,交通工具范疇的名詞可以派生動詞,但是在現代漢語里很少用,即頻率低。
以下是幾種在英語中例示能力較強而在現代漢語中例示能力較弱或缺失的轉喻圖式:
A.“有機體的一部分”直接轉喻“這一部分的去除行為”
在英語中這是一個例示能力很強的轉喻圖式,如:fin the shark、get the fin out of the shark、peel the apple、skin the cow,類似的形式還有skin the rabbit、feather the goose、shell the peanut、scale the fish、bark the tree、gill the fish、core the pear、milk the cow等(Clark&Clark 1979:772-774),在漢語中,這種轉喻圖式幾乎不能例示。在這里,奶/milk提供了一個很好的例證。
milk的意義比較含糊,可以說是有機體的一部分,也可以說是某一器官的產物。在milk the cow中,取前面的意思(get milk from the cow),在 milk the baby中,取后面的意思(give milk to the baby)。而有意思的是,在漢語中,我們可以說奶孩子(雖然也比較少用)但不可以說“奶奶牛”。因為“有機體的一部分”直接轉喻“這一部分的去除行為”這一轉喻圖式無法在漢語中得到例示。
B.“覆蓋或容納物”轉喻“致使物體被覆蓋或容納的行為”
在英語中這也是一種例示能力很強的通用轉喻認知圖式,如:nest the bird、blanket the bed、kennel the dog、sheet the furniture、oil-cloth the table、salt the meat、butter the bread、wallpaper the wall(Clark&Clark,1979:769-781)Anna、holster your weapon!(選自美國電視劇 Lost第二季),bottle some milk、garage the car、grease the bread、to porch the newspaper。
相反,在漢語中該轉喻圖式的例示能力較弱,以上諸例在漢語中都無對應表達。我們能找到的例子有限,且都已習慣化。如:把菜棚一下;棚一下芹菜,別讓它們給凍了;蓋一下咸菜缸等。
C.身體的器官轉喻身體器官的典型功能行為
英漢兩種語言在這一轉喻圖式的例示上也表現出較大的差異。如:
Mouth:the spokesman mouthed his words carefully.這位發言人說話字斟句酌。
Stop mouthing your words and speak up.別憋著嗓子說話,大聲講出來吧。
Eye:eye sb jealously
Nose:nose the smell of the shoes
Hand:Hand me the book
Foot:the students footed the whole 37 miles
Tiptoe:to tiptoe into the room LIP MANNER FOR ACTION
Lip:□a hand that kings have lipped(Shakespeare,Ant& cleop II:V)
Chest:Ian swiftly chested the ball.①此例選自 Ruiz de Mendoza Ibá1ez & Díez Velasco,2001。他們認為,chest名詞動用是因為在“行為”理想認知模式(action ICM)中發生轉喻,即用工具轉喻使用工具的行為“Instrument for action”,我們認為,這種說法不太確切,更準確更好的描述應該是:這里是用身體的部位來轉喻身體的功能行為,即“body part for body action”,因為在解讀時,我們要聯系足球運動中的身體各部分的功能,如腳、手、頭等的接球功能,而不是把它們當成工具(像球拍)一樣。而其相應的理想認知模式應該是BODY ICM+ACTION ICM.
在以上名動轉用的各例中,身體的器官均被用來激活身體器官的典型功能行為,即發生了轉喻。在漢語中,以上諸例均無對應用法。
3.2 構式脅迫產生名詞動用:轉喻圖式的特殊例示
Finley(2003)指出,個體派生是指在驅動力合適的情況下產生名源動詞,這些情況包括句法環境、詞匯短缺、表達的經濟性、概念的突顯度等。Finley(2003)在談到個體派生時,舉了一個例子,就體現了這種特點。語境是兩人在下雪天大雪覆蓋的街上走著,看到一輛倒霉的轎車,轎車上沒有雪,卻滿是匹薩。于是有一個人就說:
(11)Instead of getting snowed on that car got pizzaed on.
Pizza這個詞一般情況下是不能用作動詞的。
我們認為,一些名源動詞的個體派生與構式脅迫產生的轉喻(constructionally coerced metonymies)有關。構式脅迫產生轉喻是指語法構式可以脅迫詞匯表達作轉喻解釋。當進入一個句子的某種語言形式與句子中的另外一個形式產生沖突時,它就會改變自身特征以適應其它的形式(Panther&Thorburg,2004)。當語法構式產生合適的驅動力時,語法轉喻就有可能會發生。之所以說“有可能”,是因為往往要附加其它的條件,如詞匯短缺、表達的經濟性、概念的突顯度等。
在這里具備了經構式脅迫形成語法轉喻的條件。“Instead of getting snowed on”觸發的對比構式,脅迫“pizza”改變常規的使用形式,構成一個與其對稱的結構,這樣表達具有經濟性,再加上pizza概念在這個場景中處于突顯的地位,從而促使其在此處發生再范疇化,也即語法轉喻。這個例子體現的是構式脅迫情況下發生的“覆蓋物轉喻致使物體被覆蓋的行為”轉喻圖式的特殊例示。由于語法構式的規約性,這種特殊例示本身就有語言差異性。
漢語中存在幾種促生名詞動用的特殊句法結構,如:
A.怎么(就)+名詞+了。例如:
(12)大炮怎么啞巴了(竟成)。
B.已經+名詞+了。例如:
(13)回來的時候已經大喇叭口了(劉正光)。
(14)已經瘸腿了。
C.也+名詞+了+動量詞。例如:
(15)我也雷鋒了一回(次)。讓我也雷鋒一回(次)吧!
(16)我也大款了一次。
這些結構都帶有從無到有的動態變化意義。進入這種結構的名詞表達的一般是在某一場景中比較突顯或出乎意料的概念,體現的事物或人物一般具有顯著的或者讓人吃驚的特征。由于此構式意義與轉喻核心原則相符合,因此這些構式容易脅迫產生名詞動用,此類語法再范疇化一般都涉及到結果—行為(RESULT FOR ACTION)轉喻,具體來說,它們都是“變化結果轉喻變化行為”的特殊例示。
名詞動用“規則派生”和“個體派生”并無本質的區別,從認知本質上看,都是轉喻圖式的語言例示,只不過后者的發生具有更大的不確定性,需要特定的語法構式和較多的限定條件。
3.3 名詞動用轉喻圖式例示的規約制約
轉喻作為一般認知過程,在參與具體語言識解的過程中,不是毫無限制,而是會受到不同因素的制約,這些制約因素主要來源于規約、語境和人類認知系統的性質(Croft&Cruse:101-104)。轉喻認知圖式只是提供了識解的路徑,而具體的例示有限定條件。本節將側重探討規約的制約。前人提出了若干制約原則,如同義異形詞優先抑制原則(Finley,2003),即如果詞匯中存在了同義異形的動詞,則不能派生相關的名源動詞,比如airplane受fly的優先抑制,而 hospital受 hospitalize的優先抑制。是這屬于詞法規約限制范疇的原則。筆者(2008)指出了現代漢語名詞動用的語法規約限制原則:漢語名源動詞附帶的意義有結果、方式、工具等,可以用固定的語法構式(如動補構式和把字句式)來表達。英語中名詞動用能產性排在前面的置位動詞(如holster your weapon)和置體動詞(如saddle the horse),它們都例示了“覆蓋或容納物轉喻致使物體被覆蓋或容納的行為”的轉喻認知圖式。顯然,在表達相同的“置位”和“置體”概念時,可以很容易的套用“把”字句格式和動補結構(如:把槍收起來,把槍收回槍套里,給馬套上馬鞍,把馬鞍套在馬背上)。而由于這些結構的語義指向靈活,降低了名詞動用的必要性。這可以稱作構式優先抑制原則(Construction Pre-emption Convention)。
由于制約的因素不同,且某種因素制約的程度不同,英漢名詞動用轉喻圖式的例示在種類和頻率上都表現出較大的差異,這從以上小節論述中可以看出。有關頻率分布差異,筆者(2008)還曾根據Chan和 Tai(1995:49-74)的調查以及 Kiparsky(1997)的不完全統計在總量上作了比較,指出英語名詞動用數量遠高于漢語。筆者還指出,現代漢語的名詞動用較古代漢語減少主要歸因于動補結構的形成,即構式優先抑制原則的作用。
4.結語
王黎(2005:2-5)假設了語言表達者的概念化從感知世界到語言表達所經歷的四個階段:(1)客觀存在的事件通過感覺器官感知而形成認知圖式;(2)認知圖式投射到人類語言層面形成意義框架;(3)意義框架投射到一個具體語言(如漢語)而形成構式。(4)根據構式意義的需要在詞庫中物色具體詞語。第2、3階段也就是適應語言文化規約的具體概念化階段。而從基于類似感知經驗的一般認知圖式如何投射到具體語言層面的過程,也就是具有共性的一般認知過程參與個體語言概念化的過程,對此,我們還知之甚少,是語言對比研究應該迫切關注的問題。
本文以名詞動用為例,以轉喻的圖式—例示關系為基礎,探討了作為一般認知過程的轉喻及其一般通用圖式如何在兩種語言的具體語言表達中例示,又如何在種類和頻率上體現了差異。這一研究表明,“圖式—例示”級階可以在一定程度和范圍內幫助我們在語言對比研究中揭示一般認知過程和具體語言概念化過程的聯系。當然,此級階并不是“聯系”的全部內容,“聯系”的豐富內涵還需要我們通過更多的探索來揭示。
[1]Chan,Marjorie K.M.and James H-Y.Tai:From nouns to verbs:verbalization in Chinese dialects and East Asian languages[C]//Camacho,Jose and Lina Choueiri.Sixth North American Conference on Chinese Linguistic.NACCL 6,(two volumes).CA:GSIL Publications,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Los Angeles,1994:49 -74.
[2]Clark,E.V.& H.H.Clark.When Nouns Surface as Verbs[J].Language,1979(4):767 -811.
[3]Croft,W.& D.Alan Cruse.Cognitive Linguistics[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Reprinted by 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6:101 -104.
[4]Finley,Sara.A lexical Access Account of Denominal verbs[J/OL].University of California,Santa Cruz Honors Thesis,2003(B.A.).(Downloadable from http://www.cog.jhu.edu/grad-students/finley/thesis2.doc).
[5]Fuchs,Catherine & Stéphane Robert.Language Diversity and Cognitive Representations[C].Amsterdam/Philadelphia,1999.
[6]Kiparsky,Paul.Remarks on denominal Verbs[J/OL].http://www.standford.edu/~ bclevin/ISA05evstr.pdf)Alex Alsina,J.Bresnan and P.Sells,Argument Structure[C].Stanford:CSLI,1997.
[7]Langacker,R.W.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Vol1.Theoretical prerequisites;Vol.2Descriptive Applications[M].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1991.
[8]Langacker,Ronald W.The Contextual Basis of Cognitive Semantics[C]//Jan Nuyts and Eric Pederson.Language and Conceptualiza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
[9]Panther,Klaus-Uwe & Linda L.Thornburg.The Role of Conceptual Metonymy in Meaning Construction[J].Metaphorik.de,2004(6):1 -26.
[10]Dirven,Rene.Conversion as a Conceptual Metonymy of Event Schemata[C]//Panther,K and G.Radden.Metonymy in Language and Thought.Amsterdam/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1999:275-287.
[11]Ruiz de Mendoza Ibá1ez,F.J.& Olga Isabel Díez Velasco.High-level Metonymy and Linguistic Structure[J].Sincronía Oto1o,2001.
[12]Radden,G.& Kovecses,Z.Toward a Theory of Metonymy[C]//Panther,K and G.Radden.Metonymy in Language and Thought.Amsterdam/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1999:17-59.
[13]高芳,徐盛桓.名動轉用與語用推理[J].外國語,2000a(2):7-14.
[14]高芳,徐盛桓.名動轉用語用推理的認知策略[J].外語與外語教學,2000b(4):13-20.
[15]竟成.現代漢語里的名詞動用[J].語言教學與研究,1985(1):69-74.
[16]劉正光.名詞動用過程中的隱喻思維[J].外語教學與研究,2000,32(5):335 -339.
[17]譚業升.現代漢語名詞動用的特征及其認知闡釋[C]//語言研究的語用與認知視角(賀徐盛桓先生70華誕).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8.
[18]王黎.關于構式和詞語的多功能性[J].外國語,2005(4):2-5.
[19]周領順.英漢名動轉類詞對比研究[J].外語教學與研究,2000(5):340-3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