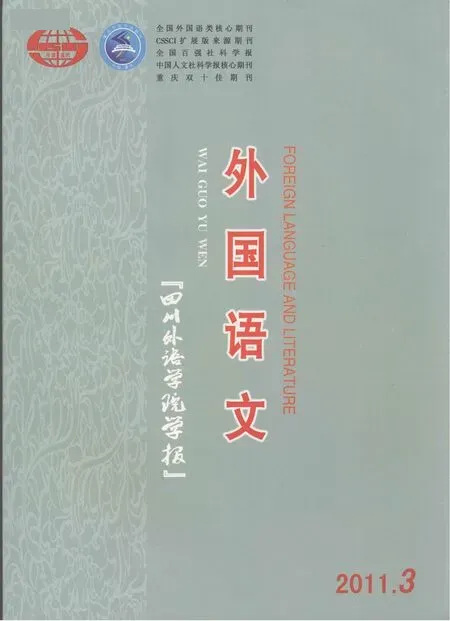文化全球化語境下華裔美國文學的漢譯:以翻譯倫理為視角
周文革 楊 琦
(湖南科技大學 外國語學院,湖南 湘潭 411201)
1.引言
華裔美國文學在經歷了從被忽略到被廣泛關注,從邊緣化到逐漸步入主流的近20年發展歷程之后,已經成為美國文壇的一道靚麗的風景線。雖然國內諸多學者將目光聚焦在華裔美國作家創作中的東方主義或自我殖民傾向等方面的研究,但在經濟、文化全球化的時代背景下,華裔美國文學仍然是中美文化交流的良好平臺以及西方讀者了解東方、了解中國的便捷渠道之一。同時,相對于許多華裔美國作品在美國成為廣大讀者炙手可熱的讀本及少數作品已成為文學經典并選作大學、高中教材而被廣泛閱讀和學習的事實,其在中國的譯介卻遠不盡如人意。本文將從翻譯倫理的角度,重新審視中國譯者在文化全球化語境下所具備的文化身份,并進一步探究在譯介華裔美國文學作品這一“最熟悉的陌生人”時應采取的翻譯策略及方法,以期更好地完成譯者跨文化交流的使命。
2.文化全球化語境與翻譯
全球化是指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全球聯系不斷擴張,人類生活在全球范圍的基礎上不斷發展及全球意識的崛起,同時也是人類社會在更廣闊的范圍內溝通、聯系和相互影響的歷史進程。盡管目前對“全球化”沒有統一的定論,但它卻客觀存在著,并從經濟領域不斷擴展到社會文化領域,成為當今時代的基本特征。全球化在文化領域的重要表現就是各民族文化通過世界性的交流,打破了原來閉關自守的狹隘界限走向開放和多元,形成一種“世界文化”的新格局。[1]換句話說,世界文化或全球性文化是由各民族文化相互交流、對話及相互融合而形成,同時也寓于不同民族文化的個性之中,且通過民族文化表現出來。由此看來,隨著信息和網絡技術的進一步發展,文化全球化以不可阻擋的勢頭為各民族語言文化的交流提供了更為廣闊而合理的對話空間。而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使得翻譯這一跨文化交際活動成為必然。翻譯以文化媒人的身份在各民族文化對話及交流中起著不可或缺的中介作用,適當的翻譯策略和方法正在某種程度上加速或改變著文化全球化的進程。
由于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也隨之帶來了文化上的失衡,文化全球化也曾一度被誤認為“西化”或“美國化”,經濟力量強盛的西方或美國文化以絕對優勢成為全球主流文化的代言人,從而使得文化全球化與民族文化之間不可避免發生沖突。如今,隨著一些曾被冠以“不發達”或“第三世界”之名的國家不斷在全球化進程中嶄露未來全球霸主之勢,在中國人熱力追捧好萊塢電影,吃著洋快餐,努力學習英語的同時,越來越多的孔子學院、太極拳、京劇以及風靡紐約街頭的西安肉夾饃等都已成為西方人所熱衷的中國或東方元素。這一切都無疑驗證了一個事實:那就是文化全球化這一幽靈般且客觀存在的歷史進程,不是西方文化炫麗獨舞或領舞的舞臺,而是世界各民族文化在文化全球化進程中重新組合及構建,形成新的世界文化體系的過程。因此作為實現中西文化對話,促進其交融溝通的媒介,中國翻譯應如何順應文化全球化的世界潮流,在避免陷入狹隘的民族主義的同時又能實現中西跨文化交流,都是文化全球化語境下翻譯研究應該予以重點探討的問題。
3.文化全球化與華裔美國文學的漢譯
不斷加速的全球化進程推動了不同文化間交流理解的必要,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多元文化文學的出現不僅有助于跨文化間交流,也為各種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提供一個良好的機會去驗證文化知識、觀點及差異的表達。華裔美國文學就是這樣一類幫助西方人了解中國文化及美國族裔文化的多元文化文學文本。在多元文化主義興起與全球化浪潮并存的美國,作為冷戰后的唯一超級大國,為扮演一個世界領導者且在國際經濟與政治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它堅持認為自己應該熟知其他各國,尤其是非西方國家或“第三世界”的文化。[2]對于華裔美國文學來說,華裔作家在其流散及跨文化經歷和二手接受中國文化的背景下,用西方人熟悉但卻夾雜著漢語元素的英語講述著自己清晰又模糊的故國記憶,其中不乏對中國傳統及神話、典故、習俗等文化元素的改寫與重構,最具代表性的作品當屬湯亭亭的《女勇士》。對于美國人甚至多數西方人來說,即使這些包含多元文化的華裔美國文學文本不能成為了解中國文化可靠的資源,但它仍是美國或西方主流社會接觸并獲知中國文化的捷徑,也實現了文化全球化語境下中西文化的相互作用與對話,華裔作家將漢語與英語以及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適度雜合與改編不僅為美國華裔找到了在美國主流社會其族裔身份認同的途徑,更是為中西文化之間,美國或西方文化與華裔美國文化之間的融合找到了契合點。
然而,正是這些在整個美國乃至西方文學界大受追捧的華裔美國文學且承載者無數華裔作家故國夢的多元文化文學文本,給中國譯者帶來了巨大挑戰和不少棘手的問題。在一般的跨文化翻譯活動中,原語文化中的特有詞匯與表達是其文化的載體,也無疑是很難被譯介到其他文化。而要將華裔美國文學中中國特有的文化意象翻譯成漢語,看似只是簡單的歸化或找到對應項的過程,實則極為困難。與以往在翻譯西方異域文本時帶給中國譯者或多或少的文化入侵的經歷不同的是,中國譯者在翻譯美國文學分支的華裔美國文學作品時,一種熟悉或親近感撲面而來,尤其是當遇到似曾相識的中國姓氏、傳統思想、習俗及表達時,中國譯者往往為了避免與國內對應的文化意象產生偏差而有意將其歸化,甚至為了保持“中國文化”的純潔且避免引起國內讀者的困惑,有些譯者省略了原文中他們認為對中國文化的虛假描寫或用其他的元素來替代。
其中,《女勇士》的譯者還在某些章節或句后加上了表達自己觀點的旁批,諸如“性品難移,煞費苦心”、“家散人亡,顧什么面子,講什么意思”等一類漢語中常用的對仗,及“月老注定,千里姻緣一線牽”、“一朝被蛇咬,三年怕井繩”等一類俗語;[3]我們姑且先撇開這些旁批表達是否準確不談,這些半古半文的表達就讓讀者產生不知所云的困惑。這本漓江出版社的中譯本1998年才出現在中國大陸,那時的中國早已借著改革開放的春風大力發展市場經濟,與世界經濟文化的密切聯系也讓中國讀者更青睞于接受異域文學或文化以豐富生活。而中國譯者此時的簡單歸化、省略抑或是不知所云的增補最終導致了《女勇士》乃至整個華裔美國文學的漢譯不盡如人意。在今天文化全球化語境下,在面對華裔美國文學的漢譯這一跨文化交流過程中出現的偏差,我們在批評中國譯者對中國文化、美國文化、甚至華裔美國文化了解多少的同時,也更應審視該漢英翻譯背后隱藏的深層問題。
4.全球化時代下譯者的翻譯倫理
所有的交際互動行為都建立在一定的價值觀、道德觀和倫理的基石上,翻譯實踐作為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也不例外,其跨文化、跨語符、跨空間的特性呼吁倫理層面的思考。無論從中國的“信、達、雅”到“神似”與“化境”等傳統譯論,還是從西方的結構主義到解構主義翻譯理論,這些翻譯理論或思想紛紛為譯者到底應該如何翻譯獻計獻策,但譯界真正將“應該怎么翻譯”這一命題置于倫理學的視野下展開研究則是始于20世紀80年代初。
第一個提出翻譯倫理這一說法的是法國當代翻譯理論家安托瓦納·貝爾曼,他認為易助長西方的文化霸權并具有“我族中心主義傾向”的“歸化”譯法,忽略了“源語文字”的含義而只注重“源語文本意義”的傳達。[4]他主張的翻譯倫理是尊重原作、尊重原語及其文化差異,翻譯的最終目標是要通過對“外來元素”的傳介來豐富本族文化。韋努蒂也在貝爾曼思想的基礎上進一步強調,翻譯要堅持“異化”而不是“通順”,要保留并突出原語文本的“異質”,因此他在更加強調翻譯活動中社會和政治因素的基礎上提出了“差異倫理”,即抵抗式的翻譯觀,以抵抗西方發達國家的文化霸權。如果說前面兩位學者討論的翻譯倫理的重點還停留在翻譯的“歸化”和“異化”的技術層面,皮姆的重點則更多體現在“譯者倫理”上,即翻譯倫理應先解決譯者應該翻譯的必然性以及為誰而翻譯等一系列關乎譯者職業性倫理方面的問題,應該如何翻譯以及怎樣才能翻譯好等問題便能迎刃而解。[5]在此,三位學者的翻譯倫理哪一個更為全面已經不是重點,關鍵是他們都將翻譯實踐上升到倫理層面,譯者的翻譯行為也成為更高的倫理選擇,而“差異”或“異質”是他們關注的共同焦點,這使得在全球化的今天,翻譯倫理,即譯者在各種政治、意識形態及贊助人等因素影響下該如何翻譯,該怎樣面對和處理“差異”、“他者”,成為譯者乃至整個翻譯界討論的熱點。
在當今高度文化全球化的語境下,各民族不同文化通過不斷地交流與對話相互依存,相互影響,文化的世界性寄居并受其民族性的影響,每一種文化在渴望被其他民族文化認同和接受的同時也保留其個性。處在個性與共性并存且競爭的復雜背景下,欲實現文化間的真正交流和理解,譯者在面對差異時所做出的倫理選擇應該是求同存異,即一方面尋求或認同異域文本中與本土文化及價值觀相同之處,借助他人文本實現自身價值,另一方面也要尊重并傳達異域文本中特有的文化價值觀。
5.翻譯倫理對華裔美國文學翻譯策略的啟示
文化全球化帶來更多的是不同文化間相互理解和融合而不是沖突,華裔美國文學這類多元文化文學文本正是這種跨文化交流的縮影,也使美國及西方讀者更多地了解中國文化,尤其是美國華裔文化。盡管美國人所倡導的文化多元主義不過是用來裝點美國主流文化,但我們不能否認此舉為美國社會了解多元文化之聲提供便利之余,也為少數族裔文化提供了相對自由的平臺展示其差異性。由于鼓勵和支持華裔美國文學的民族主義不是中國而是美國華裔,并且許多華裔美國作家致力于構建的是既有別于美國主流社會又能與主流社會平等共處的華裔族性,在東方主義的縫隙中開拓出屬于美國華裔自己的生存空間,所以翻譯華裔美國文學文本不是中國文化的回歸故國,而是第二次跨文化交流,只不過這次中國譯者面對的是華裔美國文化與中國文化之間的碰撞與交流。
由于在中國國內沒有華裔族群可以認同,通過簡單的歸化為其尋根不僅違背了原文作者塑造華裔族群身份的初衷,反而會陷入極端的民族主義,讓這些美國華裔無處安身。另一方面,雖然美國華裔文化在美國甚至是西方社會處于邊緣地帶,但是它仍是滋生于美國文化的一個分支,它在眾多華裔美國文學作品中雖與中國傳統文化息息相關卻也不盡相同,相對于中國文化仍是較為強勢的文化。如果我們過分地異化,雖然能夠抵制所謂強勢文化的霸權對中國文化的侵蝕,但華裔美國作品將無異于美國文學,其原文字里行間中所致力于展現的華裔與美國主流社會的差異將蕩然無存,這也有悖譯者最起碼的忠實倫理。由此看來,華裔美國文學的翻譯策略已不是簡單的語言學或翻譯技巧,而是具有顛覆性的政治文化策略,是譯者在全球化語境下的倫理選擇。
所以,在文化全球化滲入人類生活方方面面的今天,過度的歸化或異化都難以完成復雜的跨文化交流的使命。面對華裔美國文學這一語言文化高度雜合的多元文化文本,中國譯者應該在差異性倫理的指導下,尊重差異,應用適度雜合的異化和歸化的翻譯方法,在承認華裔美國文化與中國文化共性的同時又能保存二者的差異,使國內讀者真切感受美國華裔與祖國之間剪不斷的血脈聯系的同時又能形成對這一特殊人群的尊重與認同,從而真正實現華裔美國文化、中國文化及美國文化在更廣闊意義上的對話與交融。
6.結語
文化全球化語境對華裔美國文學的漢譯提出了更高要求,不是簡單的歸化或者異化就能實現華裔美國文化與中國文化,甚至與美國文化間的交互與共存。在面對華裔美國文學所呈現出來的熟悉卻又陌生的多元文化文本,中國譯者只有遵循差異性倫理,適度雜合歸化與異化兩種翻譯策略,求同存異,才能更好地完成跨文化交流這一歷史使命,才能為美國華裔族群尋到真正的根。
[1]張柏然.全球化語境下的翻譯理論研究[J].中國翻譯,2002(1):58-59.
[2]Zhao,Wenshu.Positioning Contemporary 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in Contested Terrains[C].Nanjing:Nanjing U-niversity Press,2004.
[3]湯亭亭.女勇士[Z].李建波、陸承毅,譯.桂林:漓江出版社,1998.
[4]崔衛.也談全球化時代的翻譯倫理[J].思考與言說,2010(7):168-169.
[5]駱賢鳳.中西翻譯倫理研究述評[J].中國翻譯,2009(3):1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