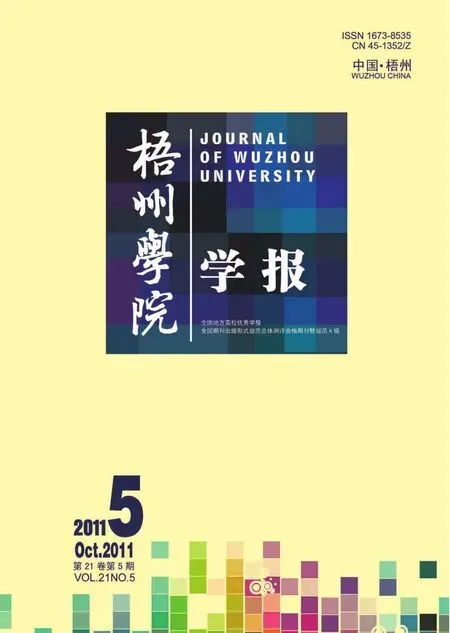淺議黨校研討課教學中教師的角色扮演與轉換
馬德翠
(中共廣西區委黨校,廣西 南寧 530023)
淺議黨校研討課教學中教師的角色扮演與轉換
馬德翠
(中共廣西區委黨校,廣西 南寧 530023)
由于生源構成的復雜性,黨校在開展研討課上具備得天獨厚的條件,其中教師的角色尤為關鍵。本文探討了研討課在黨校的地位和作用,并通過具體的案例,細致地分析了教師在研討課中所扮演的諸種角色,并就教師如何實現角色轉換提出了若干建議。
研討課;教學方法;角色;轉換
研討課(seminar)作為一種教學方式,最早起源于德國,德國高校于18世紀開始推行這種教學模式,隨后紛紛為歐美高校所仿效,逐漸占據了歐美大學課堂上的中心地位。它主要采取分組討論的方式來促進學生主動學習,即將學生分為幾個小組,就某一個確定的議題進行資料搜集、分析和研討,小組成員之間討論完畢后再進行全班交流,由每個小組推舉代表在課堂上陳述本組的觀點。這種教學方法旨在培養學生的學術研究和研討能力,同時提升他們通過獨立思考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伴隨著西學東漸的潮流,研討式教學在80年代傳入我國,迄今已有20余年的實踐歷史,廣受國內教育界所關注。
作為一種新的教學方法,研討式教學在黨校的命運卻遠不如他的兄弟姐妹如情景模擬教學、案例式教學般姹紫嫣紅,可謂是一池春水,波瀾不驚。其實,研討課在黨校也比較普遍,但問題是教師很少去認真地編寫教案和組織教學,而是將整個課堂完全交給了學員,放任自流地交由他們主持、討論。可想而知,由于教師的缺位與失職,研討課所收到的效果是不盡人意的。有鑒于此,筆者認為很有必要對教師在研討課上所扮演的角色應如何定位以及如何做到在多重角色中實現自如轉換等問題進行探究。
一、研討課中教師角色扮演與轉換的必要性
研討課注重以學習者為中心,這就需要教師成為促進學員主動學習的推動者,轉變過去單一的講授者的角色。相較于德國、英國等歐美國家自中小學課堂上就注重培養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我國教育界長期以來盛行的是教師滿堂灌、一言堂的教學模式,由教師唱獨角戲,不管臺下的觀眾反應如何,強行地將知識硬塞到他們頭腦中。尤其是我們的大學教育雖然幾經改革,但收效甚微,至今仍然沿襲的是“教師只管教,學生只管受教”的模式。和世界一流的大學比較,我們培養出的學生雖然基礎扎實、博聞強識,但科研創新能力明顯不足。所以應多借鑒國外的先進教學經驗,在課堂上大膽采用研討式教學,及時地轉換教師角色,由講授者變為主持者,推動學生主動地去發現問題、分析問題進而解決問題。我國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育才十字訣》中說過這樣一段話:“與其把學生當作天津鴨兒填入一些零碎知識,不如給他們幾把鑰匙,使他們可以自動的去開發文化的金庫和宇宙之寶藏。”這里的“幾把鑰匙”就是培養學生研討、創新的能力。教師在研討課上應充分調動學員學習的自覺性、主動性。在傳統的教學中,學生只需帶著書本來到課堂,張大耳朵聽老師講就可以了。而研討課沒有固定的教材,教師需要經過周密的教學組織設計,引導學員為了一個議題在課余時間花費很大的精力去搜集資料、閱讀材料,并且讓學員在反復的分析、研討中找到通往學問之門的金鑰匙。陶行知先生就常強調:“教學就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我們要在做上教,在做上學。不在做上用功夫,教固不成為教,學也不成為學。”德國著名教育家第斯多惠也有一句名言:“壞的教師奉送真理,好的教師則教人發現真理。”教師應該通過研討課為學員在理論與實踐結合、知識與能力轉換之間搭建一個最佳的舞臺,激活學員自主學習、自覺探索的潛能。
黨校生源構成的復雜性也決定了教師必須實現角色轉換。和普通高校相比,黨校在開展研討課方面具備得天獨厚的條件,這是由黨校學員生源構成的特殊性決定的。黨校學員經歷了從學生到領導干部再由領導干部轉為學員的雙重轉變,當他們以干部的身份重回學校學習,他們的問題意識更加強烈。可以說,他們是帶著問題來到黨校,希望通過學員之間、師生之間的思想碰撞來澄清理論上的誤區,解決工作中碰到的困惑,單純地汲取知識獲得高分已不再是他們學習的目的。同時,他們還希望通過開放的、激烈的討論來增進彼此間的了解,從各個行業、各個層級的師生之間獲取新的信息。實踐證明,教師必須在課堂上改變過去“你講我聽”布道式的宣講才能實現教學效果的優化。而且,黨校的學員大多來自各行各業,他們在本單位擔任著領導崗位,有著強烈的參政議政意識。而且,他們一般都具有大學學歷,甚至在一個主體班中擁有博士學位的同學也不鮮見。針對這樣高學歷、高能力的學員群體,傳統的教師角色顯然無法滿足他們的需求,教師必須在教學中扮演多重角色。
二、教師在研討課上應扮演的多重角色
研討課在黨校十分重要。一次成功的研討課,應該充分調動學員學習的積極性,通過“頭腦風暴”來實現心智模式、行為方式的完全突破,而且課堂上的知識可以直接運用到日后的工作實踐中。這就需要教師有效駕馭變化而連貫的教學環節,隨著教學過程的推進適時轉換自己的角色。
(一)教師是研討課的組織者
有些教師會有一個錯覺,以為所謂的研討課就是讓學員去討論、發言,自己則抱著雙臂樂得輕松。其實不然。研討課的開展更需要教師認真地設計教學內容,并根據學員的需求和研討的課題做出新的構思和安排,否則研討課就亂哄哄的。這就需要教師扮演好導演這一角色。筆者在不同的主體班中開設過“民族文化的傳承與創新”的研討課,針對不同的班次反復研討,不斷調整教學方案,從議題的設計、場地的安排、學員的分組、課件的制作、播放等等都事無巨細加以考慮,以期取得滿意的教學效果。僅就議題的設計,就耗費了很多時間。我們四個教師商討多次,最后選取了兩個大問題:一是在全球化與現代化的背景下我們的民族文化遭遇了哪些危機?二是我們應該怎樣傳承與創新民族文化?為了方便學員如抽絲剝繭般層層思考,我們另外還就后一個大議題設計了若干環環相扣的小問題。根據學員的表現與需求適時調整教學方案,實踐證明我們的努力沒有白費,我們的研討課一次比一次完善。除了做好編寫的工作,教師還需要根據手中的劇本“說戲”,引導學員按照預設的程序和目的走完每一個過場。領導干部一般都具有強烈的表現欲,有時個別的領導干部會成為麥霸,口若懸河說了半個小時不停,這時教師就應該像導演一樣果斷地大喊NG,以便給更多的同學發言的機會;當學員爭辯過于激烈又偏離了議題時,教師要像導演一樣現場調度,重新將學員拉回到鋪設的軌道上;研討課結束后,教師也應該像導演一樣召集參演的演員開慶功會,毫不吝嗇地道出學員的精彩表現,并善意地指出他們尚存在的問題與不足。當然,有些時候教師還必須像姜文、周星馳等一樣集編導演于一身,不過,教師在和學員“飆戲”的同時,要時刻銘記學員才是整場戲的主角,而教師只不過是路過打醬油的某甲某乙。
對一堂成功的研討課來說,教師既是運籌帷幄的導演,同時還要甘當睿智低調的主持人。
黨校學員構成的復雜性迫使黨校教師必須放棄師道尊嚴這一古訓,教師既要像電網一樣釋放能量,同時還必須像海綿一樣善于汲取學員的能量。正象美國教育家杜威所說:“要使教育過程成為真正的師生共同參與的過程,成為真正合作的相互作用的過程。”在研討課的課堂上,教師要甘當一名主持人,用自己的睿智征服學員,同時又能從頭至尾欣賞整場演出,從學員的表現中有所領悟有所收獲。作為主持人,教師在課程開始時要通過開場白迅速地讓學員進入角色。俗話說的好“好的開頭是成功的一半”,所以開場白一定要做好充分的準備,因為它會奠定整堂課的基調。筆者在“民族文化的傳承與創新”研討課上,首先播放了一段題為“貴州:苗鄉故里難覓美麗苗繡”的視頻,時間很短,僅為兩分鐘,但所起的效果卻是顯而易見的。通過視頻的觀看和老師的點撥,學員很快進入到我們預設的情境與問題中,開始思索我們的民族文化在現代化和全球化的浪潮中究竟遭遇了哪些危機。在課程進行中,教師要準確地把握并記住學員發言的要點,要像主持人一樣善于敏銳地捕捉到每個學員的興奮點和發光點,并對出現的一些小狀況能夠沉著以對。比如當研討遇到冷場時,教師就應該活躍一下氣氛,并引導學員向縱深處邁進;當學員之間就一個問題分成對立的兩派爭吵不休甚至出言不遜時,教師就應該出來圓場,最終四兩撥千斤化險為夷。
在研討時,有些學員思維分散,長篇大論卻不知所終,教師要善于對冗長而零碎的內容進行歸納總結,同時不能礙于情面任其一瀉千里,而應該像主持人一樣,讓研討的流向“行于所當行,止于不可不止”。當然,更多時候,教師要像優秀的主持人一樣諳熟串詞的藝術,在起承轉合之間巧妙地鋪路搭橋,及時地串聯起研討中的裂縫和漏洞。
(二)教師是研討課的輔助者
近幾年,由哈佛大學政治哲學教授桑德爾執教的《公正》課視頻在互聯網上廣泛流傳,被譽為“哈佛第一課”。他本人在復旦、清華開設的講座也異常火爆,場面堪比追星,國內的學子對其在講座中所用案例的熟稔程度令桑德爾也出乎意外。桑德爾教授在哈佛執教30余年每兩年就會開設一次《公正》課,迄今已有一萬多名學生注冊選修了這門課。其實,桑德爾的課并不艱深,他一般都會從一個常見的生活場景講起,他的成功除了活潑的生活素材以外,更在于他對蘇格拉底式討論法的出色運用。所謂蘇格拉底式的討論就是不停地詰問、應答、追問、反駁再追問。蘇格拉底的母親是個助產婆,所以蘇格拉底對人宣稱要追隨母親的腳步,立志做“精神的助產士”,幫助別人產生他們自己的思想。
桑德爾的成功及其他的授課模式帶給我們有益的啟示和借鑒。我們應該像一名助產婆一樣不要過高地估計自己,也不要過低地評價學員。學員其實個個滿腹經綸,但是目前他們還只是在心上“懷了胎”,需要通過老師的提問、逼問、追問來逐漸認識自己學說中的謬誤和無知,進而建立正確的知識觀念。針對學員的回答,教師要善于拋出一個又一個的問題去質疑、反駁學員,揭露他們提出的各種論點、命題的矛盾,以動搖他們論證的基礎,明白自己的無知,然后引導他們通過進一步的思考推動問題向縱深處發展。在幫助學員產生他們自己的思想的過程中,教師不要急于提供給他們所謂正確的積極的答案,因為事實上很多問題并不是指向單一的。教師要像抽絲剝繭一樣誘導對立的雙方學員之間互相詰問、辯論,從而讓他們意識到自己面臨的兩難困境,新的思想由此如泉水般汩汩涌出。一堂成功的研討課重點不在于給學員灌注了多少知識,而在于教師通過何種方式讓學員達到結論。
(三)教師是研討課的激勵者
為了優化教學效果,教師在研討課上必須充分調動學員的積極性,善于發現學員的閃光點。好的教育者并不是傳授知識,而在于激勵、鼓舞、喚醒學員沉睡的思想。研討課需要學員在課前查閱大量的文獻資料,閱讀相關的背景材料,思考問題,甚至還要獨立撰寫論文,這和以前“你講我聽”布道式的傳統教學方式大異其趣。學員為了能在研討課上“出彩”,就必須做好充分的準備,全身心地投入學習,而不是被動地記筆記,囫圇吞棗地消化課堂上的知識。學生檢索文獻、閱讀資料、撰寫文稿及討論、宣講的全過程就是在學習如何做學問,也可以說是按照做學問的路徑對學員進行初步的訓練。這實際上也就是陶行知的教學做合一。這種教學方法無疑會提高學員的研究意識,激發他們的研究興趣。因此,教師應該“成為促進學生知識建構、個性發展和身心健康的促進者角色。”
在研討課上,教師需要針對學員的觀點及時地做出點評,肯定學員思想的鋒芒,這會在很大程度上增進學員心靈的滿足感,讓學員真正體會到知識所帶來的快樂。當教師將學員的學習主動性、求知積極性調動起來,“厭學之風自然停息,不用嚴厲的行政手段也可以使教學秩序維持在最佳狀態。”
三、研討課中教師角色轉換的若干注意事項
在傳統的課堂教學中,教師的角色是十分單一的,只要扮演好“喂魚者”這一角色即可。教師和學生之間是喂與被喂的關系,知識的傳輸方式是單向的。而在研討式教學中,教師和學生之間是平等友好的,是大魚和小魚的關系,知識的傳輸方向是雙向的循環的關系。這種動態的教學過程無疑給教師帶來極大的挑戰性,需要教師既是運籌帷幄的導演,又是機智靈敏的主持人;既是縝密嚴謹的編劇,又是熱情洋溢的助產婆;有時還得充當插科打諢的配角,不巧路過此地化解突如其來的尷尬。教師如何才能在若干角色中自如轉換呢?這就需要在教學中注意以下幾點。
(一)建立一支兩人以上的教學團隊共同授課有助于滿足多種角色的需求,實現教學效果的優化
每個人的知識與能力都是有限的,就連睿智如蘇格拉底者也始終坦言自己的學識不足,卑微如我等凡人更要對自身有清醒的判斷。筆者的研討課就是由四位老師組成,四人的知識背景各有不同,有的是學人類學社會學的、有的是中國語言文學和外國文學方面,可謂是五花八門,但這也正應和了學員駁雜的專業背景。此外我們四位教師的民族成分也是多元的,壯族、漢族、瑤族都有,可以從不同角度、不同身份去理解與識別各民族的文化。
(二)組織設計上要做好充分的準備
對于研討課我們不能掉以輕心,以為研討就是讓學員自由討論,沒老師什么事。其實開展一次研討課對教師是極大的挑戰,需要耗費許多的心血。為了給學員提供一個自由輕松的環境,教師在場地的選擇、學員的分組上需頗為用心,最好將學員分成10人一組圍圓桌而坐,場地的布置宜簡潔明快。這樣,學員之間可以正視對方的眼睛,便于敞開心扉侃侃而談。在議題的設置、課件的制作上同樣要不斷調整盡力完善。此外,最好讓學員事先明確學習任務,并做好相關學習資料的準備;學員間要做好分工,每組學員要有討論的發起人、記錄人、發言人等等。
(三)教師在點評時要尊重學員
聽桑德爾的《公正》課,很多人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總是不厭其煩地詢問發言學生的姓名。在清華大學的講座上曾經有一個插曲,一名女學生闡述完自己的觀點后,桑德爾照例問她的名字,因為女學生的名字對一個不懂中文的教授來說頗有些拗口,所以桑德爾試探地重復一遍,但這名女生反詰道:“Whocares(誰在乎呢)”。
確實,一般人可能會覺得一個學生的名字與整堂課來說微不足道。桑德爾頓時頗有些尷尬,但等掌聲過后他微笑著答道他在乎。一堂課上發言的學生有數十人,但他總能準確地用名字指代發言人,從未將他們的觀點和名字張冠李戴。由此可見,桑德爾對每個人的觀點都給予了足夠的關注。教師在研討課上切忌唯我獨尊,對學員的發言吹毛求疵甚至認為其不值一提,這會挫傷學員研討的積極性。
(四)要善于發現學員的優點,多從正面肯定學員
黨校的學員一般年齡偏大,是帶著職務來學習的。所以和大學生相比,他們往往有著很多的顧慮,擔心問題回答不好會有失顏面。教師應該擁有一雙善于發現真善美的眼睛,及時向學員發出鼓勵和贊賞的信息,促使他們敞開心扉,無所顧忌地侃侃而談。尤其是對內向的學員,教師要不吝惜自己的語言,在點評中及時地給予贊美,把學員的優點無限放大。學員得到教師的當眾稱贊會越發激起他們學習的主動積極性。
好的研討課是一次教學的良性循環。教師與教師之間、學員與學員之間、教師與學員之間多層次、多渠道的交流溝通,無疑會促使理智與情感在其間升華。
[1]姚春瑩.淺談教師在“研討式”教學中的角色轉變[J].科技資訊,2008(14):126.
[2]郭漢民.探索研討式教學的若干思考[J].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99(2):108-111.
D262.3
A
1673-8535(2011)05-0080-04
2011-08-13
馬德翠(1974-),女,湖北荊州人,中共廣西區委黨校講師,博士,研究方向:教育與教育學。
高 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