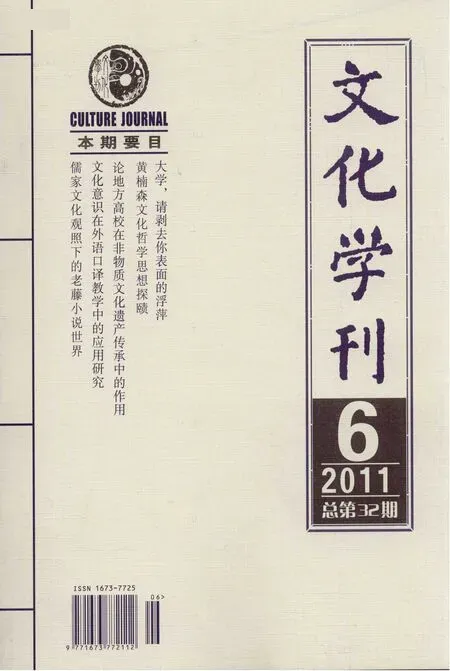略論佛教對唐代圖書事業的影響
馬小方
(福建師范大學,福建 福州 350007)
中國佛教發展到唐代進入鼎盛時期,宗派林立且理論充實。唐代佛教的觀念、信仰以及處世態度、人生哲學等,在消化理解的基礎上,滲透到社會各個領域,并產生廣泛的影響。尤其是在文化領域,佛教和中國的文化、文學深深地融合在一起。圖書事業作為唐代文化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佛教的深刻影響。
一、佛經翻譯和整理事業的空前發展
鼎盛發展的佛教促使譯經事業的發展。唐代的譯經基本上由國家主持,成績可觀。太宗貞觀三年(629)開始組織譯場,歷朝相沿,直到憲宗元和六年(811)才終止,前后譯師二十六人。譯經制度也更加完善,參與人數更多,規模更龐大,組織更嚴密,設立了譯主、筆受、度語、證梵本、潤文、證義、校勘、監護等專門的職務掌管譯經中的不同事務。這一時期的譯經可謂人材優美、原本完備、規模龐大、組織精密。著名的譯經家有玄奘、義凈、一行、不空等,中國譯經史上四大譯經家有兩家(玄奘和不空)就出現在唐代,其中,玄奘法師曾親至西域,后所攜來經論六百五十七部,使我國佛典的翻譯如日中天。“玄奘之廣弘大乘,義凈之專重律藏,……其文字教理之預備,均非前人所可企及也。”大量的佛教典籍翻譯過來,無疑成為唐代藏書的重要來源。
統治者也十分重視佛典藏量,不僅大量翻譯佛教經典,而且用官費從事寫經活動。唐代寫經活動規模很大,據統計,自太宗到德宗年間共譯出經、律、論等428部,2612卷。如唐太宗分別于貞觀五年(631)和貞觀十六年(642)“敕法師玄琬于苑內德業寺為皇后寫佛藏經”、敕“為穆太后寫佛《大藏經》,敕選法師六人校正”。又如:武則天的母親楊氏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她去世后,武則天發愿敬造三千部《妙法蓮華經》、《金剛經》為已逝父母祈福,此次寫經活動持續了七年之久。
1900年6月22日,中國甘肅敦煌莫高窟藏經洞被發現,公元四至十一世紀的佛教經卷、社會文書、刺繡、絹畫、法器等文物五萬余件問世,據統計其中佛教經卷、寫本約有25000多卷,且大多為唐代的作品。唐代的佛典藏量可見一斑。
唐朝佛教翻譯規模宏大,典藏量高,藏書處也星羅棋布,遍布都邑山鄉,政府為此建立了專門佛教藏書機構,使得經藏制度在唐代得以完善成熟。唐代諸多寺院皆為佛經典藏處,大寺都有經藏、或樓、或閣、或院、或堂,經藏內的藏書,排架有序,還專門有主藏僧管理。大量佛教翻譯作品直接影響圖書內容和數量,不僅增加了藏書量,而且豐富了藏書品種。
佛教經典的漢譯不僅促進佛法的弘傳,同時也充實了中國文學創作的內涵。佛教經典中富有文學價值的佛教經典極多,如描寫佛陀的生平事跡的《普曜經》、《維摩詰經》;采用許多譬喻故事,闡揚佛法妙義的《法華經》;采用梵文韻體敘述佛陀一生故事的《佛所行贊》;四、五、七言格律合用,文字生動精彩的《佛本行經》等,對中國文學的創作影響極大。
二、繁榮的唐代佛教文學
(一)佛教經典著述
自兩晉南北朝開始,中國僧人就已有了自己的著述,從經序、注疏、論著以至目錄、史傳的編撰,豐富和發展了“三藏”的內容。此后中國僧人的著述不斷增加,至唐代佛教撰述之豐富,數目之繁多,難以具列。初唐時的類書《法苑珠林》,言及中國僧人著述有三千余卷。尤其是開元年間,撰述作品應該十分豐富,據《新唐書》載:“藏書之盛,莫盛于開元,其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學者自為之書,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粗計《舊唐書·經籍志》和《新唐書·藝文志》著錄唐代著作2125家、2304部、40065卷,其中釋氏94家,1300余卷。
(二)佛教題材作品
首先,文人創作出大量的佛教題材作品。唐代官僚文士中很多如權德輿、韋應物、白居易、孟浩然、王維、柳宗元、李白、賈島、穆員、劉禹錫、李賀、韓偓等等,皆信仰或者不同程度地支持佛教。佛教的教義、教理也深刻地影響著唐代文人的精神世界,也為文人的文學創作提供多樣的靈感、意向和題材。反映到作品中就產生了諸多佛教題材的詩歌、散文等文學形式。士人與佛教的廣泛聯系,如游歷、交往、贈答等,諸多與僧人的廣泛交往也大量地反映到詩歌中,《全唐詩》中此類詩多達二千首。唐代的很多作家的作品中也都有佛教影響的印記。《全唐詩》里中國文人有佛教有關的作品就達兩千多首,或詩題直接與寺塔或僧人有關,或詩題未體現但詩中有與佛教相關的詞語。有的在詩中直接講佛理,如李頎《宿瑩公禪房聞梵》“始覺浮生無住著,頓令心地欲昄依”;有的則表現禪機,如王維《終南別業》“行到水窮處,坐看云起時”。《全唐文》中直接與佛教相關的作品也比比皆是,就拿佛教凈土宗來說,文中僅僅題名直接相關的就有百多篇,如蘇颋《凈信變贊》(《全唐文》卷二百五十六)、王維《西方凈土變畫贊(并序)》(卷三百二十五)、王維《西方凈土變畫贊(并序)》(卷三百二十五)、李白《金銀泥畫西方凈土變相贊(并序)》(卷三百五十)、任華《西方變畫贊》(卷三百七十六)、權德與《畫西方變贊》(卷四百九十五)、白居易《畫西方幀記》(卷六百七十六)等,不盡枚舉。
其次,僧人也創作了很多的文學作品。這在詩歌領域的表現尤為明顯。受空前發達的佛教文化的影響,唐代世俗詩人之詩多為詠僧的題材內容,而僧侶中能作詩者亦比比皆是。尤其是在中唐的大歷時期,詩僧輩出,蔚然天下。《全唐詩》卷806至卷851所收皆為僧人之詩,收了一百一十五家,共四十六卷,兩千八百余首,約占《全唐詩》的二十分之一。劉禹錫曾在《澈上人文集紀》中列舉了一大批的詩僧,又在《秋日過鴻舉法師寺院便送歸江陵詩序》中說:“自近古而降,釋子以詩聞于世者相踵焉。”雖然唐以前也有僧人寫詩,但無論是詩僧還是僧詩的數量都相對較少,東晉至隋代近百年間,有詩僧僅四十余人,且作品寥寥,而唐代無論詩僧人數之眾,還是作品之多,都是前所未有的,大量的詩篇成為全唐詩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這類詩歌加上文士所作的詠僧等作品,竟占 《全唐詩》總數的百分之十左右。
佛教在唐代的廣泛影響,直接拓廣了文學的體裁,豐富了書籍的內容。俗講與變文,就是這時出現的新文體。文學作品數量和種類的增多,無疑豐富并充實了唐代圖書事業的內涵。
三、蓬勃發展的寺院藏書
唐代寺院藏書在中國古代藏書史上占據重要的地位,有唐一代圖書數量增長極快,與佛教的發展和寺院藏書有直接的關系。唐代的東林、西明等著名的寺院,都藏有大量的佛經。
寺院藏書的發展是寺院佛教活動影響的結果。寺院是弘揚宗教、講經說法、修身養性的場所,藏書也主要以佛家典籍為主。寺院時常組織辯經、講經活動,寺院會將這些活動中的各種資料加以整理、抄寫成書,有時一些高僧親自參與,促進了藏書的發展。唐代佛寺藏經十分豐富,史載初唐的西明寺,有藏經三千三百余卷,其藏書至龍朔初年達5000余卷;中唐的廬山東林寺,有圖書一萬卷。
由于唐統治者信奉佛教,因此受宗教風氣的影響,很多居士文人與僧侶交往甚密,甚至將自己的文集贈于寺院收藏,而且“天下名山僧占多”,絕大多數名山都有寺院,遠離塵世的地理優勢也利于保存文化典籍,是頗為理想的藏書之所。白居易就曾分藏自己文集于圣善寺、東林寺、南禪院,并將自己的文集贈于香山寺、東林寺等,僅在龍門香山寺的藏書就多達5270卷,此舉無疑豐富和發展了佛寺藏書。
唐朝寫經活動,為寺院藏書打下了基礎,刺激了寺院藏書的快速發展。官方寫經如上述唐太宗與武則天之例,規模宏大,唐代宗時曾從宮里拉出兩車《護國仁王經》送給資圣寺、西明寺。至于民間的抄經、誦經更是達到驚人的地步。
此外,中國僧人的著述、中外佛家弟子的交流以及名士的贈藏也是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且唐代中外文化交流日頻,佛僧交往尤其明顯,往來僧人多攜經書翻譯研究,如玄奘歸國時就帶回經論657部。
寺院佛教藏書也是國家圖書館——秘閣佛經藏書的一大來源,同時為國家編纂工具書的組織活動提供豐富的文獻支持。唐代諸多的寺院皆為佛經典藏處,且有專門的主藏僧負責管理經書,其藏書自身的整理工作,又產生了大量佛經目錄。
四、成果豐富的佛經目錄
唐代佛教的發展亦在目錄學中得到反映并影響其發展,應該說佛教豐富并完善了唐代圖書目錄和分類學。
隨著佛經翻譯和著述的大量增加,約在公元二世紀后半葉就已開始了漢譯佛經目錄的整理,隨后,由于統治者的鼓勵和組織,產生了不少有影響的目錄學著作。官修目錄中西晉荀勗的《中經新簿》已經著錄佛經,發展至《七錄》已經對換了《七志》中道、佛兩類的位置,先佛而后道。
唐代鼎盛的佛教衍生出數量眾多的佛教經錄著作,如貞觀初年玄琬所編德業、延興二寺《寫紀目錄》、顯慶三年(658)所編西明寺大藏經的《入藏錄》、龍朔三年(663)靜泰所編《東京大敬愛寺一切經論目錄》等。另外更多帶有經錄性質的,如麟德元年道宣編《大唐內典錄》、靖邁撰《古今譯經圖記》、武周天冊萬歲元年(695)明佺等編成的《大周刊定眾經目錄》、開元十八年(730)智升撰《續大唐內典錄》,后又編 《續古今譯經圖紀》、《開元釋教錄》、《開元釋教錄略出》,貞元十年(794)圓照撰《貞元續開元釋教錄》、十六年(800)又編成《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同時有華嚴寺沙門玄逸對于入藏各經的卷次、其目詳加校定而撰成的《開元釋教廣役歷章》。批量出現的佛經目錄中包含著許多版本學、目錄學上的創新之舉,促進了版本學、目錄學的發展與成熟。
這類經錄中價值較高,在我國目錄學史上影響最大的是唐開元年間智升編撰的 《開元釋教錄》。它質量精美,分類更精密,且子注詳細,成為唐代及后世一切寫經、刻經的依據。此經錄凡二十卷,分“總括群經錄”和“別分乘藏錄”兩大類,“別錄”的最后兩卷為“入藏錄”,收集經籍1076部,5084卷,集前此經錄的大成,并首次將中國僧人的著作入藏流行。智升還在《開元釋教錄略出》中創用以千字文編次的方法,這對于卷帙浩繁的佛教典籍的整理、庋藏及檢索等提供了一種科學的方法,后來我國第一部木刻版大藏經《開寶藏》就是據此雕印成書。
后世學者如梁啟超、陳源等都給予《開元釋教錄》很高的評價,綜合說來它分類體系嚴謹完備,代表了佛經目錄最大的目錄學成就;著錄詳盡,充分發揮了目錄學的推薦作用;窮源至委,竟其流別,體現了“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目錄學思想等等。
五、書籍制度及圖書版本學的新發展
佛教刺激了唐代書籍制度及圖書版本學的新發展,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首先,書籍裝幀形式的變化。在唐代,書籍制度由舊形式向新形式的發展過渡中,佛經文獻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受印度貝葉經形式的啟示,經卷改為經折裝,又稱梵夾裝。此后演化為旋風裝,從而進一步產生了冊葉制度的最早形式蝴蝶裝。由于佛經這一契機,書本的編纂體例和裝訂形式有了創新和發展。(資料待詳實)
其次,圖書出版事業的正式出現。佛教的發達,必然引起對佛教經典的大量需求,佛教信徒通常把寫經視為“功德”之事,寫經越多,功德越大。唐代社會對于佛教崇信之風已達到空前的境地,由于政府的支持和宗教宣傳的大量需要,因此只靠抄寫傳錄顯然境界已經不能滿足對佛教經典的大量需求,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這在客觀上對印刷術的產生起著催化劑的作用,具有便捷、快速的復制大量復本特性的新技術——印刷術便在這一背景下得到應用和發展。
唐代社會上的印刷品,內容已十分廣泛,其中的珍品多為佛經文獻。1990年發現的敦煌遺書中,佛教經典就占總量的百分之九十八以上,其中許多印刷珍品都在中國乃至世界印刷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有學者還認為佛教徒是雕版印刷的發明者,只是雕版印刷產生的具體時間還不能確定,但唐初已有雕版印刷品流行是不爭的事實,咸通九年的《金剛經》、武周時的《妙法蓮花經》等已是十分成熟的雕版印刷品。可以說唐代雕版印刷術的興起,促使我國古代開始有了嚴格意義上的圖書出版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