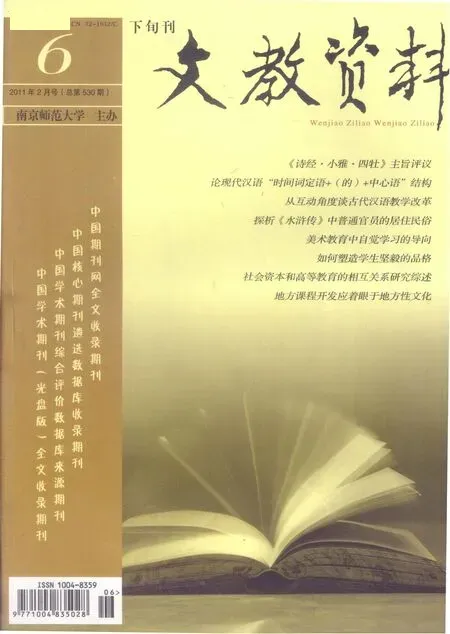《詩經·小雅·四牡》主旨評議
劉志軍
(吉首大學 文學院,湖南 吉首 416000)
對于《詩經·小雅·四牡》這一首詩的主旨,古今注家觀點約分為兩派:第一種認為是慰勞使臣的詩,以詩序、毛傳、孔穎達、朱熹等為代表;第二種認為是“念及父母、懷歸傷悲”[1](《詩三家義集疏》引齊說)、“出使的官吏思歸”[2]或“為統治者在外服役的人的辛勤與思家情緒”[3]的詩歌,近代學者程俊英、高亨、金啟華等持此觀點。
《詩序》云:“《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矣。”鄭玄《箋》闡發序亦云:“使臣以王事往來于其職,于其來也,陳其功苦以歌樂之。”孔穎達疏云:“事畢來歸,而王勞來之也。……此經五章,皆勞辭也。”《詩序》《毛傳》《鄭箋》《孔疏》一脈相承,對本篇詩旨有大致相同的看法,認為是慰勞使臣的詩篇。于末章“是用作歌,將母來諗”句下,鄭玄箋云:“故作此詩之歌,以養父母之志,來告于君也。”此語與開篇語齟齬,開篇認為是文王所作,篇末陡然改為使臣自作,認為是使臣借此詩告訴王養父母之志。孔疏忽焉不察,照鄭箋引申發揮云:“‘是用作歌,將母來諗’亦序使臣之意,明為使臣作此詩之歌,其來諗不得為告也。”孔疏沿襲了鄭玄箋的失誤。孫礦為解決此矛盾,推測云:“此自使臣在途自詠之詩。采詩者以其義盡公私,故取為勞使臣之歌。”(《詩經批評》)
產生上述兩類說法源于解說者對此詩中關鍵詞句的不同理解,認為此詩詩旨是“念及父母、懷歸傷悲”的學者,他們可能由于對篇中“王事靡盬”“是用作歌,將母來諗”等關鍵語詞的不同解讀,而得出了和傳統主流觀點不同的見解。
按照“慰勞使臣說”的觀點,首章“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句,毛傳云:“盬,不堅固也。”結合《四牡》篇原文來看,此上句意為王事無不堅固,下一句緣何說“我心仍然傷悲”?似乎于情理不合,合理的邏輯應當是:如果王事已經無不堅固,那么我應當高興,而不必傷悲。孔穎達似乎沒有注意到這一點,其疏云:“以王家之事無不堅固,我當從役以堅固之,故義不得廢,我心念父母而傷悲。”孔氏于此增字解經,多方遷就以申己說,然不顧上下文的邏輯關系,王家之事既已無不堅固,何需汝再從役以堅固之呢?
“王事靡盬”若照鄭箋、孔疏意理解為“王家之事無不堅固,我當從役以堅固之”,這表現的是一個盡心盡力為公事而努力行動之人。作如此理解方可和詩前小序協調。然其中存在的問題也引起后世好學深思者的疑慮。今世學者發現鄭玄、孔穎達注疏中存在的這個問題時,只好另尋出路,將“王事靡盬”解作“王事靡有止息”。如王引之《經義述聞》:“盬者,息也。王事靡盬者,王事靡有止息也。”馬瑞辰《詩經通釋》有大致相同的見解。他們對“王事靡盬”雖有新解,然并不反對詩序所說,依然認為此詩是慰勞使臣之詩。
后來學者在王引之將“王事靡盬”解為“王事靡有止息”的引導下,僅就詩論詩,進而提出此詩是“念及父母、懷歸傷悲”、“出使的官吏思歸”或“為統治者在外服役的人辛勤與思家情緒”的詩歌。此篇五章中有四章不斷重章復沓“王事靡盬”一語,“王事靡有止息”當然更像一個對現實抱怨、不滿意現狀的使臣的嘆息,而不類君王慰勞歸來使者的話語。于是有學者提出了和傳統不同的第二類見解——“念及父母、懷歸傷悲說”。新說“念及父母、懷歸傷悲說”不必迂曲,能使全篇句意通暢、邏輯連貫。
“念及父母、懷歸傷悲”說是在傳統主流說(即“慰勞使臣”)對本詩詩旨的解說存在缺陷的情況下而產生的新說。從歷代對本詩研究的情況來看,慰勞使臣說直到唐代一直占據主要地位,無人懷疑,間有感到前人之說有不周密的地方,亦多方辯解以圓其說。傳統的“慰勞使臣”說無法順暢解釋篇中“王事靡盬,我心傷悲”“是用作歌,將母來諗”等處。
傳統的、占據主流地位的“慰勞使臣”說為近代的學者所冷落,究其原因,大略有下面幾點:第一,從《四牡》全詩字面所寫的內容來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王事靡盬,不遑啟處”、“將母來諗”等句,體會其語氣,更像是抱怨,而不是慰勞的話語,理解為“小官吏苦于行役,嘆息他不能回鄉,奉養父母”或“為統治者在外服役的人的辛勤與思家情緒”更符合全篇字面所傳達的意思。因而“念及父母、懷歸傷悲”似乎比“慰勞使臣”更容易讓人接受;第二,自宋代朱熹解讀《詩經》主張破除《詩序》的權威,認為:“看詩不當只管去《序》中討,只當于詩辭中吟詠著,教活絡貫通方得。”(據朱鑒,《詩傳遺說》)宋代的鄭樵、王質等也認為不能太依賴詩《序》解詩,此三人以他們在學術史上崇高的地位和巨大的影響力,使《詩序》的權威性大為削弱,后世不再唯“詩序”是從的學者越來越多。
確認本詩主旨為何,我認為需要厘清本詩是否為使臣自作這一問題。
持“念及父母、懷歸傷悲”說的學者認為此詩全篇皆為使臣所作;持“慰勞使臣”說的學者(鄭玄、孔穎達)認為篇章中一部分是使臣所作,一部分是記錄君之言語,是君臣對話體。這可從注疏中窺見,本詩末章的“將母來諗”孔穎達注疏從鄭玄箋解“諗”為“告”,鄭玄箋云:“以養母之志,來告于君。”孔穎達則疏云:“謂君不知,欲陳此言來告君,使知也。”據鄭玄箋,鄭玄認為此詩是使臣所作,孔穎達與鄭氏意同,亦認為是使臣自作,至少認為此詩部分語句出自使臣之口。基于此,孔氏認為全詩為君臣對話體(并在注疏中認同鄭玄,謂為文王為西伯時事),現將《四牡》全詩依孔穎達注疏意按對話體標注于下:
文王:四牡騑騑,周道倭遲。
臣:豈不懷歸?
王事靡盬,
我心傷悲。
文王:四牡騑騑,啴啴駱馬。
臣:豈不懷歸?
王事靡盬,
不遑啟處。
文王:翩翩者鵻,載飛載下,
集于苞栩。
臣:王事靡盬,
不遑將父。
文王:翩翩者鵻,載飛載止,
集于苞杞。
臣:王事靡盬,
不遑將母。
文王:駕彼四駱,載驟骎骎。
臣:豈不懷歸?
是用作歌,
將母來諗。
我認為,全篇不當是使臣所作,全篇都為國君之辭或代國君所作之辭。對于孔氏見解,黃焯在其著作《詩說》中依據詩經篇內體例“詩中凡次章以下,其章首之語,有疊前之辭,而其下有不相連貫者”,“必明此例,方知此章不與首章行文相類也”,評孔疏曰:“此二句(指“是用作歌,將母來諗”)為全篇之總束。傳訓諗為念,謂上作此詩之歌以述使臣念養父母之心,雖文連豈不懷歸句,不得以首章為例,而謂使臣作此詩之歌也。”[4]我贊同黃焯之說,認為全篇都為國君之辭或他人代國君所作,用來慰勞使臣之辭。
綜觀全詩,以全篇都為國君之辭或代國君所作之辭來理解,本可以暢通無礙,“慰勞使臣”的主旨也非常顯豁。君王對歸來的使臣表達因為自己“靡盬”的王事,使使臣“不遑啟處”、“不遑將父”、“不遑將母”,看到這樣的結果作為國君心里很傷悲(一章“我心傷悲”)。使臣聽聞君王此類言語,知自己之功已經為君王所明察肯定(《詩序》“有功而見知則說矣”),則其以往之辛酸得以宣泄,定會深深感佩于心,起到極佳的“慰勞使臣”的目的。
全詩五章,每章的前三句都是使用賦的手法。這個不論作以上兩說的任一說法理解都沒有爭議,故不贅述。爭論的焦點在每章的后兩句。首先是對 “王事靡盬”中的“王”是指誰,鄭箋言此詩作于“文王為西伯之時”,即姬昌此時尚未為文王,故詩中之“王”不是指姬昌(后來為文王),而是指殷紂王。漢人重師法,鄭必有所本。西伯侯姬昌當時已經三分天下有其二,是當時實際的執政者。他口出此語或由他人代出此言于身份正合,與事實相合。此處的“王事”不論是指殷紂王所派發的無盡頭——靡盬的事務,還是指國家的正當的事務,對于辛苦從外歸來的使臣都是一種安慰,靡盬的王事此正體現了使臣的能耐。不是有能耐又怎能對付靡盬的事情?前四章的“王事靡盬”都是對使臣功勞的承認、認同、贊賞,贊美他們為完成靡盬的公事,而“不遑啟處”、“不遑將父”、“不遑將母”,犧牲了自己的安閑和奉養父母等個人利益。王符《潛夫論·愛日》篇解此詩云:“在古得閑暇而得行孝,今迫促不得養也。”錢鐘書先生《管錐編》亦有此意,認為:“后世小說、院本所寫‘忠孝不能兩全’,意發于此。”[5]
從詩字面意思來考察,認為詩是:“小官吏苦于行役,嘆息他不能回鄉,奉送父母。”[6]似乎文從字順。將此詩作此類解讀者忘掉了一個最大的前提——此詩在詩三百篇中屬小雅。《詩集傳》云:“正小雅,燕饗之樂也。”即指明了小雅是用在喜慶的宴會上的樂章。如果此篇抒發的是“小官吏苦于行役,嘆息不能回鄉”之類怨憤消極的情感,與宴會喜慶和樂的氛圍將完全不相符,自然不會被編排歸納入小雅之中。從《四牡》篇所處的位置來看,本篇是小雅的第二首詩。《詩經·小雅》中《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常棣》、《伐木》、《天保》、《采薇》、《出車》、《杕杜》、《魚麗》十篇,據詩前小序所言,大都為營造歡樂喜慶的氣氛而設。這些詩篇因具有大致相同的性質被類聚群分排列到一起。從孔子當年刪定編排詩經三百篇時初衷的角度推測,《四牡》為慰勞使臣的詩可能性更大。
[1]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M].北京:中華書局,1987:556.
[2]程俊英.詩經譯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289.
[3]高亨.詩經今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218.
[4]黃焯.《詩說》長江文藝出版社,1981:138.
[5]錢鐘書.管錐編(一)[M].北京:中華書局,1979:134.
[6]金啟華.詩經全譯[M].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4:3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