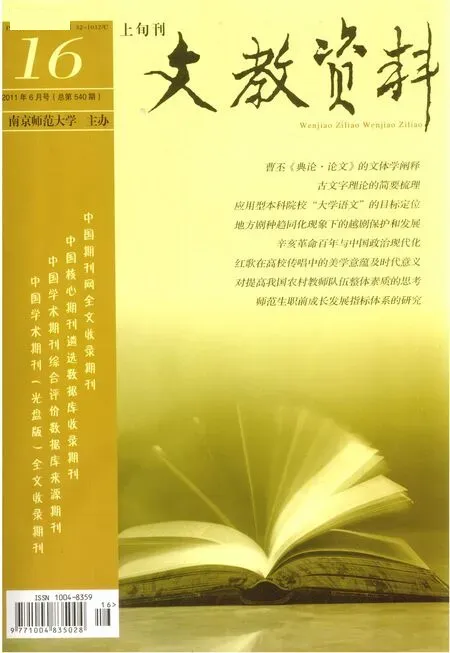試論杜威《民主主義與教育》中的課程觀
方舒婷
(福建師范大學(xué) 教育學(xué)院 課程與教學(xué)論專業(yè),福建 福州 350007)
約翰·杜威是20世紀美國實用主義哲學(xué)家和教育家,其所著的《民主主義與教育》全面闡述了實用主義教育理論,是其教育著述的代表作。他強于教育理論,且富于教育經(jīng)驗,把理論和實際有機結(jié)合起來。在教育史中,既能提出新穎的教育簡介,又能親見其實施而獲得成功者,杜威被視為第一人。他依據(jù)自己獨特的哲學(xué)觀、心理觀和社會觀,對教育問題和教育現(xiàn)象進行了系統(tǒng)的理論研究和實踐探索,建立了自己獨特的教育理論體系,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課程觀,對20世紀課程理論和課程實踐的發(fā)展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
一、實用與發(fā)展相統(tǒng)一的課程價值取向
杜威是實用主義教育家,他認為教育是“生活的需要”和“社會的職能”,在性質(zhì)上講,教育就是“生活的社會延續(xù)”,[1]是經(jīng)驗的“繼續(xù)不斷的改組和改造”,[2]而這種改組和改造又必須利用環(huán)境、通過環(huán)境才能完成,進而認為教育必須以“發(fā)展個人的創(chuàng)作能力和適應(yīng)環(huán)境的能力,也就是培養(yǎng)所謂的社會精神的社會能力”為目的。因此,作為實現(xiàn)教育目的的手段的課程就必須具有實用與發(fā)展的價值。
所謂實用的價值,就是指課程要能使兒童適應(yīng)和應(yīng)付當前的環(huán)境,能解決當前的困難。所謂發(fā)展的價值,就是指課程要能為兒童一生的發(fā)展打下基礎(chǔ),要能使兒童應(yīng)對將來環(huán)境的變化。實用指向現(xiàn)在,發(fā)展指向未來;實用解決確定的困難,發(fā)展解決不確定的困難,即為了將來的實用。
二、以兒童為中心的課程論基礎(chǔ)
杜威是現(xiàn)代教育派兒童中心主義的代言人,是繼盧梭自然教育理論提出后,主張重視兒童、解放兒童的教育家。杜威曾說:“兒童是起點,是中心,而且是目的,兒童的發(fā)展,兒童的生長,就是理想所在。只有兒童提供了標準,我們必須站在兒童的立場上,并且以兒童為自己的出發(fā)點,決定學(xué)習(xí)的質(zhì)和量的是兒童,而不是教材。”[3]因此,在他看來,其一,為了教育不至于成為機械的和死板的令兒童生厭的活動,課程應(yīng)符合兒童心理需要、興趣和能力;其二,為了保證兒童的生活和經(jīng)驗具有統(tǒng)一性和完整性,課程應(yīng)相應(yīng)地體現(xiàn)保護兒童認識的統(tǒng)一性和整體性;其三,為了使系統(tǒng)知識保持社會作用,課程應(yīng)具有社會性,在一定情境中發(fā)展學(xué)生的社會見識和社會興趣。組織課程必須圍繞著兒童的需要和經(jīng)驗,并通過這種課程,使兒童具有能夠自我發(fā)展,自由發(fā)揮主動性和創(chuàng)造性的本能。為此,活動性、經(jīng)驗性的主動作業(yè)應(yīng)該成為學(xué)校課程和教材的主要內(nèi)容,必須“把兒童自己所能處理的材料摻入課程,使他們從自己的經(jīng)驗中得到許多教訓(xùn)”。[4]
從杜威的上述觀點不難看出,兒童中心的課程論的實質(zhì)就是注重兒童個人經(jīng)驗,讓兒童的學(xué)習(xí)與兒童的生活、生長密切聯(lián)系起來。這樣,從課程的組織形式、教材的編排及選擇,到教法的具體實施形式,歸根結(jié)底都成為兒童本身的問題。兒童無疑成了課程的中心,一切都是以兒童為中心而安排和展開的。
三、活動課程與學(xué)科課程相結(jié)合的課程模式
杜威強調(diào)兒童和社會的聯(lián)系,認為在兩者中有一個聯(lián)接的共同要求——活動。他從實用主義的經(jīng)驗出發(fā),認為課程的本質(zhì)是直接經(jīng)驗的總和,任何知識都是活動的結(jié)果,兒童生來就有探究活動的本能和興趣。因此,他主張課程應(yīng)以兒童日常生活經(jīng)驗為轉(zhuǎn)移,以兒童自身的能力和興趣為主旨,讓兒童從自己的生活和經(jīng)驗中去學(xué)習(xí)直接經(jīng)驗。所以他提出了 “從經(jīng)驗中學(xué)”、“做中學(xué)”的口號,并把它看成課程實施的基本方式,確立了活動在課程中的地位,倡導(dǎo)活動課程,改造學(xué)科課程,試圖實現(xiàn)活動課程與學(xué)科課程在課程形態(tài)上的統(tǒng)一。
杜威活動課程的基本形態(tài)是主動作業(yè)。他十分強調(diào)主動作業(yè)在學(xué)校課程中的重要性。主動作業(yè)可以為兒童提供真正的動機和直接的經(jīng)驗,并使兒童接觸現(xiàn)實。通過主動作業(yè),可使“學(xué)校的整個精神得到新生”。[5]杜威所主張的教育與生活的聯(lián)系,使兒童能通過直接經(jīng)驗進行學(xué)習(xí),以及使學(xué)校成為“雛形的社會”等,主要就是通過這種主動作業(yè)而實現(xiàn)的。因此,他明確地指出:“學(xué)校所以采用游戲和主動的作業(yè),并在課程中占一明確的位置,是理智方面和社會方面的原因,并非臨時的權(quán)宜之計和片刻的愉快愜意。”[6]沒有一些游戲和工作,就不可能有正常有效的學(xué)習(xí)。學(xué)校的任務(wù),就是設(shè)置一個環(huán)境,在這種環(huán)境里,“游戲和工作的進行,應(yīng)能促進青年智力和道德的成長”。[7]由此可見,杜威把游戲和主動作業(yè)看作活動課程的兩個基本形式,并且游戲必須是“自由的”和“可塑的”,主動作業(yè)必須面向全體人;必須滿足兒童興趣,適應(yīng)兒童生活需要,必須代表社會情境,使課程與社會和兒童結(jié)合起來,同時體現(xiàn)方法與材料的同一。
杜威雖然倡導(dǎo)活動課程,但并不一味反對學(xué)科課程。相反,他認為學(xué)科課程也應(yīng)是一種重要的課程模式,但同時他又看到了已有學(xué)科課程的兩大弊病:一是學(xué)科課程中人文與科學(xué)分離,二是學(xué)科課程與社會生活分離。所以,他認為必須對學(xué)科課程進行改造,使學(xué)科課程成為人文與科學(xué)的統(tǒng)一體,并與社會生活緊密相聯(lián)。
四、“從做中學(xué)”的課程實施觀
課程實施是指通過教學(xué)活動將編訂的課程付諸實行。杜威活動課程為主的課程模式?jīng)Q定了“從做中學(xué)”的課程實施觀,這是杜威全部教學(xué)理論的基本原則,貫穿于杜威所論述的各個教學(xué)領(lǐng)域,倡導(dǎo)通過各種 “作業(yè)”和活動,即從做事情中獲得各種知識和技能。他說:“科學(xué)教育的教學(xué)法的新的出發(fā)點,顯然不是教一些貼有科學(xué)標簽的東西,而是利用熟悉的作業(yè)和工具,指導(dǎo)觀察和實驗,使學(xué)生在他們實際的運轉(zhuǎn)中了解它們,從而獲得一些原則的知識。”[8]“學(xué)習(xí)意味著學(xué)生學(xué)習(xí)時所做的某種事情。這是一個主動的、親自的事情,而不僅是一個人提取所儲存的知識的過程。”[9]“實驗方法作為獲取知識和確保它是知識而不只是意見的方法,既是發(fā)現(xiàn)又是證明的方法,這種方法的發(fā)展乃是造成認識論的改造的最后一個巨大的力量。”[10]總之,實驗方法的引用精確地表明,在控制的條件下所進行的這種活動,正是獲得知識和經(jīng)驗關(guān)于自然的各種有效的觀念的途徑,學(xué)校的任務(wù)“不在于把青年從一個活動的環(huán)境轉(zhuǎn)移到死記硬背別人學(xué)問的環(huán)境,而在于把他們從相對地一個偶然的活動的環(huán)境,轉(zhuǎn)移到一個按學(xué)習(xí)時指導(dǎo)的選擇的活動的環(huán)境”。[11]
杜威倡導(dǎo)“從做中學(xué)”,主張學(xué)校與生活加強聯(lián)系,較大程度上革除了傳統(tǒng)教育知行脫節(jié)、手腦脫節(jié)、兒童處處被動的弊病,含有明顯合理的因素,為現(xiàn)代教學(xué)理論中重視“發(fā)現(xiàn)法”教學(xué)方法的研究奠定了基礎(chǔ)。但其過度強調(diào)了活動或工作等直接經(jīng)驗在教育中的地位,從而相對忽視了間接經(jīng)驗在教育中的地位,這在理論上顯然是片面的,在實踐上也無法解決系統(tǒng)知識的獲得問題。
五、內(nèi)在價值與工具價值相結(jié)合的課程評價
杜威從哲學(xué)認識論的角度把教育價值分為內(nèi)在價值和工具價值。所謂內(nèi)在價值,就是欣賞的價值,能在真正的生活情境中使學(xué)生深切了解到事實、觀念、原則和問題的重要意義;所謂工具價值,即比較價值,它是對特定情境中目標的需要和滿足程度,對事物的工具價值進行排序,以便做出選擇和取舍。[12]
杜威從內(nèi)在價值與工具價值相統(tǒng)一的觀點出發(fā),反對把課程中的許多科目分為欣賞的科目 (即有內(nèi)在價值的科目)與工具的科目(即在它們本身以外還有價值的科目),并力求把兩者統(tǒng)一起來。給每門科目賦予獨立的價值,同時把整個課程視為由各種獨立的價值聚集而成的混合體,他認為“這種趨勢是社會團體和階級隔離孤立的結(jié)果”,是“在眾多的教育中”,反而“把教育遺忘了”的表現(xiàn)。在重視內(nèi)在價值與工具價值相統(tǒng)一的基礎(chǔ)上,杜威十分重視科目的內(nèi)在價值或欣賞價值。他認為,“每一科目都有一個方面應(yīng)該具有這種終極的意義”,要求每一個科目本身應(yīng)成為“對兒童有意義的東西”,使兒童在學(xué)習(xí)它的過程中產(chǎn)生心靈的愉悅與滿足。如果一個科目從來沒有“因其自身而被學(xué)生欣賞過”,那么它就“無法達到別的目的”。杜威雖然強調(diào)科目的工具價值,但認為這種工具價值應(yīng)建立在內(nèi)在價值的基礎(chǔ)上并為之服務(wù),反對課程實踐中往往脫離內(nèi)在價值去重視工具價值的做法。他對課程的評價,是立足于內(nèi)在價值與工具價值的統(tǒng)一基礎(chǔ)上的。首先注重課程的內(nèi)在價值,再考慮不同課程在特定情境中的工具價值。[13]
六、杜威課程思想評價
美國教育學(xué)者羅思指出:“未來的思想必定會超過杜威,可是很難想象,它在前進中怎樣能夠不通過杜威。”由此,對杜威教育思想在世界的影響可窺見一斑。它致力于解決傳統(tǒng)教育中存在的三個主要問題:教育與社會、兒童、實踐的脫離。他的課程思想實質(zhì)上是要努力實現(xiàn)教育的內(nèi)在價值與工具價值的結(jié)合,使教育過程充滿樂趣,富有成效,既有益于兒童個人,又有益于社會。它要求教育要尊重兒童心理發(fā)展水平,加強學(xué)校與社會生活的聯(lián)系,增強理論與實踐的聯(lián)系。也就是要通過活動性、經(jīng)驗性的課程和教學(xué)方法使學(xué)生掌握科學(xué)的思維方法。然而,杜威教育思想中也有不足之處。例如,由于過度強調(diào)兒童當前的直接經(jīng)驗,提倡“從做中學(xué)”,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間接經(jīng)驗在課程和教材中的地位或作用,輕視了系統(tǒng)知識的傳授,從而不可避免地降低了智力訓(xùn)練的標準。這是杜威教育思想受到指責最多之處。杜威是20世紀美國影響最大、爭議最多的教育家,但無論如何,他對教育理論和實踐發(fā)展的貢獻是不可抹殺的,他在課程史上所占有的重要地位不容置疑。
[1][2][4][5][6][7][8][9][10][11][美]約翰·杜威著.王承緒譯.民主主義與教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1,8,72,200,209,207-219,305,353,356,292,10.
[3]王保星主編.外國教育史[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08:362.
[12][13]侯懷銀.杜威的課程觀述評[J].課程·教材·教法,199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