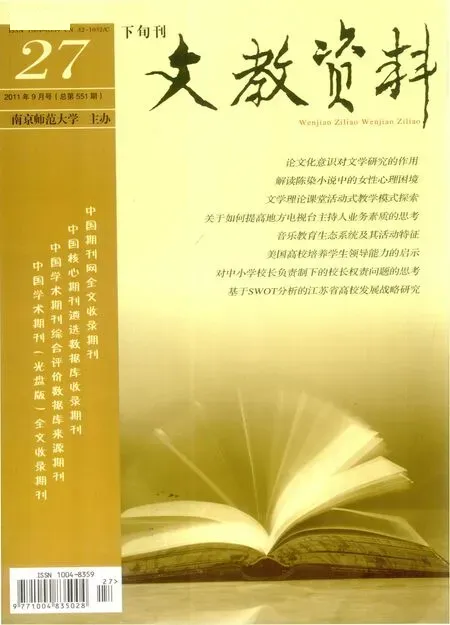從來就沒有什么救世主——《遙遠的救世主》解讀
任文匯
(蘇州職業大學 教育與人文科學系,江蘇 蘇州 215104)
20世紀90年代中期,中國北方小城——古城女刑警芮曉丹受好友肖亞文之托,為其老板丁元英在古城租一套臨時住房。丁元英清華大學本科畢業,并取得了德國柏林大學經濟學碩士學位,利用德國金融公司的資金和自己的頭腦運作私募基金公司,在中國股市進行了掠奪式的經營。可就在私募基金盈利的最高點,丁元英突然以凍結自己資金三年的代價宣布終止合作,暫時隱居古城。在與丁元英的接觸中,芮曉丹被他的叛逆、奇特、不循常規和不可預測的個性深深地吸引,對他產生了眷戀和愛慕。為了明白丁元英所論述的文化屬性,也為了有更多的時間與之相守,芮曉丹決定向丁元英要一件特殊的禮物:讓丁元英在貧困縣里的貧困村——王廟村寫一個脫貧致富的神話。就在丁元英用“殺富濟貧”的方式將要完成對神話的書寫時,芮曉丹在一次與通緝犯的偶遇中被炸毀容,她開槍自殺,而丁元英傷心吐血,最終黯然離去。
故事的結局是丁元英精心設計的格律詩音響公司強行進入市場,成為品牌,而“被劫”的樂圣公司在官司中敗訴,董事長林雨峰駕車自殺,肖亞文出任格律詩的董事長兼總經理。為了利益,樂圣被迫與格律詩在王廟村合作,而媒體則圍繞得救標準與得救之道展開了激烈的辯論。
一個商戰故事,一個愛情故事,互相交匯又各自獨立。本書最牽動讀者的是主人公丁元英,無論從哪個層面看,他都可以說是一個“高人”,不管是小說開頭即放棄的私募基金,還是對王廟村的扶貧,都顯示了他對其時社會形勢極為精準的判斷,說他運籌帷幄一點都不為過。他在股市運作中得心應手,短短幾個月就掙得將近兩倍的利潤,似乎完全破解了股市的密碼。把北京格律詩音響公司和王廟村音箱生產基地設計成兩個法律上相互獨立的實體則表現了他極高的智慧。通過對中國名牌樂圣公司采取一種“殺富濟貧”的方式來完成扶貧“神話”,在此過程中,將要發生的訴訟官司,以及勝訴的必然,格律詩幾位股東的淘汰出局,劉冰因心術不正而走向滅亡,與樂圣公司的最終合作等都在丁元英的預料之中。他對自己及周圍人的判斷幾乎無一不準,而判斷的準確甚至讓他對芮曉丹的未來具有某種預見:“你應該辭職,請注意,是你應該,而不是我希望。只要你一分鐘是警察,你這一分鐘就必須履行警察的天職,你就沒有避險的權利。”[1]丁元英的這段話幾乎準確預見了芮曉丹的死。他的朋友韓楚風、知己芮曉丹都說他“是個明白人”,助手肖亞文這樣評價他:“是魔是鬼都可以,就是不是人 (凡夫俗子,平庸的人)。認識這個人就是開了一扇窗戶,就能看到不一樣的東西,聽到不一樣的聲音,能讓你思考、覺悟,這已經夠了。 其他還有很多,比如機會、幫助,等等。 ”[2]近乎一種高山仰止的崇拜。就連他的對手林雨峰都不得不嘆服他有著“嚴謹的思維和對繁雜事物的精準判斷”。而在王廟村農民的眼里,他更是全知全能的基督耶穌再世,他們把得救的希望全部寄托在丁元英的身上。難怪他從本質上總是把自己放在一個較高位置,以一種居高臨下的姿態俯視他眼中的蕓蕓眾生,“他的每一個毛孔里都滲透著對世俗文化的居高臨下的包容”。
作者試圖把丁元英設計成“進不去,出不來”的高人形象,一個救世主的形象,可是翻開歷史看看,哪一頁哪一行能找到救世主救世的記錄?沒有,從來就沒有。從來都是救人的被救了,被救的救了人。如果一定要講救世主的話,那么符合和代表客觀規律的文化——強勢文化才是救世主,而丁元英正是作為此種文化的載體出現的。作為強勢文化的代表,丁元英對“文化屬性”有著自己的深刻解讀,他認為:“透視社會依次有三個層次,技術、制度和文化。小到個人,大到國家民族,任何一種命運歸根到底都是那種文化屬性的產物。強勢文化造就強者,弱勢文化造就弱者,這是規律,也可以理解為天道,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3]丁元英對強勢文化和弱勢文化進行了解釋:“強勢文化就是遵循事物規律的文化,弱勢文化就是依賴強者的道德期望破格獲取的文化,也是期望救主的文化。”在丁元英眼里,中國傳統文化不過是“皇天在上的文化,是救主救恩的文化”,“傳統觀念的死結就在一個‘靠’字上”。[4]由此他分析:如果一個民族的文化從骨子里就是弱勢文化屬性,怎么可能去承載強勢文化的政治、經濟?衡量一種文化的屬性不是看它積淀的時間長短,而是看它與客觀規律的距離遠近。五千年的文化是光輝、是燦爛,但傳統和習俗得過過客觀規律的篩子。丁元英對人的社會文化屬性問題的見解是如此獨到與精辟,他認為正是獨特的文化屬性造就了許多長期處于愚昧麻木之中的社會人,導致他們永遠貧窮落后。丁元英是明白的,也是孤獨的,正如尼采所說:更高級的人獨處著,這并不是因為他想孤獨,而是因為在他周圍找不到他的同類。
丁元英認為強勢文化的魂就是遵循規律和法則,正是基于這種認識,他在設計格律詩音響公司和王廟村音箱生產基地的相互關系時將兩部分各自獨立,對發燒友組成的音響公司采取股份制方式進行制約,通過強力作用的“殺富濟貧”使得格律詩強行進入市場。對王廟村音箱生產基地則采取“用小農意識治小農意識”的方式,在產品生產各道工序的農戶之間實行小農經濟的買賣關系,現金交易,一環制約一環,誰出問題誰擔責,不影響別人的利潤。允許弱勢文化背景下的農民有一個適應的過程,讓市場去糾正他們,最終用經濟杠桿來解決產品質量和生產成本問題。丁元英不是神機妙算,也不是能力超群,只是尊重市場規律和自然法則,他讓市場規律打開農民的眼界,讓市場的無形之手抑制他們的小農意識,讓那些向來只知道神和上帝是救世主的王廟村村民明白要富強不能靠別人,擺脫貧困的救世主就是他們自己。而他本人不過是在已經緣起的事情里順水推舟,借英雄好漢的嗓子喊上兩聲而已。至于這些農民是否明白市場規律這個“道”,則完全取決于他們自己是否能覺到悟到,正如丁元英說的:“允許幾個股東去扒井沿,能不能爬上來取決于他們自己,對農戶,從基礎設置就不給他們期望天上掉餡餅的機會。我救不了他們,我能做的就是通過一種方式讓他們接受市場經濟的生存觀念,能救他們的只有他們自己。”是的,對王廟村的農民來說,真正的救世主不是丁元英,而是認準市場,吃別人吃不了的苦,受別人受不了的罪,做別人做不到的成本和質量。扶貧的本質在一個“扶”字,如果你根本沒打算站起來,老天爺來了都沒用。扶貧扶什么,扶的就是一種精神,是一種觀念。它既不是簡單的市場競爭,又不是簡單的授人以魚,而是基于一種社會文化認識的自我作為。有人認為幾個股東退股,林雨峰駕車墜崖,劉冰跳樓自殺都是丁元英設計的,事實并非如此,是他們的虛榮,他們特有的文化屬性,以及他們自私的性格屬性決定了他們的結局。正如馮世杰自己所說,他們是“爛泥扶不上墻的貨”,扒著井沿看了回外面的天,又都掉了下去。馮世杰還有改變家鄉貧困的念頭,還有與王廟村的關系,所以最終能夠進入格律詩成為股東,而葉曉明的小農意識則注定他只能在小本生意里打轉轉,終難成大器。劉冰呢,雖說他只是為衣食奔忙的常人,雖說“小人無咎”,但小農意識再加上極端自私貪婪的元素最終導致他自殺。這三種人似乎昭示著三種不同的道路:本質善良還有出路,目光短淺只能在小河里游游泳,而心術不正必將走向滅亡。丁元英給過他們機會。他們“扒著井沿看過一回天”就是明證,后來的墜落不是他所設計,但在他的意料之中,所謂性格決定命運,只是自然規律所致,并非他料事如神。
在扶貧的整個事件里,丁元英沒有任何能讓人感到“神”或救主的招式,每一件具體的事都是普通人都能做到的普通的事,他的的確確是在公開、公平的條件下合理合法的競爭,沒有任何秘密和違法可言,所謂“神話”就是這么平淡、簡單。神是什么?神即道,道法自然,如來。丁元英說過,這世上原本就沒有神話,所謂神話不過是常人的思維所不易理解的平常事。誠然,他所設計的神話無非是遵循了事物的客觀規律,無非是超越了常人所能理解的因果關系而已。
原來能做到實事求是就是神話,能說老實話、辦老實事就是神。由此觀照現實社會,要做到實事求是,需要的是一雙“天眼”,一雙剝離了政治、文化、傳統、道德、宗教的眼睛,然后再如實觀照政治、文化、傳統,把被文化、道德顛倒的真理、真相再顛倒過來。用這雙“天眼”去觀照文化屬性和命運的因果關系,人們才能超越常規的因果思維,才能比較容易看到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當然這還需要當事人自身的悟性。事物的規律本身存在,許多人卻視而不見,而能否看見取決于個體的觀念和認識,取決于個體的經驗和建構,取決于個體能否覺到悟到。從覺到悟到這一點而言,丁元英顯然高于一般人。他不是神,不是救世主,但他做到了其他人做不到的事,同時影響了身邊一群人的改變,僅此而已,也許這就是強勢文化的意義。
從來就沒有什么救世主,想拯救全人類的人骨子里是寂寞,現代社會每個人更重要的使命是自我救贖,以及拒絕被人亂拯救。
[1]遙遠的救世主.作家出版社,204頁.
[2]遙遠的救世主.作家出版社,6頁.
[3]遙遠的救世主.作家出版社,15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