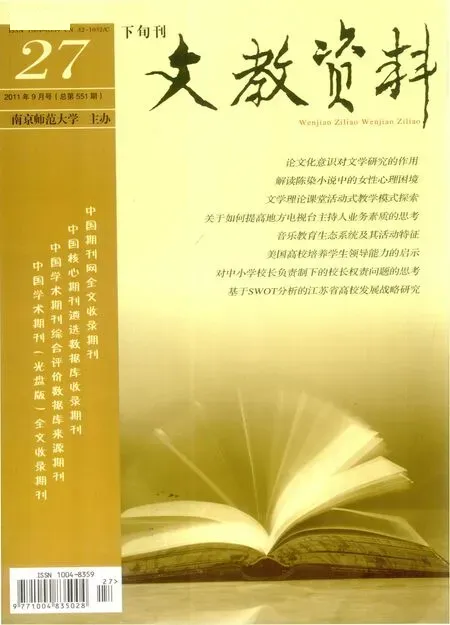從史學角度淺析譚嗣同就義對后世的積極影響
李 銘
(江南大學 萊姆頓學院 學工部,江蘇 無錫 214122)
近年來,隨著我國社會對生命價值觀認識的逐步重視,生命價值這一話題也從個人本位主義思想漸進向對歷史人物的生死價值考評轉移。譚嗣同作為我國歷史上著名的“戊戌六君子”之一,維新志士、變法流血第一人,也成為上至社會各界思想、理論家,下至“90后”年輕一代對于生死價值爭論的焦點之一。在戊戌變法中,曾現多種對于譚嗣同就義的評述。對其犧牲的價值角度而言,分為有意義論和無意義論兩種論調。
譚嗣同其人:譚嗣同,字復生,號壯飛,是清末戊戌變法時期著名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想家和政治活動家。在其三十三年短暫的生命中,有著《仁學》、創南學會、辦《湘報》、開礦山、修鐵路等系列前人未敢嘗試之壯舉。在維新變法中夜訪袁世凱的果敢精神也引得世人稱道。縱論譚嗣同的一生,最大之影響莫過于其犧牲對于后世的積極影響和對中國革命的巨大推動作用。譚氏作為一代封疆大吏之后(其父譚繼洵,咸豐九年進士,先后任甘肅按察使、布政使,湖北巡撫),家庭環境優越,符合紈绔子弟的基本條件,雖“幼喪母,為父妾所虐”,但生于官宦之家,得錦衣玉食未嘗不可,況其父也曾“用重金為譚嗣同捐了一個候補知府的官銜,分發江蘇,等待委任”。[1]可以說譚嗣同的人生之路雖不平坦,卻前途無量,無須說努力進取,只消不與維新活動人士為伍,便可保全性命而后平步青云。但他最終選擇了轟轟烈烈的維新運動,以“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的精神獻身改革。
他的就義在客觀上對歷史的前進,以及后世的革命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他的死已經超越了一個基本意義上的生死觀問題。“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他的死不僅是“重于泰山”,甚至“重逾泰山”。他為后人留下的不單是不懼死的大無畏革新氣概,更重要的是在這豪氣離世的背后,譚嗣同舍生取義的精神感染著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
一、譚嗣同犧牲意義之反對派觀點
對于譚嗣同的舍生取義,世人均給予充分肯定,但對于其放棄機會出逃、拒絕親友營救而“待死”的做法,以及他對“外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2]的觀點,時至今日,有較多的學者和網友予以批駁。主要的反對觀點包括對其繼續生存而為革命奔走的意義更為重大的角度進行假設,并通過魯迅的《藥》這篇小說作為重要的引證進行論述。
對此,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的黃征學先生對此觀點是:“革命是要付出生命的代價,但想要以幾個人的血去喚醒整個民族精神上的麻木狀態,其效果還是相當有限的,……與其這樣,倒不如活著繼續戰斗,喚起更多國人的精神覺醒。 ”[3]
網絡上有一個討論話題:《你同意譚嗣同為變法流血犧牲,最終就義嗎?為什么?》不少人對于譚氏的慷慨赴死頗有微詞:“那時候梁啟超就到逃到日本,然后回來繼續為祖國出力。譚嗣同應該是受多封建愚忠的思想,估計心里想著大不了十八年后照樣是條好漢,想以此來成就自己的威名,我個人是不屑于這種想法的,螻蟻尚且偷生,就不能存下自己的性命待來日東山再起么,而且這種犧牲有用么,魯迅的《藥》就強烈諷刺了這點,愚昧的人用烈士的血當藥引,可笑可嘆。所以我個人不同意! ”[4]
二、譚嗣同就義對于革命者的直接與間接影響
譚嗣同的犧牲對后世具有強大的現實意義,對中國革命具有推動作用。其獻身的壯舉感染著一代又一代的人。譚嗣同的選擇,直接或間接影響著不計其數的后來人。以下列舉的是譚嗣同就義對其直接影響較大的幾位知名人士。
(一)毛澤東,字潤之,中國革命家、戰略家、理論家和詩人,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和領袖,毛澤東思想的主要創立者。
1893 年出生于湖南省長沙府湘潭縣韶山沖。毛澤東所受到的譚嗣同的影響不僅在于毛澤東師從楊昌濟,轉道接受其思想,更重要的是,毛澤東在青年時代對其十分敬仰,特別是在譚嗣同就義后,謂之:“前之譚嗣同,今之陳獨秀,魄力雄大,成非今之俗學所可比。”[5]這在客觀上極大地肯定了譚嗣同就義的歷史作用。身為毛澤東老師的楊昌濟“常以這種精神教導學生,提倡一個準備肩負歷史重任的人,要有為國家、為民族而自我犧牲的獻身精神。這種為‘天下萬世’之‘大我’而敢于犧牲個人‘一身一家’之‘小我’的高尚獻身精神,曾經給毛澤東以巨大的精神激勵,毛澤東不僅恭錄了這段語錄,還記載了……悲壯故事。而譚嗣同則是把此種壯士斷碗精神推向極致的近代湘學人物。”[6]毛澤東在后來中國革命事業中,也傳承了這種不怕犧牲的思想,1945年在中國七大閉幕之際所提到的“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中“不怕犧牲、爭取勝利”的觀點,與譚嗣同就義的積極影響也不無關聯。
(二)楊昌濟,楊昌濟又名懷中,字華生,湖南長沙縣人,倫理學家,教育家。曾赴日本、英國留學。1898年,正值維新運動到達高潮,楊昌濟進入岳麓書院求學,期間,作為學生的楊昌濟積極參與譚嗣同、唐才常等在湖南地區組織的維新改良活動,并參加了譚嗣同組織的“南學會”,成為通訊會友,借此機會向譚嗣同等求教學問,交流思想。可以說譚嗣同的思想對楊昌濟的影響頗深,而譚嗣同的就義徹底驚醒了楊昌濟,之后的一段時間里他認真地分析了國家的形勢,為他在1903年選擇東渡日本求學也奠定了一定的基礎。同時,“他對譚嗣同等六君子為了國家與民族利益舍身就義的獻身精神特別欽佩,認為譚嗣同就是‘死一身一家,而生天下萬世’的‘仁人’,‘成仁而死,則身死而心生;害仁而生,則身生而心死。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譚嗣同變法流血犧牲以后,他多次說:‘譚瀏陽(譚嗣同系長沙瀏陽人,故此名)英靈充塞于宇宙之間,不復可以死矣。’”[7]以上證明,譚嗣同舍生的義舉對楊昌濟的生死觀產生了巨大影響。在譚氏精神的感召下,楊昌濟將這種精神傳遞給自己的學生蔡和森、毛澤東等,是中國革命運動中無數英烈舍生成仁的思想的重要來源之一。
(三)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就義對于康有為、梁啟超來講頗具爭議。根據一些資料記載,康、梁對于譚氏的就義有較大的震撼,很快為其寫傳記、做《六哀詩》。但康梁二人具有的保皇立場,促使他們敏銳地認識到,可以借此全國上下有識之士哀悼譚嗣同的時機,編造譚氏《絕命書》、撰寫具有康梁思想觀念的《譚嗣同傳》,目的是接具有較大影響力的譚嗣同就義之事件,傳播觀點。“他們看到譚嗣同有崇高的聲譽,就想利用譚氏的影響,宣傳自己的觀點……”[8]。對此,我們不去參與專家們對于康梁“偽造事件”真偽的辯論,也暫且不去談論康梁的行為是否是君子行為,單從“利用譚氏”就可看出,在當時的特殊歷史條件下,譚嗣同的就義對于社會影響頗深。
(四)唐才常,字伯平,號佛塵,湖南瀏陽人,清末維新派領袖,與譚嗣同同鄉,同師承歐陽中鵠,在長沙時務學堂他與譚嗣同并稱“瀏陽二杰”。譚嗣同的就義對于唐才常的影響同樣是巨大的,在得聞譚氏就義的消息后“……痛哭失聲,立即由漢口趕往上海,準備赴北京收尸”,[9]并作一挽聯致哀:“與我分別幾許時,忽警電飛來;忍不攜二十年刎項交,同赴泉臺。”[10]以上足以見得兩人感情之深厚。而在變法失敗后,我們可以認為,唐才常組建自立軍更是從實踐中回應譚嗣同的就義,以此探索通過武力改良探索出新途徑。但最終由于階級立場的不確定,以及“對康、梁則曰勤王,對留學生則曰保國保種”,[11]最終受累于康有為的起義資金未到,起義延期導致事情敗露,被張之洞逮捕就義于武昌紫陽湖畔。臨行前他吟道:“七尺微軀酬故友,一腔熱血灑神州。”[12]當中所提到的“故友”就是指譚嗣同,足以見得譚嗣同就義已深深影響著唐才常的人生觀。極為巧合的是,唐才常就義時年僅33歲(1867—1900),這與譚嗣同度過的33年生命歷程(1865-1898)有著驚人的相同之處。
(五)鄒容,原名紹陶,又名桂文,字蔚丹,留學日本時改名為鄒容。四川省巴縣(今重慶巴南區漁洞)人,是我國近代著名的資產階級革命宣傳家,《革命軍》的作者。鄒容從未與譚嗣同相逢,1898年戊戌變法,鄒容只有13歲,年輕的鄒容熱衷于讀新報,學習新知識,所以他對維新運動關注較多,在維新派中。鄒容最仰慕的就是譚嗣同,在譚氏就義后,鄒容“立志繼承譚嗣同的未竟事業,曾題悼詩曰:‘赫赫譚君故,湖湘士氣衰,惟冀后來者,繼起志勿灰。’”[13]以表達對于譚嗣同未竟事業的繼承與向往。其后鄒容為了能夠不斷激勵自己,寄托對譚氏的緬懷之情,“將譚氏的遺像放在坐側,并題詩于其上……勉勵自己以譚嗣同的奮斗犧牲精神,從事革命”。[14]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譚嗣同就義對于年輕革命者思想上的影響。“鄒容從譚的血腥味中覺悟到,滿清王朝朽木不可雕,指望和依靠清廷去擺脫這個政權體制本身所釀成的巨大危機,掃除弊癥,革新陳規,去圓強國之夢,是一個永遠達不到目的的空想”。[15]在選擇革命以外的途徑被證明行不通之后,譚嗣同的血使改良者轉變成了革命者,也只有通過暴力革命的手段,才能尋找到一條新路。
三、譚嗣同就義對于后世的精神影響
根據譚嗣同就義后對于社會各界以及不同層次人士的影響,我們不難看出,譚嗣同所具有的舍生和大無畏精神是中國革命精神的重要來源之一。以上所列舉的受其影響人物僅是十之一二,譚氏就義的影響,激勵著嚴復、黃遵憲、宋恕、孫寶瑄、蔡鍔、畢永年、林圭、陳天華等許多進步人士在各自領域去爭取變革的夢想。對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譚嗣同就義的歷史意義遠遠大于其“茍活于世”的現實生命意義。“留得青山在,不愁沒柴燒”不適合譚嗣同這類堅定的真理追求者,也并不符合他骨子里天生的“‘不合乎公理’,就是圣人的教誨,也要揮筆批判”[16]的倔強性格。魯迅先生曾說:“我們自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17]譚嗣同就是這些舍身求法之人中的典型代表。他一人之死,可以激勵千千萬萬人受他精神的感召去努力進行變革;他一人之死,要比其生存、或他人之死使社會進步所得到更多的價值。“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并不僅僅是一句聽起來氣勢磅礴的口號,那更是需要有人獻身的超人勇氣,譚嗣同做到了。譚嗣同獻身改革的精神亙古不滅,事實證明,他的血喚醒了不屈的民族抗爭精神,他的犧牲對中國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向新的社會性質變革起到了精神上的引領作用,他的就義是中國國運由衰敗到昌盛的轉折點。
[1]李喜所.譚嗣同評傳[M].河南教育出版社,1986.10:115.
[2]譚嗣同傳.戊戌變法,(第4冊),第53頁.
[3]吳曉燕.死,還是不死,這是一個問題——對哈爾威船長、項羽、譚嗣同三人生死抉擇則的探討[M].聚焦·評論.
[4]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188558658.htm l網友:夢之影2793.
[5]張昆第日記,1917-9-22.
[6]申忠民,羅金梅.論譚嗣同對青年毛澤東思想形成的影響[J].文學界(歷史回廊).
[7]論楊昌濟的民族倫理觀及對青年毛澤東的影響[J].前沿,2010,(6).
[8]王俊義.論譚嗣同的改革獻身精神.見戊戌維新運動史論集[M].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8:232.
[9]譚嗣同評傳[M].河南教育出版社,1986.10:282.
[10]飲冰室詩話十九[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