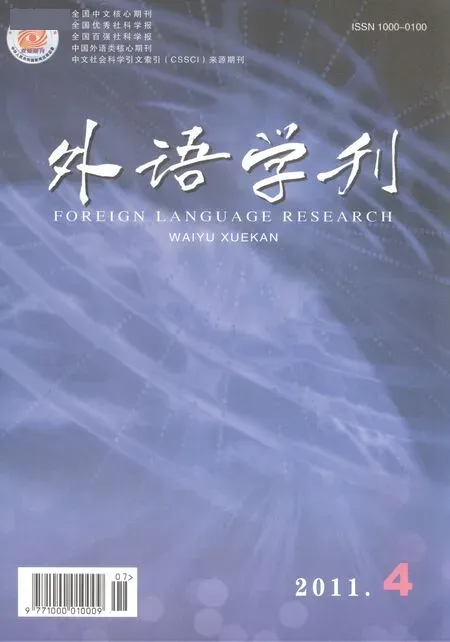人體詞語詞義轉喻性研究*
黃碧蓉 于 睿
(上海海洋大學,上海201306/復旦大學,上海200433;哈爾濱工業大學,哈爾濱150001)
我們的身體被“作為一種基質”用于“認識和體驗世界”(萬晉紅2009:9-11),歷經幾千年這種“體認”世界的過程,表身體各部位的人體詞語的意義相應地被賦予厚重的隱喻性和轉喻性。因篇幅所限,本文擬對人體詞語詞義的轉喻性做專題探討,其隱喻性將另文研究。
認知語言學家在經過大量的研究后發現,轉喻在一定程度上比隱喻更為基本,是比隱喻更為基本的認知現象(Panther& Radden 1999,Koch 1999,Taylor 1989,Radden & K?vecses 1999,Barcelona 2003)。在轉喻中,涉及的是一種“接近”和“突顯”的關系,事物容易理解或容易被感知的屬性或方面被用來代替事物的整體或事物的另外某一方面或部分(Lakoff 1987:77)。
通過對人體詞語進行批量考察,我們發現其詞義的轉喻操作依據鄰近性基本涉及以下4類情形:人體部位與其主體——人相鄰近,繼而人體詞語用作轉指人;與人們的認識、實踐活動相鄰近,繼而人體詞語用作轉指長度單位;與其某一突出特征或功能相鄰近,繼而人體詞語用作轉指人體相應部位的特征或功能等;與它相應的動作、行為等相鄰近,繼而人體詞語用作轉指人體部位相應的動作行為。下面擬對人體詞語的這4種轉喻操作類型逐一進行解析,藉此探討人體詞語詞義的轉喻性特征。
1 人體詞語轉指人
人體部位與其主體人不可分割,是人身體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用人體詞語轉指人是轉喻中部分轉喻整體的一種,或稱提喻。如一位生病住院的教師用“眼睛”轉指她的學生:“我必須盡快回到講臺,幾十雙眼睛在期待著我。”她突顯的是學生們帶著期盼神情的眼睛。同樣,我們經常會說,“今天來了不少新面孔”、“Today come some new faces.”用突出呈現于我們面前的“面孔”、“face”來轉指人。很多表外顯部位的人體詞語都能轉指人。如,“head”:a hot head(急性人),a cool head(冷靜的人),a hard head(頑固的人),a wooden head(笨蛋)等。“頭”:賊頭、姘頭、牢頭、獄頭等。
“頭”的同稱詞“首”也可轉指人:元首、首腦、首相、首長等。
此外,“mouth”/“口”、“hand”/“手”、“ear”/“耳”等均能轉喻指人。如:“mouth”/“口”、“嘴”——“the hungry mouths(饑餓的人們)”/人口、名嘴。“hand”/“手”—— a green hand,an old hand,Many hands provide great strength/新手、老手。“ear”/“耳”—— Wall has ears/隔墻有耳。“foot”/“腳”—— foot(步兵)/腳夫。
英語中,外顯部位對應的詞轉指人的現象很普遍。
“finger”—— 警察、告密者。如:Catch the finger.He set the police on us.
“nose”—— 暗探或告密者。如:Try to find out the nose.
“body”—— (法律用語中的)人。如:heir of the body(直接繼承人)。
“thumb”—— “Tom Thumb”是16世紀英國童話里的小人兒,后來指侏儒、矮子、不重要的人物。
“neck”—— a stiff neck(固執的人)。
“leg”—— 騙子:That guy is a leg— He will cheat us if he has a chance.;a leg of the law(警察、律師、執法人員);all legs(and wings)(個子過高而手腳沒處放的青年人)。
“back”—— 足球后衛。如:a full back(后衛球員)。
英漢語中的內臟詞語“heart”和“心”、“liver”和“肝”也都能轉指人:
“heart”—— one’s dear/sweet heart(愛人、情人)。
“心”—— 甜心、心腹、心肝、心尖兒。
“liver”—— a good liver(有道德的人,美食家)。
“肝”—— 心肝。
此外,能轉指人的詞還有很多,包括“bone”和“骨”、“flesh”,“brain”,“bladder”,“ass”,“lung”等。
我們認為,人體詞語部分轉喻整體是人類心理完型趨向律的作用。完型即格式塔,是一個由有著相互聯系和影響的各部分組成的有機整體,而整體大于各部分之和。完形結構作為整體比它的組成部分在認知上反而簡單,也就是容易識別、記憶和使用,這已經得到許多心理學實驗的證明(如Pomerantz et al.1977:422-435)。人的大腦在一般情況下,總是趨向于根據過往經驗或基因中所傳承的經驗,通過發現各部分的最優組合,主動地構建整體(謝之君2007)。如,你只要看到坐在主席臺上發言者的臉,根據經驗,你會自動推知他有身體和四肢,而不僅僅是一張臉。“在認知所熟悉的事物的時候,你的大腦能自動補全缺失的組成成分。”(嚴辰松2007:41-45)只要主要條件允許,心理的組織作用總是力趨于完善。這也就是人體詞語之所以能夠以人體部分轉喻人體整體的根本原因。
2 人體詞語轉指長度單位
人體部位與人們的認識和實踐活動緊密相關。人們用自己的身體親歷感知客觀世界,在客觀世界中開展實踐活動。人們的身體有時也被當做一種工具。在被當做工具時,由于鄰近性和突顯關系的作用,人體部位就被賦予相關工具的概念,從而人體詞語就被賦予這方面的意義。肢體名詞和其它表示人體外在部位的名詞用作長度單位名稱就是這種情況。
在許多語言里,非標準長度單位常與人度量時的肢體姿態有關,這是人類普遍運用手或腳作為測量工具的結果。
初民們在計算事物時,無法直接計算,只得借助自己的肢體作為計數工具。他們用來丈量長度的標尺是手、手指、肘、雙臂、腳和步子等,即所謂“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大戴禮記·王言》)。
原始語言都借用人的肢體來計量長度(斯皮爾金1956)。迄今,我們仍然沿用這種古老的方法進行一些粗略的測量(龔群虎1994:42-48)。
大家非常熟悉的英制長度單位“foot”(腳、尺)就是用腳板測量經固化后的長度單位,為人體一腳的長度,約12英寸,或13碼。漢語民族人們習慣用“(腳)步”做長度測量單位。如宋沈括《夢溪筆談·官政一》中記載:“其城不甚厚,但馬面極其長且密。予親使人步之,馬面皆長四丈,相去六七丈。”其實,“foot”和“(腳)步”作為長度測量單位,具有語言普遍性。表示“腳”的詞如拉丁語pes,法語 pied,西班牙語 pie,德語 Fuss,英語 foot,荷蘭語 voet和土耳其語ayak都在各自語言中表示“尺”這一長度單位。以與肢體名稱相關的“跬、步”為長度單位的也有普遍性。拉丁語passus(步)作為長度單位,為5羅馬尺,約1.5米;土耳其語adim(跬),也用作長度單位,其派生詞adimla意思是用步測量;古代中國周代八尺為步,秦代六尺為步,一步為二跬,與之類似。
有趣的是,古拉丁語中的固定長度單位幾乎全部是使用與人的肢體或跬步相關的詞來表達的:
拇指(pollex):寸,約2.5厘米;
掌(palmus):約7厘米;
足(pes):尺,約30厘米;
掌+足(palmipes):約37厘米;
肘(cubitus):肘尺,約44厘米;
步(passus):約1.5米;
十 +足(decempeda):約3米;
千 + 步(mille passuum):約1.5公里。
(同上)
英語中的肢體詞語,如“hand”,“thumb”,“finger”和“palm”均可作為非標準長度測量單位。“hand”為一手的寬度,約3-4英寸,多用于測量馬匹的高度。“thumb”表示一拇指寬的寬度,約等于1英寸;“finger”既可表一個手指的寬度(約3/4英寸),又可表一指的長度(約為4 1/2英寸);“palm”表示一個手掌的寬度,約3-4英寸,或整個手即手腕到手指尖的寬度,約7-9英寸。
同英語“finger”一樣,漢語“指”這個長度單位也是一個手指的寬度。“肘”為一小臂之長,這個漢語長度單位最開始借自梵語,是古印度的長度單位。唐玄奘《大唐西域記·印度總述》:“分一弓為四肘,分一肘為二十四指。”
除了肢體部分詞語外,其它部位的詞語,如“head”,“neck”和“nose”因其相應部位為三維空間實體,也被用來作長度測量工具,從而也可表示長度單位。“head”意為一個頭的高度或長度,如taller by a head,cut short by the head等。“neck”和“nose”一般用于賽馬中,表示馬頸(鼻)的距離,意為微小的距離,如to win/lose by a neck(nose)(稍勝∕負、小贏∕輸)。
人體詞語轉指長度單位是以工具代結果的部分與部分之間的轉喻關系。
3 人體詞語轉指相應部位的特征或功能
人體部位如“舌”∕“tongue”能說出話語,根據這一鄰近性特征,“舌”∕“tongue”這個詞語由本義“一種人體器官”轉指“言語”/“speech”。如:舌戰、to keep one’s tongue(不要說話)。
“tongue”說出的言語隸屬于某一種特定的語言,由這一鄰近性“tongue”可轉指“語言”,如 mother tongue,native tongue等。
可轉指“說話”、“speech”類的人體詞語還包括“口”、“嘴”∕“mouth”,“唇”∕“lip”,“齒”∕“tooth”等,這些都是與說話功能相關聯的口腔部位的詞語。如:
“口”、“嘴”∕“mouth”:口授、多嘴、smart mouth(油嘴滑舌)。
“唇”∕“lip”:唇舌;pay lip-service to(sth)(說漂亮話,花言巧語)。
“齒”∕“tooth”:不足掛齒;cast sth in sb’s teeth(意為:reproach sb with sth以某事責備某人)。
“齒”在講話發音過程中發揮重要的作用,所以,詞語“齒”還轉指“發音”。如夸獎一個人“口齒清晰”等。
另外,“齒”總是隨著年齡的變化而不斷改變,所以中國古時在年齡與牙齒間也常常出現互代的情況。年齡常被稱為“年齒”,老年被稱為“老齒”、“暮齒”,壯年、年輕時則被稱作“壯齒”、“茂齒”,幼年、童年又被成為“幼齒”、“童齒”、“弱齒”。此外,農業國的中國古代牛馬是很重要的耕地和運輸工具,人們對其關愛有加,細心觀察,發現它們每遞增一歲牙齒就多長一顆,由此,“齒”轉指“牛馬的歲數”。同樣,觀察牛馬“口”生長的情況,也能看出它們的年齡,所以,“口”也轉指“牲口的年齡”。如周立波《暴風驟雨》第二部二四:“拴在老榆樹左邊的那個青騍馬,口小,肚子里還有個崽子。”
還有一些以功能為強勢特征的部位如:“眼”∕“eye”能看;“耳”∕“ear”能聽;“鼻”∕“nose”能聞;“手”∕“hand”能創作;“腳”∕“foot”能步行,這些部位的相應詞語都能轉指這些功能。如,“眼”∕“eye”:“眼光、眼力”;“耳”:“聽力”;“ear”:“聽覺;(尤指音樂和語言的)辨音力、聽力”;“鼻”∕“nose”:“嗅覺”;“手”∕“hand”:“手藝、技能”;“腳”:“腳步、奔走”;“foot”:“步態”等。
內臟各器官內隱,一般情況下,人們缺乏對它們的直觀感知,除了對其“功能”有一些認知。然而,我們所認知到的內臟的功能并非這些器官本身真正具有的功能,而只與人們的情感、情緒、膽識密切相關。這種現象在各種語言中都很常見。Kurath(1921)指出:印歐語言表示情感的詞常常來源于某些詞,這些詞指稱物理行為,或是指稱伴隨相關情感的感覺,或是指稱受生理反應影響的身體器官。例如,心臟抽取血液的生理功能強烈而顯著地受到愛、興奮、害怕以及其他激烈情感的影響,因而“心臟”成為這些強烈情感的象征——例如“勇氣”和“激情”(Sweetser 1990:28)。這說明,人們賦予內臟情感功能是因為情感激烈時內臟功能增強,給人帶來相對直觀的體認經驗,所以詞義突顯這些功能特征并轉指這樣的功能。漢語內臟詞,不僅“心”本身具有“內心情感”之轉指義,受傳統中醫的影響,受其轄制的其它內臟器官的詞語,如“肺”、“肝”、“腸”、“膽”很早也有表情感的習慣。如“肝火”指容易急躁的情緒,“肝怒”指容易發怒的心理狀態;“愁腸”指郁結愁悶的心情,“柔腸”指纏綿的情意,“腸斷”形容極度的悲痛,“熱心腸”指熱情等。
人體詞語轉指人體相應部位的特征或功能是以施事代受事的部分與部分之間的轉喻關系。
4 人體詞語轉指人體部位相應的動作行為
事物的概念總是和其動作的概念相關聯,我們在頭腦中想象事物時經常會聯想到跟它相關的動作。就人體部位而言,我們會從人體部位聯想到它發出的動作或行為。而當我們聚焦于人體部位的動作和行為時,由于鄰近性的聯結作用,人體詞語表述的概念便可從描述人體部位的性狀域轉移到描述它的動態行為域,即人體詞語的意義發生跨類轉移,按傳統語法所說,由名詞轉變為動詞。如在I footed 20 miles home yesterday一句中,foot這個部位的部分形貌特征的義素在隱退,著眼于“用腳行走”的動作義素,從而由名詞變成動詞。我們認為詞性的轉化是其基本詞性經鄰近性關聯通過轉喻思維轉換的結果,突現的是事物的不同方面,同時也是用一種經歷、體驗或存在來構建和設定另一種經驗與存在,使之更直接,更形象。
人體詞語轉指人體部位相應的動作行為,繼而由名詞轉類為動詞,在語言中不是孤立、個別或臨時的現象,而是極為普遍的。人體部位的大部分詞語都能轉用為動詞,從而構成一個較大的人體詞語名詞動用的系統。我們以英漢語為例,以從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牛津英語大詞典》)中提取的41個英語人體詞語和從《漢語大詞典》中提取的55個漢語人體詞語(這是我們作定量考察所建的小型人體詞語語料庫)為對象進行考察。
在這些詞中,英漢語里都能名詞動用的有:“head”/“首”、“eye”/“眼”/“目”、“mouth”/“嘴”/“口”、“tooth”/“牙”/“齒”、“face”/“面”、“nose”/“鼻”/“ear”/“耳”/“brain ”/“腦 ”/“back ”/“背 ”/“arm ”/“臂 ”/“neck ”/“脖”/“shoulder”/“肩”/“body”/“身”/“體”/“hand”/“手”/“knee”/“膝”/“palm”/“掌”/“finger”/“指”/“elbow”/“肘”/“belly”/“腹”/“foot”/“腳”/“足”/“toe”/“趾”。
這類詞語數量較多,共有21組詞,其中英語人體詞語21個,漢語人體詞語26個,漢語人體詞語數量多于英語人體詞語,這是由于漢語人體詞語中存在較多的指稱同一人體部位或器官的同稱詞。
只在英語里名詞動用的:“brow”,“tongue”,“skin”,“throat”,“breast”,“heart”.
只在漢語里名詞動用的:“額”、“頂”、“顏”、“膽”。
英漢語中都不能名詞動用的:“waist”/“腰”、“wrist”/“腕”、“lung”/“肺”、“kidney”/“腎”、“liver”/“肝”。
經分析我們發現,涉及到頭部和身體其它部位的詞語,大多都能轉用為動詞,這和這些部位外露,發出的動作和行為易被察覺到,容易被作為注意的焦點而被前景化有關。但是,我們同時也注意到,同是身體部位的“waist”/“腰”、“wrist”/“腕”,無論在英語還是漢語里,都不能轉用為動詞,這也許跟這些部位不夠靈活,不易發生動作有關。
另一個顯著的現象是,內臟詞語一般難以發生名轉動的轉換。這不難解釋,因為“內臟各器官內隱,對人們來說,是抽象不可見之物,不被人注意……”(黃碧蓉2010:118-125),雖然它們在人體內為維持人的生命不斷地在運動著,但這些動作或行為因為沒能被我們所感知和體驗,不能引起我們的關注,更無法從認知上去突顯了。因此,它們很少發生轉類。
須要說明的是,英語里人體部位名詞動用的情況總的說來要比現代漢語多很多。在我們統計的漢語人體詞語的名詞動用中,有不少是古代漢語遺留下來的,因而在使用上帶有一定程度的書面語性質。這跟現代漢語的雙音節化有很大關系。如在英語里我們說The child is eyeing the chocolate.(那孩子直盯著巧克力),古漢語也有類似說法,如《漢書·樊噲傳》:“初入營,營衛止噲,噲直撞入,立帳下。項羽目之,問為誰。”在現代漢語中,由于“目”已經雙音化為“眼睛”,已經不再保留“目之”這類的用法,而用詞組“用眼睛看著他”取而代之。
人體詞語轉指人體相應部位的動作或行為是以施事代行為的部分與部分之間的轉喻關系。
5 結束語
意義是語言存在之根本。對于何為意義,它與世界的關系怎樣,一直是哲學家們和語言學家們關注的焦點。意義理論走過最初的指稱論到達現行的認知論,擯棄前者將意義等同于指稱對象的孤立、片面、靜止的詞義分析方法,選擇后者,把與語言密不可分的人的因素納入意義考慮的范圍,主張“詞的意義是人對非語言世界事物的認知結果”(李洪儒1999:61-69),與人類的身體經驗、認知過程等密切相關,關注體現在語言中的人類經驗意義的多樣形式,考察認知主體的思維操作,從而使意義研究呈現動態化、個性化和具體化特征,能夠相對較好地闡釋意義復雜的多維性。
我們特別選取被稱為元語言的人體詞語進行詞義思維操作考察,對其詞義轉喻性特征的四種情況進行較為細致的探討。
轉喻具備便利性,即只要存在鄰近性,就可發生轉喻操作,而通常人們越認識的事物或越熟悉的概念,就越能了解和挖掘到它與其它事物或概念間的鄰近性關系,轉喻操作就越頻繁,也就越能產生轉喻意義。人體的部位從民俗角度來看大部分是人們都熟知的,我們每天用手工作、用腳走路、用大腦思考問題,真切感覺到情緒變化時心跳節律的改變。因此,人體詞語詞義的轉喻性是一個極其突顯的特征,前面闡述的僅是其中的一部分,并未窮盡所有,如人體詞語還轉指人體相應部位功能之結果或產品等(“手”/“hand”:書法、手跡;“趾”:蹤跡等)。
另外,隨著客觀世界的發展,人類的認知思維不斷推進,總是由具體趨于抽象。新事物和新現象不斷涌現,由于我們身體的經常接觸和認識,新的鄰近性又被發現,新一輪的轉喻機制又開始運作,新的轉喻義又被衍生出來。這一點在“手”詞語的量詞義上表現得較為明顯。“手”由最初長期計量可數實物的“個、只”,轉為在商品社會中逐漸用于計量服裝等抽象事物。發展到現代社會,又應股票市場確定交易單位之需,被進一步抽象,得到一個表抽象量的集合性量詞,表示交易中一個整體的單位量,100股即“一手”。
因此,從共時來看,我們對人體詞語詞義的轉喻性揭示得不夠充分,尚需繼續給予關注;從歷時來看,人體詞語詞義的轉喻性處于動態變化中,對人體詞語詞義轉喻性的揭示是一個漸進的過程。
斯皮爾金.在人類發展的早期階段上抽象思維的形成[A].言語思維意志感情及其他[C].北京:科學出版社,1956.
龔群虎.人體器官名詞普遍性的意義變化及相關問題[J].語文研究,1994(4).
黃碧蓉.從人體詞語的意義分布看語義的認知性[J].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6).
李洪儒.認知鏈條上詞的意義與指稱對象[J].外語學刊,1999(1).
萬晉紅.語言與身體[J].外語學刊,2009(6).
謝之君.隱喻認知功能探索[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
嚴辰松.“給予”雙及物結構中的轉喻[J].外語學刊,2007(2).
Barcelona,A.Introduction.The Cognitive Theory of Meta-[A]. ,Antonio(eds.).Metaphor and Metonymy at the Crossroads[C].Berlin:Mouton de Gruyter,2003.
Kurath,Hans.The Semantic Sources of the Words for the E-motions in Sanskrit,Greek,Latin,and the Germanic Languages[M].Menasha(Wisc.):Banta,1921.
Lakoff,G.Women,Fire,and Dangerous Things: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7.
Panther,Klaus-Uwe& G.Radden.Metonymy in Language and Thought[C].Amsterdam:John Benjamins,1999.Pomerantz,J.P.et al.Perception of Wholes and Their Component Parts:Some Configural Superiority Effects[J].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Human Perception and Performance,1977(3).
Radden,G.& K?vecses,Z.Towards a Theory of Metonymy[A].In K.Panther& G.Radden(eds.).Metonymy in Language and Thought[C].Amsterdam:John Benjamins,1999.
Sweetser,E.From Etymology to Pragmatics:Metaphorical and Cultural Aspects of Semantic Structure[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Taylor,J.R.Linguistic Categorization:Prototypes in Linguistic Theory[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