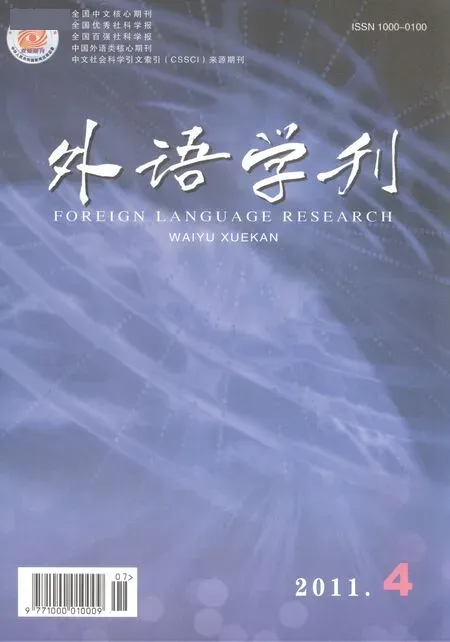俄羅斯神經心理語言學研究*
趙秋野
(哈爾濱師范大學俄語教育研究中心,哈爾濱150080)
1 引言
21世紀,世界范圍內更加關注對人類自身的認識,關于人的科學的研究、人腦科學的研究越來越受到重視。由于俄羅斯神經語言學和心理語言學研究始終結合得很緊密。在近幾年更是把對大腦中人的語言表征研究更多地與思維心理、個性、民族心理語言學等問題相結合。2007 年,俄羅斯學者謝多夫(К.Ф.Седов)首次使用神經心理語言學(нейропсихолингвистика)這個術語,試圖運用神經心理語言學方法解決言語理解和生成、言語交際的深層次問題。應該說,俄羅斯在神經語言學、心理語言學整合研究方面成績突出,得出了獨特的關于大腦兩半球俄語言語功能分布的研究結論。習得語言、學習語言、研究語言、言語交際、話語建構與理解都要通過大腦,神經心理語言學就是研究大腦的言語機制、心理機制、認知機制是如何影響言語交際的。
俄羅斯神經語言學研究始于20世紀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是心理學、語言學、神經學三個學科的交叉研究。20世紀末,俄羅斯神經語言學擴展了自己的研究領域和界限,與迅速發展的心理語言學的關系越來越密切,神經心理語言學應運而生。謝多夫(2007)指出,在某種意義上這個術語是作為神經語言學的同義詞使用的,這一知識領域應作為心理語言學的分支學科。因為俄羅斯神經語言學的研究已融合了思維心理學、個性心理學、民族心理語言學等眾多領域,而且俄羅斯心理語言學的產生和發展也始終是以神經語言學為理論基礎的。經歷了半個多世紀的發展,俄羅斯心理語言學把語言個性(языковая личность)①看做是研究客體,而作為個性心理方面的交際能力是其研究對象。對語言能力(又稱語言意識,языковое сознание)②的研究擴展到對交際能力的全方位研究,使心理語言學超越了自己的邊界,涉及到認知學、語用學、社會語言學、心理學和生理學。這樣,心理語言學研究的外部框架和內部學科的劃分都變得模糊。俄羅斯學者將心理語言學分為普通心理語言學及其分支學科。普通心理語言學包括:思維心理語言學、意識心理語言學、話語心理語言學和神經心理語言學或稱大腦心理語言學。神經心理語言學的研究對象是人的交際能力的大腦組織,人的大腦不僅反映語言結構,還反映人的交際能力。在這個交際能力的框架中語言和意識、言語和思維、詞匯和形象、言語和非言語符號成分共存、交錯。作為大腦功能的交際能力是交際者在各種不同的社會交際情境中言語生成、理解過程和復雜機制實現的保障,俄羅斯心理語言學正是研究這些過程和機制的科學,它也因此將神經語言學(大腦心理語言學)關于說和思維能力的個性心理研究問題作為自己的研究任務。
在俄羅斯心理語言學將研究領域拓展到神經語言學的同時,當代俄羅斯神經語言學流派的形成也部分地與心理語言學流派相關。20世紀60-70年代,俄羅斯心理語言學事實上已完全確定了自己的研究領域,并在語言個性的個性心理特點的理論探索方面取得了成就。維-列心理語言學學派和同樣被稱作莫斯科學派的神經語言學流派相互輝映。與俄羅斯心理語言學維-列流派并行產生的還有另一些心理語言學流派。以薩哈爾內(Л.В.Сахарный)為創始人的彼得堡心理語言學派的研究成果在神經心理語言學的形成中起到了特殊作用,以巴洛諾夫(Л.Я.Балонов)和杰格林為首的彼得堡神經語言學派與心理語言學理論進行了結合,其研究總是有著《神經+心理語言學》的聯系,而神經心理語言學這個術語更適用于這一科學流派。
2 俄羅斯神經心理語言學的理論淵源
俄羅斯神經心理語言學的產生、形成汲取了俄羅斯人文和自然科學的思想,主要是來自語言學、心理學、生理學理論的影響。
2.1 語言學的影響
俄羅斯神經心理語言學最早受到的語言學影響就是博杜恩.庫爾德內(Бодуэн де Куртенэ 1845 -1929)的當代人文中心主義語言學思想,即語言學的研究中心不是語言,而是人的語言交際能力。他的一些語言學理論表述與當今一系列體驗語義學(корпореальная семантика)、生物語言學(биолингвистика)等論著中的觀點有驚人的一致(參見 А.А.Залевская 2002;А.В.Кравченко 2004)。他指出,“由于語言的基礎是純心理的、大腦中心的,因此,語言學應屬于心理科學。但是,又由于語言僅僅在社會中才得以實現,而且由于人的心理發展通常僅僅是在同別人的交際中才是可能的,因此,語言學是社會心理科學。(Бодуэна де Куртене,1963в:217)。謝爾巴(Л.В.Щерба)以其“語言現象的重要方面的作用”這一理論基礎武裝了俄羅斯心理語言學理論,他的語言現象是指同時既是生理心理現象又是社會現象的個人言語組織。他引入了“個人生理心理言語組織”(психофизиологическая речев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индивида)的概念,這個“組織”和依靠它保障的言語活動一起成為社會產品。這個“言語活動”是“說和理解的過程”。(Л.В.Щерба 1974:25)。20世紀30年代雅可布遜(Якобсон)專門從事過神經語言學研究,他將語言學觀引入病理學中,在他之前主要描述的是大腦損傷后的神經心理指數,如動力性、知覺性,而語言學的事實(音位、形態、句法等)被忽視了。他提出的選擇二分法思想對盧利亞神經語言學形成給予了很大影響,具體是指語言單位的聚合(類似、相像)和組合(單位的外部交叉、相鄰關系)關系。巴赫金(М.М.Бахтин)的語言哲學(符號學、話語學、語言活動和人的現實社會存在的關系學說)、文化哲學思想也影響了俄羅斯心理語言學的發展,而心理語言學理論又始終影響著神經語言學的發展。
2.2 心理學影響
維果茨基(1934)創建的文化歷史心理學流派引領了俄羅斯心理學、神經語言學、心理語言學的發展。他創立了心理語言學的動態組合單位分析學說,深刻分析了語言與思維的關系,提出了“內部言語”(внутренняя речь)說,并創立了言語生成模式。他認為對作為動態的功能系統——詞匯的研究應是跨語言、跨學科的,如神經心理視角的研究。他指出,意義是從思想到詞的途徑,應探討意義的心理結構和言語句神經心理產生過程層級的內部結構。維果茨基曾寫到,“我看到了思維整體行為中的一切,但是我把言語中的一切劃分成單獨的詞……在思想中同時存在的內容,在言語中演替展開……從思想到言語的轉換過程是一個相當復雜的過程,是思想切分和思想在詞匯中再生的過程”(維氏未公開發表的手稿)。
2.3 生理學影響
別林施坦(Н.А.Бернштейн 1966)的生理積極性理論是神經心理語言學的生理基礎。他認為,人的活動是有動機、目的的,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就得計劃行為,并且必須選擇某種方式解決問題。在選擇方式之后,計劃行為并付諸實現。行為實現的機制、監控機制、矯正機制等都有神經系統的保證。別林施坦對于運動模式的描寫具有普遍意義,因為言語建構的過程也正是這樣實現的。盧利亞在《學術道路》(1982)中提到,關于運動型損傷由兩種形式(傳入的和傳出的)構成的假說正是受了別林施坦的“雙中心”原則的影響,即大腦半球后面神經系統和前面(動力)系統共同作用及相互適應原則。
3 俄羅斯神經心理語言學研究內容
3.1 莫斯科學派
神經語言學是心理語言學研究方法之一,盧利亞的神經心理理論是其神經語言學觀的基礎。他(1973:12)認為,心理過程是復雜的機能系統,它不單是局限于狹小的有限的大腦區域,而是以大腦結構共同協調的復合體來實現的。同時,每一個結構又在這個協調工作中起著獨特的作用。他把以各種形式參與心理活動的大腦分為三個主要功能區,在總結了這些功能區的工作原則后,指出:意識活動的每種形式都是一個復雜的功能體系,它的實現必須依靠大腦三個功能區的協同工作,并且每一個區域都為心理過程的整體實現起了各自的作用。換句話說,任何有目的的行為都得依靠大腦不同部位的協同工作。他關于語言結構和大腦構造的理論基礎被稱為“盧利亞-雅可布遜觀”,因為受盧利亞影響的雅可布遜的語言學思想是其理論基礎。1963年雅可布遜做了關于言語失誤類型的語言學分析的報告,而盧利亞發展了這位俄美語言學家的理論并豐富了神經心理學內容。雅可布遜關注的是大腦不同部位損傷和語言建構不同機制喪失的相互關系。他將組合機制和言語編碼的過程相聯系,而聚合機制則和解碼過程相關。盧利亞 (1950;1975)等人的研究結果驗證了維氏言語生成的內部言語學說,通過對腦損傷的研究證實了語法建構操作的自治性,探討了表層句法、形態、元語言操作和病理的關系,同時也分析了言語組織的深層結構和句法問題,發現了深層句法的兩種類型,即情景意義和語法意義的深層句法,證實了句法的三個層次:涵義的、語義的、表層的句法。阿胡金娜在《言語生成》(1989)一書中對句法進行了神經心理語言學分析,著重探討了言語活動論關于言語生成機制和句法層級的觀點、前蘇聯神經語言學句法層級理論問題,同時還重點對比了俄羅斯神經語言學與西方神經語言學理論及研究方法的異同。
3.2 任金學派
任金(Н.И.Жикин 1893-1979)學派關于“言語和思維”的理論和實驗研究是俄羅斯神經心理語言學的重要內容。任金對兒童言語、言語病理學、實驗語音學、語言教學法的研究十分深入。他的奠基作有《言語機制》(1958)、《關于內部言語中的語碼轉換》(1964)、《作為信息載體的言語》和《語言.言語.創造》(1998)。任金對“內部言語”這一言語思維活動機制進行了研究,認為它是人類符號特征的傳導性機制,這種機制能做到不僅可以從一種語言傳導至另一種語言,而且接收到的文本總是要轉成內部言語。關于在我們的意識中存在著智能特別語言的觀念假說為探討“言語和思維”問題做出了重要貢獻。這個智能的特別語言就是指“內部碼”(внутренний код),任金把這個內部碼又稱作普遍 - 物質碼 (универсально-предметный код),縮寫為 УПК.正是任金揭開了思想轉變成詞匯的神秘面紗,將普遍——物質碼的個人涵義轉碼為充滿語言意義的言語句。這和維果茨基的思想在詞匯中完善的觀點是一脈相承的,任金對言語機制的研究是開創性的。他還研究了記憶語言的生理機制和神經元的突觸機制。在接受和加工信息中,感覺器官和智力是配套的互補機制,兩者缺一不可。他在研究中還涉及到其他許多機制,如:語言可以作為向人展示意識領域的機制、作為控制人的各種動作和活動的機制、編碼和解碼的線性機制、語法機制、詞匯意義組合機制、涵義列形成機制、意義和涵義互相影響機制、減少詞匯容量的機制和調節詞匯選擇機制等。
戈列洛夫(И.Н.Горелов 1928 -1999)在日常交際中、在活的語言中找到了言語和思維關系的答案,他的科學思想補充、甚至還修正了任金的理論。在《言語活動論問題》(1987)中著重研究了下列問題:語言、邏輯與思維之間的相互關系;從思想到詞的“深層結構”問題;計算機文本處理與語言功能模型轉化。戈列洛夫和謝多夫共同編寫的《心理語言學原理》(1997)提供了許多實驗材料和在日常生活中觀察到的語料,使讀者對抽象的語言和思維、言語和意識之間的關系有深入的了解。在他的《選集》(2003)中主要研究了言語思維的功能基礎、同心理語言學和神經生理學材料相關的深層和表層問題、心理語言學的神經生理基礎等。謝多夫2007年出版了俄羅斯第一本將神經語言學和心理語言學緊密結合研究的《神經心理語言學》。
3.3 彼得堡學派
彼得堡心理語言學派的理論源于洪堡特、索緒爾、波鐵布尼亞、博杜恩.庫爾德內、別施科夫斯基(А.М.Пешковский)、特魯別茨科依(Н.С.Трубецкой)、巴赫金、謝爾巴、雅可布遜。以下學者在神經語言學研究,尤其是語言功能研究方面做出了特別貢獻。
薩哈爾內和施泰林(А.С.Штерн)將彼得堡神經語言學的研究成果與心理語言學觀念結合起來。薩哈爾內(1989)研究了左半球右半球語法、言語受損的診斷和治療。施泰林是實驗語音學家,她研究了影響感知的語言學特征層級問題以及言語研究的統計學問題(1991,1992,2003)。特拉烏果特(Н.Н.Трауготт)、巴洛諾夫、杰格林、車爾尼果夫斯卡婭等(Л.Я.Балонов,В.Л.Деглин,Я.А.Меерсон,Д.А.Кауфман,Л.И.Вассрман,С.А.Дорофеева,Т.В.Черниковская)的實驗研究回答了言語活動中每個大腦半球功能的問題,主要有以下實驗:完成描述畫中某一事物的任務;語言的聲音方面;語言的詞匯組成;句法結構的感知理解;語篇的感知理解。車爾尼果夫斯卡婭是俄羅斯神經心理語言學的代表人物,她研究了詞匯、句法過程大腦半球組織特點,研究了隱喻和意象的理解、三段論思維和格式塔思維、韻律和語調感知,還探討了大腦半球在感知音節時的專門化、語篇特點、復雜視覺形象的感知和理解及其言語化、氣味的感知及其言語化、個人大腦半球的類型和認知風格的相關性、雙語問題、二語習得等。所有這些課題研究都是在進化論、符號學、文化學的框架下,對比兒童和不同文化代表思維的發展,這些不同的文化定位于不同類型的教育和整體世界圖景,研究的理論基礎是維果茨基、雅可布遜、盧利亞、洛特曼等人的理論。研究證明,大腦右半球主要參與情感、語調的加工,以及加工在完整性/不完整性特征上有區別的語句,左半球主要感知邏輯重音。由她和果爾(К.Гор 2000;2001;2003)進行的俄美聯合實驗研究,探討了不同范疇俄語心理詞匯組織的問題,包括俄語為母語的兒童和成年人、俄語為外語的成年人、言語有障礙的人、言語發展存在問題的兒童。該項目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討俄語形態規范性/非規范性的問題,研究給俄語引入新的參數——動詞層級聚合體的復雜性。研究結果還可以解釋掌握俄語動詞聚合體成分的順序和年齡,在大腦受損傷時兒童掌握聚合體時特有的語言變化以及大腦受損傷的成年人聚合體變化特點。
梅德韋杰夫(С.В.Медведев 1996,1997)等人在人腦研究所進行了語言功能原創性研究。他和同事們(Н.П.Бехтеревая,С.В.Пахомовый,М.С.Рудас,В.А.Воробьёв)運用了大腦成像(картирование мозга)的方法之一電子照射-X線照相進行研究,研究獲得了關于閱讀時保證加工一些語法形式的功能區的數據,而且還獲得了非能產加工句法的數據。他們還研究了注意系統的相互作用和言語加工,區分了負責言語過程特有的和非特有方面的大腦區域,探討了大腦區域中取決于“注意”指向的積極性的轉換。課題組還研究了創造性地使用言語/非言語材料活動的問題,發現了大腦不同區域的積極性取決于任務《艱巨/容易》的因素。齊斯多維奇(Л.А.Чистович )和果熱夫尼果維依(В.А.Кожевниковый 從1996 年開始對不同年齡階段的兒童在正常情況下和聽的言語系統受不同損傷的情況下交際功能的形成過程進行了研究。卡洛列娃(Королева 2001;2002;2004)在彼得堡繼續了言語(耳朵、嗓子、鼻子)研究,運用了新的言語實驗模式研究了聾啞人聽的言語和語言過程。1991年赫爾岑國立師范大學建立了兒童言語研究教研室,負責人是采特林(С.Н.Цейтлин)。他們主要研究兒童如何習得母語(俄語)、兒童詞匯創新和構形創新的語言學原因、如何習得形態范疇、兒童早期習得詞匯的特點、自然習得寫作能力的特點,兒童感知書和民間故事、人稱代詞、親屬稱謂術語、空間關系以及相應的語言表達方式。該研究的理論依據是建構主義,主要觀點是每個孩子都是獨立地、漸進地在加工從成年人言語中獲得的信息基礎上建構自己的語言系統。該教研室開設了《兒童言語語言學》課程,并探討了科學的方法論基礎,他們設立了兒童言語數據庫基金,目的在于搜集、整理孩子及其家長對話的錄音。
20世紀90年代言語信號加工的計算機技術的大力應用促進了彼得堡大學幼兒言語發展的研究,主要是發音分析、知覺分析、心理語言學分析(Андреева и др.,1997,1998;Куликов и др.,2002;Куликов,Андреева,2004;Ляксо и др.,2001;Ляксо,2003)。研究證實了言語發展的連續性、不間斷性。在研究言語感知和理解的心理語言學機制時使用了不同的實驗模式,這些模式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對兒童言語、語言功能受損傷的言語過程的研究。這些研究為發展兒童言語心理語言學過程特點表征的理論做出了突出貢獻,研究對象是那些言語有障礙的兒童(Ковшиков 1994;Корнев 1995,1997,2004;Лалаева 1983,2002;Оппель 1963;Орфинская 1960)。
注釋
①語言個性:人的言語理解和生成能力。
②語言意識(языковое сознание)反映人的內在世界、意識、思想同其外部表達形式語言/言語的相互交叉和滲透關系。
Ахутина Т.В.Порождение речи.Нейро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й анализ синтаксиса[M].М.,1989.
Бодуэн де Куртене И.А.Избранные труды по общему языкознанию[С].М.,1963а.
Выготский Л.С.Мышление и речь[M].М.,1996.
Горелов И.Н.Избранные труды по психолингвистике[M].М.,2003.
Жинкин Н.И.Механизмы речи[M].М.,1958.
Жинкин Н.И.О кодовых переходах во внутренней речи//Вопросы языкознания[J].1964(6).
Жинкин Н.И.Язык.Речь.Творчество[M].М.,1998.
Лурия А.Р.Язык и сознание[M].М.,1979.
Лурия А.Р. Основные проблемы нейролингвистики[M].М.1975,2007.
Сахарный Л.В.Введение в психолингвистику[M].Ленинград.1987.
Седов К.Ф.Нейропсихолингвистика[M].М.2007.
Щерба Л.В.Языковая система и речева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M].Ленинград.1974.
Jakobson,Q.On Aphasic Disorders from a Linguistic Angle:The Framework ofLanguage,Michigan University,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