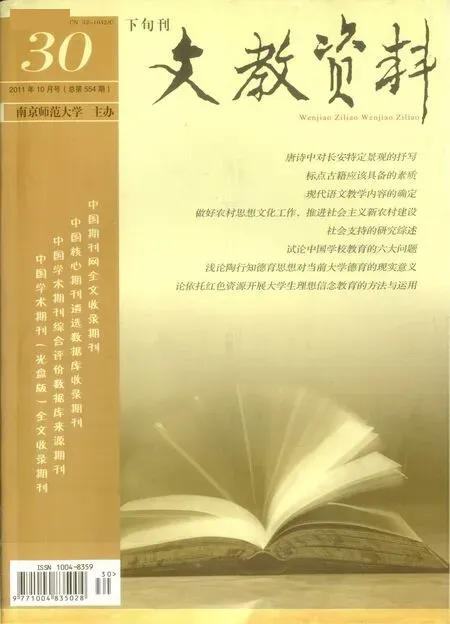淺論李商隱的詠史詩
胡洪興
(邳州市土山高級中學(xué),江蘇 邳州 221300)
李商隱(公元813—858年),字義山,號玉谿生,又號樊南生,唐懷州河內(nèi)(今河南沁陽)人,出身于小官僚家庭,從高祖至其父親,都只做過縣令一級的小官。九歲喪父后,李商隱跟母親回到鄭州,之后家境極為艱難。不久,跟隨堂叔學(xué)習(xí)古文、詩歌和書法。十六歲時著《才論》、《圣論》,以古文為士大夫所知。十七歲時,被太平節(jié)度使令狐楚辟為巡官。牛黨人令狐楚愛其才,教授駢文奏章,并令子令狐绹與李商隱同游。此后八年,除有短暫時間的宦游外,李商隱一直在令狐楚幕中。大和九年(公元835年)前后,李商隱赴玉陽山、王屋山一帶隱居學(xué)道。開成二年(公元837年)應(yīng)舉,經(jīng)令狐绹引薦登進士第。次年,令狐楚病死,李商隱失去了仕途依托,便入李黨涇原節(jié)度使王茂元幕中,茂元愛其才,以女相嫁。牛黨人因此罵他“背恩”。會昌二年(公元842年),李商隱被選為秘書省正字。同年,其母去世,他離職服孝三年。此后牛黨執(zhí)政,他一直受到排擠,在各藩鎮(zhèn)幕府中過著清寒的幕僚生活,潦倒至死。
李商隱素有大志,無意卷入了牛李黨爭傾軋的漩渦,為他仕途失意埋下了伏筆。在婚娶茂元之女后,李商隱雖曾有任秘書省正字(正九品上)的經(jīng)歷,但大部分時間卻浪跡于幕府。頓挫中總想奮起,一次次希望伴隨著一次次失望,政治上的落拓與不甘寂寞的情懷纏繞在一起,使李商隱的詩有強烈的政治要求,欲罷不能而欲言又止的結(jié)合,又使李商隱的詩曲折、隱晦、多典、難懂。
詠史詩作為一種特定的詩歌形式,既有特定的內(nèi)容,又有特定的表現(xiàn)方式。在晚唐,政治衰敗,黨爭加劇,有理想有才華的士人追慕盛世,怎么能不感慨系之。社會原因與文學(xué)因素的結(jié)合,為傷今悼古之作的蔚為大觀準(zhǔn)備了充分的條件。而在眾多的詠史詩人中,李商隱在詠史詩的發(fā)展中占有不容忽視的地位。
1.李商隱的詠史詩有明確的創(chuàng)作意圖且直指時事
李商隱是一個關(guān)心現(xiàn)實政治的人,他的詠史詩是政治詩的特殊表現(xiàn)形式。詩人因事興感,以歷史上盛衰興亡的往事作為吟詠的題材,選取封建帝王們因生活上的荒淫奢侈、政治上的昏憒腐朽而造成亡國的慘痛教訓(xùn)作為集中表現(xiàn)的主題,諷喻當(dāng)代的帝王,抒發(fā)自己理智、冷峻而感傷的亡國之憂,都是針對現(xiàn)實,有感而發(fā)。詩人辛辣地嘲諷和暴露了封建帝王色荒淫昏的各種丑態(tài),揭露其因溺聲色而導(dǎo)致亂政亡國的罪行。
李商隱詠史詩觀照現(xiàn)實是以歷史作為參照的。詩人在詠史詩中借楚靈王、吳王夫差、北齊后主、南齊廢帝、陳后主、隋煬帝乃至唐玄宗等荒淫誤國的典型托古諷時,深寓歷史教訓(xùn),具有強烈的鑒戒意義。顯然,李商隱如此的創(chuàng)作實踐增強了詠史詩的現(xiàn)實主義傾向。他以嘆古懷昔的形式,反映現(xiàn)實社會的新問題,把晚唐社會危機四伏,人心思治的狀況,以及難以排遣的興廢之感統(tǒng)統(tǒng)包容于詩中,擴大了詠史詩的容量。
作家的創(chuàng)作總要受某一思想的指導(dǎo),詠史詩也要受詩人歷史觀的制約。從李商隱的詩中,我們可以總結(jié)指導(dǎo)其創(chuàng)作的歷史觀點。在其詠史詩中,李商隱大都指責(zé)是帝王本人敗亂了國家,“系人不系天”的思想貫穿于李商隱的全部詠史詩中。比如:“北湖南埭水漫漫,一片降旗百尺竿。三百年間同曉夢,鐘山何處有龍盤?”“北湖南埭”是南朝帝王經(jīng)常在那里游宴玩樂的玄武湖和雞鳴埭,可同樣在這里能頻繁地看到降旗一片。有人說:“鐘山龍盤,石城虎踞,帝王之宅也。”但三百年間每一個皇帝夢都那樣短促,顯然,興亡之道,不關(guān)天也。他又說:“只要君流盼,君傾國自傾。 ”(《歌舞》)
2.李商隱詠史詩在藝術(shù)上有新的追求、新的創(chuàng)造
李商隱通過詠史向當(dāng)時封建統(tǒng)治者提供歷史教訓(xùn)、鑒戒時,并不是全面地闡釋某一歷史事實,而是盡可能選擇富于包孕效應(yīng)、暗示作用的典型歷史人事細(xì)節(jié),如寄慨的微物、寓意的片斷、合理的圖景等加以著力描寫,借題發(fā)揮,生發(fā)、引申出歷史故事、歷史素材中人們不易發(fā)現(xiàn)的現(xiàn)實意蘊,翻舊為新,出奇制勝,小中見大,擴展、延伸詠史的內(nèi)涵。在李商隱的作品集中,古體詩已很少,甚至連五律也為數(shù)有限,而大多采取七律、七絕的形式,特別是七絕的大量運用,是此時詠史詩變化的標(biāo)志。此后,七絕便成為人們詠史習(xí)用的體裁。
我們評價一個作家的文學(xué)成就,常常要看他相比前代作家提供了哪些新的東西,而以詠史形式寫愛情、戀情正是李商隱的新創(chuàng)造。這里值得注意的是,李商隱在運用歷史材料時,往往能跳出史料的限制,在符合當(dāng)時生活邏輯的范圍內(nèi),設(shè)想未必實有卻有可能有的感情活動,這是詠史方法在詩歌領(lǐng)域的新發(fā)展。這樣就把具體的抒情對象和具體的情感抽象升華得具有無限的超越性,往往一種具體的情感穿越于無限的藝術(shù)時空中,一波三折,甚至千回百轉(zhuǎn),變得幽恨深遠。
李商隱的詠史詩另一個顯著的特點是用典多,幾乎句句有出處。如《井絡(luò)》一詩中連續(xù)使用了“井絡(luò)”、“陣圖”、“杜宇”、“金牛”等典。用典是一柄雙刃劍,一方面可以使不便明言的意思得以暢達,使容易寫得平淡的內(nèi)容顯的新鮮,另一方面卻使了解詩意頗費周折,以至晦澀難懂。李商隱的詠史詩當(dāng)屬后一種。
李詩的多典當(dāng)然與他早年習(xí)受駢文有關(guān),但不應(yīng)是主要因素。例如作者有感于“甘露之變”而寫的《有感二首》自注云:“乙卯年有感,丙辰年詩成。”以詩人之才,寫兩首律詩并非難事,然而詩卻隔年而成,可見詩人是有感于衷,如鯁在喉,不吐不快,但事關(guān)朝政,寫作時怕意顯招難,唯恐隱之不深,即成之后,又怕無人領(lǐng)略,有負(fù)苦心,便不覺附以短注,提供一扇解詁的窗戶。詠史詩是李氏特殊需要的政治詩,李商隱寫此類詩時應(yīng)屬同樣的這一心態(tài)。這一心態(tài)直接的表現(xiàn)就是“多典”。
3.注意議論與形象或感情的結(jié)合
如《北齊》詩:“小憐玉體橫陳夜,已報周師入晉陽。”再如《賈生》:“宣室求賢訪逐臣,賈生才調(diào)更無倫。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沈德潛評此詩:“純用議論矣。然以喟嘆出之,故佳。”這種議論寓于形象之中的做法很高明,故《詩藪》評:“‘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宋人議論之祖。……然書情,則愴惻而易動人;用事,則巧切而工脫俗。”指出了李商隱詠史詩議論的好處及對后世的影響。
4.常見題材的創(chuàng)造性使用
文學(xué)創(chuàng)作是具有獨創(chuàng)性的活動,它總要求作家采用新手法,進行新構(gòu)思,表現(xiàn)新內(nèi)容。而詠史詩題材的因襲卻是常見的現(xiàn)象,這是由于某些歷史人物或事件文學(xué)性較強,從其特殊性能反映出普遍性,故易吸引作家的目光,成為詠史詩中的傳統(tǒng)題材。如商山四皓的故事,晚唐的溫庭筠、李商隱都有題詠。創(chuàng)新既是文學(xué)活動的普遍要求,詠史詩也不例外,雖然它要受到更多的限制。因此,在基本內(nèi)容一致的條件下,詩人們便要尋找新的角度及表現(xiàn)手法。溫庭筠的《四皓》詩是這樣寫的:“商於六里便成功,一寸沈機萬古同。但得戚姬甘定分,不應(yīng)真有紫芝翁。”詩意與李商隱的“本為留侯慕赤松,漢庭方識紫芝翁”同,然而細(xì)讀后,便會覺得二詩焦點仍有不同。溫詩羨慕四皓生逢其時,得以脫穎而出,言外有自嘆自惜意,而李詩特別是后兩句:“蕭何只解追韓信,豈得虛當(dāng)?shù)谝还Α!眲t不過是說用對人方可安天下。此詩其實是有感而發(fā):晚唐的皇帝多為宦官擁立,由于各種原因,這些皇帝在位時都沒有立太子,即使立了太子也是時立時廢,因為這樣的緣故,朝庭變亂不已,乃至于立儲一事成為人們時常議論的話題。由此我們可以看出,由于詩人各方面的條件不同,只要善于挖掘,那么一個習(xí)見的題材仍可以寫出有新意的作品來。
總之,李商隱多方面的藝術(shù)探索,豐富了詠史詩的內(nèi)容及表現(xiàn)手法,成為晚唐詠史詩的集大成者。他的創(chuàng)作在詠史詩的發(fā)展史中是不可或缺的一環(huán)。
[1]劉學(xué)鍇,余恕誠.李商隱詩歌集解.中華書局印行,1988.12.
[2]吳調(diào)公.李商隱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2.
[3]楊柳.李商隱評傳.江蘇人民出版社,1981.10.
[4]鐘銘均.李商隱詩傳.中州書畫社,1982.7.
[5]葉蔥奇疏注.李商隱詩集疏注.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8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