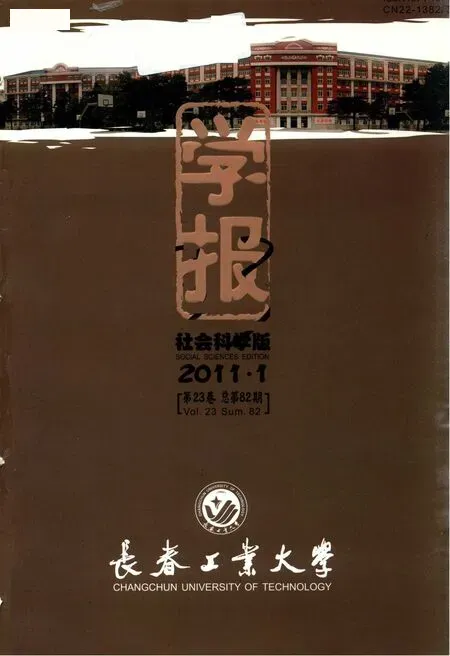城市化進程中嶺南文化的當代轉(zhuǎn)型
陳 超
(廣東金融學院 財經(jīng)傳媒系,廣東 廣州 510521)
城市化進程中嶺南文化的當代轉(zhuǎn)型
陳 超
(廣東金融學院 財經(jīng)傳媒系,廣東 廣州 510521)
城市化是中國社會發(fā)展的必然選擇,由此引發(fā)的文化轉(zhuǎn)型是不容回避的命題。作為處在改革開放前沿的廣東,快速的城市化不僅直接改變了其傳統(tǒng)的社會生產(chǎn)模式、消費模式和人的生活方式,還造成了對傳統(tǒng)嶺南文化精神內(nèi)核與價值倫理的強大沖擊。因此,從現(xiàn)實情懷出發(fā),關注轉(zhuǎn)型期嶺南文化的傳統(tǒng)嬗變與新質(zhì)素的產(chǎn)生、滲入,審視嶺南文化在這一過程如何更好地構建其新的精神與時代品質(zhì),這既是“嶺南文化”這一概念獲得當前學理價值和豐厚時代內(nèi)涵的現(xiàn)實要求,又是中國城市化過程中文化轉(zhuǎn)型過程中的理論需求。
城市化;嶺南文化;轉(zhuǎn)型
中國的城市雖然已有兩千多年甚至更長的歷史,但結(jié)束城市與鄉(xiāng)村的無差別并開始培育一種現(xiàn)代城市意識和文化精神,卻是近百年的事。1840年,帝國主義的堅船利炮轟開了大清朝的大門,中國從進行防御性的現(xiàn)代化開始,幾經(jīng)浮沉,幾經(jīng)波折,中國城市化從上海到香港,從香港到廣州、深圳,已經(jīng)碾過了一個半世紀的風塵,至今仍在延續(xù)。中國城市生活被大量的描寫最早出現(xiàn)在明朝的《三言》、《兩拍》,而從城市意識觀照現(xiàn)代城市化過程、描摹城市人處境、反思現(xiàn)代性問題的作品,則是20世紀30年代的事。當時上海作為中國大都會,憑著租界所提供的文化資源、經(jīng)濟依托和制度保障,使置身其中的人們在感受現(xiàn)代生活歡樂刺激的同時,也體味著現(xiàn)代生活的苦楚,這種兩難的境地在舊海派作家“新感覺派”里表現(xiàn)明顯。如穆時英《上海的狐步舞》頭一句就是“上海,建在地獄上面的天堂”。梁得所在《上海的鳥瞰》寫道:“黃浦灘的景象,足以代表上海,使我們知道她是一個現(xiàn)代物質(zhì)文明的都會,同時是情調(diào)深長的地方”,上海“很有詩意”。他們不乏對城市的批判和揭露,但這種批判又是根植于他們對物質(zhì)世界迷戀之上的,因這種曖昧的立場,展現(xiàn)了舊上海現(xiàn)代性和城市意識的不徹底性。1940年代末,隨著一輪一輪城市改造運動,工商業(yè)文明下培育起來的城市人格和市民精神受到質(zhì)疑,在強勢的體制文化和農(nóng)業(yè)文化威壓下,城市化的內(nèi)在制約和精神質(zhì)素都漸漸消失。于是,在冷戰(zhàn)格局下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中國城市被納入新的軌道,并中止了它在過去的發(fā)展——只有香港、澳門作為西方殖民地在全球城市化的浪潮中得以同步前行。1979年之后,中國實行了“改革開放”,才從廣東開始重啟從傳統(tǒng)到現(xiàn)代、從鄉(xiāng)村到城市的城市化進程,中國社會由此開始發(fā)生了一場“史無前例的大變遷”。
然而,隨著這場變革的深入和擴展,城市文明與生態(tài)文明的悖反日益突出,對“城市化”的批判漸呈洶涌之勢,其主要集中在對城市造成的生態(tài)污染、人性異化、人種退化和精神之根的喪失等方面。于是,一方面,張煒、賈平凹、遲子健等人從文化哲學的角度出發(fā)對當下城鄉(xiāng)倫理歧境進行了揭發(fā),在皈依傳統(tǒng)和反叛超越中,體現(xiàn)著當代知識分子的精神堅守;另一方面,當前“底層”敘事和打工文學卻從城鄉(xiāng)二元對立導致人的困境出發(fā),通過“貴鄉(xiāng)村、抑城市”的現(xiàn)實主義文學傳統(tǒng)窺視著底層生存的“無根”狀態(tài)和精神淪喪。但總的來看,當前批評界存在著說教意味過濃,對城市化所帶來啟蒙理性的認識不足,和對市場化變革和現(xiàn)代化進程存在隔膜和疑慮的現(xiàn)狀。如單世聯(lián)在《都市文化的反諷》一文中所言:“城市文化市場的消化力越來越強,昨天還聞所未聞的,今天可能十分平常,過去的對手,現(xiàn)在可以成為座上客,文化史上生前憔悴死后殊榮的現(xiàn)象并不罕見。凡·高生前貧苦至死,死后作品價值連城,整個現(xiàn)代主義文化都經(jīng)歷了從異端到正統(tǒng)的角色轉(zhuǎn)換。”[1]
這同樣體現(xiàn)在對當前嶺南文化和廣東人文精神的認知上。快速的城市化在給廣東帶來紙醉金迷、夜夜狂歡的繁華背后,在讓視聽藝術、網(wǎng)絡文化、大眾文化和通俗文化暢通無阻的同時,也使傳統(tǒng)嶺南文化的弊病與消極因素日趨體現(xiàn)明顯:追求效率、急功近利卻過度掠奪自然、污染環(huán)境;追求世俗卻使拜金主義、功利主義一度盛行;務實過頭同時陷入了經(jīng)驗主義的桎梏;注重個人生活感覺卻為黃、賭、毒提供了溫床等。面對這些問題,雖然社會媒體和文化理論界相繼開展了諸多討論和研究,但從當下文化建設的角度來看,其中的策略、意見和建議缺乏足夠的深度和應有的現(xiàn)實情懷,亟需得到進一步的梳理和提升。
目前,中國城市化過程所帶來的“趨同化”現(xiàn)象日益表現(xiàn)嚴重,主要體現(xiàn)在城市建設與舊城改造致使城市面貌日趨于同化、大眾文化與流行文化致使地方文化特質(zhì)日趨于同化、快餐文化和洋文化使人們生活方式日趨于同化,現(xiàn)代人功利虛榮、唯利是圖、個人至上的惡俗化和趨利化日趨嚴重,等等。在此種背景下,嶺南文化的社會弊病與時代痼疾也相應產(chǎn)生并表露明顯,其弊端主要體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一)追求效率卻急功近利,過度地掠奪了自然資源。改革開放三十年來,廣東特別是珠江三角洲耕地銳減,污染嚴重,令人擔憂;(二)務實過頭卻致使思維封閉,成為持續(xù)進取和發(fā)展的桎梏;(三)追求個人感官卻使享樂主義、拜金主義盛行。個人過于滿足感官的享受,為消費主義打開方便之門,廣東一度的黃、賭、毒泛濫,與這種文化觀念的影響是分不開的;(四)追求速富卻使迷信復活,近年來特別是潮汕一帶沉迷“六合彩”的現(xiàn)象就是這種思維的結(jié)果;(五)小富即安,沉醉于昔日的榮光,等等。這些文化消極困素的影響日趨于嚴重,急需得到進一步地糾正和反思。
事實上,當前中國“城市化”其認識本身就存在誤區(qū),即一方面缺乏把農(nóng)村作為現(xiàn)代進程的積極因素納入經(jīng)濟框架結(jié)構的實踐,另一方面又缺乏把農(nóng)村人尊嚴融入城市提供應有的知識和思想豁蒙的保障,造成了長期“城”、“鄉(xiāng)”二元對立的文化心理。而現(xiàn)代文明所暴露的弊端也使人們一方面先入為主地將城市文明定性為“惡”、把鄉(xiāng)土文明定性為“善”,另一方面又從日常生活到個人精神追尋和理性維度上對“城市”持有好感,這一矛盾的社會心理,讓當前廣東文學(特別打工文學)在或維護、或批判的套路上不斷徘徊。因此,對嶺南文化的內(nèi)部肌理和思想探尋,應積極審視城市化進程中農(nóng)裔知識分子、農(nóng)裔官人、農(nóng)民工、農(nóng)裔女性等的行動選擇及心路歷程,在廣度和深度上尋求傳統(tǒng)文化與城市建設和發(fā)展最為關聯(lián)的價值所在。
殷海光在《中國文化的展望》一書中認為:“倫理道德是文化的核心價值。如果一個文化的倫理道德價值解體了,那么這個文化便有解體之虞。所以,談挽救文化的人,常從挽救倫理道德開始。”[2](P94)“城市化”實現(xiàn)了農(nóng)村人口向城市人口的地域轉(zhuǎn)移,并以其特有的社會分工改變了人們原有的職業(yè)價值觀并鑄煉出城市生活所特有的現(xiàn)代性質(zhì)素。一方面,“城市化”使傳統(tǒng)道德價值觀念日趨缺失,使城市過客與新移民的物質(zhì)欲望不斷膨脹,對傳統(tǒng)嶺南文化氣質(zhì)造成了疏離。另一方面,由于現(xiàn)代性的滲入與生長,使社會文化心靈秩序重整和社會規(guī)范得于整合的同時,也催生了人們新型倫理建構和具有契約理性特征的行為選擇,以至于新的生活方式滌蕩了農(nóng)民身上積累的傳統(tǒng)因子,使他們的倫理價值觀和社會行為發(fā)生了巨大轉(zhuǎn)變,并自覺不自覺地形成了新的現(xiàn)代思維——當然這里邊也包含著傳統(tǒng)“美”的淪喪和現(xiàn)代“惡”的增殖。對此,嶺南文化理應揀拾那些因歷史功利目的而淪落或丟失的人文關懷意識來作為當下的強調(diào),以人道主義的悲憫讓其中傳統(tǒng)、古樸、謹嚴的品格留駐,以保持歷史行進中人生命的莊嚴和文化模式的康健。
同時,在具體的文化發(fā)展戰(zhàn)略和設計中,筆者認為可以運用“減長”(de-growth)模型來確立嶺南文化精神內(nèi)涵生態(tài)發(fā)展的觀念。“減長”模型是洛根(Nicholas Georgescu-Roegen)于1971年建立的一個減長和生物經(jīng)濟的模型,他認為物理上的有限性以及熱動力的第二定律表明:當熵增加時,有用的能量被不斷耗竭。基于此,人類不能設計和追求一種無限量的經(jīng)濟和社會發(fā)展模式。因此,當代嶺南文化的精神構建,宜通過適度消費、設計和發(fā)展來淡化對發(fā)展硬度、速度、頻次的崇拜,將社會資源重點轉(zhuǎn)移到具有公共性的藝術、家庭、社區(qū)、人倫等文化項目,以提升文化品質(zhì)和精神內(nèi)涵。
文化的可持續(xù)發(fā)展是具有歷史性、發(fā)展性與創(chuàng)造性的延伸,而不是毀滅的、虛無的與消解的斷裂。1970年代霍·廉姆的政治學經(jīng)典《鄉(xiāng)村與城市》(The Country and the City)提醒人們,城與鄉(xiāng)的問題不再是隔離孤立的,而是難解難分地糾纏在一起的。這種觀點為加拿大學者簡·雅各布斯的思想提供了支撐,她在《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一書中提出:“缺乏研究,缺乏尊重,城市成了犧牲品”,“不相信我們以及城市的存在本身就是自然不可分割的、合法的一部分”是危險的,[3](P127)她批判源遠流長的“反城市”思想只不過是一個騙局。這無疑為當下中國城市改造法則提供了有益的借鑒,也為方興未艾的中國城市化進程和當前嶺南文化面臨的內(nèi)涵構建提供了啟示。因此,面對現(xiàn)代城市的高速發(fā)展,當城市化、工業(yè)化和現(xiàn)代化以“三位一體”之勢成為不可抗拒的潮流時,嶺南文化理應在對歷史文化、建筑文化、自然環(huán)境文化、風俗文化和人文文化之間的融合與拓展基礎上,尋求“激活優(yōu)良傳統(tǒng)、融通歷史與現(xiàn)實、整合物質(zhì)文化與精神文化”的途徑,以此來形成一種既具現(xiàn)代“都市”文化底色又有地方傳統(tǒng)特色的文化品質(zhì),建構“延續(xù)傳統(tǒng)、突顯特色”的嶺南文化新內(nèi)涵和新質(zhì)素。
[1]單世聯(lián).都市文化的反諷[J].現(xiàn)代與傳統(tǒng),1993,(7).
[2]殷海光.中國文化的展望[M].北京:中國和平出版社,1988.
[3]簡·雅各布斯.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M].上海:譯林出版社,2006.
廣東金融學院2010年度校級青年課題:“城市化進程與嶺南文化的現(xiàn)代轉(zhuǎn)型”資助項目(編號:10XJ03-01)。
陳超(1981-),男,碩士,廣東金融學院財經(jīng)傳媒系講師,主要從事文學批評與藝術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