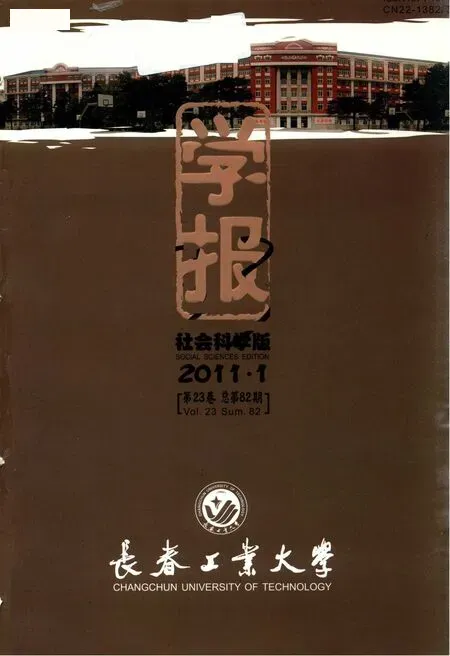大革命時期汪精衛急劇走向叛變的原由探討
王鵬程張運洪
(1.中共湖北省委黨校,湖北武漢 430022;2.防空兵指揮學院政治部,河南鄭州 450052)
大革命時期汪精衛急劇走向叛變的原由探討
王鵬程1張運洪2
(1.中共湖北省委黨校,湖北武漢 430022;2.防空兵指揮學院政治部,河南鄭州 450052)
大革命后期汪精衛的叛變是多種因素交織的結果。他叛變的根本原因,是其資產階級屬性使然。然而,“迎汪復職”、“擁汪反蔣”中對汪精衛的過分遷就,導致了他隨后的巨大心理反差,使其認為共產黨不可依靠,共產黨領導的工農運動也不可依靠,國共遲早要分家;工農運動中的過激行動,造成社會秩序動蕩,軍心不穩,對汪精衛急速右轉也有一定的影響;特別是莫斯科五月來信及羅易的“泄密”,更是在客觀上加速了汪精衛“分共”的步伐。
大革命;共產國際;中國共產黨;汪精衛;叛變
蔣介石于1927年在上海發動“四·一二”政變后,汪精衛曾一度采取“聯共反蔣”政策。但從5月底到6月初,汪精衛對國共合作的態度卻發生了急劇轉變,并最終決定“七·一五”“分共”,背叛了國民革命。汪精衛叛變的根本原因是其資產階級階級屬性使然。除此之外,共產國際代表及中國共產黨的態度和政策等,也對汪精衛的叛變產生了重大影響。本文謹就這個問題作一簡要分析。
一、“迎汪復職”“擁汪反蔣”中對汪精衛遷就,導致了其后來巨大的心理落差
1926年底,隨著北伐戰爭順利進行,蔣介石的軍事獨裁用心日漸顯露,政治態度日益右轉。在這種情況下,為遏制蔣介石專權,國民黨左派掀起了“迎汪復職”運動,希望通過汪精衛回國掌握黨權來抑制蔣介石的軍權。當時,中共主要領導人也很欣賞汪精衛,根據共產國際和聯共(布)的指示精神,1926年12月中旬,陳獨秀主持召開中共特別會議。陳獨秀在會議的政治報告中提出了“防止黨外的右傾,同時反對黨內的左傾”,“扶助左派建立以汪精衛為領袖的文人派政府”等七項挽救危局的措施。[1](P565-567)會議經過爭論,通過了這個報告。于是,“迎汪回國”、“擁汪反蔣”,便成為當時中共的重要策略。中共中央認為,只要汪精衛回國復職,國民黨左派就有了堅強的中心,就可以恢復它在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內的指導地位,從而削弱和抑制蔣介石的軍事獨裁傾向。同樣,蘇聯顧問及共產國際駐華代表也對汪精衛十分看好。蘇聯顧問鮑羅廷認為“汪精衛的名字可以把所有人聯合起來”。共產國際執委會遠東局指出,迎汪復職“這個口號確實能夠把所有革命組織聯合起來,也能博得農民群眾的同情并受到軍隊中革命人士的支持”。于是提出讓汪精衛回國、建立軍事委員會等措施以與蔣介石的戰略計劃相抗衡。[2](P261)汪精衛在歸國途中曾經路過莫斯科,在那里,他受到了熱烈歡迎并得到了蘇聯政府和共產國際都將給予全力支持的允諾。[3](P116)由于中共和共產國際代表都過于輕率地信任汪精衛,一直視他為“左派的唯一首領”,幻想依靠汪精衛和其他國民黨軍事將領來挽救危機,所以基本上對汪不設防。
中共中央期望與汪精衛合作反對蔣介石的立場,在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召開的中共“五大”上得到了確認和強調。“五大”還破天荒地邀請汪精衛列席了一天會議,并允許他旁聽羅易所作的關于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七次擴大會議討論中國問題的報告。羅易作報告時,汪精衛“非常注意傾聽”,并發表了演說。他宣稱,雖然他一般也同意提綱中談到的中國的非資本主義發展道路,但是他認為無產階級未必能成為小資產階級的領導者。[4](P274)并且他向參加大會的代表提出一個問題:共產黨是怎樣看待中國的小資產階級的,共產國際是否認為小資產階級能夠跟從革命的非資本主義發展?羅易發表講話,回答了這個問題。羅易說,在現階段共產黨將同國民黨合作,但必須以共產黨不僅分擔責任而且也要共同有權為條件。然而,三個階級(指無產階級、農民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綱領將不可避免地引向社會主義,在這一發展中,無產階級在國民黨內作為自覺的革命先鋒隊,將決定通往社會主義方向的進程。[3](P83)這個講話被某些代表批評為“不策略的攻擊”。它使汪精衛明白了在共產國際和中共的策略中,他只是小資產階級的代表,是聯合的對象,而不是像“迎汪復職”時講的請他出來領導;明白了在國民革命中無產階級是要力爭領導權的。因而他認為共產黨不可依靠,共產黨領導下的工農運動也不可依靠,國共遲早要分家。在革命的危機關頭,汪精衛一方面在口頭上高喊“革命的往左邊來,不革命的快走開去”,但另一方面又認為,國共合作不可能長久,“容共之后,必定分共”,雖然分共“時機未至,而各人已不能不做那必要的準備”。
二、工農運動中的過激行為,對其思想轉變也有一定影響
其時,由于中國共產黨領導工農運動的經驗不足和指導思想上的偏頗,兩湖一帶的工農運動中也存在著嚴重的“左”傾錯誤,發生了若干過激行為。如工人動輒罷工,“隨便逮捕人,組織法庭監獄,隨便斷絕交通,沒收分配工廠店鋪”,提出“使企業倒閉”、“縮短工時到每日四小時以下”等種種“過度”的要求;[5](P576)農會隨意行使權力,捕人、罰款、毀廟、分浮財,提出“有土必豪、無紳不劣”的口號,甚至沒收普通士兵寄回家的餉錢。這些“左”傾錯誤的蔓延,造成了社會秩序的動蕩,軍心不穩。這種情況,動搖了武漢國民政府的基礎,對汪精衛的權力和地位也構成了嚴重威脅,使汪精衛對共產黨產生了強烈不滿。對于武漢政府的危機,汪精衛把主要罪責歸結于共產黨,認為工農運動過火是武漢政府財政困難和軍人政變的直接原因,深感自己既受到蔣介石的封鎖和壓迫,又受到共產黨的“威脅”,處于“夾攻中”,要擺脫困境,必須分共。汪精衛的這一態度可以從如下材料中看出。中共五大后,陳獨秀與汪精衛等國民黨領導人舉行會談,在談話中汪精衛提出以下四點:(1)1927年1月3日占領日本租界的行動,不是根據國民黨的指示采取的,而是在共產黨人宣傳鼓動的影響下進行的。(2)何時提出“打倒蔣介石”的口號,國民黨對此一無所知,這是共產黨人未向國民黨通報的情況下提出的。(3)存在兩個黨組織是不合適的,如果領導權屬于國民黨左派,共產黨跟隨他們,那就不需要共產黨。如果是另一種情況,領導權在共產黨人手里,那就不需要國民黨。(4)蘇聯在唆使中國人民同帝國主義作斗爭,并在這一斗爭中作殘酷的自我犧牲,但蘇聯自己卻不積極參與這種斗爭。最后,“汪精衛總結說:現在的主要問題是,誰領導群眾?群眾跟誰走?跟國民黨走還是跟共產黨人走?國際關系和軍隊狀況的惡化無論過去還是現在都是共產黨人的過錯。如果國民革命因此遭到失敗,那對人民群眾來說會更糟糕。”[2](P248-249)由此可見,此時汪精衛心中已深深埋下了對蘇聯和中共不滿的種子。
三、莫斯科的《五月指示》與羅易“泄密”,加速了汪精衛“分共”的步伐
中共“五大”結束后,國內政治形勢又發生急劇變化。夏斗寅叛亂、“馬日事變”、朱培德“禮送”共產黨人出贛等事件的發生,標志著國民革命進入了緊急時期。國共合作到了最后關頭,破裂已是在所難免。在這種局勢下,共產國際代表和中共中央主要負責人仍把汪精衛等武漢國民黨領導人當作國民黨左派、小資產階級的代表,把團結汪精衛作為“全部政策的中心”,害怕他們被大資產階級拉走。1927年5月18日至30日共產國際執委會召開第八次全會,面對中國革命的危急局面,斯大林等人仍認為“武漢是中國革命的中心”,汪精衛仍是左派,稱“中國左派國民黨對現在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所起的作用,近乎蘇維埃在1905年對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所起的那種作用”。為了貫徹這一“中心”,共產國際要求中共放棄建立、掌握自己武裝的機會;放棄湖南暴動反抗許克祥叛變的計劃;放棄江西暴動討伐朱培德的計劃;放棄土地革命的原則。
但是,就在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八次全會結束的當天,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又給在中國的鮑羅廷、羅易及蘇聯駐漢口總領事柳克斯三人發出電報即“五月指示”。“五月指示”的要點是:中共應厲行土地革命;要吸收一些新的工農領袖去充實國民黨中央;要動員兩萬名共產黨員和五萬革命工農組建新軍;要成立革命軍事法庭懲辦反動軍官;等等。[2](P298-300)“五月指示”反映了莫斯科在中國革命的危急關頭對中國革命問題的舉棋不定,朝令夕改。“五月指示”一改過去共產國際的意見,轉而要求中國共產黨以激烈的手段來對付國民黨右派和改造國民黨,由此挽救中國革命。但是,根據當時的情況,這種指示是不切實際的,很難執行。中共中央最終也沒有執行,但“五月指示”仍給中共帶來了極大的麻煩。因為共產國際代表羅易把“五月指示”泄露給了汪精衛,它促使汪精衛思想進一步右轉。羅易出于“想在那個緊急關頭進行最后的努力,去重新贏得汪精衛的信任”的考慮,“于是,就把莫斯科來電送給他”。[3](P117)當汪精衛從“五月指示”得知斯大林對國民黨的“新態度”的實質時,他“非常吃驚”,覺得“嚴重的時期已到了”。在汪精衛看來,這個電報有五層意思,“都是很利害的”,“隨便實行哪一條,國民黨就完了”。[7]“天真”的羅易的魯莽言行使汪精衛覺得“共產黨在策劃政變”,[3](P119)使他進一步感到了來自共產國際和中共方面的威脅,認為國共合作同坐的船,已經到了終點,已到了爭船的時候了,已到了爭把舵的時候了,遂決心加速反共。
汪精衛在得到“五月指示”信息后不久,立即動身赴河南參加鄭州會議。鄭州會議,馮玉祥政治態度的轉變加深了武漢政府的危機,促使汪精衛進一步右轉。1927年6月13日,汪精衛等自鄭州回到武漢。15日,武漢各界召開歡迎第二期北伐將領及武裝同志凱旋大會,議決討伐蔣介石,懇請中央拿辦許克祥,抗議江西驅逐農工領袖等。會后,各團體向武漢政府請愿,湖北總工會經過中共中央秘書廳同意,散發了反對國民黨政府縱容許克祥的宣言,喊出了“打倒縱容反動勢力的國民政府”等口號。汪精衛由此更加懷疑共產黨人聯絡軍隊反對他,流淚切齒地對鮑羅廷、陳獨秀說:“我是一個文弱書生,其實他們(指總工會)何必聯絡武人來倒我!”[6](P86)此后,汪精衛集團議論的中心就是如何“分共”的問題。汪精衛“一面集合中央黨部非共產黨的同志,商量和共產黨分離的辦法;一面集合非共產黨的武裝同志,將那決議案(即‘五月指示’——作者注)宣布,請他們在軍隊中留心防范,聽候中央議決,努力奉行”。[8](P510)這時,中共主要負責人仍然把希望寄托在汪精衛身上,并且企圖以進一步的退讓來爭取汪精衛等人繼續革命。7月3日,中共中央擴大會議通過了繼續主張妥協退讓的《國共兩黨關系決議案》,其主要內容包括:承認國民黨“當然處于國民革命之領導地位”;共產黨人參加政府,只是以國民黨員的資格參加,為減少政局糾紛,可以請假;“工農等民眾團體均應受國民黨黨部之領導與監督,工農等民眾運動之要求,應依照國民黨大會與中央會議之決案及政府公布之法令”;“工農武裝隊均應服從政府之管理與訓練。武漢現有的武裝糾察隊,為因避免政局之糾紛或誤會,可以減少或編入軍隊”,等等。[9](P726)但是種種讓步都未能阻止“七·一五”反革命政變的發生。
綜上所述,對汪精衛叛變革命原因的分析,必須以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根據俄羅斯新解密的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的檔案資料,全面地歷史地進行分析,既要看到他叛變革命的主觀原因,也要分析客觀因素對其叛變革命的影響。只有這樣,才能正確總結歷史經驗,從中吸取教訓。
[1]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2)[Z].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
[2]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6—1927)(下)[Z].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
[3]〔美〕羅伯特·諾思,津尼亞·尤丁.羅易赴華使命——一九二七年的國共分裂[M].王淇,楊云若,朱菊卿,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1.
[4]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第六輯)[C].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
[5]彭明.中國現代史資料選輯第一、二冊補編(1919—1927)[Z].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1.
[6]蔡和森.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7]汪精衛.容共政策之最近經過[N].漢口民國日報,1927-07-18.
[8]劉繼增.武漢國民政府史[M].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
[9]魏宏遠.中國現代史資料選編(2)[Z].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3.
王鵬程(1970-),男,中共湖北省委黨校副教授,華中師范大學中共黨史專業博士研究生,主要從事中共黨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