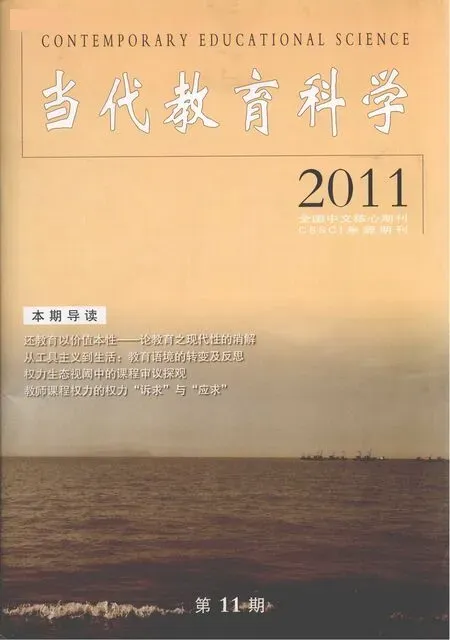論教師信念倫理的模式轉換
● 張曉陽
論教師信念倫理的模式轉換
● 張曉陽
信念倫理是教師賴以執教的內在行為準則,其古典模式可以追溯到柏拉圖“高貴的謊言”。而在啟蒙話語之下,教師紛紛向學生宣告各種“高貴的真實”,其嚴重的后果使教師信念倫理陷入崩潰邊緣。在新時代里,教師“信念倫理”如果不想被教師“責任倫理”徹底取代,只有進行恰當的模式轉換,而“高貴的沉默”可能是一種適恰的模式選擇。
教師信念倫理;高貴謊言;高貴真實;高貴沉默;模式轉換
教師在與學生的交往過程中,總要以某種信念、信仰、風俗、學說、理論等作為自己行動的理由,而在這些“理由”指導下所形成的倫理圖景,我們就可以稱作教師的“信念倫理”。中國傳統中的“師道”與其意思相近。信念倫理者認為“行為的道德價值不在于行為會達到的目標,而是在于行為據以被決定的格律。行為的價值不在于由此產生的結果,也不在于它們所帶來的好處和利益,而在于格律本身的彰顯。”[1]一方面,信念倫理往往因其動機的高尚性受到褒揚;另一方面,它也會因其手段和結果的道德不確定性而飽受詬病。隨著時代的發展,教師信念倫理動機的高尚性日益受到質疑,而手段與后果的不道德性又被過分夸大,這使得教師信念倫理似乎變成了“雞肋”,日趨走向崩潰,并大有被時髦的“責任倫理”取代之勢。教師信念倫理真的已經成為“雞肋”了嗎?如果是,我們為什么“棄之可惜”?如果不是,我們又怎樣使之煥發生機?本文試圖對教師信念倫理進行模式分析,并探討其通過模式轉換以獲得重生的可能性。
一、“高貴的謊言”——教師信念倫理的古典模式
柏拉圖在其《理想國》中專門用不少篇幅討論了“謊言”這個話題,認為謊言分三個種類,即“真正的謊言”、“言辭的謊言”與“高貴的謊言”。真正的謊言違背“理念”(柏拉圖認為的世界本體)本身,是人神共憤的,應該加以摒除。言辭的謊言則是基于“理念”的不幸的摹本,但它不像真正的謊言那樣一無是處,對人有時大有裨益:對于發瘋亂來、胡攪蠻纏和傻頭傻腦要干壞事的朋友來說,謊言可以像 “有用的藥物”那樣,起到治療和預防作用。[2]同時,蘇格拉底認為這種“處方藥”必須交給“醫生”,“私人”決不能染指,搞不好就會顛覆和毀滅城邦。[3]可見,言辭的謊言也是利弊參半的,但只要“統治者”或“哲人王”小心使用,就會不僅利人利己而且利國利民,所以“言辭的謊言”在他們那里就可以變成“高貴的謊言”。同時,他特別提到這種“高貴的謊言”是屬于哲人王和統治者的特權,不得讓平民或年輕人知曉或使用。為什么呢,因為平民或年輕人無知、愚昧、容易上當,無法分清什么是“隱微”的東西,哪些不是。柏拉圖還有一個有力的論證是“醫生對病人說謊時對病人好,病人則絕對不能對醫生撒謊,因為這樣就是對自己不負責任”。[4]這種論調很難不讓我們想到“醫生對病人”、“統治者對平民”的關系就是古典“師生關系”的模板所在,從而“高貴的謊言”則是教師面對學生的特權,只不過前者是“為病人好”、“為平民好”,而這里則是“為學生好”。
這種古典模式的教師信念倫理的動機就是“為學生好”,只要這一點保證了,教師就可以采取“各種手段甚至是錯誤的手段,來‘幫助’學生取得‘進步’”。[5]而所謂的“各種手段”往往都是以“高貴的謊言”為基礎的,在“好心主義”的旗幟下,什么都可以變得“高貴”。蘇格拉底(柏拉圖)說“他們一定要受到教育(不管它是什么)”,[6]孔子則說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7]這里還有一個教師們的“良苦用心”:既然我們的年輕人這么無知、愚昧,容易上當受騙,那么與其讓別人騙,不如讓我們騙,起碼我們是“好心的騙”、“高貴的騙”,再說了“騙”這種手段簡易便捷,對己對人都有好處,何樂而不為呢?教師們認為“有些道理”不能說的太直白,這樣對學生不好。可是,等學生一旦洞悉你的所謂的“高貴謊言”的時候,他們不僅不會聽從你的“謊言”,而且還會變得仇視“高貴”。蘇格拉底也很擔心這樣的結局,所以他說對于真相最好是閉口不談,如果有必要談的話,也應當盡量少人聽到,并把它當做不可說出去的秘密。但是當時的時代,資訊十分不發達,民智也大多處于蒙昧狀態,所以“高貴的謊言”不失為一種好的辦法,雖然仍然有風險。可是這種“高貴的謊言”背后的“理念”的正確性又有誰來保證呢,如果錯了,后果應該來讓誰來承擔呢?如果對了,學生成年之后可能“濫用謊言”的后果又有誰來承擔呢?歷史上,由于哲人們的“唯美主義”,所引發的后人的政治災難比比皆是(如盧梭之于羅伯斯皮爾、尼采之于希特勒)。我們可能會說,不應該怪“教師”和“哲人”,因為后人領會錯了,他們是“好心的”,從沒想到會“誤導”別人。蘇格拉底在這一點上是審慎的,因為他畢竟意識到這樣做的危險性,擔心“自己弄錯了,會有好多人跟著自己栽跟頭”,但蘇格拉底又是沖動的,因為他畢竟還是決定不顧危險地要去賭一把。諾貝爾后悔發明炸藥,奧本海默后悔發明原子彈,我們的哲人與教師面對“高貴的謊言”卻從未后悔過,因為“對別人好”太動人了,太高尚了,蘇格拉底為此不惜選擇去死。所以不管怎么樣,在啟蒙話語出現之前,這種“高貴謊言”都是值得崇敬的,哪怕它伴隨著隨時可能逾越界限的“欺騙”以及各種暴力與壓制,哪怕伴隨著我們的兒童大多由淚流滿面到悲觀絕望。
二、“高貴的真實”——趨于崩潰的教師信念倫理
在啟蒙運動之后,“高貴的謊言”被紛紛打翻在地。古典話語被啟蒙話語所取代,人們紛紛宣布“真實”(不管是不是真正的真實),“人是目的”、“上帝死了”、“人死了”……個個駭人聽聞。在啟蒙話語中,“真實”可以有很多版本,只有那些與“人”有關的、“噱頭”夠足的才是“高貴的真實”。這里暗含了一個預設,“高貴”的標準已經由“人性”而不是“神性”來決定。面對諸多“真實”,年輕人迷惑不解,在他們眼里所謂的各種“真實”如此之多以至于像“鬼話連篇”,但正是這些“鬼話”令“神話”變成“謊言”,而且每一種鬼話都振振有詞,讓年輕人難以辯駁。“神話”雖假,但畢竟聽起來是美好的;“鬼話”雖真,但畢竟接受起來是殘酷的。“諸神”隱退的時刻,自然“群魔”開始亂舞。不管你能不能接受,真實就是真實,雖然殘酷,卻也要你勇敢去接受這份殘酷。“啟蒙教師”們也紛紛揭竿而起控訴“古典教師”的種種罪行:“迄今為止,你的權利都是通過暴力或詭計得來的。他(學生)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權威或義務的法則,因此,必須對他進行強制或欺騙,才能使他服從你。”[8]但是不久人們就開始發現,最可怕的還不是“高貴的謊言”,而是“謊言”被揭穿后的無數“真實”。“謊言”之所以是“謊言”畢竟還有可證偽性,我們可以有證據去揭穿它,從而拋棄它。但“真實”可能出現一個,也可能出現多個,可能是能證偽的,也可能是不能證偽的。另外,“謊言”的兼容性要比“真實”大得多,它可以自相矛盾而又自圓其說,所以至少讓人可以心安理得,但真實具有排他性,為了“高貴”的稱號而角逐的“諸真實”往往打的血肉橫飛。學生們個個心煩意亂,“課堂”無疑是教師們最大的戰場,學生們的思想無疑是教師們最好的戰利品。
這種類型的教師們個個意氣風發,一副志得意滿、真理在握的神情,在自己的科目之內毫無保留的向學生們推銷自己的“信念倫理”,苦口婆心,令人感動不已。但仔細審視一下這些教師的啟蒙事業,我們會發現他們很多只能算作“啟蒙性主體”而不是“主體性的啟蒙”。前者是以教師及教師的信念倫理為核心,而后者則是以學生及學生的信念形成為核心。“啟蒙”(enlighten)原意是指“讓光照進來的意思”,教師本來應該為黑夜里的學生照亮前行的道路,而現在則是直接照向學生的眼睛。學生面對完全的黑暗一無所見,面對滿目的光亮同樣一無所見。這“正如一個夢游病者一樣,當他昏昏沉沉地在一個深淵的邊緣上徘徊的時候,如果突然一下你把他叫醒的話,他就會掉到深淵中去的。……我首先要使他離開那個深淵,然后才喚醒他,遠遠地把那個深淵指給他看。”[9]“高貴的謊言”被揭穿之后,人們對于“真實”給予厚望。但“真實”的絢麗光彩讓他們眼暈,就像一個常年居住在洞穴中的人突然來到陸地一樣,不能一下子接受陽光的照耀。更何況這些“真實”是不是“真”的自己根本沒有能力去區分與判斷。可見,“啟蒙”不是“揭密”,而是讓秘密面對學生自行展開,而要想讓秘密面對學生自行展開,而這無疑要培養學生自己的主體性,開發學生自己的理性。教師信念倫理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機,因為大家突然意識到無論是“謊言”還是“真實”都不如想象中那么高貴。如前所言,本來教師的信念倫理之所以綿延千年主要靠的就是其動機的高尚性,但當其動機無論真實與否都遭到人們的質疑的時候,教師信念倫理幾乎沒什么值得人們留戀的了,更不用提其手段與結果的道德不確定性一直就飽受詬病。再加上當代時髦的責任倫理理論的興起,無疑于加速了教師信念倫理的滅亡。依據韋伯的解釋,責任倫理者在評估行為的價值時不僅要考慮信念價值,還要考慮行動者對其行為后果的責任;而信念倫理卻是以信念價值為唯一的判準,這是兩套倫理學真正無法協調之處。[10]責任倫理看起來似乎是專門為信念倫理而量身打造的替代品。那么,教師信念倫理這塊所謂的“雞肋”到底是扔還是不扔呢?這是個問題。
三、“高貴的沉默”——教師信念倫理的現代模式
教師責任倫理是教師采取行為并不僅僅依據既定的理念規范,而是充分考慮行為的后果,并為任何可能后果承擔責任。教育責任倫理者的口號是“我愿意,我選擇,我行為,我負責”。表面看起來,它既彌補了教師信念倫理的缺陷,又很好的保留了教師信念倫理的優點。但是我們可能忽略了兩點:其一,如果教師采取的既定理念規范恰恰就是要充分考慮行為手段和后果的話,那么這種信念倫理不是也可以替代責任倫理了呢?其二,既定的信念和行為后果之間是不是本身就擁有不可調和的矛盾,也就是說強調信念就很可能忽略后果,強調后果或責任恰恰很容易忘卻我們的既定信念。如果這兩點質疑合理的話,那么我們就可以認為所謂的教師責任倫理很可能是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而并不像它描述的那樣好。在這個基礎上,我們還可以懷疑無論是傳統的教師信念倫理,還是目前時髦的教師責任倫理都存在一個很大的缺陷,即都是以“教師”為中心的。當然,你可以說“教師信念倫理”不以教師為中心不是笑話嗎?可是我們也知道教師角色的特殊性,無論哪種倫理模式,都是“為學生”的,傳統的教師信念倫理可以說“動機上”是“為學生好”,時髦的教師責任倫理則可以說“行為及后果上”是“為學生負責”。但是,關鍵就在這里,到底“為學生什么”?無論是“為學生好”,還是“為學生負責”都隱含著這樣的一個假設:“為學生什么”都是由教師決定的。從來沒有說“為學生自己去追求美好”或“為學生自己去為自己負責”。你也可以說,年齡小的學生哪里知道什么是對他好的,哪里知道怎樣對自己負責?可是你有沒有想過,信念倫理者如果錯了,他只對自己負責;責任倫理者如果錯了,他能對學生負責嗎,他的負責是什么,他的負責對已經受到傷害的學生能真正起到補償作用嗎?所以無論是傳統的教師信念倫理,還是現代的責任倫理都是在拿學生賭博,只不過后者賭的更光明磊落、理直氣壯一點罷了。
多元化價值觀下的現代教育和教師到底需要什么樣的倫理模式呢?“高貴的謊言”被摒棄掉了,“高貴的真實”正在被質疑,宣稱對自己的倫理模式“負責到底”的責任倫理也存在諸多弊端。筆者試圖提出一個新的思路,就是對教師信念倫理進行模式轉換,提倡“高貴的沉默”。“高貴的沉默”是指教師要對于自己的倫理信念持“沉默姿態”,當然這種“沉默姿態”不是“無價值立場”,更不是說“價值中立”,否則它也就不算“高貴”了。實際上,在教育領域中也不可能實現“無價值立場”或“價值中立”。教師的出場都是帶有一定的信念、價值觀的,即使是“無價值觀”本身就是一種價值表態。蘇格拉底(柏拉圖)在表述“高貴的謊言”時,順便說了另一種可能性,即對于真相最好是“閉口不談”,如果有必要談的話,也應當盡量少人聽到,并把它當做不可說出去的秘密。這意味著“謊言”可怕,但“可能的真實”同樣可怕,蘇格拉底說自己萬一錯了,他可是承擔不起這樣的責任的。雖然在柏拉圖口里他還是選擇了謊言,但也為我們保留了另外一種選擇即“高貴的沉默”。實際上,無論是“高貴的謊言”,還是“高貴的真實”都是教師“缺乏耐心”的表現,他們認為這是一條捷徑,可以幫學生省去探索的時間成本,但卻忽略了教育是一項特別需要“耐心”的事業,教師是一個特別需要“耐心”的角色。別的什么事做錯了,我們可以負責,但我們面對的是一個個活生生的人呀!誰能負責。如果是蘇格拉底時代,因為強調精英儀態,我們可以原諒他的冒險,但現在“人是目的”,“平等、自由、人權”等觀念已經深入人心,我們怎么還能拿學生們冒險呢?更何況即使是蘇格拉底的時代,他冒這個險時依然如履薄冰、思慮再三,而我們竟然敢理直氣壯的“我選擇,我負責”!另外“沉默”不表示教師無所作為,而是教師的“作為”是一種“消極作為”,重在“引導”學生樹立真正屬于自己的價值觀并讓學生學會對自己的價值觀負責,畢竟他們才是他們自身的主人。這種“引導”就是一種“春風化雨”,一種“潤物細無聲”,一種“默然有為”。“沉默”不是無話可說,恰恰是有所言說,是教師的一種殷殷的價值期待,只說可說之話,對于不可說的要堅決閉口不談,這就是教師信念倫理的“高貴的沉默”。這種倫理模式需要我們的教師需要極大的“耐心”,因為你不能說“謊話”(教師高貴的謊話),也不能說自認為的“真話”(教師高貴的真實),更不能“不管什么話”一吐為快并大言不慚的說自己可以為學生負責(教師責任倫理),只能默默的引導學生學會說出屬于自己的話 (教師高貴的沉默)。當然,本文在這里只是基于柏拉圖《理想國》“高貴謊言”的啟示而提出的一種模式設想,并沒有深層次的進行模式探討,但我們如果不想徹底拋棄教師信念倫理話,則必須對教師信念倫理模式進行改造,而任何一種改造設想無疑都是有意義的。
[1][5]梁明月,論教育中的信念倫理與責任倫理[J].當代教育科學,2010,(19).
[2][3][4][6]柏拉圖.理想國[M].郭斌和.張竹明譯.北京:商務印書社,2007,73.82.81.117.
[7]《論語·泰伯篇》
[8][9]盧 梭.愛 彌 兒[M].李 平 漚 譯.上 海 : 商 務 印 書 社 ,2001,465.471.
[10]李明輝.存心倫理學、責任倫理學與儒家思想[J].浙江學刊,2002,(5).
張曉陽/南京師范大學道德教育研究所碩士生
(責任編輯:劉吉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