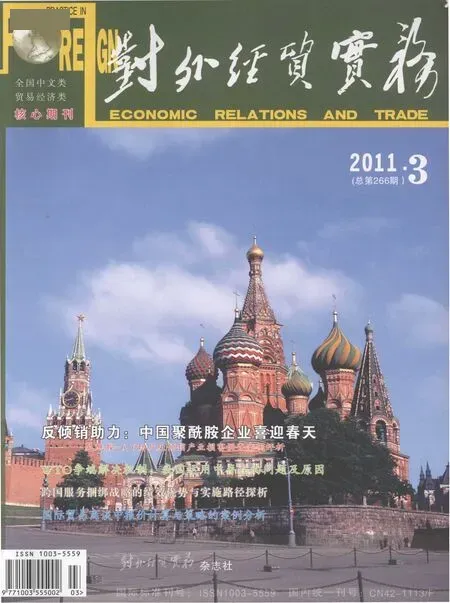馬克·扎克伯格:IT王國新國王
畢 夫 本刊特約撰稿人
馬克·扎克伯格:IT王國新國王
畢 夫 本刊特約撰稿人
馬克·扎克伯格以自己一手打造的社交網站Facebook(臉譜),顛覆著互聯網的傳統模式,推動著當代人類生活的深刻變革與改造。而在將先鋒式創新演變成橫掃世界潮流的同時,扎克伯格也實現了個人價值的加速升騰:入主福布斯400榜單,成為全球最年輕的億萬富豪;榮登2010年《時代》封面,成為該雜志自1927年以來最年輕的年度人物之一。
電腦神童與哈佛輟學生
成長于紐約富裕郊區多布斯菲利的扎克伯格應該算是一個幸運兒。在家里四姊妹中,扎克伯格排行老二,而且因為是唯一的男孩而格外受到父母的寵愛。重要的是,作為牙醫的父親和作為心理醫生的母親還有相當不錯的收入,可以使兒時的扎克伯格衣食無憂,因此,10歲時扎克伯格就從父母那里獲得了一臺昆騰486DX電腦。當然,扎克伯格也沒有讓父母失望。在得到電腦的幾個月后,他就為家里人搭建了一個家庭局域網,取名為Zuck Net。
細心的母親發現了兒子在電腦方面的特殊天賦,于是專門為扎克伯格請來了計算機課家庭教師。在老師輔導下,扎克伯格開始學會編寫各種小游戲。令輔導老師驚訝地是,并不像一般小孩只沉溺于娛樂游戲那樣,特別喜歡古典文學并且讀過許多文學名著的扎克伯格非常擅長于以文學歷史為題材開發各種故事游戲,如以古巴比倫王國的獨裁者為藍本的戰爭游戲,根據羅馬帝國故事編寫出的冒險家游戲等。觸類旁通。令扎克伯格的父親沒有想到地是,在自己生日的那天收到了12歲不到的兒子為自己的診所單獨開發和編寫出的一個提醒病人來訪的自動程序。
就讀于美國最好的高中——菲利普埃克塞特學校不僅讓扎克伯格接受到了更好的文學知識教育,而且也讓他的電腦才能第一次被社會所認知。在校期間,扎克伯格設計出了一個名為Synapse的音樂播放器,它既能跟蹤使用者的音樂愛好,還可以自動提供投其所好的音樂。扎克伯格把這款軟件上傳到互聯網上供人免費下載,他的才華很快得到了包括美國在線和微軟等大公司的賞識,微軟甚至開出了95萬美元的年薪籌碼邀請扎克伯格加盟。不過,扎克伯格還是在高中畢業后選擇去哈佛大學繼續讀書。
在哈佛,主修心理學的扎克伯格仍然癡迷電腦,并為自己設計了網站Facemash。當時哈佛大學不像其他學校那樣提供附有學生照片和基本信息的花名冊,扎克伯格就想為學校建立一個網絡版的花名冊,但學校以各種理由拒絕提供相關信息。于是,還是哈佛大一新生的扎克伯格在某個夜里入侵了學校電腦的數據庫,獲取了里面存儲的學生照片,并將這些照片放在Facemash上,以供同班同學評估彼此的吸引力。校方對扎克伯格的行為非常不滿,給了他一個“留校察看”的處分,Facemash隨即也被校方強行關閉。
背著處分的扎克伯格很快引起了另外兩位哈佛大三的學生——溫克萊沃斯兄弟的注意。當時這對孿生兄弟正在開發一個名為Connect U的哈佛內部交友網站,特別需要像扎克伯格這樣具有電腦奇才的人幫忙。而在溫克萊沃斯兄弟的反復邀請下,扎克伯格最終同意加入。然而,自信心和獨立性極強的扎克伯格并不想依附于人。在與溫克萊沃斯兄弟僅僅合作了一個月不到的時間,扎克伯格就決定自己單干。也大概僅用了一個星期的時間,扎克伯格建立起的名為Facebook的網站橫空出世。意想不到的是,網站剛一開通就走紅整個哈佛校園,24小時之內,已有一萬五千位哈佛學生注冊成為其用戶,并以極快的速度傳出哈佛校園。而為了全力和全職經營Facebook,扎克伯格決定從哈佛退學。
世界第三大“國家”
隨著注冊人數和訪問量的增加,Facebook必須擴展應用平臺以滿足用戶的需求,為此急需后續資金的注入。幸運地是,在扎克伯格走出哈佛校園前夕,出身富商并且已是哈佛大四學生的薩瓦林同意向 Facebook投資 1萬美元。作為回報,扎克伯格向薩瓦林轉讓了Facebook30%的股份,同時任命薩瓦林為網站首席財務官。不過,由于忙于到華爾街實習,薩瓦林來不及參與Facebook的具體經營與管理,為此,扎克伯格決定將Facebook注冊地從佛羅里達州轉到硅谷,以方便找到所需要的專門人才。
應當說,搬到硅谷后的Facebook當時依然是局限于哈佛的一個校園交友網站,因此,資金瓶頸打破后,扎克伯格所思考的問題是如何讓Facebook從哈佛走向其他常春藤學校。對此,扎克伯格開創出的傳播路徑也非常特別——將自己從一個影響力很強的區域或者人群,帶到另一個影響力比較弱的區域。如Facebook在哈佛大學的絕對優勢,對于西海岸的斯坦福大學卻是鞭長莫及,而扎克伯格則發現高中是連接這兩所大學的紐帶,于是Facebook通過有策略的開放高中,由哈佛的學生帶動他們讀高中時其他同學,而這些高中同學有些就在斯坦福讀書,并且由此滲透進一個新的疆土。
開拓Facebook向校園外傳播的路徑也讓人看到了扎克伯格思想的獨特。以扎克伯格建立Facemash網站時積累下來且最為拿手的功夫——圖片傳播為例,以往在互聯網上傳圖片都是用主題、時間、地點等方式來作為標簽,然后供用戶自己進行分類檢索。但是Facebook決定以每個用戶社交網絡中的關聯人物作為標簽,每個被標注到的人都會收到提示信息,進而看到這張照片。這種讓圖片基于人際關系的主動推送,大大提升了Facebook的傳播效率,進而讓網站的活躍度獲得了又一次躍升。
市場對扎克伯格的良苦用心和別出心裁給予了豐厚的額回報。2004年底,Facebook的注冊人數突破一百萬;2005年9月,Face-Book在美國的注冊用戶達到5250萬,有60%的學生和年輕人都會使用該網站;2005年底,Facebook擴展成從美國到歐洲和亞洲的全球性網站。2010年,地球上每12個人之中就有一個人在Facebook上擁有賬號,這些用戶來自世界各地,說75種不同的語言。如今,Facebook的注冊用戶已經超過了5億,而且用戶數每天正以70萬人的速度增長。因此,美國《時代》雜志指出,如果Facebook是一個國家,那它將僅次于中國和印度,為世界“第三人口大國”,而“這個國家的國民”更有優勢,因為他們掌握了最多的信息。
事實上,Facebook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社交網站除成為普通朋友間交流與溝通的平臺之外,人們還能從中看到許許多多的明星“臉譜”:美國前總統小布什專門在Facebook上推銷自己的回憶錄《抉擇時刻》,巴基斯坦遇刺身亡的“鐵蝴蝶”貝布托之子比拉瓦爾就曾在Facebook設有主頁,現任美國總統奧巴馬和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皆為Facebook的忠實用戶。也許看到了Facebook的強大眼球效應,雅虎曾向扎克伯格開出了高達10億美元的收購加碼,但被扎克伯格無情擋了回去,而扎克伯格的理由異常地簡單:因為“它是我的孩子”。
Facebook發展到今天已經遠遠超出了雅虎當時的收購價格。按照Facebook剛剛完成的15億美元融資額而對公司約500億美元的整體估值計算,Facebook市值已超過騰訊、eBay、雅虎等公司,成為全球第三大互聯網公司,僅次于谷歌和亞馬遜。而在Face book不斷變大的同時,扎克伯格的個人財富加速膨脹。根據《福布斯》2010年富豪榜排名,26歲的扎克伯格以高達245%的年財富增長率躥升至第35位,個人財富達到69億美元,成為全球財富增長速度最快的人。與此同時,扎克伯格被評為《時代》周刊2010年年度人物,成為歷史上第二年輕的《時代》年度人物,僅次于獲此殊榮的第一人——首次單人飛越大西洋的查爾斯·林白。
改造互聯網
互聯網發展到今天,既產生了如同Google的搜素引擎,也不乏如同MySpace的社交平臺,更有如同雅虎那樣的眾多資訊網站。而在短短的六年時間里,Facebook將一個又一個IT界元老遠遠甩在后面,必定有著他獨特的競爭優勢和成功密碼。對此,《時代》主編理查德·斯滕格爾這樣解釋道:這位哈佛大學的輟學生創建了一種信息交換的新體系,它既讓人覺得不可或缺,有時也有點讓人害怕;他用新鮮甚至樂觀的方式,改變了我們所有人的生活方式。而中國海爾領航人張瑞敏的評價是:Facebook是創造需求,而他的同行或者對手則是滿足需求。當然,扎克伯格的自我解釋也許更有說服力:“很多公司經營的網站都聲稱立足于社交網絡,他們的網站大同小異,提供的都是約會地點、媒體信息集粹,或者交流社區類似的信息,但是Facebook旨在幫助人們理解這個世界。”
互聯網誕生之初的設計理念是當時盛行的反傳統思維,整個網絡中沒有任何中樞,也沒有任何人統一管理。這是平等和匿名的天堂,每一個人都能夠隱去自己的身份在網絡中遨游,可以任意選擇你的年齡、性別、種族、婚姻、工作、住所等等信息,因此,人們不知道你在網上和誰在交談,只是登錄、聊天、然后下線。但隨著網絡信息量的不斷膨脹,匿名互動的體驗給網絡空間帶來了種種負面影響。平等性和匿名性反而讓互聯網成為不受監管的世界,這里日益成為黃色信息和病毒制造者的樂園。“我們嘗試著去復制現實社會中所存在的一切。”扎克伯格說:“在這個社會中,信任是最基礎的。所以我們的核心理念是,將這種信任關系在互聯網中重現。在多數時候,這種信任關系就是友情。”為此,Facebook在互聯網世界第一次引入實名制,使得原本魚龍混雜的互聯網世界第一次出現了內容同現實世界高度接近的站點,特別是在一個都不知道聊天對象是一個人還是一條狗的信息海洋里,Facebook開辟了嶄新的世界。
然而,在一個開放的網絡平臺上,實名制的引入讓人們為自己隱私是否得到保護而擔憂。在社交網站MySpace中,幾乎所用的注冊用戶都知道,只要自己愿意就可以瀏覽所有其他用戶的資料。但是,與MySpace不同,扎克伯格坦言,通常一個普通用戶只能看到 Facebook群體中不到0.5%的其他用戶信息,這是因為Facebook采取了完善的信息保護機制,不讓信息泛濫成災,保證了用戶的隱私權安然無恙。之所以如此,取決于Facebook有一套復雜的個人隱私保護法則。如果第三方想了解某個用戶的信息,該用戶很快就能洞察對方的舉動,所以用戶可以允許屬于特定群組的朋友了解他本人,同時能阻止無關緊要的其他用戶窺視自己,用戶甚至可以決定他提交給Facebook的信息究竟有多少能被第三方搜索到。為此,Facebook要求用戶提交的個人資料都是標準格式的,而不是像MySpace那樣帶有很大的隨意性。
進一步分析發現,扎克伯格不僅改變了互聯網的模式,還改變了人類的互聯網體驗。如果說21世紀的前10年,谷歌以其強大的數理邏輯能力開發出搜索引擎,滿足了海量信息條件下人類個體對于定位獨特信息的需求,從而重塑整個互聯網的話,那么Facebook的出現則意味著互聯網世界的第二次裂變。谷歌擁有強大的數據庫與計算能力,Facebook則擁有遷移自現實社會關系的一系列節點與路徑——“節點是個人,路徑是朋友關系”;谷歌利用搜索引擎溝通個人與海量的信息,Facebook將個體重新編織進入曾經存在于現實世界中的社交網絡;谷歌致力于滿足個體的信息需求,但卻不知道這需求從何而生,Facebook致力于在互聯網上還原有血有肉的現實社交生活,因為扎克伯格堅信社交才是人類需求的源泉。顯然,在Facebook里,扎克伯格所貫徹與堅守的乃是一種人性化和社會學色彩極其濃厚的嶄新世界觀與方法論,而在公眾對權威的信任感逐漸退化,對開放和透明的渴求空前狂熱的認識生態中,這種世界觀與方法論借助著互聯網平臺很容易演變成改造世界與社會的力量。
乳臭味干的“蓋茨第二”
身穿風格奇特的T恤和破爛陳舊的牛仔褲,腳蹬阿迪達斯運動鞋,講起話來甚至有點靦腆——表面上馬克·扎克伯格給人的感覺和任何普通的大學生沒有什么區別。不過,由于巨大的成功,扎克伯格已經被人描述得成熟了很多,其中最為流行的就是外界習慣稱扎克伯格為“比爾·蓋茨第二”。
對于外界的恭維,扎克伯格在Facebook網站上作出這樣的回應:“對前輩比爾·蓋茨,我個人相當尊敬,他也是IT業界的成功典范。如果外界非要給我加上‘蓋茨第二’的帽子,這是你們的一廂情愿。我為什么要成為比爾·蓋茨呢?微軟靠的是Windows和Office發家,承載我夢想的是互聯網,更具體說是Facebook。”顯然,扎克伯格并不喜歡“蓋茨第二”這個綽號。
不過,盡管扎克伯格對安在自己頭上的“蓋茨第二”不予認同,但仔細分析發現,其身上確實存在著與比爾·蓋茨許多驚人相似之處。他們都在19歲就開始創業,成立自己的公司,同樣是出身中產家庭且教育良好,同樣是哈佛大學的輟學生,同樣年紀輕輕就成為世界首富。更重要的是,二人都活躍在IT世界,并憑借著虛擬工具影響和改變著世界。其實,除了成長過程和財富膨脹速度可以找到共同點之外,扎克伯格可愛隨性的一面與比爾·蓋茨如出一轍——接受采訪時,他會露出虎牙,甚至還晃蕩著一雙光著腳丫子的拖鞋。
不可否認,扎克伯格與比爾·蓋茨確實存在著某些緣分。據傳,當年微軟向扎克伯格拋出了95萬美元的加盟“繡球”時,如果不是微軟要求早上8時會面的話,不能按時起床的扎克伯格后來可能成為蓋茨手下的一員愛將。及至后來,連扎克伯格自己也承認,促使他決定離開哈佛的是蓋茨2004年在哈佛電腦課上的一席講話。“蓋茨鼓勵我們利用課余時間從事某個項目,而當時哈佛也允許學生休學創業。當時蓋茨開玩笑對我們說‘如果微軟失敗,我會重返哈佛’。”沒有猶豫太久,扎克伯格就踏上了追隨前輩的道路。特別讓扎克伯格對比爾·蓋茨心存感恩的是,微軟投資2億美元買下了Facebook的廣告和贊助商鏈接的獨家經營權。扎克伯格認為,這筆錢能讓Facebook更集中精力考慮未來的發展思路,例如激勵用戶參與發展更多的原創運用,而不是致力于兜售廣告。
當然,外界發現,扎克伯格已經找到了與比爾·蓋茨完全重合的人生之路——社會慈善。半年之前,扎克伯格宣布捐贈1億美元贊助新澤西州紐瓦克市修繕學校,而且這次捐贈創下美國青年人慈善捐款紀錄。另外,扎克伯格加入了由蓋茨和巴菲特發起的“捐贈承諾”行列。而對于作出捐出自己一生絕大多數財富的決定,扎克伯格也在Facebook里作了這樣的表白:“一些人等到事業晚期才回饋社會,可現在就有那么多事情需要做,為何要等待?我們中一些人很可能在人生早期回饋社會,見證我們慈善努力的影響。”難能可貴地是,在慈善事業上出手大方的扎克伯格卻依然住著租來的一套一室一廳的小公寓,地板上放一個床墊,兩張椅子、一張桌子就是全部家具;他的早餐通常都是一碗麥片,每天走路或騎自行車上班。
其實,扎克伯格不喜歡人們叫自己為“蓋茨第二”,關鍵在于要突出自己與蓋茨的不同。在扎克伯格看來,數字化時代的網絡技術遠非工具,也不純是個手段,而更確實是個具備實質性內容的實體。也正是如此,我們看到,他的Facebook讓5億多人成功連接在一起,并在他們之間繪制社會關系,創造了一套交換信息的嶄新系統。同時,扎克伯格并不僅僅是將Facebook看作社交網站,就如他自己所言,Facebook不只是一個社交連接的網站,而是發揮社會效能的網絡。因此,當全球十分之一的人集結在某個個體的門下,這其中的巨大的能量已經超出了一個國家,也超出了某個巨人的范疇。
孤獨的爬涉者?
也許扎克伯格根本不會想到,自己“在去世之前就被拍成了電影”,而且這部以《社交網絡》為名的電影聲稱完全以Facebook創始人的故事為藍本。據稱,自2010年10月至今,《社交網絡》影片風靡美國大學校園和各大影院,創作人員甚至揚言可以拿到奧斯卡大獎。
在以“性、金錢、天才和背叛”為副標題的《社交網絡》影片中,個性孤僻的馬克被描述成在戀愛失敗后一夜之間搭建起Facebook的雛形——一個對哈佛女生外表進行評分的校園網站,以圖吸引心儀女孩的注意。然而事與愿違,這種傷人自尊的評比招致女生們的強烈譴責,并使馬克的處境更加孤立,乃至哈佛的任何一個高級會社都將他拒之門外。影片向人們傳送的是這樣一幅扎克伯格形象:孤獨、寂寞,難以被他人了解,一個動機不明,永遠躲藏在密不透風言語背后的混蛋。
當然,由于向《社交網絡》編制組提供基本素材——《偶然誕生的億萬富翁》一書的作者是與扎克伯格有著恩怨的薩瓦琳,扎克伯格就不缺乏為自己申辯的理由。在接受《福布斯》雜志的采訪時,扎克伯格表示:“那不過只是一部小說,而小說都是虛構的”。不過,令扎克伯格沒有想到的是,也許受到《社交網絡》影片的影響,風行硅谷的《紐約客》雜志在一篇報道中也對自己作出了十分不利的報道,該報道稱:從哈佛到硅谷,曾與他患難與共的早期合作者們一個又一個地離他而去,引發了人們對這位年輕總裁人事處理能力的嚴重懷疑。而這篇文章隨即也被《華爾街日報》等全球權威媒體廣泛轉載。
回顧Facebook的幾次重大人事變動,并不難注意到其中扎克伯格與最初合作者的恩恩怨怨和情感糾結。第一個與扎克伯格決裂的重要人物是向Facebook首批注資的薩瓦林。作為首席財務官,薩瓦林后來堅持要求在網站上投放廣告,以回收自己先前的投入并從中掙錢,而扎克伯格則堅決反對在Facebook中植入廣告,并要求薩瓦林繼續向公司注資。在遭到薩瓦林的拒絕之后,扎克伯格只得尋求硅谷風險資本的支持,而在風險資本家的建議下,扎克伯格通過多次增發股份的方式最終將薩瓦林在Facebook中的股權稀釋至千分之一并直至將薩瓦林驅逐。不過,很難說薩瓦林就是最后的輸家。通過法律訴訟,薩瓦林后來贏回了自己在Facebook中至少7%的股份,他最初的那1萬多美元投資如今已經超過了10億美元;而為了防止公司走向急功近利的誤區,扎克伯格付出了友誼的代價。
與溫克萊沃斯兄弟還沒有畫上句號的官司也成為了外界負面炒作馬克伯格的重要題材。這對孿生兄弟在訴訟中譴責Facebook盜用了Connect U的數據與創意。這場糾紛曾在2008年達成協議,扎克伯格同意用部分Facebook股權和現金來解決爭端,但隨著Facebook的股價迅速攀升,溫克萊沃斯兄弟又以當初的協議存在證券欺詐為名重新發起訴訟。
對于與自己當初創業存在極大關聯的人物以及所發生的法律糾紛和最終判決,扎克伯格總是躲得遠遠的而盡量不給出任何評價,于是出現了電影《社交網絡》中最打動人心的一段——
律師問馬克:“你到底知道不知道,你侵犯了我委托人的利益?”
馬克沒理他,只是轉過頭,盯著窗外,一臉寂寞地說:“下雨了。”
滿頭銀發的律師又問:“你是認為我剛才說的,不值得你關注嗎?”
馬克很實誠地回答:“是的。”然后又轉過頭,望著窗外的雨。
許多觀眾對于扎克伯格的態度迷惑不解,但只要看到Facebook上那句直抵心靈的說法——“愛的反義詞不是恨,而是漠然”就不難找到答案。從某種意義上而言,被《華爾街日報》稱為“娃娃CEO”的扎克伯格的確有一個成熟和進化的過程,而在這個過程中,扎克伯格付出了必然性代價。實際上,現實中的扎克伯格并不是孤家寡人和與世隔絕。他可以與工程師打賭稱一周可以完成5000個俯臥撐,并且每天定時休息去做10-15個俯臥撐,其中有一次還是在與來訪者開會期間,最后他做到了;Facebook總部采用開放式布局,室內有一個名為CafeX的咖啡廳,雇員還可以在公司外面的草坪上舉行燒烤聚會,而扎克伯格就坐在辦公室大廳中間的一張大桌子上,跟普通員工之間并沒有任何墻壁。
10.3969/j.issn.1003-5559.2011.03.003
本文作者系廣東技術師范學院天河學院經濟學教授、中國市場學會理事、本刊編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