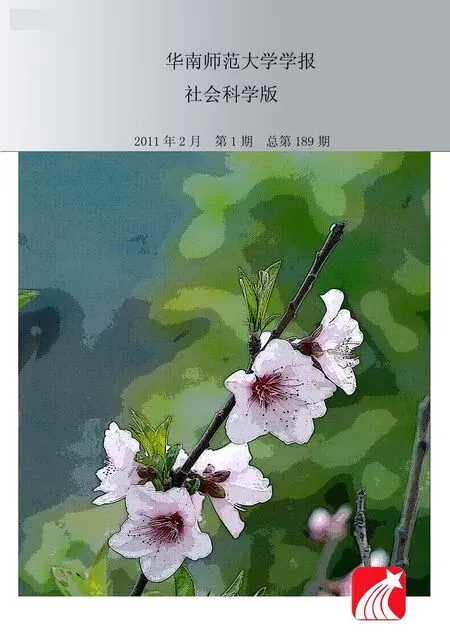牟宗三對康德“物自身”學說的改造及其內在問題
盧 興, 吳 倩
(1.南開大學 哲學院,天津 300071;2.天津外國語大學 涉外法政學院,天津 300204)
作為現代新儒家第二代的重要代表,牟宗三力圖會通中西哲學傳統以實現儒家傳統的現代轉化。在牟氏思想的西學資源中,康德哲學無疑占有突出的地位,其所建構的“兩層存有論”直接源自康德關于“現象”與“物自身”的劃界。正如許多學者所指出的,牟宗三對康德的“物自身”學說進行了儒家式的改造,實際上是借用康德的術語重建了儒家的價值本體。然而學界以往的研究或是依據于牟氏的觀點進行述介,或是站在康德哲學的立場上批評牟氏的誤讀,而對于牟氏的這種改造工作的思想理路分析得不夠細致,對于其中所存在的理論問題揭示得不夠深入。本文試從康德和牟宗三的文本著手,對上述問題予以探討,以期推進相關領域的研究。
一、牟宗三對康德“物自身”學說的改造
康德在西方哲學史上最偉大的發現在于對人的認識能力進行了批判,提出了“現象”與“物自身”的劃界,在此基礎上將知識的來源轉到主體自身,實現了認識論上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在康德的“革命”中,傳統形而上學所探討的對象都被歸入“物自身”的范圍而置于“只可思而不可知”的彼岸世界,而“物自身”卻成為康德哲學的“黑箱”,歷來為后學所爭訟不已。嚴格地說,康德所言之“物自身”不是一個“概念”(“概念”屬于知性),而是一個超驗的領域(知性所不及),其中包含了復雜的內容,只不過基于一個共同特征而被歸在一起,這個共同特征就在于“不可知”。康德有時用單數Ding an sich(英文thing in itself),有時用復數Dinge an sich(英文things in themselves)。這是一個頗有意思的問題:既然“物自身”不可知,那么何以會有復數(因為關于“量”的范疇屬于知性而不能有超驗的運用)?這就涉及“物自身”這一術語的具體所指。簡言之,其在理性的理論運用中基本是消極的含義,是“感性的來源”、“認識的界限”和“理性的理念”[注]參見李澤厚:《批判哲學的批判——康德述評》,第239-240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而在理性的實踐運用中具有積極的含義,主要指實踐理性的三個“懸設”。因此,盡管“物自身”是一個“黑箱”,但其對認識和實踐所產生作用是明確的,其自身也透露給我們一些信息,至少我們思維到有三個不同的理念歸屬于其中,故而可以將“物自身”的所指符號化為“3+X”:其中的“3”指“意志自由”、“上帝存在”和“靈魂不朽”三個純粹理性的理念,在這個意義上的“物自身”屬于“本體”(Noumenon);其中的“X”指刺激感性直觀產生經驗卻不為直觀所及、同時作為知性之統覺所對之“物”而作用于經驗,這個意義上的“物自身”是“先驗客體”(das transzendentale Objekt)。以上所言之“本體”與“先驗客體”在消極意義上(不可知)可以等同,而在積極意義上有細微的差別。這樣,在康德看來,所謂“物”(Ding)或“對象”(Gegenstand)被區分為兩重身份:“現象之物”(“感性直觀”的對象)和“自在之物”(“智性直觀”的對象)。康德進一步在“物”(“對象”)的兩重身份的意義上,以拉丁文“Phaenomena”與“Noumena”表示兩個世界的劃分,這兩個世界分別是經驗的“感知世界”和超驗的“理知世界”。實際上康德所謂的“Noumena”是一個表征范圍的概念(代表了整個“理知世界”),而不是表征實體的概念(因為不存在這樣一個“實體”),因而“本體”可以是復數。
牟宗三不贊同將康德所說的“Noumena”直譯為“本體”,而譯之為“智思物”。因為這一概念與中國哲學中所講的“形而上的實體”意義上的“本體”很不相同:后者是唯一的、絕對而無限的;而康德所講的“Noumena”卻是一個復數的概念,代表了一種“散列的態度”,其既包括“自由”、“靈魂”和“上帝”三個理念,也包括“物之在其自己”即作為“Noumena”身份的“物”。[注]牟宗三:《現象與物自身》,第44、3、7頁,(臺北)學生書局1975年版。在牟宗三本人的使用中,“本體”指“本心仁體”或“知體明覺”;“物自身”既指狹義上的“智思之物”(與三個理念并列),也指廣義上的“本體界”(“睿智界”):當牟氏依據康德的二元劃分而建立“兩層存有論”時,“無執的存有論”對應于廣義的“物自身”;當牟氏講“心物一起朗現”時,這里的“物”是狹義的“物自身”。
盡管牟宗三大量借鑒了康德的術語,但兩者根本不同在于牟氏完全摒除了康德賦予“物自身”的“不可知性”,由于承認人具有“智的直覺”(一般譯為“智性直觀”)的能力,可以直覺到甚至創造出狹義的“物自身”,因而后者成為一個確定性的表征實體的概念,這樣的“Noumena”就是一個實實在在的“物之本來面目”,并且我們的“心”對其有完全的把握。這樣進一步引起了牟氏的追問:“問題底關鍵似乎是在:這‘物自身’之概念是一個事實問題底概念呢,抑還是一個價值意味底概念?這點,康德并未點明,是以讀者惑焉。”[注]牟宗三:《現象與物自身》,第44、3、7頁,(臺北)學生書局1975年版。需要指出的是,這個問題并不是康德的問題,而是牟氏自身的問題。因為如果我們能夠分辨清楚“物自身”是“事實的”還是“價值的”,那么其無疑就是可知的,這顯然不是康德的思路。牟氏之所以有此問題,在于其肯定了“智的直覺”能夠完全把握“物自身”,因而必須把“物自身”的內容說明白,而后者是康德說不明白抑或沒必要說明白的問題。牟氏進一步指出,“物自身”不是一個認知對象意義上的“事實上的原樣”,而是一個“高度價值意味的原樣”,如禪宗所說的“本來面目”。“如果‘物自身’之概念是一個價值意味的概念,而不是一個事實概念,則現象與物自身之分是超越的,乃始穩定得住,而吾人之認知心(知性)之不能認識它乃始真為一超越問題,而不是一程度問題。”[注]牟宗三:《現象與物自身》,第44、3、7頁,(臺北)學生書局1975年版。這樣,在康德那里消極意義上的“物自身”(狹義)被轉化為積極意義上的“價值本體”,進而將整個“本體界”(廣義的“物自身”)轉化為一個“價值世界”,這里既顯示出牟氏將本體世界價值化的儒家立場,也可以看到其對康德哲學的一種創造性的“誤讀”。牟氏認定“物自身”是一個高度價值意味的概念,其實質在于:首先將“先驗客體”意義上的“物自身”收攝于“Noumena”意義上的“物自身”之中,大大弱化了“物自身”在認識過程中作為經驗統一性之基礎的意義;其次將“Noumena”意義上的“物自身”實體化為“智的直覺”所對之“內生自在相”(Eject),成為宇宙本源意義上的“實體”,類似于神學中上帝所造之“物”;再次將這個“物”納入儒家“道德的形上學”體系而價值化為道德意義上的“實理實事實物”,成為價值意義上的“物”。經過這一實體化、價值化的過程,“物自身”就成為了王陽明所講的“明覺之感應”意義上的“物”;與此同時,三個超驗理念“自由”、“靈魂”和“上帝”轉化為一個呈現即“自由無限心”,故而在明覺之感應中“心”與“物”呈現為一種“體用互即”、“如如朗現”的關系。這樣,康德那里廣義的“物自身”概念所蘊含的“3+X”的結構就被牟宗三改造為“心體物用”的結構,整個“本體界”就等同于“價值世界”;而康德關于“現象”和“物自身”的區分就被改造為“事實世界”與“價值世界”之間的劃界。
二、牟宗三“物自身”學說的內在問題
如前所論,牟宗三對康德的“物自身”概念進行了儒家式的改造,肯斷“物自身”是一個高度價值意味的概念,將這個概念進行了“實體化”和“價值化”,這顯然并不符合康德的原意。同時在這種改造中包含著一個嚴重的問題,就是在康德那里作為認識來源的“物自身”的意義被牟氏極大地弱化了。因此在他的哲學體系中,本體界僅僅是道德的世界,認知主體和認知對象都不具有真正意義上的本體地位,整個認知活動以及事實世界都缺少形上根據。這一做法的結果是,盡管牟氏在“現象界的存有論”層面進行了知識論的建構,但這種知識論僅僅成為一種無根的附屬物(用牟氏自己的話說是一個“虛執”和“權用”),難以真正為經驗知識以及科學民主奠定基礎。
以下具體分析牟宗三對“物自身”概念的“實體化”和“價值化”過程,進一步揭示其中所存在的問題。先看第一步“物自身的實體化”。前文已述,康德所謂“物自身”的內涵是“3+X”,其中的“X”是“先驗客體”。“先驗客體意味著一個等于X的某物,我們對它一無所知,而且一般說來(按照我們知性現有的構造)也不可能有所知,相反,它只能作為統覺的統一性的相關物而充當感性直觀中雜多的統一,知性借助于這種統一而把雜多結合成一個對象的概念。”[注][德]康德:《純粹理性批判》,第228-229、331頁,鄧曉芒譯,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先驗客體”既為外部現象奠定基礎,也為內部直觀奠定基礎[注][德]康德:《純粹理性批判》,第228-229、331頁,鄧曉芒譯,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康德對“先驗客體”的描述表明這是一個認識論意義上的術語。一方面刺激感官產生直觀中的雜多,另一方面作為統覺的相對之物確保表象的統一性,這些對認識過程都有積極的作用。牟宗三通過研讀康德的著作,指出其所使用的“先驗客體”與“本體”兩術語容易引起混淆,認為“‘超越的對象’(本文譯為‘先驗客體’——引者注)一詞實是不幸之名,亦即是措辭之不諦”[注]牟宗三:《智的直覺與中國哲學》,第76、90頁,臺灣商務印書館1994年版。,因而可以把康德“先驗客體”之名取消。在牟氏看來,“物自體(本文譯為‘本體’——引者注),假定預設一智的直覺時,它可以為一‘真正的對象’。”[注]牟宗三:《智的直覺與中國哲學》,第76、90頁,臺灣商務印書館1994年版。牟宗三之所以取消了康德這個認識論上具有積極作用的概念,實質上是將虛指的“先驗客體”收攝于實指的“本體”(Noumena)之中,這樣就完成了“物自身”實體化的轉變。這個實體性的“物自身”就是“智的直覺”所呈現的“物”,亦即“自由無限心”之“經用”。
再看第二步“物自身的價值化”,牟宗三進而證明這個實體性的“物自身”必然是價值意義上的實體而不能是事實意義上的實體。在解析康德關于“現象”與“物自身”之間先驗的區分時,他曾多次引用康德《遺著》中的話:“物自身之概念與現象之概念間的區別不是客觀的,但只是主觀的。物自身不是另一個對象,但只是關于同一對象的表象之另一面相。”[注]Kant: Opus postumum,科學院版《康德全集》, Bd.ⅩⅫ, S.26. 這里引用是牟宗三的譯文,見氏著《智的直覺與中國哲學》,第37頁。康德在這里所謂“主觀的”(subjektiv)意思是說以上區分是對人的認識能力而言的,而其對人之外的存在者是否依然有效是我們不得而知的。這更不意味著確定有一個“上帝”在人之外實存著。而牟宗三則將這里的“主觀的”理解為對于兩種不同的“直覺”而言,認為對于同一個“物”,以“智的直覺”觀之為“物自身”,以“感觸直覺”觀之為“現象”;而康德只承認人具有“感觸直覺”,將“智的直覺”交托給上帝,故此康德不能充分證成“現象”與“物自身”的先驗區分。由于牟氏將“物自身”實體化了。因此必然實存著一個“智的直覺”去創造它,這樣“上帝”就作為一個實體性概念被牟氏引入了康德的哲學框架中:“如果我們把上帝類比于本體,則依康德,上帝所面對的不是現象,乃是物自身。如是,這乃成上帝、物自身、現象之三分。這是客觀的、籠統的說法。如果詳細言之,同一物也,對上帝而言,為物自身,對人類而言,則為現象。”[注]牟宗三:《現象與物自身》,第14-15、10、111頁。在牟氏看來,康德為了保證兩層的區分,必須請出一個實存的“上帝”來創造“物自身”,這就將“上帝造物”的神學問題引入康德的論述:“吾人根據神學知道上帝以智的直覺去覺一物即是創造地去實現一物。”[注]牟宗三:《現象與物自身》,第14-15、10、111頁。就“上帝造物”而言,就出現了“無限”(“上帝”)如何創造“有限”(“被造物”)的問題,這里牟氏又將康德關于時空的觀念性引入這個神學問題的解釋中,指出上帝所造之物(“物自身”)不在時空之中(因為時空是人的先天直觀形式)。“如果真要肯定它無時空性,它之為有限物而在其自己決不是一個事實概念,而是一個價值意味的概念。只有在此一轉上,它始可不是一決定的有限物,因此,始可于有限物上而說無限性或無限性之意義。”[注]牟宗三:《現象與物自身》,第14-15、10、111頁。這里,“有限物具有無限的意義”就是說物自身“無而能有、有而能無”,這就是牟氏所謂的“價值”的含義,因而他得出了“物自身是一個價值意味的概念”的結論。接下來牟氏就比較順利地將“智的直覺”歸屬于人之“自由無限心”,以此價值性之“心”呈現價值性之“物”,成就“本體界的存有論”。
牟氏的基本理路如上所述,但論證過程頗為繁瑣,在本文看來至少存在著以下幾方面的混淆不清。第一,牟宗三混淆了康德哲學的語境和神學的語境。在康德那里,上帝只是一個實踐理性的“懸設”,盡管有“上帝創造自在之物本身”的類似提法*康德:《實踐理性批判》,第140頁,鄧曉芒譯,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但相關文本旨在說明:說上帝在“感知世界”中(遵從自然因果律)創造“物”(現象)是一個自相矛盾的命題,而只有在“理知世界”中“上帝造物”才能夠避免矛盾,但究竟這個上帝是否實存、如何造物等都是我們人類所不可能知道的;在基督教正統神學看來,“上帝造物”是創造物的個體之實存,不僅創造物的形式,也創造物的質料,并且是使其形式與質料結合的動力因,甚至于人心中關于“物”的觀念也是上帝所賦予的,這也就是說康德意義上的“現象”也是上帝的創造物,這里由“無限”到“有限”的轉變是上帝之“全能”的表現,不同于牟氏所謂“覺之即生之”的創造方式。因此可以說,“上帝造物”的問題不是康德哲學中的問題,而是一個神學中的問題;而牟宗三將這一神學問題改造為“上帝以智的直覺去覺一物即是創造地去實現一物”,實際上是儒家道德的形上學“本體之創生性(活動性)”的投影。第二,牟宗三混淆了“時空中之物”的有限性和“上帝所造之物”的有限性。在康德哲學中,前者是現象身份的物,其有限性來自人的感性直觀形式;后者物自身身份的物,其是否為“有限”或“無限”是我們人類所不得而知的。因為“限制性”(Limitation)是康德所謂十二個知性“范疇”之一,其只能用之于感性直觀所得的經驗,而不能用于物自身。在康德那里,不僅不存在“上帝造物”的問題,而且不存在“無限”創造“有限”的問題,因此牟氏就“創造”問題上講價值性的說法就難以成立。因為康德所說的“物自身”不存在“有限”或“無限”的問題,也不能確定是“事實概念”還是“價值概念”,說其“空洞”也可,說其“并無實義”也行,這正是康德“經驗實在論”的本義。總之,牟宗三并未能成功地證明康德的“物自身”是一個價值意味的概念。盡管他處處依托康德的術語,但在根本精神上與康德背道而馳,甚至有回歸于神學的取向,因此有的學者指出這種做法是對康德“物自身”概念的“去批判化”*參見鄧曉芒:《牟宗三對康德之誤讀舉要(之三)——關于“物自身”》,載《學習與探索》2006年第6期。。拋開康德哲學而不論,牟氏通過繁瑣的論證而將“物自身”價值化的過程包含了許多混淆和臆斷,不能真正使人信服。
由此我們可以確知,牟宗三所堅持的“價值優位”的立場無疑來自于儒家傳統,而不是康德哲學。牟氏將康德所講的“實踐理性”對“理論理性”在“先驗人類學”意義上的優先性轉變為在“存有論”意義上的優先性,力圖證明康德也是一個“價值優位者”,這是對康德哲學的一種誤讀。牟宗三所處的“后工業時代”與康德所處的“啟蒙時代”已然有相當大的差別。18世紀的思想家力圖達到“理論理性”與“實踐理性”、“事實世界”與“價值世界”的并重雙顯與和諧統一,而“現代性”演進到20世紀卻出現了“科學”意識形態化、“工具合理性”一方獨大之勢,“事實”與“價值”之間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對立。牟宗三的“良知坎陷說”具有為西方現代性補偏救弊的針對性,力圖通過重建“價值之體”而為事實世界和科學知識奠基,其作為“科學一層論”、“事實一元論”的反話語出現,卻以同樣極端的方式予以表達。正如傅偉勛所指出的,這種“泛道德主義”與“唯科學主義”一樣,同樣具有“化約主義”的弊病*參見傅偉勛:《中國哲學往何處去——宏觀的哲學反思與建議》,見氏著《“文化中國”與中國文化》,臺灣東大圖書公司1988年版。。同時也應該看到,牟宗三“泛道德主義”(或者說“泛價值主義”)的思想傾向根源于儒家傳統本身,而這種“價值的泛化”只是在“現代性”之兩個世界分化對立的語境中才成為問題的。易言之,就以關懷人之德性生命為根本特質的儒家系統自身而言,無所謂價值之“泛化”,只是一個“生生大化”之價值宇宙;只有對以“工具合理性”為基本動力的“現代性”而言,“道德”或“價值”的獨尊性才對知識的獨立性產生阻礙。綜上所論,牟宗三哲學帶給我們的啟示在于,儒家傳統的現代轉化必然要走出“泛道德主義”的思想窠臼,必須將“本體/現象”的劃界與“價值/事實”的劃界區別開來,以便在“本體”的層面為“事實世界”奠定基礎,成就獨立的、有根基的知識論,在這個意義上,康德的“物自身”學說包含著值得進一步挖掘的思想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