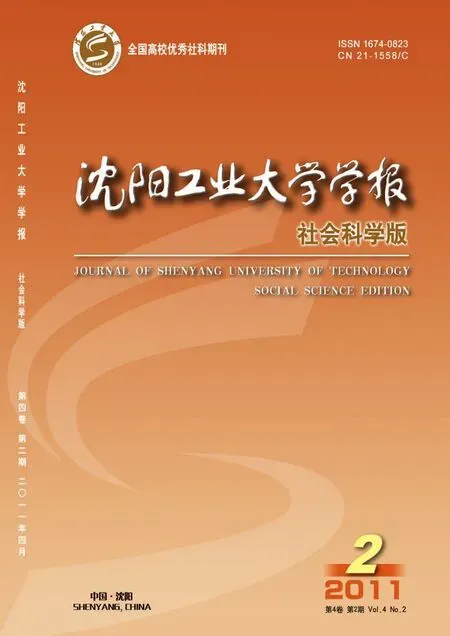理論刑法向經驗刑法的邁進
——刑事和解視野下被害人地位的補足
廖 璐, 吳 瑩
(1. 中國青年政治學院 法律系, 北京 100089; 2. 遼寧大學 法學院, 沈陽 110036)
近年來,刑事和解在我國很多地方的司法機關進行試點,呼吁刑事和解引入刑事法律體系的聲音愈加高漲,同時,反對刑事和解的觀點也撲面而來。或許這場較量的結果并不重要,值得關注的是在刑事和解愈演愈烈的態勢中能夠看到的刑法理論的發展方向。
一、被害人地位的補足
在“國家-犯罪人”二元模式下,國家代表被害人懲罰犯罪分子,被害人僅僅是協助國家追訴犯罪分子的證人,處于客體地位。受到傷害的被害人沒有追究犯罪分子刑事責任的主體地位,而其代表者卻越權享有了這一主體地位,這顯然是一個悖論。這一悖論引發的另一個悖論便是:在民事侵權中,被害人享有處分權,不僅可以撤訴,還可以接受調解,甚至于與加害方自行和解;而構成犯罪的侵權行為的性質重于民事侵權,被害人的程序權利卻大大縮水。正如Nils Christie所言,現代刑事程序的關鍵之處就在于,它將沖突從具體的當事人處剝離而轉換為其中一方與國家之間的沖突。作為一方當事人的被害人徹底被國家代表,以致其在程序的大多數階段中完全被排斥在外,而淪落為整個事件單純的啟動者。最終,被害人成為雙重的失敗者,首先是對犯罪人,隨之是對國家[1]。
1941年,德國犯罪學家漢斯·馮·亨蒂首次提出:“被害人在犯罪與預防犯罪的過程中,不只是一個被動的客體,而且是一個積極的主體。不能只強調罪犯的人權,而且要全面地肯定和堅決保護被害人的人權。”[2]419從此,被害人理論研究成為刑事法學界理論創新的一個全新領域。我國的被害人研究于20世紀90年代才剛剛起步,更為不幸的是,與刑事訴訟領域高漲的研究盛況相比,實體法對此問題的關注卻甚為慘淡。被害人從客體到主體地位的轉變不是訴訟法所能解決的,解鈴還須系鈴人,既然刑事實體法構建的“國家-犯罪人”二元模式把被害人剝離出去,其就應把“失蹤”的被害人再重新找回來。誠如我國刑法學者勞東燕所言,如果不從實體法的角度去反思現有刑事法律制度的內在邏輯,對于被害人缺席的反思就不可能觸及根基[1]。筆者認為,被害人地位的改變對刑法理論來說不是簡單的縫縫補補,而是需要動大手術,作為實體法的刑法應該成為這次大手術的主治醫師,換句話說,被害人地位改變的成與敗取決于刑法理論的邁進。
刑事古典學派以行為為中心,強調一般預防;刑事實證學派則以行為人為中心,強調特殊預防。不難看出,無論行為主義刑法還是行為人主義刑法,均是圍繞著犯罪人展開的,從其客觀行為到主觀人身危險性,由表及里。在犯罪案件中,犯罪人似乎永遠都是被關注的焦點,也被視為所謂的法學專家呼吁保護人權的典型對象。在這里,被害人被邊緣化了。同樣是國家的公民,更是犯罪案件的受害者,被害人的人權在哪里呢?刑法不僅是犯罪人的大憲章,還是善良公民的大憲章,更是被害人的大憲章。犯罪人的權利需要保護,被害人的權利同樣需要保護。盡管保護犯罪人利益與保護被害人利益之間代表著不同的價值,但這些價值之間通常是正與正的較量,而非真與偽的對抗[3]。誠如張明楷所言,任何權益,只要是受刑法保護的,不管權益主體是誰都應當平等地得到保護,而不能只保護部分主體的利益[4]。法律的天平傾向于任何一方都是非正義的,二者的平衡才是法律的本旨所在。
鑒于“國家-犯罪人”二元模式下對犯罪人的過于關注和對被害人的過于冷落,法律的天平已明顯偏向了犯罪者,被害人的地位需要提升,其在法律天平中的分量需要加重。于是,有學者提出了“三元結構模式”、“四元構造模式”等理論,其無非是把被害人作為一方主體,與犯罪人、國家處于相當的地位。筆者認為,“國家-犯罪人”二元模式應當予以堅持,但被害人的權利應該得到擴充,不管是實體權利還是程序權利均應如此。刑事犯罪畢竟不同于民事侵權,對犯罪人的懲罰和預防僅靠個人的力量是遠遠不夠的,拒絕私力救濟已成為刑法難以撼動的基本原則。被害人主體地位的獲得不需要使其與國家的地位相當,他們需要的是在追訴犯罪人時國家必須聽取其建議,尊重其意愿。在被害人無任何表達時,國家成為完全的主體;在被害人想表達自身意愿時,在合法合理的前提下國家必須尊聽和履行,此時國家的主體地位有所減弱。因而,被害人權利保障的前提是其地位得到補足。
二、法益分類下個人法益的突破
通說認為,犯罪的本質在于侵犯法益。根據享有主體的不同,法益分為個人法益、社會法益和國家法益(后兩者統稱為公共法益)。刑事和解適用于侵犯個人法益的犯罪似乎沒有疑問,但能否適用于侵犯公共法益的犯罪呢?在人權保障作為首要價值的今天,似乎是個人法益高于社會法益和國家法益,但在刑事和解中是否也如此呢?有學者認為,犯罪客體涉及社會、國家等公共法益時不得適用刑事和解,僅在犯罪所侵犯的法益為簡單客體中的個人法益和復雜客體中主要客體與次要客體均為個人法益時,被害人才有刑事和解的權利[5]。換言之,在犯罪所侵害的簡單客體為社會法益或國家法益時,復雜客體中的主要客體或次要客體為社會法益或國家法益時,被害人均無權代表社會或國家與犯罪人達成和解。筆者對此不予贊同。
1. 誰是真正的被害人
持上述觀點的學者認為,侵犯公共法益的犯罪其被害人是不特定的,不能把實際受到傷害的被害人等同于潛在的不特定的多數的“被害人”,因而實際受到傷害的被害人無權代表潛在的不特定的多數的“被害人”進行刑事和解。筆者不禁質疑,誰才是真正的被害人?實際受到侵害的被害人和潛在的被害人哪一個更值得刑法伸出援助之手?以潛在的“被害人”不同意為由否定實際被害人的刑事和解權只能是一個虛假的理由,因為潛在的“被害人”是看不見、摸不著的,他們對已經發生的犯罪毫不知情,甚至可能毫不關心,盡管犯罪可能就在其身邊。他們對已經發生的犯罪的感觸無非是同情受到實際傷害的被害人、懲罰犯罪人,甚至對于自己幸免于難感到慶幸,而對于自己是否有權決定刑事和解的觀念則讓位于救助實際被害人的同情心。用虛無縹緲的“被害人”權利阻止亟需救助的活生生的被害人權利是有違人性的。以交通肇事罪為例,此罪所侵犯的客體是交通領域的公共安全,即不特定多數人的生命、健康或重大公私財產利益,屬于公共法益。假設在一次交通事故中有一人重傷,急需大量治療費用,如果可以刑事和解,被害人就可以獲得足額的賠償,經過治療康復出院,恢復正常生活。但按上述觀點,這一被害人無權代表社會同犯罪人和解。筆者的疑問是:社會,即不特定的多數人能否代表被害人呢?盡管發生在公共交通領域,但受到侵害的法益是實實在在的個人法益;基于假定的社會法益也間接地受到了侵害,但除被害人外的不特定的多數人只能是潛在的受害者,而且這種潛在性具有極大的偶然性,用極不確定的偶然性代替確定的實然是否正當呢?
2. 公共法益—— 一個偽命題
公共法益由社會法益和國家法益組成。國家是根據公民之間的契約組建起來的,公民為了讓國家更好地保護自己而被迫讓渡給國家一些權力,而這些權力僅以足以保護公民個人的利益和集體的生存而存在,任何其他動機只能構成權力的濫用和非正當性。誠如盧梭所言,每個人由于社會公約而轉讓出去的自己的一切權力、財富、自由,僅僅是全部之中其用途對于集體有重要關系的那部分。但是也必須承認,唯有主權者才是這種重要性的裁判者[6]38。換言之,作為主權者的公民才是國家權力的設定者。但是,國家權力具有天然的膨脹性,超出公民授權的行為也屢見不鮮,這不禁令我們在贊賞社會契約論完美的同時,也惋惜這一理論在現實生活中的水土不服。國家行為的正當性越來越遭受質疑,國家立法與公民內心自然法的距離也相去甚遠。那么,國家法益是否就是全體公民所認同的對于集體有重要關系的那部分呢?某一國家法益是否是權力膨脹后個別統治者創立的呢?我們有理由質疑。
社會法益是現代社會由個人本位發展到社會本位后誕生的新利益。社會介于國家和公民個人之間,其利益沒有具體的承載主體,那么究竟是國家還是公民個人才是社會法益的代言人呢?有學者認為,只能以國家作為社會法益的代位者,應將社會法益關系納入到公法的調整領域從而形成公法上的關系[7]63-69。筆者認為,社會法益是個人法益的集合,其本質是個人法益,只有個人法益才能決定社會法益的內容。如果將國家作為社會法益的代位者,就會以政治國家的利益作為評判依據,而不是市民社會的利益,這顯然是一種價值錯位、本末倒置。同時,簡單的公民個人的訴求也不能代表社會的聲音,因為他畢竟只是汪洋大海中的一滴水而已。多少個人才能代表社會呢?這是難以用實證研究的。因而,公共法益是一個偽命題。
在刑事和解中,應突破個人法益的藩籬,以被害人的權利為中心展開。現代社會中占主導地位的觀念認為,國家存在的目的是保護個人的利益,具體來說是為了個人自由而全面的發展,舍此之外,沒有也不應當還有其他目的[8]。個人法益是社會法益和國家法益的根基和源泉,不能保護好個人法益,就沒有可能保護好社會法益和國家法益。
家中的女人牝雞司晨,總是喜歡爬到他的頭上來做窠拉屎,樂此不疲。人要是一倒霉,喝口涼水就塞牙,出門會碰到什么鳥屎落到頭頂上,一路上烏鴉愛不停地朝你叫。風影弄不懂紅琴臉上的表情,有時候會莫名其妙的笑,詭譎而神秘,佛陀拈花微笑,他尚且略懂一二,她臉上的笑他實在弄不明白,而有時候她又會陰霾密布,比當下那種霧霾天氣還要厲害,弄不好會突然炸出個驚雷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現在總算淺層次地理解了一些師父話中的意思,山下的女人是老虎,老虎是要吃人的。
三、賠償——刑法的第三條道路
刑事和解的主要運行模式是加害人給予被害人足額或更多的經濟賠償,被害人向司法機關表示對加害人予以諒解,請求司法機關從輕、減輕或免于處罰加害人,司法機關對此予以尊重并付諸實踐。不可否認,刑事和解給人的表面印象就是“以錢買刑”,這正是理論界對刑事和解進行批判的箭靶所在。因此,“以錢買刑”是否具有正當化根據,就關系到刑事和解能否合法地存在。
反對刑事和解的觀點認為,“以錢買刑”往往會使富人逃避刑罰處罰,有違刑法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刑罰是不能用金錢衡量的,“以錢抵刑”嚴重破壞了刑法的根基性原則——罪刑法定原則。
首先,就設立刑事和解制度的直接目的及原因來看,它并非為了對犯罪人進行刑罰減免的“非正義”需求,而是為了對被害人保護及完善法制的更為正義的目的。或者說,刑事和解中的“以錢買刑”只是結果而非原因,更非目的[9]124。
其次,從預防犯罪的角度來說,以監禁刑為代表的刑罰措施對每一個犯罪人的效果是不同的。正如加羅法洛所指出的,不可能建立一種絕對公平的遏制制度,因為同樣的刑罰措施對于不同人所起到的效果是完全不同的。譬如,對習慣于較高生活水準的人來說,監獄是一種持續不斷的折磨;而對另外一些人,監獄則提供了比其家庭更為舒適的生活,提供了一種比他們在自由時更有保障且不那么令人勞累的生活[10]385。可見,對所有犯罪人都毫無例外地執行刑罰并不是明智的,對某些犯罪人來說,金錢可能比自由更可貴難得,金錢賠償更能起到遏制犯罪的作用,因而也就獲得了正當性。
最后,要想證明刑事和解與罪刑法定原則不沖突,就必須確立賠償的刑事懲罰性和贖罪性。“一般契約僅僅實現私人目的,刑事和解契約同樣實現刑罰目的。賠償與刑事和解都是對犯罪的回應,……從這一意義上來說,賠償與刑事和解也可視為一種刑罰措施。”[11]。刑事和解中的賠償已突破了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中的賠償,盡管后者是被害人應得的,但由于加害人在承受刑罰之苦后就不愿再進行經濟賠償,而且他們往往認為自己坐牢就是在贖罪,被害人是很難拿到急需的救助賠償的。這時被害人只能妥協,以許諾諒解并請求司法機關給予加害人從輕處罰來換取急需的賠償,刑法的強制刑罰在此沒有任何意義。在這里,賠償演變成一種強制刑罰的替代措施。正如德國著名刑法學家羅克辛所指出的,賠償已經不再是一個純粹的民法問題,因為它在本質上是有利于實現刑罰目的的,并具有重新社會化的功能。它的確強制著行為人在對自己行為的后果進行深入分析后與被害人達成協議,并且認識被害人的合法利益。行為人能夠將它——經常比刑罰還有效的手段——作為必要的和應得的經歷,并能夠由此增進自己對法律規范的認識[12]55。因而,賠償作為繼刑罰和保安處分之后的刑法“第三條道路”就具有了正當化根據。羅克辛還認為,以賠償作為“第三條道路”來減輕刑罰或者代替刑罰時,賠償與未減輕的刑罰相比,卻能夠使刑罰目的和被害人的需求得到同樣的或者更好的實現和滿足。可見,刑罰并非犯罪的必然結果,賠償同樣能起到懲罰和預防的作用,甚至效果會更好。
四、刑法的大膽邁進
事實證明,任何一個偉大理論的誕生都離不開方法論的變革,僅在既有理論之上創新是徒勞的,只會把簡單的問題搞復雜。理論源于實踐,法學理論更是如此。美國大法官霍姆斯曾言:“法律的生命在與經驗,而非邏輯。”黑格爾也曾說過,一部刑法只是屬于它所在的時代。18世紀確立的罪刑法定原則是否還能夠原封不動地適用于我們這個時代呢?強制的刑罰是否還是犯罪的必然結果呢?答案就在現實經驗中。
刑事和解之所以在司法實踐中廣為流行,在于它平衡了犯罪人、被害人和國家之間的利益,每一方都能從中獲得應有的利益。和解后,犯罪人的部分刑罰或全部刑罰由賠償代替了,可以及早重歸社會;被害人獲得了足額的甚至更多的賠償,得到了及時的救助和安慰;國家節省了有限的司法資源。刑法的根基恰恰在于人的欲求[13]125,刑事和解正是在滿足人們的欲求后獲得生命力的,因為人對于利益具有永恒的欲求。理論界應給予這一欲求以應有的尊重和關注,而不是用僵化的傳統理論扼殺這一符合人性的欲求。
刑法理論邁進所面臨的一個必須回答的問題就是,人們的這種利益欲求是否符合正義呢?“正義有著一張普洛透斯似的臉,變化無常,隨時可呈不同形狀并具有極不相同的面貌。”[14]252博登海默告訴我們,不存在絕對的正義,換言之,在不同的場合下正義會呈現出不同的“面貌”。人人心懷正義,可誰心中的正義才是真正的正義呢?對此,法學大師凱爾森不得不承認,正義是一個人的認識所不能接近的理想[15]13。在刑法領域,傳統的正義觀認為犯罪分子只有受到應有的刑罰才是正義的,用金錢賠償抵刑是非正義的。可刑事和解所依據的恢復正義觀卻給出了對正義的另一種解讀:正義的實現途徑不再是刑罰與服從,而是社會關系的良性互動;正義的評價標準不是有罪必罰,而是被加害人所破壞的社會關系是否得到修復[16]。被害人因得不到賠償而難以生存;犯罪分子長時間與世隔絕,釋放后難以融入社會;國家把有限的司法資源都用于輕微案件,十惡不赦的犯罪分子卻仍逍遙法外,難道這就是正義嗎?沖突的化解和社會的和諧才是人們所期待的正義。
作為一種自生自發的刑事司法改革試驗,刑事和解制度從一開始就不是法學家們倡導下的產物,而是各地公檢法機關進行制度探索的結果。這種探索與其說是在某種理念指引下所作的改革努力,倒不如說是建立在一種利益兼得基礎上的制度調整[17]。刑事和解恰恰是擺脫傳統理論刑法而向經驗刑法邁進的一個重要契機,刑法理論要想獲得持久的生命力,就必須不斷地從實踐經驗中汲取養分。從犯罪人到被害人,從個人法益到公共法益,從“以錢買刑”到“第三條道路”,從正義到恢復正義,刑事和解使得刑法理論正在發生這樣的變化——理論刑法在向經驗刑法邁進。
五、由經驗到規范——刑事實體法的完善
經驗刑法的發展成果最終要由法律規范予以保障和推廣,刑事和解中被害人地位的保障需要刑事實體法的變動,而這一變動涉及到現行刑法理論“國家-犯罪人”的二元論基礎。誠如有的學者所言:“從刑法的國家本位價值觀到個人本位價值觀的轉變,是對犯罪本質進行反思與重新認識的基礎。”[18]這種顛覆傳統理論的變動不是一蹴而就的,就刑事和解發展的現狀而言,可以從兩個方面完善刑事實體法規范。
1. 重新解釋現行刑法中的量刑根據
我國刑法第61條規定:“對于犯罪分子決定刑罰的時候,應當根據犯罪的事實、犯罪的性質、情節和對于社會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關規定判處。”筆者認為,在刑事和解程序中,判定犯罪對于社會危害程度的大小時,犯罪的直接被害人具有參與判斷的權利,其量刑的意見應當被尊重。這是被害人參與刑事和解、具有主體地位的體現,同時,正是由于被害人作為主體有權作出量刑建議,具有要求加害人賠償以悔過、恢復被其破壞的社會關系的選擇,才使得賠償的懲罰機能在刑法中得以滲透。
2. 完善刑法中的非監禁刑措施
刑事和解倡導恢復被破壞的社會關系,這意味著將有大量的刑事加害人被執行非自由刑,在社區中執行刑罰。目前我國刑法中規定的主刑種類中,只有管制屬于在社區中執行的非自由刑,況且其對于按現行刑法及刑訴法本不應判處管制,但由于適用刑事和解程序而在社區中執行刑罰的加害人并不適用。因此,有必要在現行刑法的刑罰這一章中,新增與刑事和解配套的非監禁刑措施。例如,設立社區服務刑,讓加害人在社區中義務勞動、服務社區,以恢復其之前破壞的社會關系。
刑法規范的完善是對實踐中發展起來的經驗刑法的呼應,規范與經驗的互動,牽引著刑事法律的不斷發展。
參考文獻:
[1]勞東燕.事實與規范之間:從被害人視角對刑事實體法體系的反思 [J].中外法學,2006(3):294-309.
[2]漢斯·約阿希德·施耐德.國際范圍內的被害人 [M].許章潤,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2.
[3]勞東燕.被害人視角與刑法理論的重構 [J].政法論壇,2006(5):128-136.
[4]張明楷.芻議刑法面前人人平等 [J].中國刑事法雜志,1999(1):9-16.
[5]于志剛.論刑事和解視野下的犯罪客體價值:對誤入歧途的刑事和解制度的批判 [J].現代法學,2009(1):95-112.
[6]盧梭.社會契約論 [M].何兆武,譯.3版.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7]童偉華.犯罪客體研究 [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5.
[8]黎宏.刑事和解:一種新的刑罰改革理念 [J].法學論壇,2006(4):13-18.
[9]武小風.刑事和解與刑法正義價值、平等原則的沖突與對接:以“以錢買刑“為核心 [C]//趙秉志.刑法論叢:第14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10]加羅法洛.犯罪學 [M].耿偉,等譯.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6.
[11]德特拉夫·弗里希.德國刑法中的和解與賠償 [EB/OL].[2010-05-30].http://vip.chinalawinfo.com/newlaw2002/SLC/slc.asp?gid=335567562&db=art.
[12]克勞斯·羅克辛.德國刑法學總論 [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
[13]西原春夫.刑法的根基與哲學 [M].顧肖榮,等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14]博登海默.法理學:法哲學與法律方法 [M].鄧正來,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
[15]漢斯·凱爾森.法與國家的一般理論 [M].沈宗靈,譯.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6.
[16]馬靜華.刑事和解制度論綱 [J].政治與法律,2003(4):113-122.
[17]陳瑞華.刑事訴訟的私力合作模式:刑事和解在中國的興起 [J].中國法學,2006(5):15-30.
[18]孫文紅,張華麗.刑事和解的理論基礎與制度構建 [J].沈陽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1):75-79.